- +1
“我的小孩一直很乖,怎么会得抑郁症?”
原创 李荣荣 单读

在 10 月发布的《2022 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中,写着“全国的抑郁症患者中,有 50% 尚是学生”。
这与我们日常看到的景象不符——大多数不为此留心的人,都没能从半数青少年的眼神中,看见困惑与遮掩。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家庭中,更多抑郁症患者被冠以边缘、软弱、性格差、问题学生的名号,为了不被排挤,或被学校记录在案,许多青少年即使意识到自身需要治疗,也会保持沉默,自行处理情绪。前往精神病院看病,一直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这一无法自动消失的疾病,成为一个又一个极端事件的动因。
如果我们能够对精神疾病以及精神疾病的临床治疗更多些了解,这一现象是否能够有所改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李荣荣将她在精神科室内的观察写成了一份田野笔记,希望能够从医生的视角,为这一被污名化许久的疾病提供更加中肯、清晰的介绍。
在这份笔记的前篇中,作者从青少年面对的真实问题,到如何辨认“疾病”以及进行药物治疗,再到青少年精神问题背后的社会、文化与道德内涵,详细介绍了儿童精神科医生如何进行临床分析与治疗。今天单读分享这份笔记的续篇,作者深入精神科医师的诊疗实践,为我们更加详尽地介绍了既以诊断标准、诊疗指南、测评量表为支撑,又同时融合医生本人的临床推理、临床直觉与个人风格的精神医学技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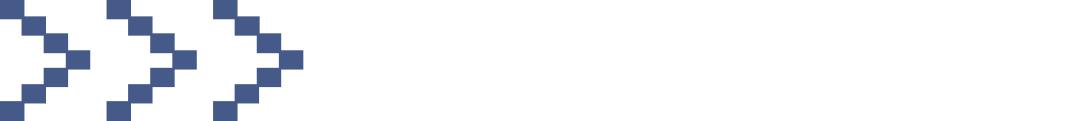
走近精神科医生(续)
撰文:李荣荣
一
医生的默会知识
我刚开始做田野调查时,曾经问了精神科医生王瑜一个非常浅显的问题:什么是抑郁情绪、焦虑情绪,什么是抑郁症、焦虑症,你如何判定来人是生病了?王瑜顿了顿,耐着性子回答到:“精神科有国际化的诊断标准手册,还有诊疗指南与心理测试量表,达到一定指标,病程达到一定时间,同时又影响了社会功能,就属于抑郁症、焦虑症,就是生病意义上的抑郁症、焦虑症。”说完,她又补充了一句:“你还得在这里头多混混,你的问题太基础了”。
拉图尔曾经用人类学方法研究生物实验室里科学家的工作细节。他提到,除非是向初来乍到者介绍实验室,否则实验室成员很少讨论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新人越无知,成员就需要越彻底地挖掘默会知识。如果新人不停地问“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那么,在超出一定限度后,他就会被认为不善社交。[1]确实,王瑜没有太多兴趣和我谈论诊断标准、诊疗指南以及量表问卷,这些都是她习以为常的事,不需要时刻反思,临床工作中照着做就行。王瑜更没精力谈论这些手册、量表的制定过程或来龙去脉,因为这些内容不属于临床工作的重心。
作为一个试着去了解精神医学的外行,我却很好奇医生的这些默会知识是如何形成的。
王瑜所说的国际化的诊断标准手册,指的是当前临床参考的美国精神医学会制定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国际疾病分类》(ICD)。至于诊疗指南及心理测试问卷,也都是基于诊断标准而制定。我没读过社会科学关于《国际疾病分类》形成过程的讨论,只看过关于《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的讨论。例如,医学史学者安德鲁·斯卡尔回顾了《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出现的历史:美国精神医学会为了解决对精神病学诊断能力的怀疑,开始对诊断进行标准化工作。由于无法围绕任何一个精神障碍的主要形式构建有说服力的因果链,斯皮策小组的方向就是指定症状列表。列表里归纳了各种形式的精神障碍的特点,然后用列表“逐项核对”进行诊断。达到特定阈值时,就可打上某种诊断标签。当诊断出不止一项“疾病”时,就用“共病”来解释。如果对哪些诊断应该写入手册存在争议,就通过委员会表决来裁定。斯卡尔还指出,DSM 系统本身的逻辑就是要避免复杂因素,以及不要关注个别病例的特殊情况。[2]

可惜,我没法观察诊断手册的制定过程,也难以追溯诊疗指南或测试量表的形成过程。精神医学内部如何规定特定阈值、如何协商诊疗指南、如何制定测评问卷等等,我统统不得而知。我能做的只是换种方式、换种角度来了解精神科医生的默会知识——观察医生在临床工作中怎么做。
恰如人类学家谭亚·鲁尔曼(Tanya Luhrmann)所说,精神医学是一门技艺,它涉及的是知行并重的实践知识。技艺娴熟的医生未必擅长描述自己所做的事,但必定擅长“实践精神医学”(do psychiatry)。[3]既然我没办法通过问来理解,那么,观察王瑜和她的同事夏思医生如何问诊、如何诊断、如何用药,或者说,观察她们如何用精神医学语言来表述、回应她们所看到的纷繁复杂的身心表现,或许是作为外行的我理解精神医学的一种可行方式。
当然,我能接触的只是王瑜和夏思的语言与行动,她们的思维方式我只能通过观察来部分地推测、通过交谈来部分地了解。显然,我的认识是有限的,但我希望这些观察能够为我们走近精神科医生以及她们的诊疗实践提供一种视角。
下面,我会从最基础的问诊步骤开始叙述王瑜和夏思的工作。读者会看到,在综合性医院的精神科门诊,就诊者往往带着或是明确、或是模糊的线索及诉求来到诊室,医生则在与就诊者的微观互动和协作中回应这些线索及诉求。在这个过程中,医生如同探案一般不断寻找诊疗证据。读者还会看到,医生会尝试将自我带进诊疗实践,但这样做时她们也会面临各种困惑。总的说来,我试图说的是,一方面,王瑜和夏思所实践的精神医学技艺以诊断标准、诊疗指南、测评量表为支撑,同时融合了医生本人的临床推理、临床直觉与个人风格。另一方面,这种技艺还嵌入在具体的诊疗环境,以及更广阔的精神医疗资源有限的社会现实之中。当然,生物精神医学的全球化也是她们炼就技艺的大背景。

电影《儿子的房间》
二
精神科医生的临床诊断实践
理论上讲,由于缺乏医学意义上明确的疾病类别,精神医学的分类与命名系统目前较少使用疾病(disease)这一概念,而是更多使用精神障碍(mental disorder)这一概念。[4][5]目前,在临床实践中,精神科医生无法通过化学检验、影像检查来获得明确的生物标记物作为诊断依据。对于王瑜和夏思来讲,她俩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就诊者的主诉,以及她俩的观察、询问和聆听来锁定诊断方向,并依据各种测评量表的辅证来作出诊断。
在实际诊断过程中,就诊者既会述说纷繁复杂的内心感受与苦痛困扰,也会提起心慌、气短、头疼、腹痛、疲劳、失眠等等躯体表现。这些表现可能在不同的精神障碍诊断类别中都能找到对应描述。然而,对每种可能性都进行检验往往是行不通的。显然,太多的检验既占据医疗资源,也让就诊者难以负担。
于是,王瑜和夏思必须仔细关注临床线索,将观察、询问、聆听得来的各种信息加以整合,经过一番融合了医生本人学识、经验与直觉的临床推理与分析,然后在脑子里对各种可能性进行排序(症状表现不复杂的,不同的可能性相对就少;症状表现复杂的,不同的可能性相对就多),并从最大的可能性出发继续寻找诊断证据,也就是更有的放矢地、深入地观察、询问、聆听以及使用测评量表。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她们还会通过采集病史以及开具验血、心电图及头颅 MRI 平扫等检查单,来排外导致精神问题的常见脑及躯体疾病以及部分用药禁忌。
(一)
有明确诉求与线索的诊疗实践
一般情况下,成年人相对清楚自己的身心状态。不少时候,成年人既会明确地诉说工作压力大、疫情影响业绩、产后带孩子焦虑等等造成情绪问题的明确诱因,也会清晰地描述情绪状态与躯体症状。
某天,夏思的诊室来了一位成年男子,坐下来开门见山就说自己抑郁。陪同的家人补充男子最近一直在求职。紧接着,男子自诉集中不了精神、睡眠不好、心情低落、做事提不起兴趣,症状持续几个月,最近两周尤其明显。如果我们看过抑郁筛查量表 PHQ-9,就不难发现男子的叙述格式几乎就是对照量表而来,只是他叙述的问题没有量表罗列的多而已。或许,男子在来诊室之前已经在网上搜索到各种心理自评量表,来医院只是想知道确切的答案以及下一步该怎么办。
听完这些叙述,夏思先问了一个与生命相关的问题“有没有想过用什么方法结束生命?”得知男子答案后,夏思又问了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这样的时候有自救的方法吗?”随后,夏思宽慰了男子几句,人生总有不如意,建议他情绪低落时一定要找身边人陪伴,同时又叮嘱男子家人务必多理解、多支持。接下来,夏思按照问诊程序相继询问了人际关系、会不会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会不会看见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会不会觉得有人议论自己、会不会有时特别兴奋或有活力等等常规问题。随后,夏思根据观察与询问获得的线索建议男子完善相关心理测评量表,同时还开了常规验血单子用以排除不能用药的情况。在拿到测评结果之后,夏思结合问诊与测评分数在病历上写下了“精神科检查:存抑郁、消极情绪,诊断:抑郁障碍”等字样。
带着“自我诊断”来到诊室的成年人并不少见。不过,尽管就诊者熟悉自己的身心状态,甚至还会将这些症状与某种精神障碍或某种药物联系起来,最终的诊断与治疗方案仍由王瑜和夏思作出。她们通常只是将就诊者的“自我诊断”作为病史采集的一部分,或者说只是部分接受他们的叙述和分析。在此过程中,王瑜和夏思作为权威知识的代表,或许还会给就诊者普及相关医药知识。
某天,夏思的门诊来了一位言语利落,想要明确自己是否患有焦虑症的女性。这位就诊者坐下就说前段时间同事体检发现有肺结节,最近自己也检查出肺结节,随即出现心慌、早醒、小腿抽筋等症状。因为睡眠不好,自己在家服用了唑吡坦。心情最近几天好些了,但身体还有不适,感觉像是焦虑症的躯体症状。
待就诊者述说完毕,夏思表示理解,并逐一回应了她的问题:确实如您所讲,焦虑会影响睡眠、带来各种躯体表现。您很熟悉您的身体,自我照顾也很好。现在检查出肺结节的很多,不必太过焦虑。但另一方面,您需要关注一下心脏,如心慌还是会发作的话得做一下心电图检查。待就诊女性表示做过心电图明确没有问题后,夏思又接着解释道,抽筋与焦虑的躯体化关系不大,与中老年女性缺钙有关,可以做骨密度测试看一看。另外,唑吡坦针对的是入睡困难而非早醒,并且这个药并不改善焦虑,对症的其实是既针对失眠又针对焦虑的阿普唑仑。
当然,不是每位就诊者都能清晰地描述自己的体验。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更是既会出现不愿意或者难以描述自身体验的情况,也会出现父母等知情人的观察与表述未必全面的情况。并非每次问诊都如上面的案例一般快速、顺畅。
(二)
不断寻找证据的诊疗过程
诊断过程包括常规问题的问答,但王瑜和夏思不可能单纯依靠结构化测评量表来机械提问。更多的时候,她们需要在问诊过程中仔细观察以寻找线索。当发现一点线索时,脑子里就会提出某个诊断方向的怀疑;再询问、再观察,又会发现新的线索,或是证实、或是推翻之前的怀疑。
某天,夏思的门诊来了一对母子,男孩上小学二年级。当听到母亲描述孩子好动、在教室坐不住、下课总是不顾老师要求就喜欢跑去操场玩时,夏思有点怀疑孩子可能确实是其母所说的多动,于是拿出一箱早已准备好的玩具,观察男孩面对玩具的表现。
按照夏思的经验,多动的小孩看到玩具很可能拿起来就玩,或许还会在箱子里不停地翻找,每个玩具都拿起来玩一下。然而,小男孩看了一眼之后并没有动。夏思问他为什么不玩,男孩很干脆地回答说这些玩具太幼稚。夏思又问男孩喜欢什么玩具,男孩说喜欢玩乐高。妈妈补充说男孩喜欢复杂的、几千个颗粒的乐高,可以玩几个小时不停歇。
听了男孩母亲的描述,夏思开始进一步了解男孩的语言能力以及与人交往的情况。她又让男孩复述自己喜欢的故事,并用动物来比喻自己的家人,说一说爸爸像什么动物,妈妈像什么动物。小男孩非常生动、流利地讲述了自己喜欢的故事,还把性格各异的家人比作了不同的动物,并作了一番解释,边讲还边与医生、妈妈进行眼神交流,不时露出调皮的笑容。
于是,虽然母亲描述男孩不听老师招呼便自顾自地跑出教室,但他在访谈中表现出的良好沟通能力恰好帮助夏思解除了对孤独症谱系障碍的怀疑。与此同时,男孩稳定的情绪、可以长时间专注于某件事的线索又都在告诉夏思,可以暂缓对情绪障碍的怀疑。这时,为了进一步验证男孩母亲的主诉,打消她的顾虑,夏思又回到她之前的诉说,并请她扫码完成 SNAP-IV(注意力缺陷与多动评定量表)测试。
(三)
在协作与互动中显现的诊断线索
诊断实际上涉及医生与就诊者及其陪同家人之间的各种微观互动与协作,诊断线索也正是在这样的微观层面渐次出现。
在下面的个案中可以看到,王瑜依据男孩母亲的代诉,以及她自己的观察来开始鉴别诊断。与此同时,当天门诊需要看一百二十多人,王瑜不得不尽可能地提高效率,压缩分配给每位就诊者的时间。事实上,小小的诊室里时不时就人头攒动。没挂上号的家长不断地推门进来请医生加号;之前开单做测评的就诊者也会回来请医生看结果;还有人进来问上午能不能看到自家孩子,他们做高铁从外省来,当天傍晚还得坐高铁回家。喧闹甚至凌乱的景象使得诊室更像是露天市场吸引了众多顾客的摊位。
于是,在这里可以看到:
首先,研究生辅助王瑜看门诊的模式帮助她提高了工作效率。每次门诊,王瑜都会安排三到四位研究生全程参与。其中有人负责坐在电脑前记录病历、开具处方;有人负责安排加号及维持诊室秩序;有人负责让首诊者填写《首诊青少年测评表》——王瑜与研究生编制的用于初步了解 10~17 岁首诊者大概情况的测评表。让就诊者填表而非由医生逐一询问,事实上起到了在最短时间内最大限度地了解首诊者概况的作用。[6]在就诊人数有限的特需门诊,王瑜便不需要研究生辅助。夏思没有带研究生,她就得独自一人面对所有情况。当然,研究生参与门诊本身便是医学生“在做中学”的重要反映,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谈。
其次,倘若男孩母亲没有抓住机会在第一次走出诊室前进一步描述男孩的表现,王瑜或许便捕捉不到线索来怀疑男孩可能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那么,该诊断在这一次的就诊中就很有可能会被遗漏。
某天早晨,王瑜的门诊来了母子二人。男孩上五年级,在诊室里不怎么说话,所有情况几乎都是母亲代诉。一开始,母亲说孩子的姥爷几个月前去世了,孩子自小就与他关系亲密,有时会因此哭得喘不过气来。不过,男孩母亲接着也说,男孩在遭遇变故前也容易哭得比较激烈,只是遭遇变故后变得更甚。
《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对于抑郁障碍与因丧亲出现的悲痛反应有一定区分。因此,关于孩子在姥爷去世后伤心这一点吸引王瑜关注的是伤心持续的时间与程度。与此同时,“哭得喘不过气”也引导她去追问孩子哭泣后是否会感到心慌、胸闷,以便初步排查是否存在其他躯体问题。接下来,王瑜循例询问了孩子是否有兴趣外出、是否愿意与同学玩耍、往常的兴趣有没有消失等常规问题。
当天挂出去了一百多个号,王瑜没有太多时间依次询问所有可能需要了解的情况,于是便将口头问诊转化成为问卷填写的形式,让母子俩到诊室外找她的研究生完成《首诊青少年测评表》。同时,为了辅助诊断,王瑜也开了单子让母子俩完善 PHQ-9(抑郁筛查)、GAD-7(广泛性焦虑筛查)、CBCL(儿童行为测评)等测评。
就在王瑜让研究生开好单子,准备叫下一位就诊者时,这位母亲又抓紧时间补充说孩子临近期末时开始出现明显问题,一旦在学校感到有压力就会抗拒、暴怒。说完,母亲又加了一句说孩子幼时就性子急躁,幼儿园老师就有过反映。听到这些信息,王瑜顿了一下,她隐约怀疑孩子抗拒学习以及冲动易怒或许与被精神医学归结为神经发育障碍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有关。于是,她又让男孩母亲扫码完成 SNAP-IV 测评量表,并让她将测评二维码发给孩子的班主任和主科老师完成,同时又补充了一个韦氏智力测评的单子。
下午,完成了各项测评的母子俩再次走进诊室。王瑜一边检查测评量表,一边继续问孩子母亲妊娠期与分娩期间的情况、孩子出生时的情况——当诊断方向指向神经发育障碍而不仅是抑郁或焦虑时,这些内容就变成了医生采集病史必须了解的信息。随后,王瑜指着测评结果说,孩子有一些抑郁、焦虑症状,同时还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他在高年级出现抗拒学习的心理与他注意力不集中影响学习成绩、学业压力过大有关。此时,男孩母亲已经完成 SNAP-IV 测评,也看了宣传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小册子,便回应说道,孩子从小确实注意力不集中,写作业磨蹭,遇事也难控制情绪。
这时,电脑显示时间已是下午 2 点多,后面还有五十多位就诊者在等待。王瑜从早晨 8 点开始已经连续工作了六个多小时,半小时前她匆匆吃了几口盒饭、去了一趟卫生间,除此之外没有一刻停歇,来自工作与身体的多重压力这时已开始向她袭来。她必须加快节奏,否则当天晚上十二点也没法下班。并且,即便她撑到那个时候,她必然已经精疲力竭,脑子里很难再作临床推理,临床直觉也可能会消失不见。
于是,王瑜没有与男孩母亲就孩子的行为表现继续讨论下去,她在病历上写下了“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抑郁焦虑症状”的诊断。剩下的工作就是制定药物治疗方案与开具处方了。当然,那是另一层面的工作,这里暂不赘述。

电影《大象席地而坐》
三
淡化生活脉络的病历书写
不论就诊者的故事多么异乎寻常,或者多么让人心有戚戚,病历格式都是固定的,病历篇幅也相差无几——所有记录最后都会打印在在一张 A5 大小的纸上。
Y 院精神科的病历由医生在电脑上记录。它有标准格式,在固定位置依次记录主诉、现病史、既往史和其他病史、过敏史、婚育史、月经史、体温、新冠情况、体重、辅助检查、精神检查、诊断、建议。其中,主诉、现病史、既往史、精神检查、诊断、建议等是主要栏目。在这些主要栏目中,诊断一栏是从系统提供的诊断类别备选项中进行选择,如不能确定,则在选项后手动加一个问号以作标记;其他栏目的内容由医生根据问诊情况进行记录。
对于医生来说,病历最主要的临床意义在于它是对诊疗实践的一种过程性记录。首诊时,医生便会将就诊者的基本情况与诊疗方案进行记录。当就诊者复诊时,医生通过浏览首诊记录就能快速掌握其基本情况,并回忆起自己之前做诊断时的思维过程。与此同时,医生会在复诊时更新就诊者的情况以及诊断、治疗方案的变动。
站在观察者的视角可以看到一些有意思的点。比如说,主诉与现病史这两栏所记述的内容往往不是那么泾渭分明,这或许与精神医学处理的多是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认知、情感、情绪等方面的问题有关。又比如说,恰如诊断指南关注的不是个人的生命历程,而是用列表来“逐项核对”看是否达到特定阈值那样,医生在问诊过程中会获知就诊者的生活史与造成情绪问题的诸多琐事、细节,但病历书写却表现出对之作出淡化、简化的倾向。
某天,王瑜门诊来了一对复诊母女,王瑜对她俩还有印象。母亲四十出头,一脸强忍的怒气,女儿正上初中,满脸的不以为然。一进诊室,母亲就当着孩子的面抱怨她懒散、叛逆、不听话、用刀划手、在家不洗漱。接着又恨恨地说,“家里没矿,不学怎么办”。待王瑜将她请出诊室,让孩子单独述说时,女孩开始忿忿不平地说妈妈实在太强势,不但总是批评自己学习成绩不好,还没收了自己的手机不让自己和朋友联系。接下来,王瑜循例进行心理测评、心理疏导与药物调整。
在记录病历时,女孩幼时父母离家经商、女孩由外祖父母带大、女孩用刀片划手等内容都被记录了下来。这样,当女孩下次再来复诊时,王瑜打开电脑系统查看记录就能快速回顾她的情况。不过,王瑜在记录病历的同时又在抽象或提取她认为重要的关键信息。母女俩在诊室里的互动、各自关于家庭生活与对方言行的叙述、母亲的愤怒与女孩的翻白眼等等,以及诸多细节折射出的背景信息,统统在记录的当下被简化为“亲子关系不佳”。
更关键的是,病历的核心信息其实是将医生观察、问诊以及量表测评加以整合浓缩后的一行字:“精神检查:存抑郁情绪,伴消极自伤行为,PHQ-9:17 分;GAD-7:15 分”,以及“艾司西酞普兰(早餐后 1/4 片)、舒肝解郁胶囊(早晚各 1 片)”的药物建议。

电影《阳光普照》
四
对症下药的治疗策略
鲁尔曼在《两种心灵》里曾提到,精神科新手最初或许会怀疑精神医学的内在模糊性,但医学院通过培训他们做大量诊断、撰写入院病例以及用药,不断地在他们的认知经验中强化精神病痛的疾病模式,让他们日渐相信病痛背后“有一种潜在的本质,这种本质可以被看见、被命名,而且可能有办法被控制”。[7]王瑜刚读研究生时不相信药物能治疗抑郁,博士毕业又做了十多年临床后则越来越强调“精神疾病症状较轻可以单纯心理治疗,中度及以上症状需要考虑药物治疗”“对于精神疾病的治疗需要早发现、早治疗,从低剂量用药开始”。(她在日常交谈中并不严格区分“疾病”与“障碍”)
虽然精神障碍不具有狭隘的生物学意义,但药物治疗仍是精神科针对中、重度精神障碍的主要治疗方式。
王瑜和夏思在门诊接触了大量的人间百态与内心苦痛,但与心理咨询不一样的是,生物医学才是她们临床实践的底色。诊室里,错综复杂的身心苦痛,说不清、道不明的幽深内心,别人听不见的声音、看不到的影像、闻不到的味道,纷纷被概括为抑郁、焦虑、强迫、躁狂、精神分裂、人格解离等等精神障碍,并迎来以药物为主的治疗方案。除去诊断以及时间有限的心理疏导外(特需门诊时间相对充裕,可以留出时间专门进行心理治疗,但药物治疗也是特需门诊的重要部分),王瑜和夏思的很大一部分精力都放在对症下药以及调整药物治疗方案上面。
在她们看来,倘若病情重,当务之急必定是用药;倘若没有生活事件、家庭因素等明确起病原因,心理干预也难以有效开展。此外,经济条件、心理咨询机构质量良莠不齐等因素也都会影响就诊者的选择。因此,在诊室里不难看到,相当多的就诊者最后都会拿到一纸药物处方,从针对失眠早醒的艾司唑仑、阿普唑仑,到控制幻觉妄想、辅助稳定情绪的喹硫平、利培酮、鲁拉西酮,以及稳定心境的碳酸锂等等,都有可能。
精神科医生用药通常采取症状取向的方式。倘若不考虑与症状相缠绕的生活脉络,那么,精神科医生面对的症状数量与其他科室相比并不算多。并且,精神科药物种类相对说来也比较少。在熟知药物适应症、禁忌症的基础上,再以药物的安全性或耐受性、效果、价格、可获得性(原研/仿制或进口/国产)等因素为参考依据,王瑜和夏思可以娴熟地处理常规症状的用药。
当然,外行的观察不可避免地会简化医生的用药思路。缺少精神药理学知识,我终究难以理解王瑜所说的单通道药物、双通道药物、大脑脑区、多巴胺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等等概念与临床所见症状之间的关系。医生用药远远不是像阅读说明书那样,知道有什么症状、知道有什么药物,然后简单对应就可。
最后,处方需要经过医院药房审方。从电脑显示来看,药房审方速度很快。除了审核药物适用性、安全性等因素外,开药量也是一个审核要素。王瑜和夏思偶尔也会遇到长期服药的患者与家属的抱怨,“每次就只给开一两盒,不知道跑医院难吗?”“药房不给拿药,非要等到只剩一颗才给!”对此,她俩也没办法。毕竟,对症下药还须与用药安全、从国家层面到医院层面的制度安排、乃至模块化的电子审方系统等复杂因素相协商。
显然,药物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当年轻的大学生心情沉重地诉说自己难以适应大学生活与节奏、和同学关系疏远、从所学专业中感受不到意义、孤零零一个人看不到前路时,医生只能针对他的失眠予以对症药物。当最早一代的独生子女焦虑地诉说,人到中年,时常在梦中惊醒,忍不住想家中老人生病怎么办,自己生病老人和孩子又怎么办时,医生也只能针对失眠予以对症药物。这时,药物只能回应某种症状,而不能回应人生处境。

电影《地久天长》
五
临床技艺中的“艺术”
临床中的精神医学是一门技艺,不只有技术的成分,也有艺术的成分。我曾和夏思说,用药思路实在是太复杂了。夏思的回答却是:“药物其实不是难点,其他科的医生只要跟着看几次就会知道用药套路。难点在于诊疗过程中的人文性内容,患者愿不愿意来看你?你能不能在问诊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做到心理疏导?你有没有这样的气场?这些才是难点,这些才是 AI 取代不了的,否则以后都可以用 AI 来诊断了。”
确实,虽说生物精神医学聚焦对症下药,但临床医生要想把工作做好,就得去关注眼前的这个人是谁,而不仅仅是这个病是什么。
某天,王瑜门诊,电脑叫号之后进来一位成年女性。女子坐下就说其实是带刚考完中考的女儿来看,但没敢和孩子说是带她来看病,只说是自己看病。接着,这位母亲担忧地说孩子会划手进行自我伤害,说完又向医生描述了女儿自小学以来的学业情况。待她说完,王瑜示意她去诊室外等候并让女孩进屋。女孩进来后,王瑜没有循例问她精神科检查的常规问题,而是温和地对她说:你妈妈有点儿焦虑,需要你配合一下。待女孩放下戒备之后王瑜才开始问“你们是不是关系不好?”“你自己情绪怎么样?”等问题。之后,王瑜起身叫女孩的母亲进屋,建议母亲做心理测评量表,并请女孩也陪妈妈一起做。待两人完成测评后,王瑜拿着量表对女孩说:你俩都需要调整一下,女儿分数比妈妈高,年轻人就更需要调整了。说完,王瑜再次示意女孩的母亲去诊室外等候,单独问女孩要不要参与调整。整个过程中,王瑜并没有直接将女孩当作问诊对象,而是引导她认为自己是帮助母亲进行治疗的重要参与者,并因此获得女孩信任,成功地将其纳入治疗。
为了让就诊者更容易理解药物属性,她们还得学会用日常语言表达医学知识。
某天,夏思门诊来了一位失眠的中年人。这位就诊者长期服用艾司唑仑,听说还有阿普唑仑也能改善睡眠,就问夏思阿普唑仑和艾司唑仑有什么区别。夏思自然没法给他详细讲解药物机制,但却巧妙地说:打个比方来说,这两种药就像馒头和花卷,都是主食,花卷花样多点儿、还有盐味,艾司唑仑和阿普唑仑都能帮助睡眠,只是阿普唑仑还可以对抗焦虑抑郁。这么一说,就诊者立马明白了两种药物的区别,也知道自己更适用哪种药了。
有时,王瑜和夏思在进行心理疏导心理时还会将自己的性格、个人经历、生活故事等等呈现给就诊者,以此来形成一种平等的、共情的交流气氛。
在开导一位因朋友少而自我怀疑的少年时,夏思分享了自己的性格故事:每个人性格不一样。我自己其实也是话不多,从小不论在哪里都是喜欢缩在角落里,我曾经也不喜欢我自己这样。但长大后我发现我能静得下来,我能保持对我想做的事情的兴趣并一直探索下去。我还发现虽然我的朋友不多,但我的友情质量更高,我和我的朋友可以有很深入的交谈,我们彼此理解,非常投契。
在开导一位抑郁焦虑的女孩时,王瑜先是教女孩以事件、看法和情绪为要素来记录心情日记,告诉她对同一个事件的看法与情绪就像山的阳面与阴面,心情日记上可以写下负面的、感性的看法与情绪,也可以写下正面的、理性的看法与情绪。接着,王瑜以自己为例向女孩解释如何尽可能地增加正面看法和情绪:“比如我参加一场考试,考上了可以升职,但我没考上。那么,我会想升不上去工资就少,但我也可以想,没升上去工作负担就没那么重,多出的时间可以写论文、可以多照顾家庭和孩子。有时候我们心情不好,我们可以去分析为什么不好,把正面的、负面的情绪写上,哦,原来我会因为这些事不愉快,因为这些事愉快。”最后,王瑜又让女孩回家之后坚持记录心情日记,并告诉她“我们医生要坚持写两年,长期下来形成固定思维,凡事就会往好了想。”
不过,王瑜也说,将自我投入诊疗也可能带来想不到的后果。曾经有位医生为了打消患者的疑虑,和患者说自己也曾服用某种精神科药物,没想到随后被患者举报: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如何能担当医生?因此,王瑜和夏思也会斟酌什么样的投入才是合适的。
同时,与苦于量化考核的其他学科的研究者类似,她们有时也会困惑,医院考核制度只计算门诊量,却没看到医生在每位患者身上如何投入,如何影响患者的人生。KPI 也会给她们带来焦虑。
近距离观察工作中的王瑜和夏思给我一种感觉,她俩既是医生,也是侦探、手艺人、艺术家。当然,她俩还是嵌入在制度环境里的行动者。对于她们来说,诊疗有时是按部就班的操作,有时则是复杂且漫长的求证过程。出现在她们工作中的不仅有药理学、病理学、生理学知识以及各种诊断标准和诊疗指南,还有每天数不清的微观互动与沟通艺术,以及管理她们工作的系统设计与制度环境。
科学社会学家哈利·柯林斯和崔弗·平区曾提到,历史上的医患关系并不像今天这样科学与外行的关系,而是如同顾客与美发师的关系那样,患者与医生就疾病进行协商。随着医学日益被视为一种“科学”,医生的力量也日渐增强。[8]其实,王瑜和夏思并不喜欢被视为无所不能的权威。精神医学及精神障碍、心灵苦痛本身的特殊性也对医患之间的协商、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这篇描述王瑜、夏思工作的笔记能为读者理解精神科医生的日常诊疗实践提供一种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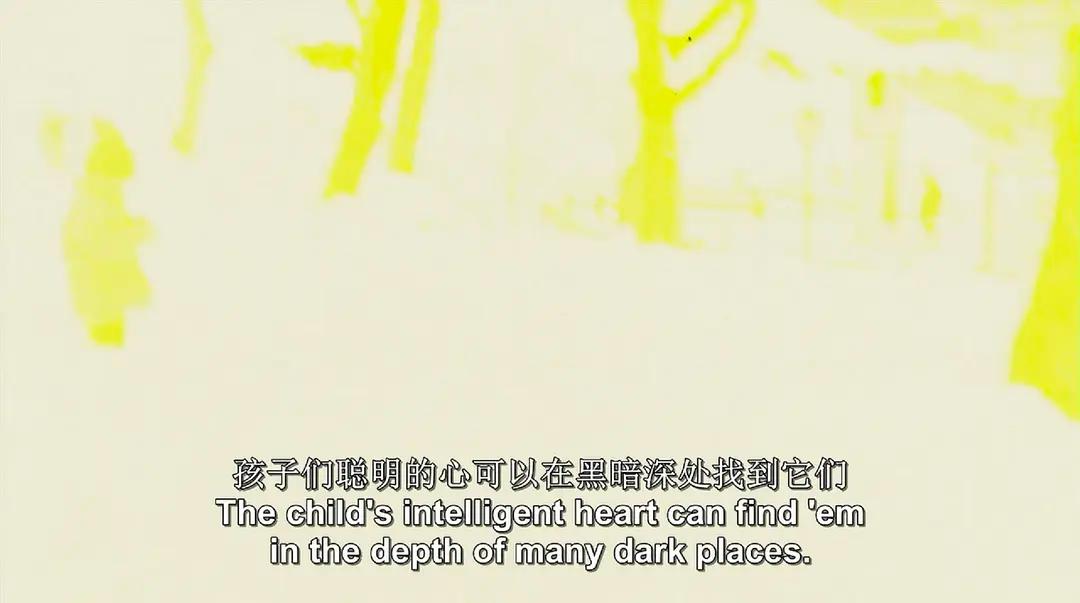
电影《超脱》
六
设想一种对话的可能
我曾把这篇笔记的初稿发给王瑜和夏思。医生没兴趣谈论习以为常之事引起了王瑜的注意。她解释说“确实时间有限,不能完全关心患者内心所想”“患者经常抱怨五分钟就诊断一个抑郁症”。王瑜打算在网络医生平台上介绍一下如何诊断精神障碍,但我不知道她后来能否安排出时间。
前不久,王瑜给我讲了一则故事。
住院部收治了一名来自农村地区的患有躁狂症的少女。女孩在躁狂发作时会骂医护人员,还会动手打她父亲。有一次,女孩死死掐住父亲的脖子,力气突然大到掐着脖子就可以把父亲举起来。女孩的父亲既生气又悲伤,他想不通自己的孩子为什么成这样了,躁狂症的医学解释并不足以让他心安。这时候,女孩开始提出自己的解释,她说自己是被鬼附体了。令医护人员没想到的是,父亲相信了女儿说的话,同意她是被鬼附体了。之后,这位父亲不再生气,也不再难过。女孩是因为鬼附体才那么暴躁,才有那么大的力气,才会打父亲,其实不是女儿要做这样的事,而是鬼在做这样的事。最后,这位父亲和医生提出请假,晚上不住院,要回家做法事驱鬼。医护团队中不少成员很生气,“要么相信医学,要么相信法事”。但王瑜在硕士研究生期间就接触了人类学,她意见却是“可以医学、法事都相信,只要别停药就行。”
这个故事其实有很多有意思的讨论点。不过我现在引述这则故事想说的是,人类学与精神医学或许可以有更多的合作与对话。一方面,人类学可以超越强建构论的激进想法,通过经验研究来了解精神医学的制度、信念与实践,了解精神科医生的工作和付出,以及她们面临的挑战和困境。另一方面,精神医学需要人类学的视角,尤其是在生物精神医学越来越占据主流、病痛也越来越被还原为各种生化指标的今天。最终,对话的目的是去探索一种更有温度的生活处境。
备注:文中所用人名为匿名,部分个案是混合不同案例而成的典型案例。感谢王瑜与夏思在田野调查及文章写作中提供的帮助与支持。
注释
[1] 布鲁诺·拉图尔、史蒂夫·伍尔加著,修丁译,《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 年,第 78 页。
[2] 安德鲁·斯卡尔著,经雷译,《文明中的疯癫——一部关于精神错乱的文化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年,第 429 页、第 434 页。
[3] 谭亚·鲁尔曼著,张復舜、廖伟翔译,《两种心灵——一个人类学家对精神医学的观察》,左岸文化,2021 年,第 43 页。
[4] 陆林主编,《沈渔邨精神病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 年第 6 版,第 207 页。
[5] 许又新著,《精神病理学》,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1 年第 2 版,第 6 页。
[6] 该量表囊括了家庭经济、个人经历、行为习惯、饮食睡眠、人际关系、手机及平板使用情况、校园欺凌、自伤行为、自杀意念与行为等诸多信息。
[7] 《两种心灵》,第 98 页。
[8] 哈利•柯林斯、崔弗•平区著,李尚仁译,《科伦医生吐真言——医学争议教我们的二三事》,左岸文化,2016 年,第 25-27 页。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