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政治、文化与社会:多元视角下的宋史研究与写作
2023大学问首届年度学术出版论坛于今年10月在桂林举行,邀请北京大学博雅荣休教授邓小南,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虞云国,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王瑞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围绕“政治、文化与社会:多元视角下的宋史研究与写作”做圆桌讨论,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黄博主持。本文系圆桌讨论文字稿,经主讲人审定,由澎湃新闻首发。

黄博:大家好,我是今天下午活动的主持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黄博。关于宋代文化,陈寅恪曾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也曾评价:“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在此也想问问四位老师,相对于汉唐,相对于明清,宋代文化“造极”和“空前绝后”的地方,到底体现在哪些地方?又为什么会出现在宋,而不是唐或者明呢?比如说大唐盛世万国来朝,不是更能代表中国鼎盛时期呢?就这个问题,我们想请教一下四位老师。
邓小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或者说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关于所谓“造极”,其实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些主要的王朝,可能各有其“造极”之处。现在陈先生所说的是华夏民族的文化,在宋代达到了一个“造极”的程度。
对这个“造极说”,我今天上午稍微提到过一点,我觉得要分几个层面来看。“造极说”和是否“造极”,意思或许不完全相同。像我们说“唐宋变革说”,不等于说唐宋变革:“唐宋变革说”是一种假说,是一种认识的框架;而唐宋变革,指的是一种历史上的一种现象,一种状态。对于“造极说”,我们也应该分两个层次来看。
首先,所谓“造极说”,是我们从陈先生文章中抽象出来的一种概括方式,不完全是陈先生的理论创设。我们要把这一说法放到特定的语境下,不能把它孤立地看。今天上午曾经在屏幕上展示出来,1943年我父亲的文章前面陈寅恪先生的序,还有1948年重印时陈先生的序,当然这两句的文字没有什么区别。我是想说,我们不能从陈先生的序文里单独拎出一句话来讲,我们是要看这一句话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下提出来的,那个时候是1943年,1943年是什么时候?是抗日战争最紧张的时候,是最惨烈的时候,还看不到最后胜利的曙光的时候。

我觉得,就像陈先生在给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下册写的审查意见里面,所说“古人的著述立说,皆有所谓而发”,就是都是有目的的,都是有针对性的。所以对前人说这个话的环境、背景,我们必须得完全明了,要不然就很难准确地对前人的学说有所把握。陈先生1943年的时候特别强调华夏文明之文化是有特定的原因的。他所期待的是那种树木“本根”的顽强再生,是在阳春气暖时候的复苏。而且我们也知道,陈先生本人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在他的很多文章里面,都在强调胡汉的融合,讨论印度佛教的传来对于中国文化起到的甚至于是改造的作用,至少是一种调节和丰富的作用。所以我觉得对于所谓的“造极说”,我们要在比较通达的语境下予以认识。
至于是不是“造极”,这是另一个问题。刚才黄博老师说到,我父亲曾经在一篇文章里面说,“两宋期间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达到了一种空前绝后的程度”,他指的是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里面,宋代的文明程度是空前绝后的。这一说法也是经常受到质疑的。
无论是邓先生还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陈先生,其实他们的说法都是有针对性的。换句话说,陈先生讲到的华夏民族的文化,我父亲讲到的两宋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不是对宋代的政治、军事、外交的全面评价,至少不能笼统地一概包括在内。
另外,所谓的“高度”,我觉得其实也是指相对的高度。他们两位从来没有说过,而且我想他们从来没有认为宋代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所以我觉得认识这个问题,是要把握一个分寸的。老先生当时其实是有很强的分寸感的,他们的说法、针对性,都把握在特定的分寸内。我们今天回过头认识这个问题,也是要有分寸感的。不是说宋代就是方方面面都是一个黄金时代,我觉得这个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另外,刚才主持人也提到,提到造极,为什么不是说汉,为什么不是说唐,为什么不是说万国来朝?其实我们说到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大概不一定是和万国来朝联系在一起的,陈先生所说华夏民族的文化,也不是和万国来朝联系在一起的。
历史上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有成就基本上不是偶然迸发的,不是某一个时期突然一下冒出来的,而是长期积累后的凸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汉唐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给宋代奠定了基础,它们当年都有空前的成就:汉代有它的空前的成就,唐代有它的空前的成就。没有汉唐就没有宋代,我们应该可以这样说。
但是这里的问题,可能还在于“绝后”。是不是绝后?我们基本可以说历史上各个时代大体上还是在往前走,当然也不是直线发展。这个“绝后”也是有限定的,这个特定所指也是陈先生和邓先生曾经说到过的。宋代以后,王瑞来先生讲宋元之间的变革,我自己是觉得,从蒙元时期到明清时期,在物质文化这个层面,肯定是有进步的,学术方面也有不同方面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在精神文明的一些侧面也是有提高的。但是,比如经济上的周折和曾经的萧条也是很明显的;另外,政治制度方面的专制和管控的方式,这样的变化带来的集权、专制、独裁,和唐宋以来的趋势相比,是严酷得多了。而且,我们也会看到,相对来说,人的发展空间、士人是否受到尊重,在蒙元以后,在明清时期,和宋代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有些调节机制逐渐丧失。有一些做蒙元史的学者对此看得很清楚,像周良霄先生在他的著述《皇帝与皇权》里面会说,元代之后,极端专制主义皇权恶性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走上了另一条路。我就说这些。

黄博:谢谢邓老师。邓老师刚才讲的意思是,我们对于历史的阅读也好,理解也好,要有历史感。另一方面,我们去看历史上的学者们做的“断语”做的研究,也要有历史感,或者对他们的历史感也要有一定的同情和了解。所以如何看待“造极说”?我们要对这一段历史的历史有一定的理解。下面我们请虞老师谈谈。
虞云国:刚才邓老师提出一个观点,对于陈寅恪先生的著名的论断——“造极说”,要从历史的角度去全面认识。我记得改革开放不久中央就说,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全面准确”这个话也适合于我们了解历史研究上的有关的名言,包括对于整个宋代的理解,也应该是全面和准确的。
我接着刚才邓老师的话,想说一下我的看法。陈寅恪先生在1943年提出这个话,肯定是有他自己的寄寓在里面,他是藉宋朝的文化之酒杯来浇自己胸中之块垒。如果通观陈寅恪先生关于宋代的一系列论述的话,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他对宋代文化的评价总体是相当高的。
比如他在给蒋天枢《赠蒋秉南序》里面,也有类似的说法:“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我想陈先生主要是从人文思想角度肯定宋朝的。我们说宋朝的文化实际有好多层面,像我们说的制度层面、精神文化层面、物质文化层面,都体现了宋代文化的不同面向。
陈先生主要是从人文思想角度来说的。相对说起来,宋代确实是比较自由、比较开放,我认为他所肯定的,也就是他在为王国维先生所写的纪念碑里面的话,也就是说,强调它的“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在这点上,宋代比起其他的帝制时代来看,确实是达到了他的评价的。
所以所谓的“文化造极说”,并不是说宋代一切文化都造极了,所有的文化层面都造极了,这点刚才邓老师也说了,在以后的明清时代,还有各自发展的方面。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另外一个看法,后面还有一段话,是“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对于我们一般的读者,不是搞宋史研究的大众来讲,恐怕就会引起另外一种误解:所谓“终必复振”,是不是一定要回到宋代文化上面去?我们还是要全面准确地来理解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终必复振”的意思,我们还是要全面把握陈寅恪先生关于中国文化的论断。就像上午邓老师提的,要以蛮族的精神再加上我们原生的文化的底蕴创造一种新的文化。
他在另外一个地方还为我们中华文化提出了一个方向,是一方面要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另外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它是很辩证的,也就是说外来的好东西我们要把它吸收过来,无论是制度、文化还是其他的科技方面的东西。在文化上面,我们还要秉持开放的态度。我们现在说要改革开放,这个开放很重要。
另外一方面,本民族优秀的东西,也就是陈先生所强调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们也还要把它秉持下去,不要把它抛掉。这个才是陈先生心目中的中华文化之复振。
陈先生这个话是为邓广铭先生《宋史职官志考正》写的序言,我们作为搞宋史的学者,当然也很关心邓广铭先生的有关的著述。这方面最有发言权的是邓小南老师。我把邓广铭先生关于宋代文化的论述,做了一个排序:在1986年,邓先生说过这么一句话:“两宋期间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这是邓广铭先生在1986年的论述。他提出了“空前绝后”,当然对这个“绝后”怎么理解,刚才邓老师也发表了她的见解。
邓广铭先生的论述,我认为和陈寅恪先生的“造极说”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邓先生对于宋代文化“空前绝后”的评价,后来好像有所修正。他为陈植锷先生的《北宋文化史述论》写了一个序引,在里面一开头是这么表述的:“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止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它是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的。”而后又说:“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能及。”这是他在1990年的一段论述。
这里面我认为,他是把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以后的文化划出来进行一个比较,在明清之际,西学东渐以后,我们的文化又有一个新的发展。在这以前,是空前绝后的。
而后在1992年,我们中国宋史研究会有一次国际宋史讨论会,邓广铭先生做了一次开幕讲话,在开幕词里说了这么一段话:“宋代文化发展所达到的高度,从10世纪后半期到13世纪中叶这段历史时期,是居于全世界的领先地位的。”所以我认为,对于陈先生的论述,要从他的整个宋史观、他的整个中国文化观去理解。我认为,对于邓广铭先生关于宋史、关于宋代文化的论述,也要把所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串起来,才能得出一种比较准确、比较全面而不走样的理解,这是我对两位大师的著名论断的一种理解,并不一定准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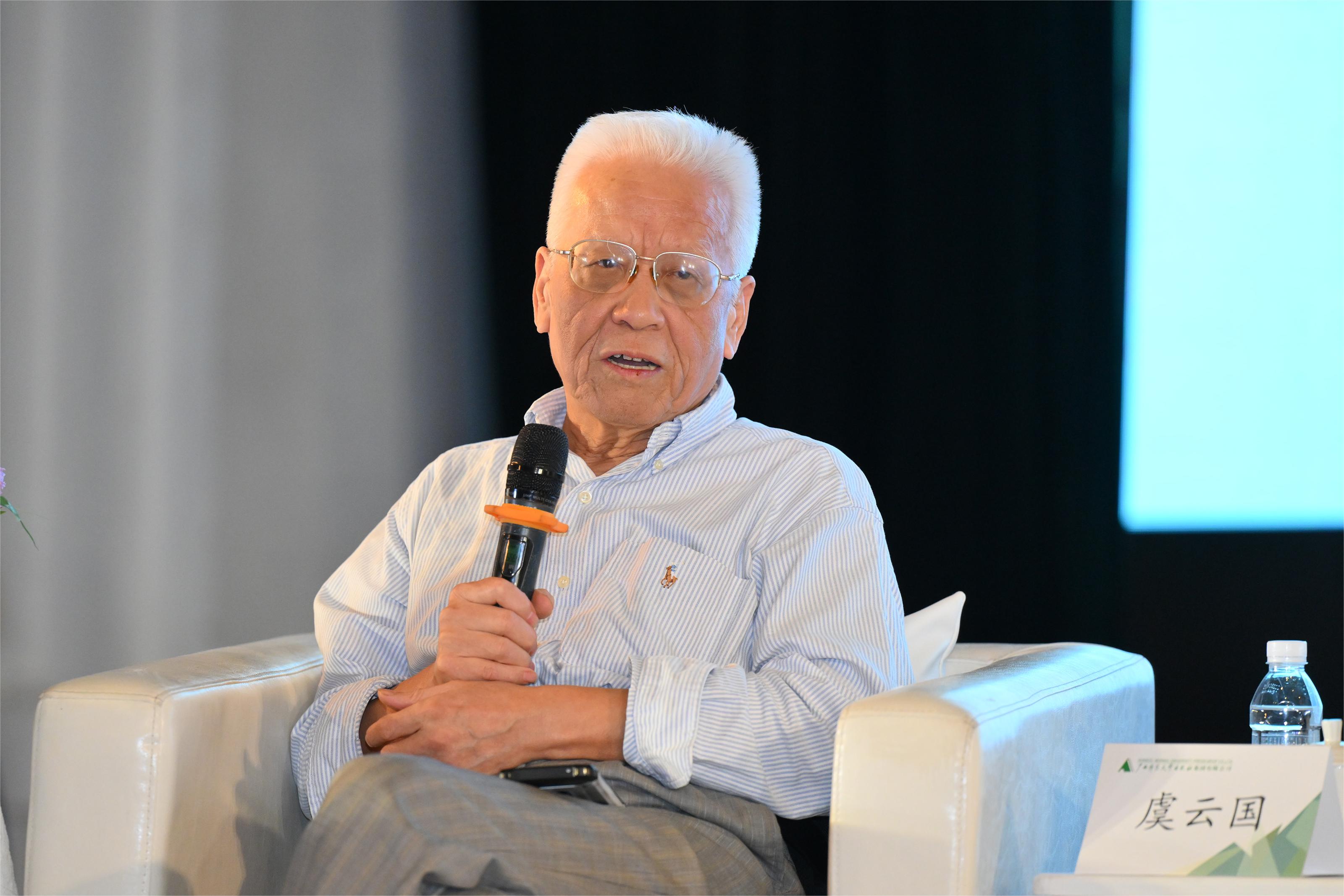
黄博:谢谢虞老师精彩的分享。听了之后我感觉当年陈寅恪、邓广铭先生当年的“造极”以及“空前绝后”说,都是带着强烈的文化自信提出的。我突然想到,我们刚才说汉唐明清在很多地方的强势远超宋代,但是南宋初年面临跟陈寅恪先生相同社会困境的时候,有一个叫作史尧弼的人,在南宋初年大宋风雨飘摇的时候,他竟然还敢说“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我宋朝文物之盛,比汉唐还要厉害。我觉得这样一种宋人的自信,是我们今天理解宋代文化的“造极”,或者说宋代文化魅力的切入点。我想请王老师围绕这个问题,以及刚才谈到的怎么理解“造极”,还有“造极说”谈一下。
王瑞来:刚才邓小南老师、虞云国老师,讲的都是这次山水阅读节的一个主题,就是追问“何以造极”。实际上,准确理解陈寅恪先生的“造极说”是很困难的。或者说,这个问题分很多层面。何以造极?这实际是包含了我们如何认识宋代历史的问题。过去有一句话说,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包括我们宋史研究者心目中的宋代都不一样。刚才虞云国先生讲的一句话非常好,用陈寅恪先生纪念王国维那段话,“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用这句话来诠释何以造极,我觉得是抓住了它的本质。
为什么这样讲?我的学术研究的一个主题,或者说研究的主线是士大夫政治。士大夫政治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宋代开始的。大家就会问了,任何时代都有士大夫,为什么士大夫政治是宋代开始的?这个就和北宋扩大科举规模有关系。大家知道,科举从隋朝开始发端,唐朝的时候,一直是涓涓细流,每一科合格者登第者都只有十几个人、几十个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北宋太祖朝,还是这样仅仅是“不绝若线”。不过从太宗朝开始,大规模扩大科举考试,一次取士达到几百人甚至上千人。十几年持续下来,到了太宗朝后期,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已经登上了政治舞台的顶端。包括我和赵冬梅老师都写过的寇准,就是其中之一。
宋代的科举和唐代的科举有什么不一样?——实际我这个问题也是在回答“造极于宋代,为什么不是强盛的汉唐”?——最大的不同,就是有士大夫政治。我们也可以用“唐宋变革说”的话语脉络来讲,士大夫政治是继承了一种平民化的方式,“一切以程文为去留”,人人都可以参加考试,凭成绩来录取。在唐代的时候,要想考科举,还要行卷——把自己的一些好的文章拿给一些有影响的高官看,然后才能获得机会。但是宋代是“弥封糊名”,做到了相对公平,平民通过努力,也可以走入仕途。比如说范仲淹就是这样。
这种士大夫政治,它造就了我们所说的中国历史上最好的40年,就是宋仁宗时期。当然这个时期是不是最好,也有另外的说法,这里是一般普通的说法。
扩大科举有它的必然性,但是这个举措也有它的偶然性。但是这种偶然性的举措,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所以我就在想,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是针对什么来讲的呢?我觉得这其中就包括宋代和汉唐最大的区别,这个区别就是士大夫政治。
今天上午提到了文彦博“为与士大夫治天下”,大家都拿这句话来讲宋代的君臣共治,这是一个很大的特点。不光是君臣共治,士大夫几乎是在实际上和具体的皇帝平起平坐。王安石讲过这样一句话:“虽天子,北面而问焉。”即使你面南背北为王,也要转过身来(面北)恭恭敬敬向我来请教。
“为与士大夫治天下”讲如何共治,但北宋张载的那句话更重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里面没有君主的影子,充满了士大夫的自豪。
我曾经在我的一篇文章《将错就错——宋代士大夫的“原道”论》中说道,汉字里的君,一般是指君主,指皇帝。但是在先秦并不是这样。在先秦,君是指诸侯国国君。天下共主,周天子那才是天子,相当于后来的皇帝。在战国时期,竞争比较激烈,人们都想把人才聚拢到自己门下。比如战国时孟尝君的招贤养士。《论语》也有讲到,春秋时代就这样,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都是在招揽人才。这个时候,哪个地方政治清明,人们就到哪里去,没有太多的顾虑。连孔子都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时候就产生了很多限制君权的言论。大家都知道孟子讲“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还有讲,如果你把我当草芥,我就把你当寇仇。为什么有这些言论?后来朱元璋看了这些言论非常不爽,认为这些都不应当是做臣下说的,后来作了《孟子节文》。
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动荡,君的意思,就是指诸侯国君。但是到了大一统,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秦汉以后的君就是指皇帝。宋人以他们的儒学素养,完全清楚这就是用来限制诸侯国国君的言论。他们把这个思想资源作为一个武器来限制宋代的皇帝,所以才使得他们有昂扬的斗志和深刻的自信。
关于宋代士大夫的这种精神——我讲士大夫是一个集合的概念,并不是个人。士大夫中不乏无耻者,但是从整体上说,即使只是少数人能够体现这种精神,它也是值得赞扬值得继承下来的。——这种宋代士大夫精神后来是为中国士人所继承了,“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作为一种基因,已经植入后来士人的精神血脉当中。所以像明代,具体皇权发挥得很厉害,动辄廷杖士大夫,但是前面打倒了后面接上去,这种士大夫精神就是来自宋代。所以,“造极之世”何以不是强盛的汉唐,而是宋朝,是因为它有士大夫政治。士大夫政治体现的精神之一就是一种自由的精神。我觉得这一点是陈寅恪先生内心里面深深向往、羡慕和希望能够发扬光大的东西。当我们了解陈寅恪的思想脉络之后,我觉得这种诠释应当可以成为一说。谢谢。

黄博:谢谢王老师,王老师给我们阐发了宋代的魅力来自于自信,而这种自信来自于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崛起和士大夫政治的运作。不过包括君臣共治在内的士大夫政治,有多少是他们的理想,有多少是实操中的现实?这个其实是值得我们考虑的。包括“造极”的问题,我想从这个角度,请教一下赵老师。
赵冬梅:我们今天在这谈“造极说”,其实是可以分为若干层面。第一,陈先生讲“造极”的时候,他讲的造极究竟是什么,还有陈先生、邓先生对于宋代的观点,如果“造极说”在本质上是对于宋代在中国历史当中所处的地位的一个性质认定的话,陈先生究竟是怎么看的?他在说“造极”的时候,他在1943年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他写完之后仰天长叹的时候,叹的是什么,想的是什么。邓老师和虞老师都指出,尤其邓老师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回到历史情境当中去理解古人,同时在历史情境当中认识学者所写下的那些文字。陈先生说“造极”,邓先生说“空前绝后”。其实我印象中的邓先生说的空前绝后,是说“在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西学东渐为止”。我感觉邓先生和陈先生相比,一方面在时间上是往回收了,在面向上,可能又是比陈先生大了。
我们怎么理解陈先生的“造极说”,这是另一个层面的意思。第二个层面,在我们这个时代怎么理解陈先生的“造极说”。陈先生是1943年,80年前,他为邓先生的《宋史职官志考正》作序,那时是中国现代范畴的宋史研究刚刚开始的时候,那是奠基之作。在80年之后,我们有了80年的海峡两岸、世界各地的学者对宋代的研究,在80年研究的基础之上,今天的我们如何定位宋朝,就是给宋朝的历史定位究竟是什么?我觉得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我自己今天上午说,我在政治文化的意义上,接受陈先生的“造极说”。以上是我们怎么认识陈先生所说的“造极说”,以及“造极说”接受史层面的讨论。
还有一个跟接受史有关联的问题是,为什么今天,2023年,我们会在桂林开这样一个会。为什么过去的大概二十年间,宋朝在中国普通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心目中的印象,变得完全不同了。传统上讲,中国人谈我们自己的历史,最自豪的部分是汉唐,宋代其实是不被重视的一个部分。可是在过去大约二十年间,宋朝就变成了一个受人待见的朝代,甚至坊间还有年轻一代的“宋粉”出现。我记得张邦炜先生的《两宋王朝史》在北京开发布会的时候,我跟邓老师、包伟民老师、曹家齐老师,等等那一圈人,每人都说了同样的一句话,就是“我不是宋粉”。今天我们在谈“造极”的时候,我想这也是刚才邓老师说的,不同的时代肯定有不同的造极的面向,如果说宋代在政治、文化上,确实有它独到的地方,确实有它值得赞美的地方,那么,我们应该去学习那个好的地方。我们要把好的地方理清楚、讲明白。但是,我们看历史的方法,不是说宋代有一些很先进的东西,我们就拿来,然后就用现代的语言,把它放到一个现代的认识的框架当中去重新摆放它。我们从宋朝的历史当中,拿过来一些积木,然后放置到一个现代框架的高楼大厦里面,这儿放一块、那儿放一块,然后说:啊!宋朝多伟大!那不是宋。这就是为什么那天发布会上,宋史学者都在说“我不是宋粉”。
今天当我们赞美宋朝的时候,我们要赞美的是什么?宋朝毕竟是在传统中国的帝制发展脉络中的一个链环,它是前面的朝代的延续,也是在它之后的朝代的前身。这个没有办法,是剪不断的,所以没有单摆浮搁地对宋的赞美,就像曾经对汉唐的赞美一样。如果要么赞美,要么反对,那这个赞美和反对同样都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不值得赞成的。我们今天应该有一个更加理性的态度,首先学术界的梳理,对于宋代实际状况的梳理,就该有更理性的态度。还有面向公众的阅读,我想至少来到这里的和在网上陪伴我们的读者,都是有能力来区分、认识更加复杂的事物的,有能力以更接近事物本来面貌的形式去认识它,比如说宋朝。
我在某些方面是同意“造极说”的,但是为什么会在宋朝出现造极?其实陈寅恪先生还有一句话:“六朝及天水一朝,思想最为自由。”如果我们用它来解释“造极”,这会是一个特别简单的答案。但是我们要回到陈先生的原话,这话在说什么?他是在说骈体文的写作。骈体文是一种高度讲究形式美的文字,很难写。既要这么讲究形式美,又要能够表达思想,陈先生说这个太难了,所以只有在一些思想最为自由的时代,才能写出真正好的,既有形式上的美观,又载道的文字。刚才我解释了陈先生所说的“六朝及天水一朝,思想最为自由”。
再接下来就是我对陈先生的阐发。我觉得陈先生说的六朝及天水一朝的“自由”,可以放在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当中来看。六朝的自由是一种破坏性的自由,是旧有的经学已经禁锢思想,所以要打破传统,把道家的东西,还要把佛教的东西引进来,打破旧的思想框架。
然后宋朝的自由,从打破旧思想框架开始,经过了漫长的时间,在一千年之中,比如说佛教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让中国人的思想变得更加深邃。可是,中国毕竟是中国,我们最终还要“有我的”建设。所以前面的自由是一种破坏的自由,到宋朝,思想的自由是一种“建设”的自由。比如到南宋,我们看到了集大成者朱熹。但是当朱熹的理学被立为官方正统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新的教条开始了。
另外还有一个我自己的感受,我之所以觉得宋朝造极,其实就是承认宋朝在某些方面是空前的,是绝后的。我和我们系的一些搞元明清史研究的同事们聊天的时候,大家都比较一致地非常心悦诚服地认为,宋朝在国家治理的层面上,治理的水平就是很高的,就是比元明清高。关于君臣关系,我推荐大家读姚大力老师很早的一篇论文,题目我忘了,就是谈君臣关系,谈宋代还是承认“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就是以礼义换忠诚。但是到了朱元璋的时代,我们看他在说什么。如果和宋朝相比的话,思想的自由度大大降低了。比如说明朝人会觉得,“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本身就不对,谁敢说这样的话?可这是夫子说的话呀,就连孔子说过的很讲道理的话,明朝人也会diss它。
所以在这个角度上说,我个人觉得,宋朝确实在政治文化上有出现过“造极”的现象,但是没扛住,其实我上午就是在讲为什么没扛住。

黄博:谢谢,赵老师把宋代文化的魅力以及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阐发得非常精彩。通过刚才赵老师讲的宋代文化的“破”和“立”的两方面,我们能够感受到宋代的思想的深刻程度是真的很厉害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何以造极”不是数量上的造极,而是深度上的造极。
我们要把“造极”放到历史的长河里去看。陈寅恪先生讲的那句话,我自己觉得最有意思的,其实是后面的“后渐衰微”四个字。我们怎么理解这个衰微?为什么会衰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衰微的?是不是北宋的灭亡?北宋的灭亡又起源于什么时候?
今天上午老师们都讲到《元祐党籍碑》。当然现在这块碑是艺术以及历史文化的宝贵遗产,但是如果了解这块碑的历史的话,我们今天看它有多么宝贵,当年的人看它就有多么惊心动魄。它背负了太多人的颠沛流离、家破人亡。这就是“造极”之后,宋代面临诸多问题,大家想维持繁荣、挽救大宋,不同人有不同的解决方案,最后却换来了一个可怕的后果。比如神宗、王安石,一顿很猛的改革操作;比方说徽宗、蔡京,虽然现在我们说徽宗是昏君,但是当时他本意是想让大宋走向更加繁荣昌盛,铸就更伟大的盛世。为什么会这样呢?不知我们在座嘉宾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我想请四位老师谈一谈。
虞云国:主持人提了这么一个问题,“后渐衰微”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王安石变法开始,还是元祐党争以后,北宋政治进一步黑暗所造成的?我还是接着刚才陈寅恪先生的话来考虑这个问题。“文化造极”和所谓的“后渐衰微”,还是要扩大到整个宋代文化上面来说。但是我们讲文化又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综合体,在讨论“后渐衰微”上面,恐怕还要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把它细化来讨论。这个时候应该宜细不宜粗。
比如思想的衰微,南宋还有陆九渊的心学的创立,还有上午所提到过的南宋浙东学派(事功学派)的创立,说明整个宋代的学术在北宋灭亡以后,南宋时期也还在进一步朝前推。它显然也应该属于“造极”的范围,而不能说它是全面的衰微了。朱熹对于宋学,尤其是宋学里面的理学层面,做了一个集大成的工作。当然,在朱熹去世以后,到了理宗时期,理学官学化。我认为,思想层面的话,这个才算开始衰微。
物质文化的层面就更复杂了。在某一些方面,我认为南宋的发展势头,也还在某种程度上面继续着。当然某些层面的势头,好像不如北宋上升期来得那么健旺,来得那么蓬勃,来得那么创新。但是我认为大体上是向前发展的,可以做这么一个认识。
另外,讲到宋代,唐宋转型也好,唐宋变革也好,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城市的兴起。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和市民阶层的出现,这些出现以后,就有了市民文化。从市民文化角度来看,南宋还在方兴未艾之间。因为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市民文化出现,起码要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标志,那就是比较成型的戏剧,还有长篇的市民小说,这个要到元明之际才出现,戏剧稍微早一点,金元时期就形成了。所以从市民文化角度来看,就不能说北宋以后文化就开始衰微了。
但是,从制度文化角度来看,这是值得我们搞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人再三追究、再三诘问的。上午赵冬梅老师提到,在王安石变法以后,有一个转向,这个观点我基本是同意的。当然,是不是法家转向还可以讨论。我们知道,王安石的变法,它的一个最主要的成功的关键,就是所谓“得君行道”,在这里面,君主的支持是很关键的,而所谓“道”,就是王安石变法的理想和观念。
“得君行道”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让王安石通过一些行政的、思想层面的等等手段,把他的变法主张朝前推进,以便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出现了刘子健先生在《中国转向内在》里面提到的一个命题,因为是君主和宰相,宋神宗和王安石两个人在共同理想的支配下面,去实行变法。他们认为,我们所做的就是利国利民。因此,在变法体制下面,政府就变得自信而武断。
总体上来看,王安石变法我们一般把它划为两个时期:熙宁时期和元丰时期。元丰时期的变法,一个重要内容是元丰官制。宋史学界的普遍看法是,元丰官制的变法,实际是在某种程度上面,要加强君主集权。通过“三省制”的重建,来加强君权。从刚才所讲到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变化,我们就可以看到,通过宋神宗和王安石时期的一系列的变法改制,就把权力进一步集中了。这么一来以后,在宋仁宗时期,庆历和嘉祐年间,曾经一度繁荣的、士大夫官僚对政治发表意见、对君权起一种制约作用的重要职能就被大大削弱了,甚至在某些程度上是有所转向了。
因此,可以看到,实际上“得君行道”——推动王安石变法的一个主要的方针,实际上就变成后来皇帝和代理人独立行使中央控制权的一种模式的开端。人可以不一样——皇帝不一样,宰相不一样,但是这个模式既然开了一个头,就会继续朝前推进。君主专制在这些方面是有它的路径依赖的。
到宋徽宗时期,按照刘子健先生的话来说,是宫廷集权的形态了,由宋徽宗和蔡京为主,来决定整个政治的走向。
从徽宗时期,然后到南宋,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悬在头上的外敌压迫的压力越来越大,改革变法在南宋就基本停止了。再加上宋高宗个人的因素,很快就出现了在宋高宗默许下的秦桧专政,以及南宋中后期不断出现的权相专政。所以说,从政治制度层面来看,恐怕王安石的变法是开了一个不好的头。而后可以看到,这个走向,就一步一步地向更严重的境地滑下去,从这个角度看,政治文化的“衰微”从北宋中后期开始,是基本上可以成立的,当然这是我的一种个人的看法。
黄博:谢谢虞老师。对于“造极说”要全面准确地认识,刚才虞老师就用全面准确的思路谈了怎么看衰微的问题。其他老师有什么要补充的,或者有其他想法?
邓小南:刚才主持人说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说到元祐党籍碑作为“衰微”的一个表征。其实目前存世的《元祐党籍碑》背后的情形比我们看到的要复杂得多,目前能看到的元祐党籍碑在全国仅有两块,都是在我们广西。至少龙隐岩这一份是非常醒目的,当年胡适也专门来找过这一份元祐党籍碑。
值得特别注意的,一个是:当年的元祐党籍碑,就是蔡京当政的时候,这份政治整肃的“元祐党籍”为什么要刻成碑,那个时候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在地方上的影响是什么,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元祐党籍碑是什么时候刻为摩崖的。我们看到,它是在南宋中期庆元党禁期间刻出来的。庆元党禁,我们知道是宁宗时韩侂胄等人整治他政治上的对立派——不仅仅是道学家,对他们有多方面的压制。 而正在这个时候,桂林这个地方一些当年的元祐党——我们姑且说是“党”吧,其实也说不上有什么党——一些所谓元祐党人的同情者,他们的后人,在龙隐岩相当醒目的位置上刻了这样一块元祐党籍碑。到底他们当年为什么要刻这个,是仅仅想为他们的前辈刊刻一个光荣榜,还是说有他们当时的反思和警惕?这种警惕可能是对于徽宗蔡京等当年整肃政治上对立派,制造元祐党籍,以至于造成了北宋灭亡这样一个惨痛教训的警惕;当然也是对于朝廷这样的打击、抑制,是不是会造成刚才各位老师都说到的人文精神——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泯灭、消沉,对于这样一种趋向的警惕。
所以我觉得《元祐党籍碑》这个问题,其实可能比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以为这就是元祐年间的事——还要更复杂。
另外,我赞成刚才几位老师说的,有一些东西我们应该细化讨论,比如刚才说到“后渐衰微”的问题。衰微实际上是一个历史过程,“渐”是有若干节点的,这些节点各自在这个过程里面起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作用,使得这个过程如何曲折地发展下去,我觉得这个是要厘清的,恐怕这不是一个节点所能解决的问题。
我们做历史一般都是往前面时代看,比方我做宋史,相对来说熟悉唐朝,但是我可能不像王瑞来老师同时熟悉元朝。做唐朝的老师可能比较熟悉魏晋南北朝,就不那么熟悉宋朝。这个也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研究的时代是从前面发展而来,我们想把握这个时代,就要看它是怎么发展过来的。
我们现在会看到,像周良霄老师、姚大力老师、张帆老师,都是元史专家。这些国内外顶级的学者,他们都会说到皇权在宋代到蒙元时期的一个重大变化。当然刚才有老师也说到,明清时期延续了这样一种变化的趋势。另外从制度方面来看,草原游牧民族相对来说制度比较粗放,这和宋代的相对繁密、琐细的制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这个对比不是为了区分好和坏、是和非,我们只是说一种客观的现实。
刚才虞云国老师说到,像宋代的制度,像元丰改制,这是宋代制度史上的一个大事,那么它究竟“大”在什么地方?最主要的,其实是试图改变朝廷的一种权力结构:原来的行政机构中书门下分为三省,三省本身要内循环,要相互制约;同时又按照事任分工的原则,行政、军政、监察部门还要彼此相互制衡——这样就形成了多重制约。在宋神宗的时候,可能还勉强能够实行下去,但是到司马光他们回来主政以后,一直讲这样信息不畅效率低,其实是做不下去的。到了南宋,又有重新的调整。元丰时期这种多重制约、多重循环,乃至对于士大夫权利的限制,实际上是皇帝强烈希望能够强化君主集权的一个映射。宋神宗为什么这么强烈地希望强化集权?我觉得跟王安石变法后期皇帝的主观感受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些事情,我们可能要从更多的、更丰富的角度来进行讨论。北宋灭亡是不是一个节点呢?上午赵老师说到大变法,刚才说到北宋灭亡,这些是不是节点呢?理学官学化是不是节点呢?我觉得这些都是节点,包括宋朝灭亡,被元朝取代,这些都是节点。节点的实际意义可能不同。另外,比方说我们通常会说到的“国是”,刚才虞云国老师说到,王安石那时候就是希望“得君行道”;与此同时,当时的士大夫,包括王安石在内,也有一种“致君尧舜”的努力,这也是很多学者曾经讨论过的。实际上这在当时形成一种张力,一方面忠君的思想,“得君行道”的思想是强化了;但是另一方面,希望“致君尧舜”——就是对皇帝有一定的限制,有一定的要求——这样的一种努力,当时也是在强化之中。
所以,说到“后渐衰微”,如果有断限,我觉得至少在陈先生心目中,不应该指的是北宋,也不是指“国是”的出现。像南宋,刚才虞老师说到,南宋的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等这些人在当时代表着新的学术思潮,包括道学、心学、事功学派等等,在一段时期里面,可以说是蓬勃发展。还有就是文化重心的全面下移,包括文学各种各样体裁和题材的多样性,包括文学的创作者,不仅仅限制于士人书斋,甚至于街头说书的市井之人,也参与了多元的创作。当时文化的受众,应该说也是面向更广大的社会阶层。这些都应该是在华夏文化的整体成就之中的。
所以我个人是想,我们讨论后渐衰微这个问题,不能一刀切出唯一的断点来,而是要把它看作一个逐渐的过程,其中一些重要的节点,可能有标志性,对这些节点,我们应该有所把握。
黄博:谢谢邓老师。我们对于“衰微”理解也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过程。也是有起伏的,我的理解是在衰微的过程中也有闪光点出现,包括刚才各位老师都讲到这个问题。王老师有没有补充的?
王瑞来:我非常赞同邓老师的说法,后渐衰微的“渐”,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它不是哪一天早上突然出现的,这个“渐”本身就是渐渐地意思。
讨论这个问题要区别出几个问题,我们要把思考细分化。首先要从王朝史的窠臼中摆脱出来;另外一个是,制度的规定和实际的实施,它是两回事。把它们区别开来,我们才能更为清晰地得到一些认识。
如果我们非常明确地把这个衰微的节点定在北宋,甚至是王安石变法,实际上就跟“王安石变法亡国论”一致了。南宋的时候特别盛行这个说法,北宋灭亡以后,痛定思痛,反思、追寻历史教训,最后归结于王安石变法。
实际文化的层面是多层面的,政治文化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还有更多的社会文化在里面。怎样理解“造极于赵宋”的宋,还有今天虞云国老师引用的陈邦瞻讲的“无一不与宋近者”。对于这个“宋”如何理解?两宋320年,是有北宋,有南宋,实际两宋的状况甚至性质是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理解,“造极于赵宋”的这个宋,恐怕更多的是指南宋。如果讲衰微,从北宋就开始了,那么南宋道学的兴盛、思想的发达如何解释?
还有我刚才讲,从王朝史的研究范畴里摆脱出来,因为历史有更多的面向。前些年在倡导宋元变革论的时候,我就组织一个笔谈,叫做“向下看历史”。一个是针对唐宋变革论,向上跟中唐以上的时代相比,得出的结论来看,我是向明清、向近代,探讨中国历史如何走过宋元,经历明清,走到近代,走到今天,这是一个“向下”。另外一个“向下”,就是从并不仅仅着眼于王朝政治、中央政治,而是着眼于地方社会的发展,向下——民间社会。所以这次我这本书,我们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的,就叫做《士人走向民间》,强调这个民间,强调地域。
南宋刚才邓小南老师也讲到,说书业等等文化的发达,这里面我们今天讲新媒体,实际南宋就产生了新媒体——印刷业。印刷业大家都知道,从唐末五代就开始有雕版印刷了,但是在南宋的时候,由于造纸技术的改进,纸张得到了大量廉价的普及,而北宋的印刷业繁荣还属于在宫廷之内,今天上午赵冬梅老师讲到雕版的榜文,南宋的时候民间书坊兴起,大家都来印刷,普通的老百姓童蒙、历算等等这些书都要买。而且那个时候出书也很简单,像朱熹到哪儿去刻部书,比方说到建阳书坊去刻书,这都有记录的。
所以新媒体革命带来了文化下移的风潮,在这个风潮中,新媒体起到一个催化剂的作用。所以我讲南宋在文化的兴盛,包括市民文化,小说、戏曲、话本,都是很有特色的,而且这些都被元明所继承。如果从政治文化的层面上,稍稍摆脱开来,转向社会文化来看,这个面向就大不一样。
所以在我看来,陈寅恪先生说的“造极于赵宋”的这个宋,很大程度上是指南宋。另外“后渐衰微”,这是一种宏观的历史观察,这种观察不仅仅包括政治文化,它包括各个方面,也包括当时在被非中原文化统治下的市民社会文化。
黄博:我的感觉是,王老师也未必会觉得元代就真的那么糟糕。
王瑞来:是的,我一直觉得,大家往往会想当然地来理解元代,因为元代是中国全域第一次被非汉族所统治。在以前有过魏晋南北朝,有过辽宋分立,有过宋金分立,那都是区域性的统治。到了元代,那个时候“遗民忍死望恢复”,是没办法恢复的。
怎么来看元代,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宋元变革论,而且还涉及“是不是北宋灭亡开始是一个节点,然后就衰微了”这个问题。北宋的灭亡有很大的偶然性,不是一个王朝逐渐腐败、黑暗,最后自然走向灭亡,不是这样。它是女真人的突袭,在北宋发展到最鼎盛的时期被灭亡的。
所以,它有实力,可以如不死鸟一样在江南重生。南宋和北宋为什么不一样?北宋政治重心是在中原、在开封。经济重心,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已经在江南形成。所以从隋唐到北宋,一直是经济、政治中心二元化的状态。所以隋炀帝要修大运河,要把物资运到北方。南宋不一样,按我的一句话说,南宋仿佛又回到了南朝,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合一。宋元社会转型,在我看来就是从南宋发端的。
对元代的认识,我想说很多都是想当然的,因为大家都讲元代是四等人制: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民族歧视压迫,而且还有奴隶(驱口)这些,很黑暗。法国学者谢和耐有一本书叫做《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他就讲中国早已进入了近代化的程序,但是是蒙元入侵中断了这种发展;接着他从《马可波罗游记》中找到了杭州等一些城市在南宋灭亡之后元代初期经济繁荣的情况,直接否定了他自己想当然的推论。
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从社会经济、社会生活的角度来看,元代是不是黑暗?我觉得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蒙元征服江南,基本上是不流血征服。蒙古人征服世界各个地方,有一个做法:你只要抵抗,我就屠城。赵冬梅老师翻译的贾志扬的《天潢贵胄》书中就讲到了这一点,屠城是蒙古人征服世界各地的一个标志性行为。征服南宋的时候,也做了一些屠城,比如说常州屠城,因为我整理过《宋季三朝政要》,具体史料我非常清楚。但是多数情况是不流血的征服,这就有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于,保全了江南近千年的生产力、社会结构、经济结构,使它们没有遭到重大的破坏,所以社会经济还可以正常向前发展。
所以接下来就顺利进入明清。当然在明初,由于战乱,也有一些经济上衰退的现象,但后来又很快地恢复过来。所以江南最后成为最具中国元素的地方。过去像国外的一些学者讲的,研究中国,说的中国,主要是江南。所以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元代如果用黑暗来概括,是很不准确的。
还有,刚才我自己讲的时候,会随口把口误纠正过来:我一直说不要讲宋朝、元朝,我们要讲时代,宋代、元代。因为“朝”主要是指王朝,如果我们讲王朝的制度、王朝的政治运作,可以讲宋朝,但是一般泛泛而言,我还是讲宋代、元代。
我就讲这么多。
黄博:王老师讲宋元,实际上把从唐宋元整个长时段的角度去理解和认识宋代地位这个问题,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概括。请赵老师说两句吧。
赵冬梅:我觉得还是那句话,陈先生说的究竟是什么,以及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什么,其实是有分割的。另外还有一个,刚才这个问题的设定,“后渐衰微,终必复振”的前提,我们承认宋代是造极,但是说的只是文化。文化的造极以及衰微,一定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长的过程。而且文化之中,大概也可以分为若干的层次。我们谈文化,大概不太适合和一个政权的生灭线性地挂在一起。刚才各位老师谈了这么多,我就略补充一句,其实诸位可能已经发现了:历史学者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可能会问简单的问题,但是我们的目标——其实也是历史学的优势——就是进入到具体,去挖掘复杂的面向,然后如果可能,我们会给出一个从多种可能性到发展到唯一结果的这样一个过程。而且可能这个过程还不是单一过程,如果说时间是一条线的话,其实这条线是无限粗的,里面有若干变化的线条在里面,伴随着这个时间线,不同变化的节奏是不一样的。
一个靠谱的历史学者,其实不太能够给出简单的答案来。我们倾向于回答说,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以及这个问题我们要分成若干层面。
黄博:谢谢赵老师。赵老师把我们历史学怎么思考和回答问题的思路,展现给了我们。“后渐衰微”之后是“终必复振”,这个信心在哪里?换句话说,宋代文化所取得的成就在衰微以后怎么样了,到元明清时期,甚至包括到今天,还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联系或者传承?想请几位老师简单地说一下。
虞云国:我理解你提的问题,陈寅恪先生既然讲到宋代文化是“造极”之说,然后又讲到终必复振。所谓衰微,就是文化受阻,是不是会用另外一种转型的方式继续发展下去,继续朝前推进。我们史学界对于宋代文化之所以能够形成被陈寅恪先生所推崇的东西,有一个很著名的论断,就是唐宋变革说,我现在是主张唐宋转型,包伟民先生主张的是唐宋转折。各位研究者有自己细微的拿捏在里面。
另外,上午的讲演也好,下午的各位的发言也好,再三提到赵冬梅教授所翻译的刘子健先生《中国转向内在》。书里提出另外一个说法,两宋之际转向内在说。从政治文化角度来看,他的说法我认为是基本应该成立的。在座的王瑞来教授这次推出的大作,主张的是宋元变革说。他认为经过南宋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科举制度也遭到了瓶颈状态,士人由于当时的政治生态,进一步走向民间,而且趋向在元代以后又由于科举暂时停考,因此走向民间的深度和速度,更深、更快了。这实际上就牵涉到,我们研究宋代这段历史,我们各自提出的假说,到底应该怎么看。
我们今天这个对谈的主题,是多元视角下的宋史研究。就我个人角度来看,我认为刚才赵冬梅教授说了,历史学者很难有一个标准的唯一的答案,历史研究本身就是开放和多元的。我记得刘子健先生在他的论著里面说,他看宋史的问题,打了个比方,就好像一块钻石,每一个历史学家可以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去打量宋史这个钻石。
从这个角度出发,他提出了所谓两宋之际转向内在说。我个人的看法,我倒是主张把“唐宋转型说”,“两宋之际转向内在说”和“宋元变革说”,都把它统在一个解释的大箩筐里面,因为这恰恰符合了宋代文化多种的复杂的面向。
唐宋之际,很明显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宋史研究,这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多的成果,唐宋之际的转折也好,转型也好,它的时间跨度比较长,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我认为大体上面,到北宋中期已经表现出成果出来了。可能社会结构方面的转型,也基本上在宋代中期有了一个比较大的结果。但是,家族制度的转型,恐怕宋代刚刚开始;到南宋,包括到元代,家族制度才转变为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所说的家族制。
在文化领域里面,以理学为主体的宋学,应该讲经过北宋五子的创造性阐发,它的基本内容已经呈现;到南宋,经过朱熹的进一步集大成的融合而取得了成果。刚才我说到,市民文化的转型,恐怕还要晚一些。
从这个角度来看,毫无疑问,唐宋转型说是有它合理的解释的穿透力。但是就像刚才我们所讲到的,从政治文化角度来看,确实刘子健先生提出,君主统治可以有四种模式:一种就是刚才王瑞来先生所说的,君臣共治的模式;第二种就是君主和代理人对朝廷大政做出决断,旁边的那些士大夫官僚只能参与;第三个阶段,就是君主和他的代理人是独断,对于国政的决策,其他官员甚至不能参与,只能接受——这个大体上面是南宋初期,高宗前期,大概是绍兴和议建立以前的体制,刘子健先生把它叫做专制的体制;第四种,就是君主和代理人是完全独断朝政,而且打击一切反对他们对于朝政处理意见的反对派的官僚,甚至士大夫。这样就提出了君主官僚政治的这么四种模式。这四种模式,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种模式的最理想状态,就是我们所说的宋仁宗的庆历、嘉祐年间。第二种模式,是宋徽宗时期;第三、四种模式,是宋高宗绍兴和议为界的前期和后期。从这个角度来看,刘子健先生的两宋之际文化转向内在说,主要是指政治转化。这个解释我认为还是基本能够覆盖南宋中后期的权相政治。
另外,由于南宋政治生态的恶化,由于南宋科举制度碰到了瓶颈,因此一些还保持操守的士大夫,即便走上科举道路以后,要正式从政,实现理想,政治生态不允许,然后官阙又很少,就像罗大经一样,待阙了八年才好不容易到广西来做一个小小的地方官。这样一来,他们新儒学的所谓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和热情,还没有完全泯灭。所以,既然当时的社会经济在南宋还在进一步朝前推进,那我就到民间去进行教育,进行乡村建设,进行宗族的重建,等等。这样就出现了王瑞来先生所说的“士人走向民间”——宋元变革说的一个重要的支柱。所以我在这方面,我又是赞同宋元变革的。
我要补充一句的是,一方面我们看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要注意到社会经济的下层民众的或者一般市民的、一般读书人的趋向和变化;另外一方面,我认为我们还要关注上层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态的变化。这一点我认为刘子健先生是讲得很有道理,他说,南宋的经济还在不断地发展,南宋的士大夫包括道学家,他们治国平天下的意念还存在,他们希望出现好皇帝,然后实现他们的“为生民立命”的思想。但是他提醒一句:在帝制时代,君主集权政治是一个硬核,你的社会经济再发展,也不能熔化这个硬核。
因此我就在想,我们也可以把“宋元变革说”分成两个层面来解读:在下层社会、基层社会方面,士人走向民间,包括南方经济进一步发展,可以讲,元朝的统治具有两元化、两重性的方面。在整个政治层面只要能够维护蒙元贵族的统治就可以了。然后派达鲁花赤去监视汉人的官员。很明显,北方经济和南方经济出现了两种形态,北方经济一度破坏比较严重,当然到元朝中后期也有所恢复。而南方经济,蒙元接手了南方政权以后,基本是按照南宋社会、南宋经济发展的路线进一步朝前推进。因此,这种士绅社会和南宋经济的活力,在元代没有被严重打断。所以很快就发展到明朝初期建国以后,在江南出现了类似沈万山之类的富翁。元史研究者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方面的研究成果——我对元史研究没有什么发言权,但是周良霄先生的《皇帝与皇权》我是翻过的,姚大力先生的文章我也读过,包括我所关注的台谏制度。我在上午充分肯定了在君主如果保护士大夫官僚的言事权、论政权,在比较宽松的政治生态下,台谏制度是能够起到制约君权的作用的。但是在政治生态恶化的情况下,台谏官就会成为权相政治的鹰犬和走狗。可以看到,有一点很明显,蒙元贵族入主中原以后,在政治制度层面上,他们把宋代制度里能够维护君主集权的东西都拿过去了,然后又保持了自己的游牧民族的落后的东西,包括达鲁花赤、四等人制等等。
在整个政治制度层面,比如说台谏,取消了谏官,只保留了御史;宋代的御史也是有“言责”,也可以起谏官的作用,但是进入元代以后,整个御史就成为只是监督百官的工具,而对蒙元的皇权实际上不起到多大的制约作用。这种情况到了明代,进一步恶性发作。刚才瑞来先生也提到明代政治的另一个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进入明代以后,整个监察制度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变,就是叫做六道给事中制度,只让这些所谓具有御史职能的官员去监督百官。如果他们要去试图监督君权、制约君权的话,皇帝万一不高兴,那就要廷杖。
现在史学界也有宋元明变革说,关注宋元明之间的连续性变化,可以看到,在政治制度层面上,宋、元、明是变得越来越专制,它把南宋那些负面的东西都拿过去了,而且做了君主集权体制下的进一步发展。这个情况到清代可以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满人统治,汉人士大夫官僚“要做奴才而不可得”,我们就要把它凸出来,讲清楚。
所以我们在讲到宋代文化“造极”的时候,要肯定它在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统治思想方面,那些陈寅恪先生所赞同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是另一方面,要把它放在更大的帝制中国政治这个大框架里面去考察。所谓“二千年来皆秦政也”,我们应该把君主专政的根子追到秦朝为止,这样才能把秦朝到清朝的帝制做一个通贯性的了解,我们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宋代,所谓君臣共治,所谓士大夫的言论自由只出现短短的40年。
王瑞来:我先补充一下刚才讲的,我们讲皇帝行使皇权的时候,包括今天上午赵冬梅老师讲的一些具体的案例,我在想,在君主独裁的背后,最好是把党争的因素充分地考虑进去,这是士大夫之间的一种政治争执。
另外,虞云国先生讲的从宏观的通史的视野来看宋代政治、文化的衰微,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我想陈寅恪先生讲的“后渐衰微”,实际是从综合层面来讲的,一直到其身处的民国年间,针对日寇入侵、中国孱弱的情况发出的一个感怀。然后“后必复振”,那是一种期待。中华文化必定要重新复兴,所以这一点我很认可。
另外关于刘子健先生的《中国转向内在》,我非常赞同他的“两宋之际变革说”,这个“变革说”极大地启发了我的宋元变革论。但是刘子健先生两宋之际变革说,开启的时间是两宋之际,什么时候终了,他没有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宋元变革论对他多少是一个补充。
另外,中国是不是两宋之际就“转向内在”,如果从政治文化的层面上讲,也许可以这样讲;但是如果从全面来看,我在书中直接就讲到,我不同意两宋之际“中国转向内在”。因为后来有很多方面是变得越来越开放的,根本不是转向内在、内敛的状况。但是从政治文化讲,这个问题不大。
虞云国:刘子健先生没有说两宋之际变革,只是强调两宋之际政治文化内转、内向。实际上,王先生是在刘子健先生这么一个前提下面,看到了南宋社会有另外一个发展的面向,做了一个补充。所以我刚才一开始这段发言之前就说了,我是主张把唐宋转型、两宋之际转向内在和王先生的宋元变革论糅合在一起,对宋史,对宋代社会,对宋代文化做一个融通起来的解释,这样也许我们可以从更多层面上,看到这颗钻石的各个方面。
王瑞来:虞云国先生归纳得非常好,而且是基于理想性的设想。但是,是不是从唐宋变革一直到元明清转型,都能在一个范畴下、一个议题下来进行解释?这恐怕是比较困难。起码在我看来,唐宋变革论走到北宋已经是举步维艰了,对南宋的一些现象没法解释,到了元代就更没法解释。所以过去讲宋元变革论是一个框,什么都能往里装,把它当做一个理论范式来套,这根本是一种不科学的做法。
还有,变革也好,转折也好,转型也好,具体用语并不重要,只是如何解释,能够更准确地观察到中国历史走向的一种形态。而且变化并不是一个突然性的变化,都是一种渐变。至于唐宋变革也好,两宋之际也好,宋元变革也好,都是不同学者站在不同的角度进行的归纳,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我就讲一句话,我们研究历史有时就像盲人摸象,各得其真,各得其形。
虞云国:我同意王瑞来教授的说法。我们刚才所说唐宋转型也好,两宋之际转向内在也好,宋元变革也好,实际上都是对历史的某些方面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用刘子健先生的话来说,是大的概括,有的时候总会有它顾不周全的地方,问题是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历史课题方面来采纳有关解释的某种模式。比如说唐宋转型,刚才瑞来先生说了,基本上到北宋停止了。实际上,如果我们把有些问题再进一步讨论下去的话,恐怕“到北宋停止”这个结论也还不能完全有一种涵盖性。比如说在法律层面,当然法律层面北宋有很大的变化,我记得我们宋史学界搞法律史的戴建国老师,他就认为从法律制度层面来看,转型大概到北宋后期结束了。但是在有一些身份法上,南宋进一步有所改变,包括对家里奴婢的身份认定,有一些法律的细节改变,仍然值得我们重视的。
所以,历史一旦细化以后,恐怕其展现出来的光彩真的不是我们固执的那一面所能够涵盖的。因此我就想,包括刚才你说到的,唐宋转型是所谓近世说,这是按照日本学者来讲的。而近世说里一个主要的成分,就是所谓市民文化,市民文化的真正成熟,要到元明之际,尤其明代中后期才蔚为大观的。
我们著名的四大古典小说(这里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基本上都是元明时期才出现的。所以这样一来肯定要把它的下限往下推,但是另一方面,并不妨碍在政治文化层面上,采纳刘子健的说法。而在采纳他的说法的时候,又不妨采纳王瑞来先生“在南宋以后,社会经济、基层结构的另外一个方面的变化”这一说法。模式越多,看待钻石的层面也广,我们对历史的真实度就越高。这正是历史的魅力,也是让我们不断追求它的一种动力。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