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来自张生的小说课:从《人间喜剧》谈到《故事新编》,小说的素材必须有根有据 | 新批评
原创 张生
评论家张生近年来关注小说内核和外延的各个细部,对小说写作与小说批评进行深入探究,以小说的素材、背景、人物、动作、视角等为切入点,析毫剖厘,见微知著。在本报《新批评》刊发的《小说的素材:有根有据》一文中,他以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与鲁迅《故事新编》为例,阐释小说素材的两种来源:直接从生活中开掘,或从已有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取材。而无论是何种素材,最关键的标准都是有根有据。
更重要的是,一个素材能否成为小说,除了它本身的小说性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怎么写”的问题存在。也就是说,一个作家对素材的选择,其实有意无意也受到自己的文学经验和写作能力的影响。

本期封面人物
评论家张生,郭天容/绘
小说的素材:有根有据
文/张生
在小说写作中,素材是重要一环。对于小说素材的开掘来说,最关键的一个标准就是要做到“有根有据”,就是说能从生活中或者从书本中找到线索。同时,一个作家对素材的选择,也有意无意受到自己的文学经验和写作能力的影响。
对于小说家来说,素材的选择是写作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因为“写什么”,永远是第一位的问题,作家只有在确定了“写什么”之后,才能考虑“怎么写”的问题。对于一篇小说来说,素材也很重要,有时素材的选择可以决定一篇小说的成败。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可对于作家来说,还不仅仅是有无素材可用的问题,还牵涉到自身的可持续性写作的问题。如果作家不能持续地开发素材,那么创作就会受到影响,很容易原地打转,给人以重复之感。
很多作家曾经红极一时,后来却忽然销声匿迹,这背后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素材的匮乏或者枯竭。有时素材的枯竭比灵感的枯竭还要致命。一个作家“江郎才尽”,很可能不是这个作家的写作才能或者说那只“五色笔”没有了,而是他的素材没有了。
实际上,做一个小说家不难,难的是一直做个小说家。因为这需要对素材的不断选择与持续开发,所以素材的问题对作家来说至关重要。
而对于小说素材的开掘来说,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标准就是要做到“有根有据”。所谓“有根有据”,就是在选择或者发掘小说的素材时,最好能从生活中或者从书本中找到线索,有一定的“根据”。因为如果素材纯粹是凭空虚构的话,在写作的过程中就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人物不可信,环境不可靠,故事展不开等。从这个前提出发,可以把素材的来源分成两种类型,一是直接从生活里开掘素材,借用巴尔扎克系列小说的名字,就是取材于“人间喜剧”;二是从已有的文学艺术作品里发掘素材,进行再创作,这种做法可以用鲁迅一部小说集的名字来描述,就是所谓的“故事新编”。当然,这两种做法各有千秋,可以并行不悖。

“人间喜剧”:从生活中开掘素材
首先谈谈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式的直接从生活中开掘素材的方法。这种方法一是从“道听途说”中也就是他人的生活中获得合适的素材,二是从个人的生活中提炼素材。这两种方法虽有不同,但都离不开具体的生活。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的前言里谈到这部由九十多部小说和两千多个人物构成的巨著时,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偶然是世上最伟大的小说家:如果想取得丰硕的成果,就必须将它仔细研究。法国社会将成为历史家,我只应该充当它的秘书。编制恶习与美德的清单,搜集激情的主要表现,刻画性格,选取社会上的重要事件,就若干同质的性格特征博采约取,从中糅合出一些典型;做到了这些,笔者或许就能够写出一部许多历史家所忽略了的那种历史,也就是风俗史。我将不厌其烦,不畏其难,来努力完成这套关于十九世纪法国的著作。
这其中,他特别提到了自己开掘小说素材的渠道,那就是“选取社会上的重要事件,就若干同质的性格特征博采约取,从中糅合出一些典型”。像他的《高老头》,就取材于他从“道听途说”中知道的一个真实事件。有个可怜的老父亲在生命垂危,奄奄一息之际,只想喝口水,可他叫喊了二十个小时,也没有人理他,而此时他的两个女儿却一个在看戏,一个在跳舞。巴尔扎克在《高老头》这部小说里,几乎“再现”了这一幕。这样悲剧性的故事本身就已经颇让人震撼,而巴尔扎克又把“神圣的父爱”赋予了高老头,他的那种不顾一切的无条件的乃至病态的对女儿的爱,使得这部小说成为感人至深的杰作。当然,这样的素材可遇不可求。巴尔扎克也可能是从报纸的新闻中看到的,他本人曾经在律师事务所工作过,知道很多这样的“人间悲剧”。至于小说人物活动的主要环境伏盖公寓,巴尔扎克同样毫不陌生,伏盖公寓得名就来自于他熟悉的公寓里的一个小姐的名字,而这个伏盖小姐的家与巴尔扎克的家早有交往,正是有了这些切身的体验,所以巴尔扎克笔下的伏盖公寓才会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
巴尔扎克这种通过自己的“道听途说”从生活里开掘素材的方法,是作家最为常规的做法,比如老舍《骆驼祥子》的素材,也是这么得来的。1936年,老舍在青岛大学教书,他从一个朋友那里听到了两个北平的车夫的故事,因而萌生了写作《骆驼祥子》的灵感。老舍被这两个车夫的不无传奇色彩的故事所吸引,将这两个人的故事融为一体,塑造出了骆驼祥子这个栩栩如生的黄包车夫,不仅把从军队里带回三头骆驼的故事加在祥子身上,而且小说也让祥子“三起三落”,最后沦为穷人,一个靠给人出殡混饭吃的悲剧人物。但是,如果老舍没有听到朋友的这个故事,即使他有生花妙笔,《骆驼祥子》也不可能写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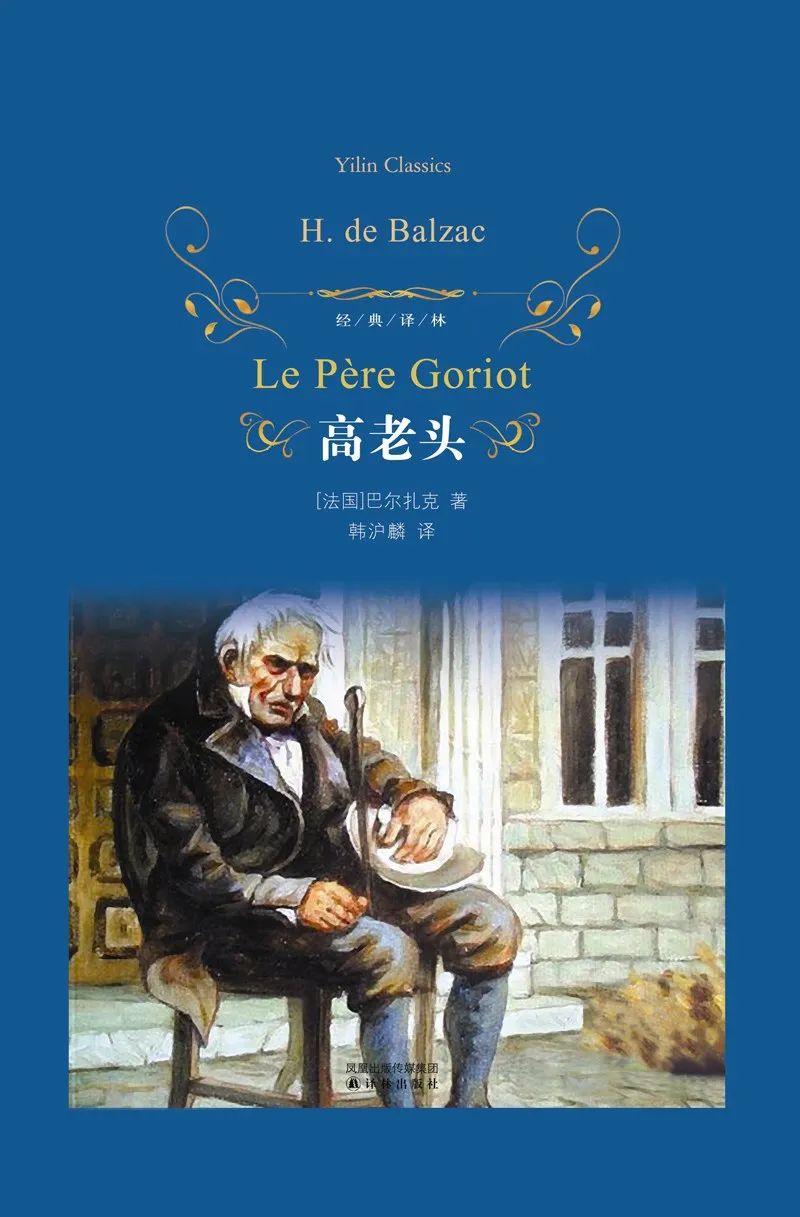
当然,从生活里开掘素材的渠道很多,除了可以“道听途说”他人的故事之外,还有更为直接的方法,那就是从自己的生活经验里取材,既可以从自己的成长经历,也可以从自己的家族故事中取材。
从个人的成长经历取材是作家创作中最常见的开掘素材的方式,比如1932年沈从文30岁时写于青岛的《从文自传》,就是以自己青少年时期在故乡湘西的成长为素材的。他在书的第一节《我所生长的地方》,就开章明义,“拿起我这支笔来,想写点我在这地面上二十年所过的日子,所见的人物,所听的声音,所嗅的气味,也就是说我真真实实所受的人生教育。”因为每个人的成长环境都不一样,每个人在成长时的经历也不一样,所以,写出来的故事也都会不一样。沈从文因为生活在湘西这个“边地”,汉苗杂居,文化多样,加上他精妙的语言和叙述,使得这部“自传”出版后享誉一时。1934年出版后,老舍等人推举沈从文的这本书为“1934年我最爱的一本书”。
而家族故事也是作家素材开源的富矿。因为一个家族庞大的支脉和自身的变迁,本身就是社会变化的晴雨表,其中所蕴含的悲欢离合,自有不为外人所知的感人魅力。正因为此,很多以讲述家族的兴衰为素材的小说,被人冠以“家族小说”的名称。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曹雪芹的《红楼梦》了,还有就是巴金的《家》。巴金自己说:“《家》是一部写实小说,书中的那些人物都是我爱过或者是恨过的,书中有些场面还是我亲眼见过或者亲身经历过的。我写《家》就像在挖开回忆的坟墓。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被迫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得到悲惨的结局。”
巴金的《家》明显受到了《红楼梦》的影响,但巴金自己说他的《家》受到的是左拉《卢贡马卡尔家族》这部由二十多部长篇小说构成的更为庞大的“家族小说”的影响。但不管怎样,家族故事是每一个作家天生的素材宝库,只要予以重视,总能找到合适的素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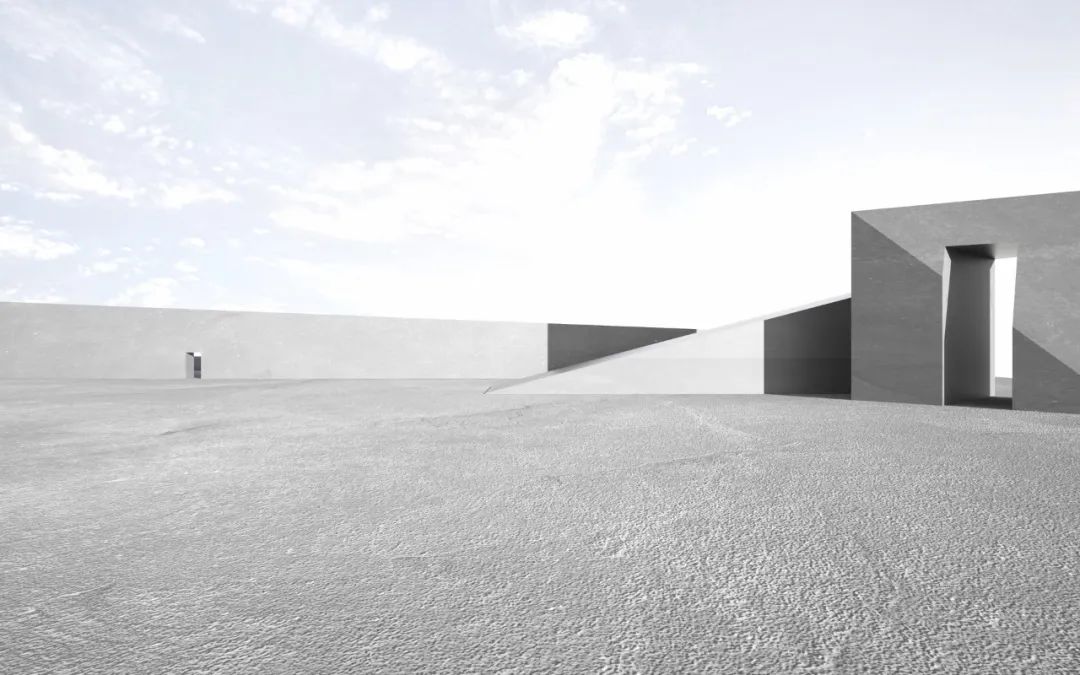
“故事新编”:从文艺作品中取材
其次就是从已有的文艺作品中取材进行再创作的“故事新编”了。这种方法一是可以以各种传说及“故事”为素材进行再创作,另外也可以对已经有的文艺作品作出“改写”。
第一种方法可以从鲁迅1936年出版的《故事新编》讲起。这个小说集由八个短篇组成,与之前鲁迅取材于现实生活的《呐喊》《彷徨》不同,《故事新编》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补天》《奔月》《理水》就分别取自“古代的传说”,即女娲补天,嫦娥奔月,大禹治水;《铸剑》取材于《搜神记》卷十一的《三王墓》等。当然,鲁迅在对这些“故事”进行“新编”时,并非为“故事而故事”,而是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和创造,比如《补天》这篇小说,他自述是“采取弗洛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讲述“精力洋溢”的女娲因为“无聊”而抟土造人的故事。
而“女娲造人”的故事见于《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汉代应劭的《风俗通》,而鲁迅在小说里将其与“女娲补天”的故事予以融合发挥,敷衍成一篇小说,也可以见其才情,所以,即使是批评他的成仿吾也称赞这篇小说。不过,鲁迅的此类小说并不拘泥于史实,或是“言必有据”的“历史小说”,而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或“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由,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
第二种方法就是对已有的文艺作品予以改写,这也是常见的方法。有“新感觉派”小说家之称的施蛰存就是一个好手。他利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激活和处理古人的性欲,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他的《石秀》改编自《水浒传》第四十五回:“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鸠摩罗什》《将军底头》等也都是试图用弗洛伊德的性欲理论去重新演绎过去故事的成功的探索。
那么具体而言,这种故事“新编”的可能性又有哪些呢?或许大致可以分为,故事框架,人物形象叙事的方式,以及主题等几个方面予以新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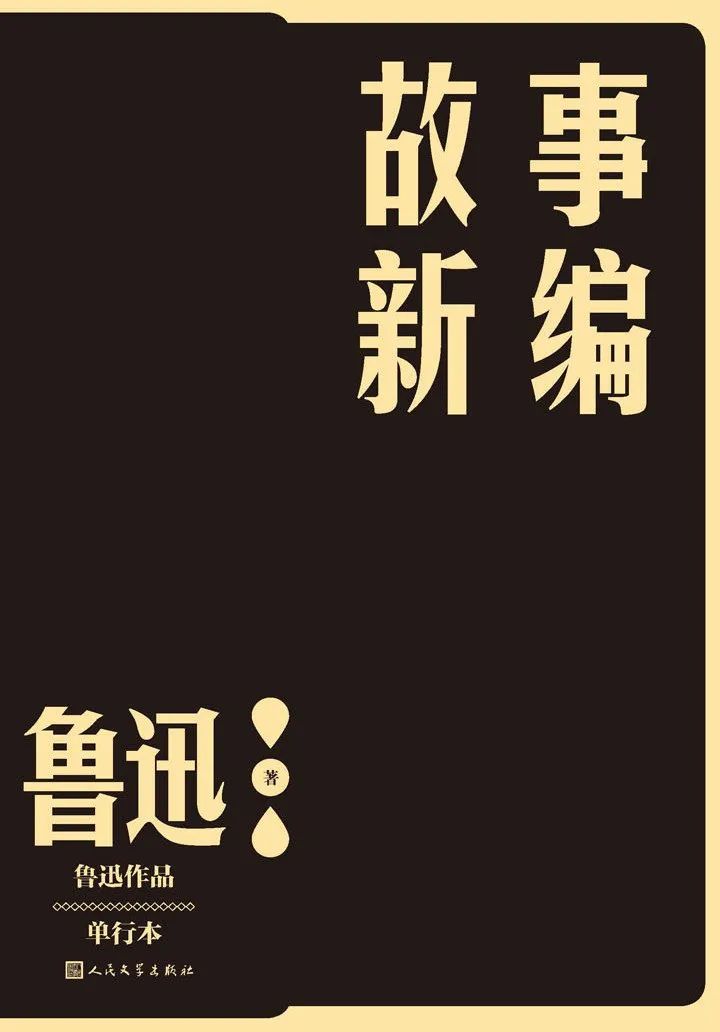
“有根有据”:左右逢缘
如果说从生活里取材叫“有根”,从书本里取材,就可以叫“有据”。
对一个作家来说,选择“有根”的素材,也即直接从生活里开掘素材当然是最重要的。鲁迅虽然写了《故事新编》,可他之前的小说创作,却是很重视这种“有根”的素材的,“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者听过的缘由,但决不会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者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见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
巴金《家》的人物也是如此,当然并不是说和生活一模一样,巴金曾讲到其中的几位女性的人物的由来及变化:“有些读者关心小说中的几个女主人公:瑞珏、梅、鸣凤、琴,希望多知道一点关于她们的事情。她们四个人代表着四种不同的性格,也有两种不同的结局。瑞珏的性格跟我嫂嫂的不同,虽然我祖父死后我嫂嫂被逼着搬到城外茅舍里去生产,可是她并未像瑞珏那样悲惨地死在那里。我也有过一个像梅那样年纪的表姐,她当初跟我大哥感情好。她常常到我们家来玩,我们这一辈人不论男女都喜欢她。我们都盼望她能够成为我们的嫂嫂,后来听说姑母不愿意‘亲上加亲’(她自己已经受够亲上加亲的痛苦了,我的三婶是我姑母夫家的小姐),因此这一对有情人不能成为眷属。四五年后我的表姐做了富家的填房少奶奶。以后的十几年内她生了一大群儿女,一九四二年我在成都重见她的时候,她已经成了一个爱钱如命的可笑的胖女人。我们家里有过一个叫做翠凤的丫头,关于她我什么记忆也没有了,我只记得一件事情:我们有一个远房的亲戚托人来说话,要讨她做姨太太,她的叔父征求她本人的意见,她坚决地拒绝。虽然她并没有爱上哪一位少爷,她倒宁愿后来嫁一个贫家丈夫。她的性格跟鸣凤的不同,而且她是一个‘寄饭’的丫头。所谓‘奇饭’,就是用劳动换来她的饮食和居住。她仍然有权做自己的主人。她的叔父是我们家的老听差。他并不虐待她。所以她比鸣凤幸运,用不着在湖水里去找归宿。”
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亭林文集》中《与人书十》讲,做学问写书有两种方式,一是“采铜于山”,二是“买旧钱铸新钱”。“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从生活中挖掘素材就是采铜于山,采用别人的故事就是所谓的买旧钱铸新钱。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但毕竟逊色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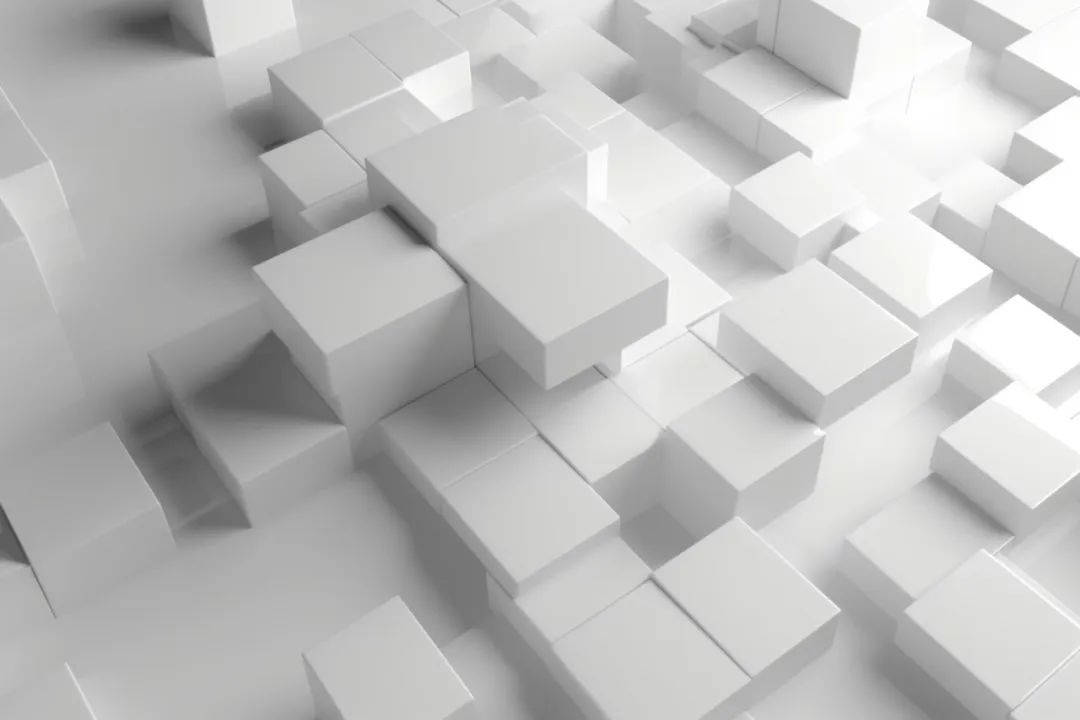
不过,对于素材的选择,不必勉强,也不必攀比,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性格、趣味和写作的兴奋点,所以在选择素材的时候也各有不同,有时即使是同一个素材,不同的作家也会处理得面目全非。
当然,小说的素材也不是决定性的,因为一个素材能否成为小说,除了它本身的小说性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怎么写”的问题存在。博尔赫斯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只能写我能写的东西,而不是想写的东西。这个能写,就是他以自己比较擅长的方式处理素材的能力,有些素材虽然很好,自己也很想写,可是却不一定能写出来。
所以,一个作家对素材的选择,其实有意无意也受到自己的文学经验和写作能力的影响,就像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也没有那么简单,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也对他有启发,李尔王与他的两个忘恩负义的女儿的关系,与高老头和他的两个女儿之间的关系如出一辙。也许,正是李尔王的两个女儿之间的不和,才让巴尔扎克从现实的素材中看到了其所蕴含的文学的意义,写出了高老头的两个女儿之间那种让人感到既可恨又可怜的关系。
新媒体编辑:何晶
配图:摄图网

原标题:《来自张生的小说课:从《人间喜剧》谈到《故事新编》,小说的素材必须有根有据 | 新批评》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