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一位40岁女性,如何确定自己想当丁克?

采访、撰文 | 芝士咸鱼 翻译 | 阚梓文
十点人物志原创
丁克,音译自英文词汇“DINK”(Double Incomes No Kids),原本指“没有孩子的双收入家庭”。社会学家李银河认为,对丁克更贴切的解释是“自愿不育的人”。
即使到了今天,在传统的东亚社会,丁克们依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选择不生育的人会被家庭和社会视为“自私、只顾当下、不考虑未来”。
丁克主义者中,女性的压力更大,甚至会被怀疑身体或心理罹患某种疾病。
比起周围人的异样目光,丁克女性受到的最大阻碍,是内心的不断摇摆。大多数女性很难下定百分之百的决心,此生绝对不想生孩子。
那么,选择丁克的女性,都是如何确定自己不想要孩子的?

42岁的韩国作家崔至恩,就是一位已婚的丁克女性,她早已决定不生育,偶尔还是会为此感到不安,担心自己做了个“错误的决定”。
为了听一听做出同样决定的女性的声音,她用了半年多时间,采访17位不同职业、年龄、经历的丁克女性,并集结出版为书籍,引发很多东亚女性读者的共鸣。
今年9月,《成为母亲的自由》(原译名《我不想当妈妈》)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有中国读者评论,“为什么选择不生也会痛苦”“成为母亲或不成为母亲,都需要深思熟虑”。
“十点人物志”联系上作家崔至恩,聊了聊崔至恩及17位女性访谈者成为丁克的过程,以及她们是如何克服内心的摇摆,坚定地发出“我不想当妈妈”的声音。

崔至恩:韩国作家、记者,常年关注女性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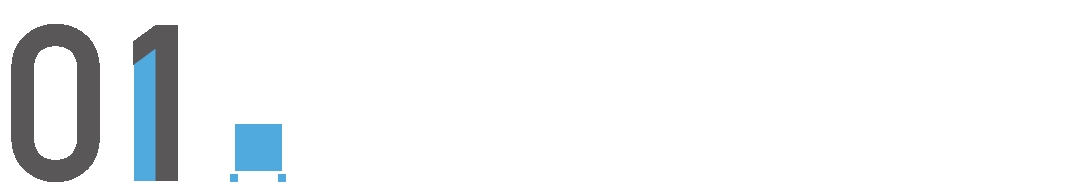
我不想当妈妈:
那些决定与摇摆的时刻
三年前,崔至恩39岁,结婚5年,虽然已与丈夫约定好不生孩子,但真正推动着她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还是一次和姐姐的聚会。
那是个下着微雨的夜晚,她来到姐姐的家里,姐姐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下班后比上班更忙碌,一边陪大孩子聊天,一边安抚哭闹的老二,还要时刻保持着稳定的情绪。
崔至恩心想:姐姐在公司从早忙到晚,下班又要做家务、陪孩子,实在太辛苦了。而她刚和外甥们相处一个小时,已经累得筋疲力尽。

《82年的金智英》,探讨生育和性别不平等的作品。
这时姐姐朝她走来说了句:“如果你也生个孩子就好了。”
因为这句话,崔至恩失眠了一整晚。她一边为不用每天照顾孩子而松口气,一边感到焦虑,“生育是否隐藏着某种幸福密码,所以姐姐会劝我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孩子?”
“结婚前,我曾模糊地想过总有一天会有孩子。”崔至恩说,但直到接近40岁,她依然没有产生生育的念头。她偶尔也会感到不安和孤独,这让她担心,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
为了打消心中的疑虑,她看了很多有关丁克话题的书籍,也去见同样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女性,在交谈的过程中,终于确定自己的内心:我现在很幸福,不需要改变现有的生活。
在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育儿成本高的韩国,很多都市女性和崔至恩的想法不谋而合。
据韩国统计厅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韩国登记结婚不到五年的新婚夫妇共81.5357万对,其中丁克族占了23.4006万对,占比接近30%。这意味着,近三分之一的夫妇选择不要孩子,丁克族成为韩国社会不容忽视的庞大群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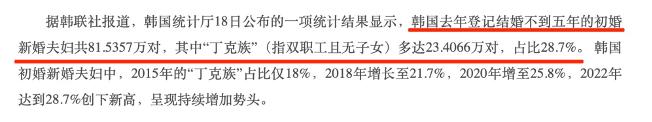
图源:光明网
另一项研究表明,进入21世纪后,“丁克潮”正在全球普及。不同地域、文化、种族的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丁克:西方人不要孩子多数为了“追求自由”,日本人在父权制文化影响下,女性的地位和话语权较低,又背负过高的母职期待,“成为母亲”变得越来越有压力;韩国人迫于育儿成本、职场与家庭中的性别不平等不愿生育。
亲密关系的不稳定性、城市的不断扩张与房价的攀升、通勤的时间成本增大,也成为影响都市年轻人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上班族持续着早出晚归的工作模式,失业风险不断增加,让年轻人“趁年轻多赚钱”“一人吃饱全家不愁”的想法,压倒了结婚生育等人生目标。
崔至恩在和17位丁克女性的交流中,有人因为育儿成本被迫选择丁克;有人并非刻意丁克,而是将全部精力放在了工作上;还有人天生不喜欢孩子,担心生育让自己失去娱乐、社交和休息的空间。

即使是同样选择丁克,女性也比男性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崔至恩提到,社会对丁克女性的评价以“自私”为主,对丁克男性的评价则是“为了迁就固执女人的善良男人”。或许因为这点,不少女性决定丁克后,都在摇摆中度过。
结婚十五年的度允,婚前和丈夫默契地就丁克一事达成共识,但她很长一段时间仍为是否生育感到困扰,“真的没关系吗?如果我永远没有孩子会怎么样?”
结婚六年的柳林,从小循规蹈矩地学习、工作、结婚,人生从未偏离过轨道。同时,她的内心十分渴望自由与独立。心里出现两种声音:一种让她“遵从自己的心”,另一种则劝她“尽管那是个未知的世界,但成年人就要勇于尝试”。

图源:《东京女子图鉴》剧照
反复动摇是不可避免的。在《最好的决定》一书中,67岁的心理咨询师兼作家珍妮·赛佛还原了自己的丁克历程,她在过去的几十年经历了剧烈的内心斗争,逐渐不再摇摆。她认为丁克女性需要付出持续努力,才能维持“没有孩子的人生”。
崔至恩对度允和柳林的摇摆感同身受,她也曾多次为此动摇过。
但在她看来,“比起下定百分百决心的故事,这些与动摇有关的故事更为关键。”
“假如能够自始至终坚定地选择生或不生孩子,那是十分值得庆幸的事情。但即便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女性,也要有足够的时间,去集中审视和思考内心的焦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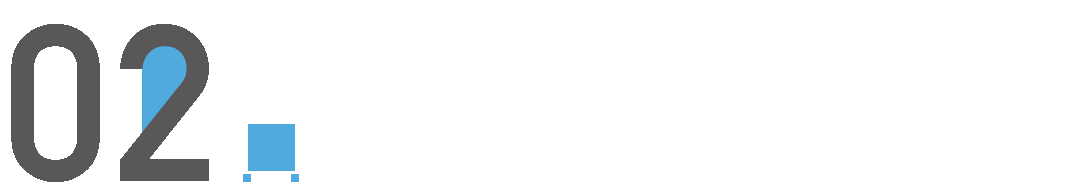
你适合丁克吗?
丁克了,然后呢?
如何判断自己是否适合丁克,崔至恩给出建议:花足够的时间,去思考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想要怎样的生活,适不适合养育孩子?
重要的是,要根据自己的意愿做决定。
但如果此刻你的身边有关系稳定的长期伴侣,要不要孩子,也需要两个人共同商议。
部分丁克女性会在婚前告知恋爱的对象:“如果跟我结婚,就要做好不生孩子的准备。”等双方就生育问题达成一致,再筹备结婚的诸多流程。
有些丁克夫妻,直到结婚后,才缓慢地看清内心,决定过无子女生活。
崔至恩在婚前没有和丈夫具体聊过是否生育的问题。丈夫不讨厌小孩,他曾在跆拳道馆做兼职,照顾几十个学龄前的孩子,偶尔也帮孩子们洗换衣物,多半能够照顾好孩子。
两人婚后花了约三年时间,基于双方性格和工作性质,才得出不育儿的共识。

不是所有丁克族都能和伴侣在生育问题上达成共识。但即使选择不生育会导致自己与本想共度一生的爱人分开,这些韩国女性也没有为此而担忧。
正在攻读经营学硕士的圣珠称,“我不害怕离婚,我害怕的是失去自我。”
另一位访谈者点明了丁克女性的底气来源:经济能力和精神独立。她认为,没有经济能力或是依附于丈夫生活的女性,才会担心两人因生育观念不合而分手。
向外界宣布自己将要过没有孩子的人生,与配偶达成共识是第一道关卡。
此外,婆家和娘家施加的压力也不可小觑。
东亚社会的长辈们普遍认为:婚姻不仅是两个人的结合,也是两个家庭的结合。几乎所有访谈者都被双方父母直接或间接地催生过,老一辈人无法理解,年轻人既然选择结婚,为何又不要孩子。
崔至恩不认可将婚姻和生育相互捆绑的观念,“结婚和生育是两个毫不相干的选择。即使不想要孩子,也可以结婚。反之亦然。”

图源:《淑女的品格》剧照
像大多数老人那样,崔至恩的公婆希望能有孙子或孙女,但她和丈夫经济独立,买房和结婚的过程中没跟两家老人要钱。“谁也不欠”的状态,让她和丈夫的丁克生活没有受到太多来自长辈的阻力。
崔至恩住在首尔,生活在不同城市,丁克女性感受到的氛围也大相径庭。
大城市的邻里关系疏远,缺乏人情味,好在邻里间有着清晰的边界。她周围有很多丁克族,还有一些不结婚的朋友,如果感受到压力和孤独,可以在社交圈找志趣相投的朋友聚会。
但对于住在小城市的丁克女性,压力成倍增长。33岁的善雨回到江原道老家后,她称,每当自己坐出租车,司机们都会顺口问她,“结婚了吗?有没有孩子”。如果坦诚地告知自己没有孩子,未来也不想要孩子。对方会非常惊讶,“不生孩子可不行……”
不过,比起外界的压力,丁克女性面临的最大难题其实是养老问题。

大多活跃在社交媒体的丁克族,处于二十四五岁到四十出头的年纪,她们在人际关系和日常生活没有附加困难。无子女生活的困难,通常要到老年才会显现。
“不生孩子谁来养老”,是她们最常听见的劝阻声音。
日本和韩国频繁出现“孤独死”新闻,没有收入、无人照顾的老人独自死在了房子里,直到尸体发臭才被发现。
但丁克们认为,养儿未必能防老。“养儿防老”的理由,听上去比丁克族“只顾享乐”更自私。“孤独死”的老人,也不全是无孩人士,有些老人的孩子成年后不愿赡养父母,同样无法指望孩子养老。
养老是复杂的社会问题,绝不仅仅是丁克族才会遇到的难题。
有些丁克女性会提前设定退休后的储蓄目标,也有人坚持每天锻炼,将身体调养得更轻盈健康,还有人提前为自己囤药、买保险,用来抵抗未知的老后风险。

NHK纪录片《7位单身女人:如果大家一起生活》
当年看非常新颖,现在抱团养老渐渐走入现实。
2019年,NHK纪录片《7位单身女人:如果大家一起生活》中,七位老人在同一座公寓楼买了不同的房间,组成养老姐妹团,彼此照顾。
这在当时属于一种陌生的养老模式,到了今天,现实中出现了越来越多“抱团养老”“以房养老”“旅居式养老”……甚至有人期待,人工智能发展日新月异,在不远的未来,看护型机器人会从概念走进现实。
多元化的养老模式,像是给丁克女性注入了安心剂,告诉她们:不必太过担忧,姑娘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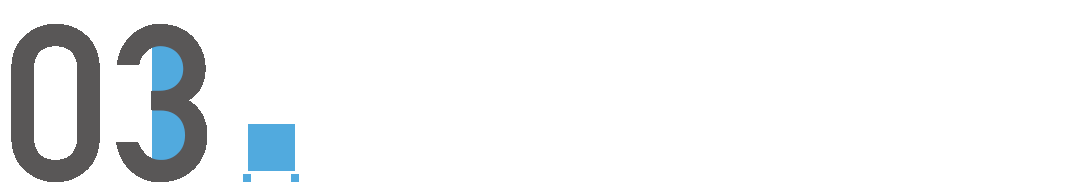
无孩时光如何度过:
没有毫无遗憾度过一生的人
在过去的八年婚姻中,崔至恩一直持续着无孩生活。她和丈夫是自由撰稿人,收入不高,不用坐班,只有两个人的生活,让他们的关系更亲密。
由于身边没有一个不断成长和变化的孩子,她对时间流逝的感知也变得有些迟钝。
相比有孩子的家庭,丁克女性通常会拥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
工作之余,崔至恩在去年开启了关于丁克的邮件问答服务,也进入研究生院,最近正在准备有关韩国丁克话题的论文。
参与访谈的其他丁克女性中,有人将闲暇的时间用来看书和写作,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作品;也有人将时间用来参与社交活动,尽可能多认识一些人,夯实职业发展的黄金期;还有人辞职去旅游,经济上或许有压力,精神生活却更富足。
对无孩时光的使用方式中,令崔至恩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36岁的女律师——素妍。
素妍为自己保留了日常开销的费用,其余的所有金钱和时间都用在了助学事业上,她组建了一个奖学金财团,资助发展中国家的女学生上学。

这样的投资很可能得不到回馈,却为素妍带来强烈的满足感。她将其视为一场人生实验:培养一批优秀女性,长大后参与社会福利体系、教育行业的建设与改进,从而帮助更多人。
在与这17位丁克女性的交谈中,崔至恩愈发意识到,人们以往对丁克女性“工作狂、自私、讨厌孩子”等刻板印象,是非常错误的偏见。
每位丁克女性都有着丰富的、截然不同的生活。
她也从中得到了安慰,“选择和我同样生活方式的人们,各自在某个地方坚强地活着”。
她将自己和这些丁克女性的对话集结成册,在韩国和日本引发了极高的关注度,并于今年9月在中国大陆出版,更名为《成为母亲的自由》,旨在缓解女性的生育压力。
本书的译者阚梓文和编辑程斌称,这本书讲述的不仅仅是韩国女性的故事,“近些年,中国女性对婚姻和生育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女性逐渐对生育这件事变得疏离,生育违背了自己的意愿,不生育又与传统观念相矛盾。他们看见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不断地在这种矛盾中挣扎。
《成为母亲的自由》书封 /
“当不当妈妈是一种选择自由,没有对错。”
作者崔至恩也提到:中国女性和韩国女性在婚姻、生育观念、家庭文化、性别角色规范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选择不生育的女性往往被视为“不正常且需要被纠正”的对象,容易在情感上感到孤立。
她想借这些韩国丁克女性的故事,告诉其他不生育的女性:我们的生活方式没有错误,只是有些不同而已。
采访的最后,笔者问了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如果丁克女性在育龄之后后悔了怎么办?”
崔至恩引用了一位60岁丁克女性的回答,“你问我是否后悔?谁不会后悔呢”,她接着说,“这世上本就没有毫无遗憾度过一生的人。与其担心未来会不会后悔,不如让当下的自己活得更充实,这样未来的后悔可能会少一些。”
“过了生育年龄后,如果我开始想要养育孩子,那个孩子不一定非要是遗传我的基因的后代,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需要爱和关怀的孩子。”
首图源于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
原标题:《一位40岁女性,如何确定自己想当丁克?》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