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她们在祈祷孩子安然无恙,我却在祈求我的孩子能够死去……
1999年4月20日,埃里克·哈里斯和迪伦·克莱伯德携带着枪支和炸药走进了科伦拜恩高中开始了一场有预谋的屠杀。
他们杀害了12名学生和1名教师,24人在炸弹和他们的疯狂扫射中受伤,平静的校园变成了血色地狱。
做完这些,两人殉道般饮弹自杀。

这场惨烈的校园枪击案震惊了美国,当时还是1999年,这个事件给美国社会平静的生活假象投下了一枚深水炸弹,数年来被无数的人争论、思考,到底是什么让原本成长中的他们变成了恶魔。
迪伦·克莱伯德的母亲苏珊·克莱伯德成为众矢之的,二十年来她以泪洗面,反思着过去他们生活中的一切细节。
身为父母,为了预防这场悲剧的发生,本来可以做些什么。
今天的文摘,就是选自她的回忆录:《谜一样的孩子》。我们将通过两段文字,了解这个母亲背后的泪水和沉思。
第一段来自母亲苏珊·克莱伯德自己:
迪伦·克莱伯德是我儿子。
我愿意牺牲我的生命去扭转那天所发生的一切,哪怕能换回一条生命。然而我知道,这样的交易是无法实现的。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都不可能丝毫弥补那场大屠杀所带来的重创。

Dylan Klebold,1998
那可怕的一天已经过去了16年,每一天我都在试图理解,一个有前途的男孩的生活是怎么演变成一场灾难的呢?况且一切都发生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我至今也理解不了。我追问家人、迪伦的朋友,追问专家,最重要的是叩问我自己。
我忽视了什么,怎么会错过?我一遍遍翻阅日记,像法医、专家、学者一样穷追不舍地剖析我们的家庭生活,连琐碎小事和交流也不放过,试图找出自己错过的线索。我本应该注意什么?本该有什么不同处理方式?
起初,我寻求答案的过程纯粹是个人使命的驱使。强烈的羞耻感、恐惧和悲伤让我不知所措,同样强烈的是我对这些答案的渴求。然后,还有许多人渴望解决的难题,我看到自己逐渐掌握的碎片能够为之提供些许线索。我希望我所获得的信息或许有所帮助,这个过程一步步引领着我最终将自己的故事公之于众。
回望来路,科伦拜恩事件之前的一切恍如隔世。那时,我们的家庭生活就像一个普普通通的美国郊区家庭。在十多年的探索中,透过废墟,我睁开了眼睛,不仅看到了迪伦曾经隐瞒过的事情,也看到了他一步步铺垫,直到最后悲剧的发生。同时我也意识到,这些见解所包含的意义,远远超出科伦拜恩事件本身的范畴。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能否阻止迪伦当天在大屠杀中的可怕行径。但是,我逐渐认识到当时可以用不同方式处理一些事。这些都是琐碎的小事。在枪击案发生之前,即使用最先进的变焦镜头聚焦我们的生活,我相信任何人都会觉得再平凡不过了,无异于全国各地无数的普通家庭。
汤姆和我是有爱心的、细心的、积极参与的父母,迪伦也是个热情有爱的孩子。我们不必为他忧虑和祈祷他改邪归正好好生活。我们称他为“阳光男孩”,不只是因为他金色的头发,也是因为一切对他来说,似乎都很自然和积极。身为他的母亲,我全心全意地爱着他,非常感恩。
在枪击案发生之前,我们的生活是正常的。这一点对人们来说,可能是最难理解的事情。对我来说,这也是最重要的。我们的家庭生活并非困难重重、不堪其扰。我们的小儿子也不让人头疼,更别提我们(或其他认识他的人)觉得他会想伤害自己或是他人。我希望很多事情都有所不同,但最紧要的是,我希望当时知道,孩子看上去似乎一切正常的表象之下,一切反常均有可能。

当谈到大脑健康问题时,许多孩子是软弱无助的,正如一百年前的儿童面对传染病。太多情况下,正如我们的案例,他们的脆弱和敏感被忽视了。一个孩子会被什么情景激怒,或是会影响他们的快乐感和潜力,这些情况都可能让人迷惑,令人心碎。如果我们对这些漏洞缺乏辨识能力,将会付出更多、更可怕的代价。这些代价将不仅仅是诸如科伦拜恩、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纽敦、查尔斯顿等校园悲剧背后的伤亡数字,更有无数悲剧在悄无声息地上演,缓慢地吞噬着我们的同事、朋友和亲人的家庭生活的日日夜夜。
仅仅有爱是不够的。对父母来说,也许没有什么比这更难接受的事实了,世上没有哪个父母对此比我体会更深。尽管我对迪伦有着无穷无尽的爱,却连他的命都没保住,还搭上了当天在科伦拜恩高中被杀害的13人,以及其他伤者。我错过了本该注意到表明迪伦心理健康状况恶化的迹象。如果我没有错过这些迹象,迪伦和那些受害者可能都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即使对我本人不利,我还是要如实讲述自己的故事,希望能对其他父母有益,帮助他们看到孩子表面之下的反常迹象,以便在需要的时候,能够为孩子们提供救助。
了解了我们的故事之后,许多朋友和同事改变了对待和养育孩子的方式。在某些案例中,他们的干预已经取得了显著的结果:一位同事注意到她13岁的女儿似乎有点萎靡不振,她想起迪伦的故事,于是在不断追问之下,她的女儿崩溃了,承认有一次从家里溜出去跟朋友玩的时候,被陌生人强奸了。这个姑娘极度沮丧、羞愧和害怕,正在认真考虑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的同事能够帮助到女儿,是因为她注意到了孩子微妙的变化,从而不断地追问。由于读了我们的故事,同事的女儿的事得以有了平安的结局,我感到深深的欣慰。我相信让更多的人了解迪伦的故事,能够使更多的人和家庭受益。

对我来说,挺身而出并不容易,但如果我从科伦拜恩事件这个可怕的火炉里得到了启示和见解,那么我在道义上有责任去分享。尽管公开发声会让人产生恐惧,但这是我该做的事情。我的清单上有诸多条目,当初我若是知道的话,会采取不同的做法。这些都是我的失败之处。我所渐渐了解到的,验证了一个事实——为了防止类似的事件,更为了防止任何孩子可能隐藏内心的痛苦,需要有更大范围的行动和广阔的视野来看待情势。
第二段来自心理学家安德鲁·所罗门:
未成年人犯罪是父母没做好教育的缘故,社会对此见解紧抓不放,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严重的虐待和忽视确实会激发性格脆弱的人做出某些变态的行为,这是毋庸置疑的。养育不当也会将孩子推向吸毒、结交黑帮、家暴和盗窃等深渊。由于年幼时受到的摧残,他们会对他人有强烈的依赖性,并且他们会不由自主地强迫重复着成长过程中经历的无助和愤怒。有些父母确实毁了孩子,但并不是所有惹麻烦的孩子的父母都是无能的。特别是极端的、毫无理智的犯罪行为往往与父母的行为并无关联。这些行为可以归因于缺乏逻辑原理,其中的深奥远远不止曾经遭受过心灵创伤这么简单。
第二,更有说服力的是,我们“想要”相信是父母“制造”了这些未成年罪犯。如果这个假设成立,我们就能安慰自己,在自家的屋檐下,我们遵纪守法,这样的灾祸就不会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我现在意识到,这种想法纯属错觉。

2005年2月19日,我第一次与汤姆和苏珊·克莱伯德见面,我想当然地认为自己能迅速发现他们是哪里做错了。彼时,我正在写一本名为《那些与众不同的孩子》(Far from the Tree)的书,是关于父母与难对付的孩子的。于是在我想象中,这对父母绝对是个典型,在抚育孩子的过程中一定错误连连,罪责难逃。我也真诚地认为他们的经历能够阐明其他数不清的显而易见的错误。我本不想对克莱伯德夫妇有好感,因为如果我对他们心生好感,那么相应地,就得承认发生的悲剧不是他们的过错。如果不是他们的错,那么我们这些父母,谁也安心不了。出乎意料,我与他们非常投缘,以至于分别时我脑海里有个念头——科伦拜恩枪击案背后的心理因素是有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家庭里的。甚至,类似的悲剧好比海啸一般无法预见或察觉。无论如何做到有备无患,都是徒劳。

根据苏珊·克莱伯德的叙述,科伦拜恩惨案发生之前,她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住在郊区的母亲。我们那时素不相识。惨案发生后,她最终坚强起来,从绝望中汲取了智慧。在这样的状况下还能坚定不移地去爱,完全是勇气的表现。我很荣幸能够了解到她的慷慨和热情;她充满活力地爱别人,能对别人施以真挚的关注。这一切,反衬得那起惨案愈加让人伤痛和迷惑。起初我猜想,克莱伯德夫妇肯定是对他们的孩子不闻不问。结果我意识到,孩子处心积虑地策划惨案,远远不是缺乏父母的爱能够诠释的。这本书的每一页都透露出苏珊对儿子深切的爱,同时也证明了这起惨案的复杂性。她认为好人也会做坏事,我们每个人在道德上都会有迷失;并且即使做了坏事,也不能全盘否定他们的其他行为和动机。这本书的终极信息让人心生恐惧:你可能根本不了解你的孩子;更糟糕的是,你的孩子可能对你隐藏了自己。你所害怕的“陌生人”可能会是你的儿女。
两种类型的犯罪行为最让我们痛恨:孩子是受害者,以及孩子是始作俑者。第一种情况下,我们为无辜的孩子哀伤;第二种情况令我们不能理解,因为孩子本来应该是纯真无邪的。校园枪击案是最让人惊心动魄的,因为这种事件同时涉及了以上两类。在校园枪击案中,科伦拜恩事件又一直是被作为典型来看待的,是步其后尘的案件的终极典范。埃里克·哈里斯和迪伦·克莱伯德思想里的极度自我主义与施虐的欲望混杂,枪杀目标的随意性、前期的精心筹备,都使他们在大批年轻的叛逆者心中被当作英雄来看待。大部分人都坚定地认为他们心理不正常,一些宗教群体还认为是典型的撒旦主义在作祟。人们不愿悲剧重演,想保护自己的孩子,于是一遍遍地分析这两个男孩子的动机和目的。最有勇气的父母也在考量,如何才能确保自己的孩子不会犯下这样大的罪行。古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科伦拜恩事件是突如其来的最为严重的一场浩劫,并且事前在光天化日之下,隐藏得密不透风。


从两名枪手的表现分析,埃里克是一个具有杀人倾向的精神病患者,迪伦则是一个具有自杀倾向的抑郁症患者,他们的不同之处都是彼此走向极端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埃里克的领导能力,迪伦的抑郁情绪不会上升为谋杀念头。与此同时,如果不是拉着迪伦一起下水的刺激推动着埃里克,或许他内心的动机也会慢慢消亡。埃里克的凶神恶煞让人震惊,同样让人震惊的是迪伦对其的默许。迪伦曾经写道:“想到自杀,能给我带来希望,从而到达一个属于我的地方,不再与自我、与世界、与整个宇宙争战;我的意念和身体会彻底得到平静——我——我的灵魂,”他是这样描绘自己当时状态的,“在没完没了的现实里、无休无止的方向中,经受着永恒的痛苦。”他文字中最常出现的词是“爱”。埃里克却写道:“你凭什么说我们是同一类生物,我们完完全全不同……你不是人,是机器人;假如你以前得罪过我,让我看见你的话,你就活不成了。”他的日记里写了想象中未来的大学生活,他会引诱女孩子到他房间强奸她们。又写道:“我想像拉易拉罐一样撕裂人的喉咙。我想像一只狼一样揪住一个小新生,让他们瞧瞧到底谁是上帝。”

精神疾病的维权者指出,大多数罪行不是出自精神病患者之手,大多数精神病患者也不会犯罪。那么,如果认为科伦拜恩惨案不是精神病导致的祸患,这样的说法对于现实有什么意义?人们对犯罪行为之所以抗拒,是因为人们要么知道自己会被抓住,要么已经学会了遵守道德规范。大多数人都见到过自己想偷的东西;大多数人脑子里也瞬间闪过把自己身边最亲密的人给杀了的念头。然而,人一般不会去杀害学校里几乎不认识的孩子,同时将整个地方当作质押,并不是因为畏惧惩罚或是谨守着所接受的道德准则,而是因为正常的思维里一般不会有这个念头。尽管患有抑郁症,但是迪伦没有精神分裂症、创伤后应激障碍、双相障碍,抑或其他符合精神病诊断范畴的状况。他脑海中存有扭曲的想法,但是这不能降低他所作所为的狠毒程度。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没有试图为迪伦的行为追究缘由。苏珊拒绝指责学生之间的欺凌,拒绝指责学校,或者归因于儿子的生理化学测验结果。这一切都反映出,她是下定决心要去接受任何无法解释的事情。她也未曾尝试去诠释邪恶和疾病之间那永远混淆不清的界限。
我们第一次会面,苏珊就跟我说了她在1999年4月20日那天听到科伦拜恩高中惨案发生的那一刻。“利特尔顿的母亲们都在祈祷自己的孩子安然无恙,我却在祈求我的孩子能够死掉,不要再伤害另一个人。”她说,“我想到,如果这一切是真的,他还能从现场存活,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最后被判死刑。我没办法忍受两次失去儿子,我做了此生最艰难的祷告——祈求他自杀。因为那样起码我知道,他是想死的。假如他是被警察打死,那么我就要面对更多的疑问。也许我是对的,但是我又长时间地为这个祈祷而悔恨:我祈愿儿子自杀——他真的去做了。”
与他们会面的周末即将结束,我问汤姆和苏珊,如果迪伦此刻在屋里与我们坐在一起,他们有什么话想对他说。汤姆说:“我要问他,他到底在想什么,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苏珊盯着地板想了一下,低声说:“我要请他原谅我,原谅我作为母亲,不知道他头脑里出了什么问题,原谅我不能帮助他,原谅我不是他能吐露心声的那个人。”5年以后,我再次提起这个对话,她说:“事情刚发生时,我都宁愿从来没生过孩子、从来没有结过婚。如果早在俄亥俄大学,汤姆和我从未相遇,迪伦就不会存在,这件恐怖的事情也不会发生。但是渐渐地,我感到很高兴做了母亲,生了两个孩子。因为,对他们的爱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喜乐,即使代价是如此深刻的痛。我这么说,是指我自己的痛,不是旁人的。我也接受自己的这份痛,人生充满痛苦,这是我的一份。我知道,对旁人来说,最好迪伦没有存在,可对我而言,没有过迪伦这个儿子,我并不会更好。”

一般来说,我们失去一个人是一次性的,但是苏珊的失去是一波一波的:先是儿子自杀身亡,然后是儿子在她心目中的形象,接着她又放弃了自己对儿子黑暗的一面有所认知的想法。接下来,除去“凶手的母亲”,她失去了本身的其他身份。最后,她放弃了基本信念:生活是有逻辑可循的,假若你做了一些正确的事,是可以避免某些不祥后果的。确实,拿哀伤与哀伤相比,没有什么益处;如果说苏珊的哀伤是利特尔顿最惨的哀伤,也不合适。然而,她困扰在两种痛苦之间缠结不清,无法解开:她发现自己从未了解过儿子的那种痛苦与看到儿子给别人带来的绝望和痛苦。她始终在几种悲伤中挣扎——儿子死去的悲伤,对其他遇害孩子的悲伤,以及未曾养育一个快乐的、对社会有益的孩子的悲伤。
奥维德曾表达过一个著名的教诲:“拥抱这样的痛苦吧,你将从中有所学习。”然而,对于这样的痛苦,我们似乎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也没有不欢迎的选项。痛苦来临时,你可以表示不满,但是你无法叫它离开。苏珊·克莱伯德未把自己当作一个受害者抱怨过;可她的陈述回应着《圣经》里约伯的哭诉:“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也不受祸吗?”“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苏珊叙述了她如同约伯一样,坠入了深不可测的地狱。她在书中承认,即便站出来发声,哀痛也不得消减。这本书是一份记录,叙述她接受现实的过程,与心灵的争战,使得她能安放自己的痛苦,寄予一种希望:再也不要有人遭受她所遭受的痛苦、她儿子的痛苦以及受害者的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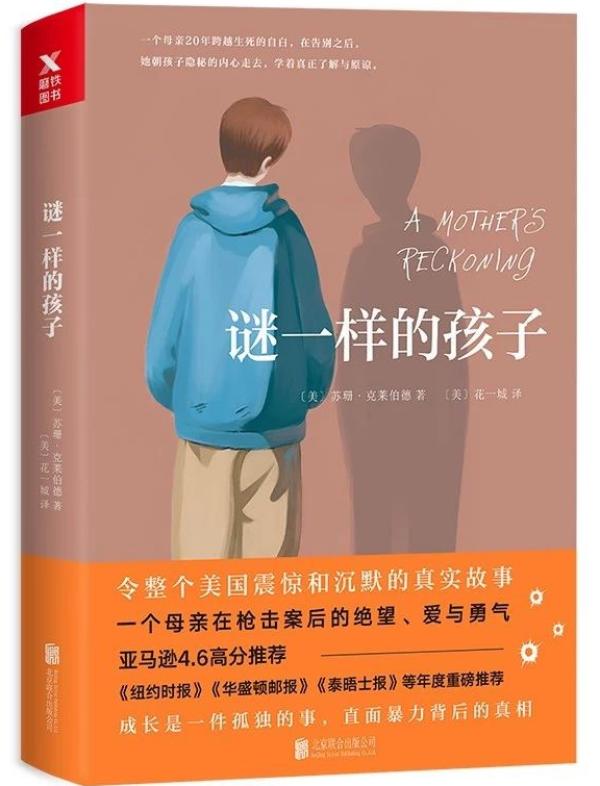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6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