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一个有阿尔茨海默病人的家庭,会经历些什么?|翻翻书·送书
 “我清晰地记得他哪一天开始不再认识自己的家,又是在哪一天不再认识我们,他的妻子,他的女儿和儿子,我同样记得,他突然不会走路的那一天来临的时刻。”
“我清晰地记得他哪一天开始不再认识自己的家,又是在哪一天不再认识我们,他的妻子,他的女儿和儿子,我同样记得,他突然不会走路的那一天来临的时刻。”2015年,《远去的人》初版问世,记录了作者薛舒的父亲自2012年患阿尔茨海默病后失忆失智的全过程,作者的父亲用了三年时间,从失忆,发展到失智、失能,最后,在2015年的春天,因失能被送去了一所小镇医院。
辗转于卫生所、安宁医院的父亲在医院躺了整整五年,直至2020年,作者的父亲在病房去世。这五年间,作者没有再去写他。当时正处于新冠疫情最为严重时,没有告别仪式,没有众多亲友为他送行,作为女儿的作者未能为父亲写悼词。这种遗憾,让作者决定“写一写生活在终点站里的人,那些陪伴着他度过五年时光的护工和病友,写一写他,这个还在我心里缓慢地活着的人”。
2023年《生活在临终医院》(原文《太阳透过玻璃》刊于《收获》)问世,记录了父亲从失智到失能直至生命终结,一次漫长的告别。医院里二十六张病床,除了阿尔茨海默病人,有的因为中风、脑溢血而导致瘫痪,还有少数癌症晚期病人……他们都在这里等待着生命最后的归期。在这部作品里,薛舒把目光从父亲个体、家庭内部转移到更广大的社会图景,生动地讲述了鲜少被留意的医院护工的生活,“她们壮阔的嗓门,她们劳作的身影,她们热火朝天地生活在这里,她们使一家‘临终医院’常年充满莫名其妙的欢愉气息……”
今天,第二十三期「翻翻书•写写字」的征集就为大家带来这部《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这本书送给年轻的、健康的,积极抑或颓废地生活着的人,你能在这里看见未来,有一天,当疾病抑或垂老迫近时,你也可以坦然地追念曾经青春的自己。
◎ 薛舒“生命两部曲”之二,记录从父亲住进临终医院直至生命终结的最后光阴;
◎ 聚焦生活在临终医院的老人们和他们的家庭,看见普通家庭的真实困境和中国社会几代人的悲欣过往;
◎ 记录常常被忽略的“照护者”的生活与日常:生活在最迫近“死亡”的地方,陪伴临终医院的老年病人走完最后一程;
◎ 透过临终医院反思、追问:今天的我们,该如何面对衰老、疾病与死亡?
▼第二十三期书目:《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

《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
薛舒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单读 2024年1月出品
▼书籍简介
《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是薛舒在2020年创作的长篇非虚构作品,作为她第一部关于父亲身患阿尔茨海默病的作品的续作,讲述了父亲完全失去自理能力、住进临终病房后的五年时光,这五年里,父亲从精神上的告别走到了生命的终结。在这部作品里,作者将目光从父亲个体、家庭内部转移到更广大的社会图景,生动地讲述了鲜少被留意的医院护工的生活,描述了病房中其他病人和家庭相似但也不同的困境……生的活力与死的阴霾穿插,爱的治愈力与疾病的破坏力交织,在一个个看似沉重的议题背后,揭开有关生命的那抹醇厚、质朴的底色。
▼作者简介
薛舒,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发表于《收获》《人民文学》《十月》等刊物。曾获《人民文学》奖,《上海文学》奖,《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中国作家》奖,《长江文艺》双年奖等,多次入选《收获》文学排行榜、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年度排行榜、城市文学排行榜等。出版长篇小说《残镇》、小说集《成人记》、长篇非虚构《远去的人》等十余部。部分小说被译为英语、法语、德语、波兰语、葡萄牙语发表或出版。
▼读者书评
不同于第一本书《当父亲把我忘记》的家庭内部的视角,第二本《生活在临终医院》则是将视角拓展到乡村诊所(临终医院)外,通过不停变换的病床、对于临终医院病患及其家属的点点滴滴,折射出当下中国社会老龄化的真实现状,给予人以深思。
——浮生半日闲(豆瓣读者)
作为《父亲把我忘记:隐秘的告别》的续篇,《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同样是一部感人至深的作品。阅读时同样会心悸。不仅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脆弱和短暂,更让我们重视爱的力量和生命的价值。
——威尼斯男人(豆瓣读者)
一个有阿尔茨海默病人的家庭,会经历些什么?透过让人揪心又泪目的文字,作者让我们看到了更多普通家庭所面对的困境,它们是那么相似,可又是那么不同。
——小七(豆瓣读者)
▼内文试读
一、 他是谁
他躺在离窗户最近的床上,太阳透过玻璃照进来落在他身上,斑驳的光影几乎晃着我的眼睛。我伸出手,轻轻抚了抚他左脸颊下端的一颗黑痣:爸爸,认识我吗? 我是囡嗯(女儿)……他没有回答我,他瞪着眼睛看向窗外,眼球里没有反照出任何景物。窗外没有景物,窗外只是一片茫白的天空。
他在老年病房里住了整整五年,他失智、失能、丑随、菱靡……他以一具不断散发出败坏气息的躯体的形式存在,像一头受伤的老动物,浑身破碎,奄奄一息。五年中,他的身躯从未离开过床,他全身的肌肤与一张一米宽、两米长的床紧密接触,白色的床单,以及床单上加铺的一层尿垫,成为他的第二或第三层皮肤,属于他自己的原生皮肤不断起屑、糜烂、生出脓疮、结痴鱼鳞般脱落,然后,竭尽所能地重新生长,机体愈新的能力远远赶不上溃败的速度。
他一无所能,不认识任何人,不会说话,更没有能力主宰自己,哪怕换一个躺的姿势。唯一能脱离床的引力的,是他的双腿。在无法动弹的日子里,他拱起膝盖把被子撑出一个小帐篷。这是他所剩无几的自由,除此以外,便是双手,但是,手的功能只剩下破坏。为了防止他抓自己的尿袋,扯碎绑在身上的尿裤,捞自己的粪便抠坏自己的脸,护工把他的双手用看护带分别拴在床栏两侧。看护带留出十五厘米左右长度,于是,他的手就拥有了半径十五厘米的自由,他可以挥舞拳头,可以张开手掌拍打病床,围栏被拍得“呕呕”响……
最伶俐活泼的是他的嘴,咿呀呢喃,或者嘶吼啸叫,不知所云,却也不知疲倦。他嗓门很大,声线却并不光滑,像一把带倒刺的锥子,所到之处,把空气刮出毛毛刺刺的碎片。没有人对他空洞的嘶吼和啸叫提出异议,在这里,他不是唯一的噪音制造者。他的病友们,左邻右舍,各自发出属于他们的生命独奏,小声的哼哼、永不停歇的鼾声、痰气深重的呼吸、突如其来的呐喊,以及,不知缘由的号哭…… 这些声音,汇合成一支交响乐,终日持续演奏着。问题是,缺少一个指挥,没有人能让他们有序地开始,以及有序地停下。我总是想象,他是这支乐队里的小号手,不时吹出几个音节,高亢、啼亮,只是演奏水平不够高超,乐器还用旧了,常常破音,或者漏气,不过这也并不能打击到他的自信,在“乐队”里,他是最乐此不疲的小号手。
进食是他最后的智商,喂给他食物,他会张嘴,努动几下腮帮子,一股脑儿地咽下去,一天比一天懒得咀嚼。那些食物,曾经是一个由马蹄碎与肉糜混合而成的肉丸子、一块浓油赤酱的大排骨、一条炸得焦香酥脆的鸡腿,或者青翠碧绿的小青菜,它们有着诱人的香味葱姜、油、鼓汁,它们以色香味俱全的美食的样子被送进病房,但是,当它们即将进入他的嘴巴时,一定被打磨成了一团浆糊,介于白、绿、黄、棕、黑之间,色泽的复杂与不可言说,令人产生来历不明的怀疑。可是无论如何,他需要吃,于是喂给他,用小汤勺,或者大针简。浆糊注入他的口腔,就像授进一口昏黑的无底洞,源源不断地进去,一天以后,没有悬念地变成排泄物。
他因此而维持着生命,让他活着是我们的目标。可是,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
意义,是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活着要有意义,这是我们从小被教育的人生追求,譬如,把爱奉献给他人,把智力与体力贡献给社会与人类,哪怕是一名最普通的劳动者,渺小,却如同长城上的一块无名砖,没有任何人记得,却以螺丝钉的功能存在于一项伟大的工程,于是,它渺小的生命就变得有意义了。
然而,他,对于这世上的任何一切,都不再具备哪怕一丝意义。他不创造价值,他不劳动,他还霸占了至少两个全劳动力,他每天消耗的资源可以养活至少三个贫困地区的孩童,他接纳以及获得别人对他的照顾与奉献,但他不会反哺,不会回馈,不会感恩,因为,他完全忘了自己是谁。过往的一切,在他脑中消隐得极其干净。他像一条鱼,七秒钟的记忆令他的大脑像一块光滑的玻璃,细沙飘落在玻璃上,微风拂过,沙子飞扬而起,玻璃洁净如初。
然而对于我们,似乎,他依然具备活着的意义,他以他的活着,让我们感到自已正被需要,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我母亲共同生活了五十年的爱人,他与我们有过许许多多共同的时光,我们挽留他,一如挽留属于自己的时光。只是,他好像早已顾不上我们,他要追上他的时光比赛一般往前飞奔,那些时光不会回来了,他便也把我们丢下,不再回头。而我们,就这么守着他,守着这个失去了所有记忆的人,捍卫着我们自己的记忆。
可是,我们的记忆并不能改变他,安抚他,让他变得健康,我们的记忆只是我们的,不是他的。所以,他这样没有记忆地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 不明白失去与获得,不爱、不恨、不忧伤、不快乐……可是,谁知道呢?也许他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懂得,只不过,他无法让我们知道,他是明白的,他是懂得的。
这就是我的父亲,从七十岁开始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某一天,他失控的大脑自行决定退休,然后,用了三年时间,大脑从指挥官的位置一点点卸任,最后成为一件再也无法修复的“报废”设备。
我清晰地记得他哪一天开始不再认识自己的家,又是在哪一天不再认识我们,他的妻子,他的女儿和儿子,我同样记得,他突然不会走路的那一天来临的时刻。
那天下午,他如同以往任何一天一样在客厅与卧室之间蹒跚移步,没有目标的行动很快使他失去耐心,他忽然让自己席地坐下,沉默着,再不肯起来。他深陷在自己的世界中,垂着眼皮,若有所思,他听不见我们劝他起来的声音,自始至终不屑于看我们一眼。我们动用了两个人,试图让他站起来,他被我们拉着手,臀部却紧紧贴着地板,没有一丝要借力的主动性。我们只能分别夹住他的两条手臂,托住他腋下,用尽全力把他提起来。他被我们牵扯着,终于发出一些如同劳动号子一般的声音,“哎哟噪、哎哟嚓”,脚上却没有使出一丝力气。他像一个狡猾的孩子,用“哎哟唾”骗取我们的信心。我们哄他,承诺于他:起来,起来吃蛋糕……他不要蛋糕,他就是不要起来,狡猾的孩子变成了耍赖的孩子,他懒得和我们周旋,就那么坐在地板上,无声,目光空洞。最后,我们动用了四个人,把他抬到了床上。
我知道,他不是不愿意站起来,而是,他的大脑再也无法对他的肌体和器官发出有效的指令,他以不配合的姿态宣布,从此以后,他失智与失能的积累达到了质的飞跃。
在这之前一年,我们就开始考察周边的一些养老院和护理院,谁都知道,未来,他一定需要住进那样的地方。只不过那时候,他还能走路,还能自已拿着筷子扒饭吃,尿急时还会提着裤子兜兜转找马桶,还能和我们交谈几句,像两三岁的孩子,鹦鹉学舌,答非所问。他被我们关在家里,无所事事却不忘寻找出路,院门锁住了,他出不去,便在三个房间与一个客厅之间兜圈子。偶尔,进入洗手间,却再也找不到出来的门,四面都是墙壁,他就面对着其中一堵墙,一站就是半天,无声无息,像一个因为老去而思过的浪子。直到母亲找到他,把他拉出卫生间。他不再如发病最初两年那般躁狂、恐惧,他变得越来越温顺,我猜测,他脑库中的记忆已然消失殆尽再没有令他留恋、追悔、惧怕,以及唯恐失去而挣扎夺取的东西,他正日益变成一具空壳,有血有肉的空壳。
那个周末,我的先生开着车,我们载着父亲和母亲出了门。他问:去哪里?
我说:爸爸,带你出去玩,好不好?
他举起双手,张开巴掌拍起来:好噢好噢!去玩了!
哈哈……
▼如何参加共读?
希望你是
1. 关注大背景下的小人物,对身处的时代有自己的理解,具有独立判断和思考的能力
2. 有表达的欲望,能用文字表达内心的感受
3. 尊重彼此的时间,遵守我们的约定
▼你需要做
1. 前往“湃客工坊”微信公众号,在文章评论区告诉我们为什么想读《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包括但不限于你对相关议题的了解及兴趣。截止时间为1月14日24时。
2. 1月15日我们会选出3名读者,请留意公众号文章的回复,并及时添加“湃客小助手”微信,发送地址和联系方式,我们会第一时间邮寄图书。
3. 在10天内(从收到书当日起计)把书读完,发回800-1000字的评论。你的文字,将有机会在澎湃新闻客户端及“湃客工坊”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如果你成为当期的图书推荐人,我们将邀请你加入“湃客读者”微信群,让你与来自各行各业的喜欢阅读、享受思考、愿意表达的读者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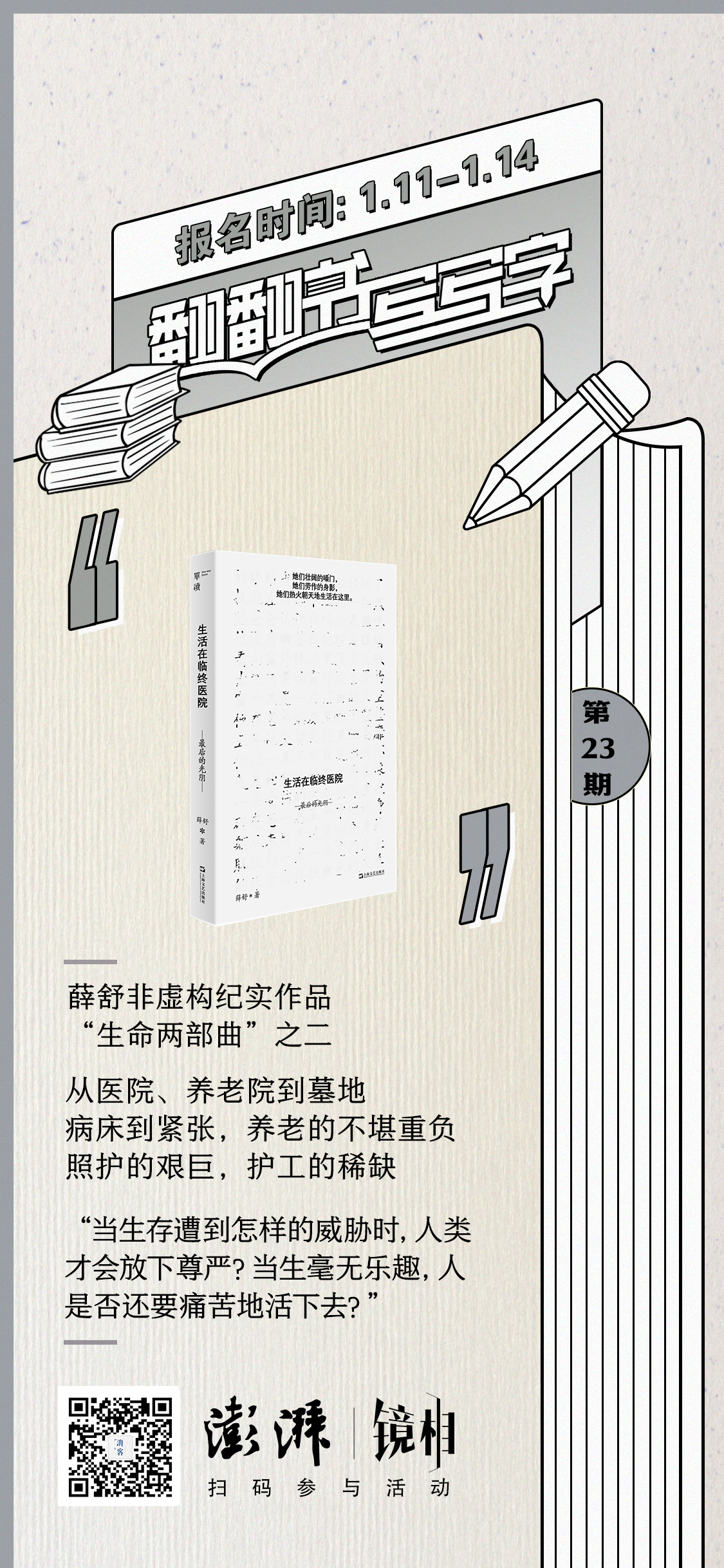
策划/编辑:吴筱慧
海报设计:王璐瑶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6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