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鲁迅说,观察上海,要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
电视剧《繁花》迎来大结局。剧集的热播,使得90年代初的上海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之一。当时整个城市正经历着“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高速发展,到处都有新的工作机会和投资机会。

电视剧《繁花》台词:“一只龙虾就是一个机会。”
其实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就被称为“不夜城”。习惯于夜间写作的鲁迅曾写有一组描写“夜上海”的文字,包括《夜颂》《弄堂生意古今谈》《秋夜纪游》等,都可以看作是上海都市文化的观察,并且处处显示鲁迅目光的犀利。
钱理群教授在《钱理群讲鲁迅》一书中曾介绍鲁迅和上海的故事,他将鲁迅及其作品置于特定的“空间”与“时间”来进行考察与阅读。鲁迅笔下30年代的上海有哪些令人深刻的时代细节?在《夜颂》中鲁迅强调的要有“看夜的眼睛”隐藏有哪些深意?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钱理群教授的讲析《鲁迅和上海的故事》。

鲁迅和上海的故事

本文为节选,原刊《钱理群讲鲁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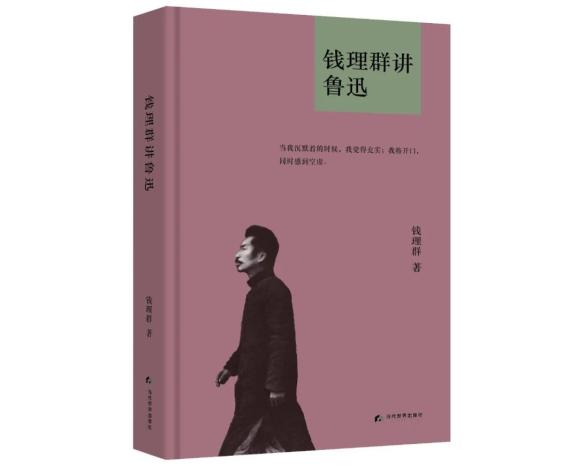
鲁迅一生中有几次重要的空间转移。自从一八九八年,十八岁的鲁迅离开绍兴到南京矿路学堂学习,他就辗转于“南京——东京——杭州——北京——厦门——上海”几座城市之间;而每一次转移都对他的人生之路、文学之路产生重大影响,留下鲜明的印记。其中日本东京这个东方大都市,为他打开了通向世界的窗口,是他独立的人生之路与文学之路的起点,意义自是十分重大;而居住时间最长、体验最深的,是一个乡镇——他的故乡绍兴,与两个城市——北京与上海。他的创作激情正是源于从这三大空间所获取的乡村记忆与都市体验,而他由此而创造的“鲁镇(绍兴)世界”、“北京世界”与“上海世界”构成了鲁迅文学世界的主体。
在经历了“五四”的落潮以后,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厦门、广州,目睹了革命高潮中的混乱与失败后的幻灭,于一九二七年末起,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定居上海。这是一个适时的空间转移,中国文化、文学的重心,正由北京为中心的大学学园转向以上海为中心的文化、文学市场;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都市化、现代化发展也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正是身处这样的旋涡中心,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深切体验,成就了杂文家的鲁迅。
我们把关注的焦点集中特定历史时空中所发生的故事。我们更感兴趣的,是鲁迅在这样的时间的流动、空间的转徙中的心理反应和心态。也就是说,我们所要讲的故事,主要是一个“心灵的故事”——这可能更是文学化的观照。但能够提供做这方面的考察的材料很少,我们现在只能利用书信与日记里的一些线索。
初到上海,无法融入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日,鲁迅来到上海。这是鲁迅在这一天的日记:“晴。午后抵上海,寓共和旅馆。”十多天以后,鲁迅写信给他的广东学生,说:“这里的情形,我觉得比广东有趣一点,因为各式的人物较多,刊物也有各种,不像广州那么单调”,看来上海给他的第一印象是不错的。但他也谈到了自己的某些不适应:“熟人太多,一直静不下,几乎日日喝酒,看电影。倘若这样下去,是不好的,书也不看,文章也不做。”还有一点也让鲁迅感到不安:“我初到时,报上便造谣言,说我要开书店了,因为上海人惯于用商人眼光看人。”但鲁迅仍希望能最终“静下来,专做译著的事”。“我仍想读书和作文章”。
但希望很快就破灭了,敏感的鲁迅发现,这一切其实都是上海的常态,是这座城市所固有的:“上海的情形,比北京复杂得多,攻击法也不同,须一一对付,真是糟极了”;“上海的出版界糟极了,许多人大嚷革命文学,而无一好作,大家仍大印吊膀子小说骗钱,这样下去,文艺只有堕落”;“上海到处是商人气(北新也大为商业化了),住得真不舒服”;“终日伏案写字,晚上是打牌声,往往睡不着,所以又很想变换变换了,不过也无处可走,大约总还是在上海”;“一点也静不下,时常使我想躲到乡下去。所以我或者要离开上海也难说”。鲁迅终于明白:上海其实并不适合他,他无法融入这座城市,至多只是一个客居者。
“真的知识阶级”的立场与眼光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五日,鲁迅到劳动大学作了题为“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提出了一个“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其内涵有二:一是“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因而是永远的批判者;二是永远“为平民说话”,并且“不顾利害”,“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看作是鲁迅的自我宣言。他在上海的最后十年,正是坚守了这样的真的知识阶级的基本立场。这就意味着,鲁迅是作为一个批判的知识分子,以平民本位的价值观念去观察与表现上海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正经历着一个工业化、商业化的进程。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现代都市文明得到畸形发展,消费文化也有了极度的膨胀。这样,历史又给鲁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使他在对他所说的“古之京”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性的审视以后,又能够对“今之海”所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化进行近距离的考察,并且作出即时性的反应。
如果说鲁迅对他的故乡绍兴的文学表达(散文与小说)是回忆性的,是以时间与空间的距离为前提的;那么他对上海的描述与评论却采取了杂文的形式,如鲁迅所说,“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这样的“现在进行式”的社会、文化观察与文学表达,是别具魅力的。
夜上海

我们首先要读的是一组描写“夜上海”的文字:这是最具典型性的上海风景与上海意象。
鲁迅在《夜颂》里提醒我们,观察上海,要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要能够在“白天”的“热闹,喧嚣”中,看见“惊人的真的大黑暗”。这是鲁迅才有的都市体验:人们早已被上海滩的五光十色弄得目眩神迷,有谁会看到繁华背后的罪恶,有谁能够听到“高墙后面,大厦中间,深闺里,黑狱里,客室里,秘密机关里”冤魂的呻吟?鲁迅一语道破:“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这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这样的都市文明观对于许多人无疑是一服清醒剂。
于是出现了夜上海风景中不可或缺的“高跟鞋的摩登女郎”。“在马路边的电光灯下,阁阁地走得很起劲,但鼻尖也闪烁着一点油汗,在证明她是初学的时髦。”这“初学的时髦”又未尝不可看作是上海自身的象征。
还有在夜上海如鱼得水的上海娘姨阿金。她的主人是洋人,又会轧姘头,在弄堂“论战”中常占上风,就总能聚集一大批人,搅得四邻不得安宁。
习惯于夜间写作、自称“爱夜者”的鲁迅,于是就与摩登女郎、阿金“同时领受了夜所给予的恩惠”。
而且还有迥异于北京的街头小景:北京古城是空寂的——老舍先生就说,北平的好处“在它处处有空儿,可以使人自由的喘气”。而上海大都会则是拥挤、热闹的,推、爬、冲、撞、踢,就成了人们见怪不怪的街市景观。唯有鲁迅,以其深邃的目光、非凡的联想力,揭示出其背后隐藏的都市文明的残酷与血腥。
这是鲁迅眼里的“推”:“洋大人”“只将直直的长脚,如入无人之境似的踏过来”;“高等华人”“手掌向外,像蝎子的两个钳一样,一路推过去”。鲁迅说:“住在上海,想不遇到推与踏,是不能的,而且这推与踏也还要廓大开去。要推倒一切下等华人中的幼弱者,要踏倒一切下等华人。这时就只剩下高等华人颂祝着——‘阿唷,真好白相来希呀’。”“推”的背后是上海社会结构中的新的等级压迫。
鲁迅在一篇演讲里这样谈到上海的“租界”社会:“外国人是处在中央,那外面,围着一群翻译,包探,巡捕,西崽......之类,是懂得外国话,熟悉租界章程的。这一圈之外,才是许多老百姓。三十年代的上海,不过是租界的扩大而已。也就是说,三十年代上海的都市化、现代化是以自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化为代价的:这个事实正是许多人至今也还想遮蔽甚至否定的。
还有“爬”。鲁迅的老对手梁实秋曾将据说是无限美好的“资产文明”推荐给中国老百姓:“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地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也就是只要努力往上“爬”,就可以爬到富翁的地位,天下也因此而太平。鲁迅眼里的“爬”却是另一番景观:“爬的人那么多,而路只有一条,十分拥挤。老实的照着章程规规矩矩的爬,大都是爬不上去的。聪明人就会推,把别人推开,推倒,踏在脚底下,踹着他们的肩膀和头顶,爬上去了。大多数人却还只是爬,认定自己的冤家并不在上面,而只在旁边——是那些一同在爬的人。他们大都忍耐着一切,两脚两手都着地,一步步的挨上去又挤下来,挤下来又挨上去,没有休止的。”在被“梁实秋们”无条件地认同与美化的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背后,鲁迅看见的是血淋淋的倾轧和压榨。
“京派”与“海派”,北人与南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知识分子间,曾有“京派”与“海派”之争,鲁迅根据他在北京与上海两座城市的观察与体验,做了这样的概括:“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后来他又发现了“京海杂烩”:“也许是因为帮闲帮忙,近来都有些‘不景气’,所以只好两界合办,把断砖,旧袜,皮袍,洋服,巧克力,梅什儿......之类,凑在一处,重行开张,算是新公司,想借此来新一下主顾们的耳目罢。”其实这是更深刻地反映了(北)京、(上)海两座城市的文化与知识分子的发展趋势的:不仅充当“官”的帮忙、帮闲,而且是“商”的帮忙、帮闲。
鲁迅还有一篇《北人与南人》,鲁迅说,这是由“京派”与“海派”的讨论而“牵连想到的”,其中自然就包括了他对北京人与上海人的观察,那确实也是入木三分:“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指顾炎武)曾经指出缺点道:北方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人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就有闲阶级而言,我以为大体是的确的。”
当然,也还有另一种存在。鲁迅曾引用苏联作家爱伦堡的一句名言,来说明现在的中国与上海:“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鲁迅同时指出,那些“庄严的工作”着的人们,那些为中国的现在与未来“前仆后继的战斗”者,“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沉重之语:“我每当朋友或学生的死,倘不知时日,不知地点,不知死法,总比知道的更悲哀和不安;由此推想那一边,在暗室中毕命于几个屠夫的手里,也一定比当众而死的更寂寞。”鲁迅因此提醒人们:要真正认识中国,“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我们也因此懂得了鲁迅说要有“看夜的眼睛”的深意:不仅要看到被“光明”的外表掩饰的黑暗,也要看到“消灭于黑暗中”的真正支撑着民族精神的“筋骨与脊梁”。
相关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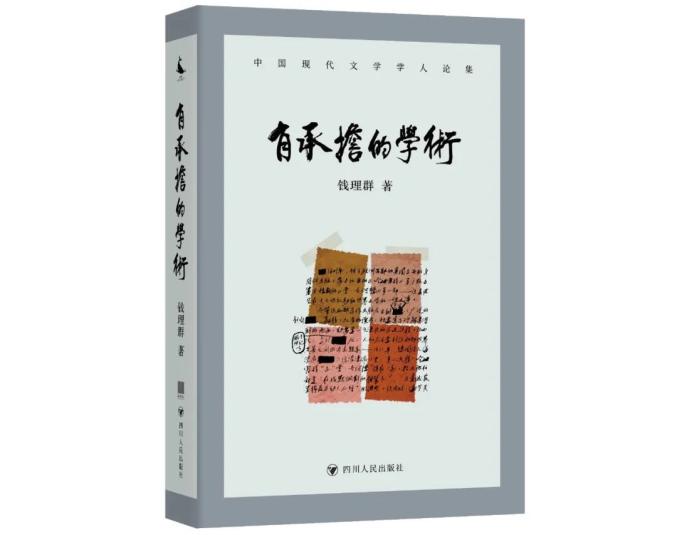
钱理群 著
活字文化 策划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3年
《有承担的学术》是学者钱理群知人论世的有情之作,集中书写了二十余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人学者。钱理群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学人”的影响比“学问”的传授更重要,更根本,更带基础性。
全书分五辑,从“史家的风范”、“人的标尺”、“传统的构建”、“同时代人”、“怀念、回忆与祝福”等不同角度立意,评述、回忆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中王瑶、林庚、贾植芳、钱谷融等第一代学人,严家炎、樊骏、孙玉石等第二代学人,以及王富仁、赵园等与钱理群同时代的学人,其中既有对学人行谊的追述,又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立源头直述至今,兼有文学史、心灵史的意义。
这些越经磨难越显纯真的学人使我们看到,在这“喧闹的世界”里,依然存在着“生命的、学术的沉潜”。
《有承担的学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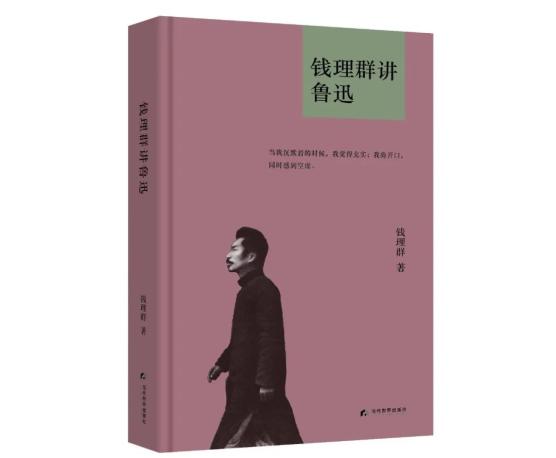
钱理群 著
活字文化 策划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21-12
当代著名学者钱理群,在晚年重新回到鲁迅研究,采用讲演的方式向大众再谈鲁迅。
这是一幅鲁迅的简笔画像。
作者从三个角度勾勒鲁迅的面貌和他的作品。第一部分是鲁迅和当代的关系,追问当下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为什么还要阅读一个140年前的作家的文章,这个问题最为迫切也最需要先行解决;第二部分对鲁迅的小说、散文、杂文等不同题材的代表作品进行文本阅读和分析,令人切实感受到鲁迅作品的魅力;最后一部分,则是回到鲁迅的年代,还原他的真实生活、工作场景,让读者从另外一个具象的层面获得对鲁迅其人的生动感受。
《钱理群讲鲁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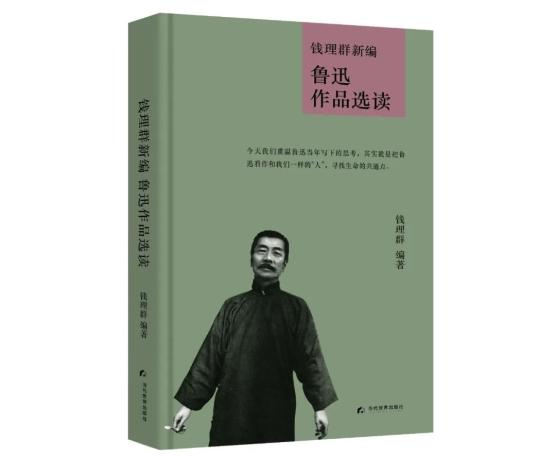
钱理群 著
活字文化 策划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21-12
2020年全球性的灾难和危机,使人类陷入了困惑和焦虑。这时候,人们迫切希望有一个可以坦诚交换意见、自由讨论的“真朋友”,钱理群想起了鲁迅——他就是这样的“真朋友”。
鲁迅是一个“真”的人,他不仅敢于公开说出别人不敢说、不愿说、不能说的一切真实,更从不向他人隐瞒自己内心的矛盾、痛苦、迷惘、缺陷、不足和失误;他敢于面对自身的局限,更无情地解剖自己;他从不以真理的化身自居,更拒绝充当“导师”。
钱理群结合自己的困惑和毕生对鲁迅研究的积累,精心挑选23篇鲁迅的经典杂文名作,逐一与它们对话交流。全书分成七部分,以“怎样——”作为引导,鲁迅原文+钱理群导读,从怎样看、想、说、写,到怎样读书、做人、做事,全景展示鲁迅的思想光芒和精神气质,让鲁迅走进当代生活,与青年读者对话。
在鲁迅140诞辰之际,这样一本鲜活的小书,是当代青年亲近鲁迅的不二选择。

活字文化
原标题:《鲁迅说,观察上海,要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