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韩水法|乡音里的江南
题记
清时越语相飘逸,
醉里吴音自媚好;
犹问青梅何处有,
竹林流水过小桥。
一
2023年清明前后到杭州行了一趟暮春之游,遂了这几年来要在清明节为父母扫墓的心愿;在会议和讲座的间歇,又在杭州周边走了一圈,与老友和学生,踏访了几处古迹名胜。在烟花三月的江南,闻一闻故乡的气味,听一听久违的乡音。
三月的最后一天,我们一行从杭州城里来到仓前老街参观太炎先生故居。看到余杭塘河边临街一色新修的仿旧房屋,不免想起多年前的那次过访。那时,仓前老街尚存一些古朴的风貌,若干老而旧的古宅,而太炎先生故居应是刚刚简单地修缮过的,深色的梁柱和地板显露了岁月消磨的痕迹,泛亮的油色则表示它的更新,但故居里面却空空荡荡的,并没有什么陈列的物品。今天的再到,太炎先生故居的大门已是不同先前,不过依然是旧宅的模样,这大抵是不会错的。

仓前章太炎故居(文兵摄)
在故居门口徘徊细观时,看到一位中年人路过,便向他打听故居修复和老街变迁的故事,确知他是本地人,便以乡音与他交谈。留下话与仓前话原本差不多。他听了我的口音,便很自信地认定我是小和山人,即留下镇下辖的一个村子。我说,我是留下镇上人。不过,小和山口音和留下本地话并无差别,但那里土著的母语却是闽南话,即本地人所谓的温州厂里话。他说,他在小和山有熟人,又说,他其实是上坟山人,后来才搬到仓前。上坟山在余杭镇外,是当年杭徽公路留下至余杭道中的一站。我曾祖父的墓就位于此地,少时曾与父亲和一众堂伯父们和堂兄弟来此扫墓。这里的墓后来被平掉了,我们也就成了不孝子孙。
闲谈的乡音透出陈年的醇厚味道,河里的流水和水面的薄雾也一时散发当年的生色。如不是要陪着文兵和欢欢两位参观,我大约会拎过一把竹椅,坐在这条我父亲少年时代常常走过的河街,与这位老乡谈谈海天,打听仓前的老底子事情。他不一定清楚太炎先生的学问,但会知道许多仓前的掌故,周围村坊的传说。
太炎先生的故居布置得素雅大方,颇觉适宜,展出了不易见到的一些老物件,比如汤夫人的书信,先生后人所赠送的实物,这是令人尤其喜欢的。参观名人故居,最扫兴的就是只能见到几张照片,一堆东拼西凑的仿品。
仓前虽在故乡的范围之内,但这回才彻底弄明白了镇名的来源。原来南宋在此地设有官仓储粮,而镇就在官仓之前。今天,南宋的粮仓已了无遗踪。不过,传统有其惯性,或许地理有其优势,后来的朝代就断断续续在此设立官仓。现在的仓前粮仓,镇上另一个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由清朝的两栋老仓和五六十年代两栋苏式仓构成。它在五十年代成为全国首个四无粮仓,由此闻名于世。它现在的功能演变为展览馆,除了空空的粮仓,还设有一个大厅,展出古今中外的各式粮仓模型,展示人们每天赖以为生却所知甚少的一种制度及其建筑的知识。讲解员是一位来自径山的姑娘。我问她是否会说径山话,她说会,便说了几句,听起来与仓前话大同小异。我就说起,有一年在径山开会,正值春茶季节,我逛到附近的村子里,与正在家里筛茶叶的茶农以乡音交谈,得知日本抹茶的原料原来多出自此乡。小姑娘便说,她家也是茶农。
从粮仓出来,我要请文兵和欢欢吃一回当地有名的白切羊肉和捞豆皮。在仓前街上问了好几个人后才得知,最好的白切羊肉店不在镇上,而在附近的市场。至于捞豆皮,他们都表示不知道,这个美味或许在这里已经淹没了。依着导航,开了十几分钟的车,我们来到了一条餐厅街,农家乐一家挨着一家,一眼望去,却萧条得很。我们走到网上推荐的那家餐厅门口,貌似老板夫妇的两人正在门口吃午饭。我直接用留下话打了声招呼,并问为什么客人那么稀落。留着络腮胡须的男子说,现在是淡季。我于是直问,你们家有没有白切羊肉和捞豆皮,老板娘用仓前话答道,白切羊肉有的,捞豆皮没有,不过,有咸肉煨芋艿。我问,咸肉是家乡肉吗?她说,不是,是他们自己腌的咸腿。家乡肉其实是杭州城里和余杭一带对冬天自腌咸肉的叫法。我说,那我去看看,她就带我到厨房,打开架在灶头上的一只不锈钢锅的锅盖,一股蒸汽带着咸香味扑鼻而来,锅里芋艿和咸肉正在浓汤中咕嘟咕嘟地滚着。这是故乡传统的家常菜肴。我说,来一碗,便回到堂前的餐桌。
老板娘走过来用仓前话跟我谈天,不免夸赞自家的羊肉好,说她家祖上就是做羊肉的,本地许多羊肉店的老板都是她父亲的徒弟或亲戚。她又说,儿子不愿意接他们的生意,只有女儿在帮忙。我说,有女儿帮忙也不错。仓前话属于余杭镇上的方言,这正是父亲的母语。父亲在余杭出生长大,一直到老,还保留有余杭口音。比如,留下话大约受杭州城里话的影响,码头的码念成ma,而余杭话的发音则是 mo。文兵是重庆人氏,听不懂我与老板娘的对话,有些懵懂;欢欢则坐在桌边笑,她是富阳人,大半能听懂,大概在好奇我们如此这般的家长里短的闲谈。
仓前现在成了杭州有名的梦想小镇,同时火起来的还有羊肉节。媒体报道,这里举办一年一度的捣羊锅节——捣的写法肯定是错的,其实是淘。本地风俗,煮羊肉将羊肉、羊头和内脏等一锅煮熟,然后想吃什么捞什么,这就是淘的意思。
文兵憋不住了终于问道:怎么杭州人也吃羊肉?这是北方人的口味。我说,杭嘉湖一带原有养羊的传统,湖羊羔羊皮是这里的特产;其次是羊肉,白切羊肉就是这里的特有的做法。说话间,老板娘端上来我们点的菜,一盘白切羊肉,一碗咸肉炖芋艿,几个青团,青团也叫清明团子,现在正是吃青团的时候。文兵和欢欢尝到了我以为好的家乡菜,而我则在乡谈间重温了故乡的风物人情。
二
在富阳开会的第二天,一早就醒了,于是就走到富春江边去看风景。富春江流到富阳城边转个大弯,一时开阔起来。远处晨雾飘渺,春树朦胧,江这边春水波荡,缓缓东去。如此烟树春岚,看得心旷神怡,不觉就踱到鹳山脚下子陵钓台边的一个埠头,见有两三个人坐在那里钓鱼,稍远岸边的江岩上耸立着子陵垂钓的塑像,平添了三分的趣味。
我问其中一位中年模样的钓者是不是富阳本地人,他说是。我就用乡谈问他,一天能钓多少,他回了一句“没有多少”,就不再多话了。这时,科林也款款从江岸走来,驻足听我们有一句无一句的对话,很有兴致,便问道:那个自动航行的小船是什么?钓者似乎用方言回复了一句,科林没有听懂,却很想弄清楚这句话的意思,我则在琢磨他的话是方言还是普通话,也没有听清楚。科林便转而问起富阳话与杭州话的区别。这时,我才醒悟,富阳话与留下话的语音是有差异的,而与萧山话相近,应属于宁绍。我便说,它与杭州话和余杭话都不一样,但如果讲得不快也是听得懂的,可以交谈。
河埠的石阶上默默地坐着一位年纪稍轻的男子,看人钓鱼。我问他为什么不钓,他说,他是公务员,并不钓鱼,只是每天上班之前来看一会儿。他只用普通话交谈,与几位钓者的寥寥数语,操的也是软软的官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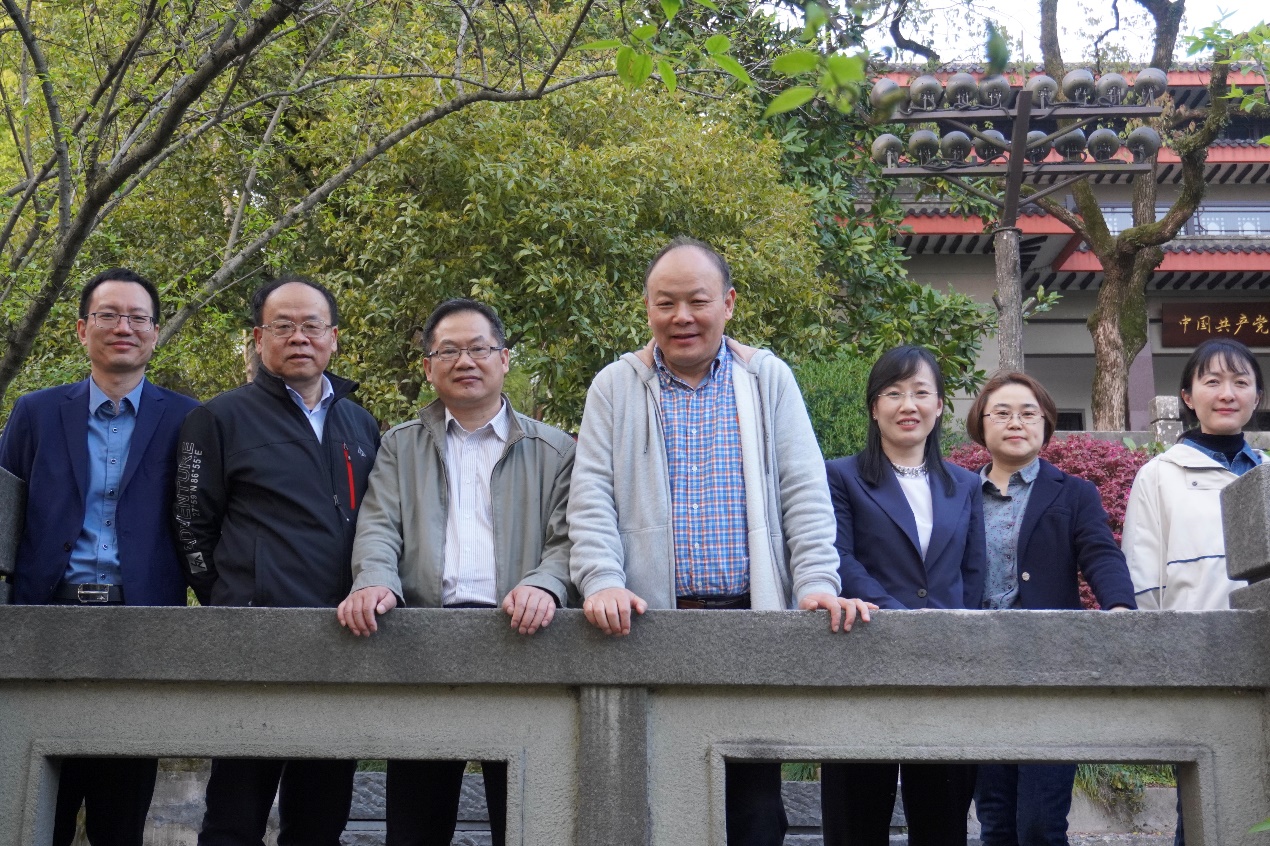
富阳鹳山·富春江边(王恒摄)
当天下午,参观黄公望隐居地后出山坞等车,我走到一片树冠下站定,就听见有人在用本地话谈天。三个约为保安的中年人,坐在浓荫下的椅子上,抽着烟,其中一人颇有兴致地大谈其家常,并不顾及周围等车的人等。那人讲的是他为家人做饭的事情,大意是,他按家人的要求做饭,做了这个菜,有人不想吃,再做另一个菜,还有人不喜欢。他就到街上买了菜再另做,家人大约也不满意。于是,到了晚饭时,他就热一热再端上桌。这原是家常琐事,以方言说出来却有格外的生动,抑扬的声调带着起伏的情绪,令人一时回到过去辰光的人世情态。他们的谈话用了许多方言特有的语词,有些原本也藏在我的脑海深处,平时并不容易想起,即使讲乡谈,也不会自动出口,如不调用,就永远静默了。但他人一说出口,即刻激活,造就了当下语境里一时特别的醇厚。然而,这已是普通话的世界,过几天它们又会被悬搁起来。
前两天参观中国美院博物馆“宋韵今辉”展览,我的一句杭州话逗乐了保安小哥,激起了科林对杭州话的好奇。我说,杭州话现在口音的主要历史源头应是在汴京。先前在划分方言区域时,杭州城里话几乎要被定为北方话孤岛,后来大约因为它的词汇大多为吴方言,依旧被划在吴方言区,单独成为杭州小片。不过,现在即便在杭州城里,杭州话的活动范围也成了一片一片的孤岛。杭州话也就活动在特定的环境和区域里,比如老旧尚未拆迁的小区。几天前在参观南宋遗址太庙广场时,看到四周有许多棋摊,一阵阵地道的杭州话,且是老杭州话——带点绍兴话的韵味,从那些棋友群里飞了出来。这块地方原来是杭州市的中心。
我虽然自小就会说杭州话,但在离杭赴京就学前,从来不说。当时在留下镇上流行一种态度,留下人如说杭州话,就被人说成“寿头寿脑,背时滴答”。“背时”是苕溪小片和杭州小片通用的词语,意思是不合时宜。杭州话,留下人亦称为杭白儿,但这儿字其实就是杭州话的影响。杭州话原来就流行于杭州老城里面,以及城外的近郊,真正很小的一片,而留下话所属的苕溪小片,通行的区域很大。留下是杭州西出的交通要道,镇上有不少人是说杭州话的,中小学老师不少亦为讲杭州话的城里人,后来周边建有许多大厂,大厂子弟普遍说杭州话,所以耳濡目染,不经意间就会了杭州话。其实留下话原本也受了杭州话的不小影响,语音要比苕溪小片其他地区硬一些。
三
清明前两天,跟大姐和弟弟等约好从留下出发去给父母亲扫墓。父母墓位于五潮山公墓的山坡之上,可谓高敞地,四围群峰耸立。这里原来是留下公社石马大队的地界。提前两天扫墓是为了避开清明那一天的拥堵。在墓前,凝视着墓碑的父母照片,父母生前的往事一一浮现在脑际,情不自禁对他们喃喃而言,说得是牙牙学语时就说的母语。
扫墓归来,我走到留下大街,看到一副萧条到没有什么行人的景象,不免有些伤感,便联想到,有司自以为是的过分干预造成了许多江南古镇老街的败落。
走过大桥,在我家居住多年的老房子的地面走了走,房子拆掉之后这里种了一行树和花木,都已长得很高了。又走上大桥,这座少年时代几乎天天都要在此嬉戏,上小学和中学每天都要走的大桥。不过,这次惊愕地发现,这座已被列为国保的文物竟然已经被人大大地改动过了。大桥的东堍原来是半圆形的踏步,一并通向茶市街和北星街两条街。现在通向北星街一侧的台阶全部被拆除了,其本来面貌受到严重损害。突然想起,这类事情在杭州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临安钱镠墓的被盗算是另外一例吧。
多年没有爬平基山(安乐山)了,这次我决意登一回。外甥和侄女们表示要与我一起爬山。山麓早已失去原先的地貌和风情,只是支离的小块菜地和原先小学上面一片茶地还依稀残留了当年的景象。茶地以上筑有一条散布着星星点点青苔的步道,看来少有人行走,步道上面则是遮天的树木。少年时代,这里只有人踏出来的土路,除了灌木就是马尾松,都不高,随处可四望。步道一直修到了山顶。当年每到山顶必举目远眺,这块现在被称为西溪湿地的土地,它周边的山和村坊,都尽收眼底;如遇天气晴朗,则可极目辽阔的杭嘉湖平原,直至云水之际。平基山就是杭嘉湖平原的西南边界,再向西南,它与群山相连逶迤直至福建乃至更远的南方丛山。但现在,林木高秀,遮住望眼,寻不到一个可做远眺的高点。这情景一时令自己觉得现在所登的不是少时几乎天天要上来一趟的那座山。
晚餐的桌上,只有姐姐、姐夫和外甥还讲着大致地道的留下话,不过许多词语已经受到了杭州话和普通话的浸润。比较之下,还是我的留下话更纯正,因为我的母语在北京的语言环境中是被隔离在大脑中的。先前留下镇虽然向来多有外来人,本镇的土著只说留下话。留下话里还有一句贬损外来人的话,“氽来货”,意即从河里漂来的,在本地没有根底。但现在,外省来的人口已经远超本地人口,所以普通话就成了通用语。只是在老留下人聚居的地方,留下话还在顽强地保留自己的剩余势力。我家的家庭聚会,留下话、杭州话和普通话并用,幸好大家都听得懂,尽管晚辈不一定说得来。年轻一代之所以不会说方言,各种原因中有看似奇怪的现象:在稍大的城镇,更不用说大城市,孩子自出生起,就被当作来自普通话乡的人对待的,牙牙学语时,甚至祖父母们都操着乡普话教孩子说话,生怕他们听不懂方言。
四
清明前一天,我和少年同学军英及学生丹妮、牧今和阿坚一起去访海宁古迹。王国维故居依旧在闭馆,观潮胜地公园不得其门而入,于是我说,那我们就去长安镇吧。这个近在杭州周边的古镇我却一直没有来过。当即就在网上查到镇上有一座长安镇画像石墓,相传为三国时东吴孙权第三女的安葬处,俗称“三女堆”。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却正好位于海宁中学校园内。到得学校门口,电动伸缩门紧闭。我们喊出门卫,说明来意,但门卫说:参观这座墓,要预约,你们不能入内。我就说,我们从北京和上海过来,很想看看这座国宝墓,请他与校长说明一下。门卫见我们诚恳,就给校长打了电话,满口海宁话,虽然隔了一道门,我听明白了结果:校长同意我们进去看看。呵呵,海宁话与留下话同属苕溪小片。

长安镇仰山书院
这时,门卫相当客气地开门让我们进,他说,墓室是锁住的,进不去,墓室的壁画等物也移到博物馆去了,但学校尽头的墙上有它的图片,尽可以看看。他还特意推荐说,校内还有一处名胜仰山书院,今天正好开放,也可去一看。平时它是不怎么开放的,他也只进去过一、两次。到了画像石墓入口的房子,我们围着转了一圈,看了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之后,就来到仰山书院。说是书院,其实只有一座楼,两个墙门,半个院子,在扶苏的花木掩映中,尤显清雅。书院初开时,黄宗羲曾来此讲学;现存的建筑据说是经洪杨之役残毁后修过的遗存,不过,它反倒有了别致的味道。我们一行人在楼上楼下,院子走廊参观拍照,流连了好些时候。
从海宁中学出来,我们又去寻访大运河长安闸。上塘河边的博物馆即“大运河(长安闸)遗产展示馆”已经闭馆,我们沿河走到了长安闸遗址。它是根据2012年的考古在元末运河老坝的旧址上重建的,再现了当年翻坝的现场。遗址现场建有翻坝的轱辘、绞盘等物,上面覆有草顶的亭子,做得相当雅致。
从虹桥沿上塘河往来长安闸,见对岸临水民居,河埠驳岸,尚存旧时风貌,若干民居下建水阁,有一、两水阁还筑有河埠,提示着当年这个运河商业重镇曾经的繁华。
元末张士诚主持开挖了杭州城江涨桥至塘栖的河道,北上的运河于是不再由上塘河经临平过长安,长安闸的地位就降低了。据记载,元末修建的长安老坝的规模已远逊两宋时的长安闸。遗址靠河的一个小屋里保存了一块《新老两坝示禁勒索碑》,海宁知州汪肇敏立于清光绪八年(1882)正月二十二日,它禁止坝夫勒索和刁难过往船只等事项。由此可见,一直到清朝上塘河依然是重要的航道,长安闸依然发挥作用。有人说,现在长江大坝船闸的原理与长安闸是同样的,不知是否受了它的启发。
长安镇之行的收获出乎意料,大家都很开心。军英总结说,在这个古镇上,我们参观了一处世界文化遗产,一处国家重点保护单位,一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很齐全,相当圆满。回到杭州城里,已是万家灯火。振华老早在他侄子开的“堂前屋后”订好包间,以普通话招呼军英和三位学生,而我与振华说话总是乡音的对谈。他侄子自酿的风味醇厚的米酒,鲜美无比的特制清水鱼,令人很觉得杭州为美食荒漠的说法的不实。记得那天欢欢在西湖边上的味庄做东,点的蟹酿橙等菜品的鲜美,堪与窗外湖天比色,文兵、科林和丹妮都夸她为美食家,长年在杭州国清自然一起称好。就在美食和美景的激发下,我们当场商定了第七届汉语哲学论坛的题目为“语言表达与绘画表达”。
五
自从回北大教书之后,每次回乡都匆匆而来,匆匆而去,时有愧疚之心,常生在故乡小住一段时间的想法,但一直未能落实。此次杭州之行又强化了这样的念头,寻一个近山傍水的惬意古镇老街,游山玩水;时或上茶馆与本地老人,谈谈海天;亦不妨在街头巷尾,在一把小竹椅上坐下,听街人说家长里短;不妨可以混迹于公园的亭子曲廊之下,旁听乡音里的天下大事,人间道理;更可过访少年同学,追忆旧日时光,只说乡谈。
然而,这次的故乡漫游让我蓦然觉醒,乡音在它的原乡里已消退为一片一片的孤岛。在我离开故乡赴京上学的年代,江南还是五色斑斓的吴方言天地,从一个村镇到另一个村镇,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人们讲着不同方言,经历交流的不便,感受异乡方言的独特韵味。今天,它已经成了普通话海洋中的一个一个岛礁,甚至乡镇上,人们的共同语是普通话,只是当聚集在一起的人以本地人为主时,方言才从普通话的海水中露出来。我辈将万般不舍而无可奈何地见证它们的慢慢消失,不仅有我的母语,还有自小会说的其他方言。
方言原本也是一片一片的,吴方言就分成了许多小片,不过,除了瓯江小片即温州话外,其他小片之间大多是可以交流的,虽然有时不免略有困难。同一小片内各乡镇村坊的语音和词汇也多少会有差异,方言因村而异,逐镇而别。比如,杭州城外四周,仅仅我、你、他,以及我们、你们、他们的说法就有四、五种之多,因此,仅凭这些人称代词就能大致分辨说话人是周边哪一村哪一坊的人,更不用说,哪个地区的人了。所谓母语也就是一村一镇的方言。过去在留下镇街上,讲杭州话的、宁波话的、绍兴话的、安徽话、苏北话和普通话的各色人等,自如地以自家方言彼此说话,可以谈得热火朝天,毫无违和感,而用自家方言骂人,同样的侮辱和威吓,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容易上手,更加本真。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我未曾到过上海时就学会了上海话。流行于上海和杭州的滑稽戏就是再现了这样的风情。戏中的人物来自不同地区,操着各色吴方言,亦讲北方话,它的方言大杂烩,名为滑稽,却是江南世情的现实情景。
乡音是与乡邦的风物、建筑、制度、人情世故融合在一体的。一些感觉、情感、态度、关系甚至状态我可以用方言很贴切地表达出来,然而却难以找到对等的普通话词语。方言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世界。在古典中国,汉字作为普世的符号构成了社会共同感的框架,但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历史则是以乡音串连起来的。今天,人们在追复先前时代特定地区日常的社会生活,不可避免地要以语言的现代形式来重述,这就会过滤掉许多情感、人情和风情的独特表现。历史叙述的隔膜也就由此而产生了。
从历史发展的源流来看,方言的衰落和消失,就如那些濒危语言的衰落和消失,是一个必然而难以挽回的趋势。方言形成的原因,就是聚落而居的人们与其他地区的同类长期隔绝或极少交通。其实,历史上人口的大规模交流与迁移也会改变语言和方言的分布和发展。然而,从情感上从文学上从艺术来说,没有了乡音,乡愁也失去了其主要的依凭。乡音从牙牙学语起就融化在我的血液之中,当它在原乡逐渐消失,就慢慢地困守在我的脑海里面。我想,我人生的最后一句话可能会以无人能懂的乡音说出,那可能是回归故乡的呢喃。
2023年4月6日
2023年8月1日改毕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