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我的天才女友和她的前半生|镜相
镜相栏目首发独家非虚构作品,如需转载,请至“湃客工坊”微信后台联系。
作者 | 胡卉
编辑 | 吴筱慧
编者按:
朋友眼中,漫漫就像是《我的天才女友》里的Lila,人群里最聪明的女孩。她从小就是学霸,大学考上名校,走出了自己出生的小镇。十年前,漫漫硕士毕业,开始在全国知名的商学院做行政老师。外人看来,求学和就业,漫漫去的都是大名鼎鼎的好地方。而后,结婚、买房、生孩子,漫漫也都一一给出了标准答案。然而三十多岁开始,漫漫看见自己陷在了某种巨大的惯性里,找不到出路。或许是想要冲破惯性的圈套,漫漫给了自己租了一个带院子的老房子,挂了个牌子,叫漫漫工作室。这是漫漫重新开始的地方,我却突然感到不安,我害怕它变回一个重复的昨日世界……

本文配图除特别标注外,均来自《我的天才女友 第二季》剧照

朋友们都说,得离漫漫远点儿,不然她会把咱们带坏的。我丈夫也这么说。
漫漫是个智商特别高的家伙,想要什么,想做什么,身上有股势不可挡的决心。这样的人,天生是个学霸。她出生的那个镇子,离我出生的那个镇子只有二十里路,但我们在不同的乡中学读书。通过高考,我从湖南去了山东,而漫漫去了北京大学。这么说,我的人生几乎要错过漫漫了。然而后来,我和漫漫都来上海读研究生。她和我当时的男朋友是同班同学。
我和漫漫认识十年了。我见过了她的草坪婚礼,一对龙凤胎孩子的出生,腹肌撕裂到四指宽,康复后又一点点锻炼出平坦紧实的腹肌。
今年,漫漫换掉了她的白色宝马,买了一辆黑色的奔驰。如果没有犹豫那么一下的话,漫漫说,她会买那辆明黄色的玛莎拉蒂。现在,她有点后悔。因为那辆玛莎拉蒂明黄色的身影时不时地还在她眼前晃,像狗一样缠着她。
漫漫喜欢歌手泰勒·斯威夫特。B站上,泰勒·斯威夫特在2013年音乐节上弹唱的一个视频,漫漫不知看了多少遍,却从来没有麻木过。她说,心里涌动着兴奋的时候,就是人活着的时候。对于她喜欢的东西,漫漫的表达很有感染力。那个视频我马上去看了。歌词第一句话是,“爱他,就像开着一辆崭新的玛莎拉蒂冲向绝路”。
漫漫摆脱了社会底层农民家庭的出身,不仅内在如此,连表面上也看不出来了。漫漫听我这么一说,非常高兴,她说:“没错,我要捏紧上海送我的这块橡皮,把那些痕迹擦得一干二净。”
漫漫的眼睛黑如棋子,乍看总含着笑意,一副很容易高兴的样子。二十岁那会儿,她的眼角就有一对浅浅的鱼尾纹,微微上扬,颇有神采。我们隔着小圆桌喝咖啡,近距离注视漫漫的时候,我也感觉那对深邃温润的眼睛,像一个半遮半掩的谜面。
漫漫今年三十五岁了。大家都说,她比二十岁那会儿更好看了,也更吸引人了。不然,为什么我们总想往她那儿跑呢。
 我住浦东,漫漫住浦西,中间隔着一条黄浦江。9号线地铁穿过江底的时候,丈夫问我:“漫漫不上班,在忙什么?”
我住浦东,漫漫住浦西,中间隔着一条黄浦江。9号线地铁穿过江底的时候,丈夫问我:“漫漫不上班,在忙什么?”我告诉他,漫漫在徐家汇租了一个带院子的老房子,挂了个牌子,叫漫漫工作室。
“工作室做什么呢?”我丈夫问。
我告诉他,漫漫还没想好拿它做什么。但是也不着急。因为漫漫光是给工作室找心仪的房子,就找了五六个月。漫漫走完下一步,可能也得花上五六个月。我说:“至于你说房子拿来做什么,那是第三步的考虑了。漫漫现在还在忙着搞装修。”
我丈夫不明白。他这么说漫漫的工作室:“那就是一个空房子。”
男人总认为一个人做事要有目标,似乎还在原始社会打猎,每天都得瞄准什么。按他的看法,如果行动没有目标,无异于下楼梯故意一脚踏空。我说,话也不能这么说。他调整了一下措辞说,那至少要有一个“动机”。
看来我没办法让他明白。我只好找了个动机说:“白天孩子上学去了,漫漫、保姆、婆婆三个女人待在家里,漫漫觉得不自在。她容易受到打扰,这才决心要出门的。”这是漫漫说的。
 漫漫还有些话我没有说,因为我从地铁车厢的窗子里瞥见我丈夫皱起了眉头,他看上去不认同,还有些疑虑。
漫漫还有些话我没有说,因为我从地铁车厢的窗子里瞥见我丈夫皱起了眉头,他看上去不认同,还有些疑虑。比如,听说漫漫不要管家庭住房的房贷,还有了一间自己的房子,我表示了祝贺和羡慕。伍尔夫那句名言,“女人要想写作,她就必须有钱,还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漫漫也许没有听过,但她已经拥有了充分理想的条件。
对此,漫漫是这么说的:“女人不写作,她也必须有钱,还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
漫漫还说:“家庭生活之所以让人难以忍受,是因为它不让你独处。这和监狱让人难以忍受的理由是一样的。它们本质上都是一种集体生活。”
出了徐家汇地铁站,沿着宽阔繁忙的华山路走到交通大学,转角进入一条夹在别墅高墙之下的安静马路,继续走上两百米,就到了漫漫工作室的弄堂。
漫漫工作室在弄堂最尽头。一大丛沿着围墙攀缘的月季花下面,停放着漫漫的奔驰车。我们敲错了门。一位瘦小的银发老太探头出来,一看是陌生人,谨小沉默地掩上了门。我们退身张望,看见隔壁的门上挂了一块圆形的木牌,平底锅大小,年轮清晰,白色水彩勾勒出一只眯着眼睛打盹的猫,猫背如一段起伏的波浪,脊椎线之上,用圆体字斜斜地刻着:
“漫漫工作室,请进。”
漫漫听见了我们的动静,她热情悠扬的声音从门里面传来:“朋友们,我来啦——”
 门开了。漫漫握着门把手,笑容灿烂地侧身站着,让我们快进。漫漫说,她正在剪下花园里种剩下的几朵绣球。她要把花朵浸泡在装满水的玻璃瓶里,作为客厅的装饰。我在哪儿看过这样的照片,可能是在网上买菜时无意中刷到的。
门开了。漫漫握着门把手,笑容灿烂地侧身站着,让我们快进。漫漫说,她正在剪下花园里种剩下的几朵绣球。她要把花朵浸泡在装满水的玻璃瓶里,作为客厅的装饰。我在哪儿看过这样的照片,可能是在网上买菜时无意中刷到的。漫漫说:“我刷抖音学到的。”
漫漫像我们父母那样歪在沙发里刷看抖音短视频,一副安装了机械臂的样子。那超出了我的想象。在我的印象中,漫漫可不是容易入圈套的人。她不属于那个阶层。
室内的设计有点特别,的确不是居家的风格。进门右手边是卫浴间,被一张淡绿色的移门掩藏在里面。在移门和墙壁之间,有一个窄窄的L形过道,迎面悬挂着一个毛茸茸的鹿头鹿角标本。这头驯鹿的眼珠子特别亮,像活生生的驯鹿的眼睛在用上帝的视角俯瞰着我们,里面映照出我们十分渺小的身影。因为它只有一颗生动的头而没有身体,显得有些阴森可怕。这玩意一定还很贵。
漫漫笑着说,鹿头是房东留下来的。不过,她喜欢。漫漫小时候在山野之中奔跑,天然地亲近与野外有关的事物。时过境迁,城市生活正在抹去她对山野的记忆。不只那位房东,换做她,也愿意遵循上海的游戏规则,花费昂贵的价格去保留一点寄托,一点想象。

漫漫工作室 作者供图
漫漫的花园贴着墙根种植了一圈花木。如果点开手机,拍照识别,你会看到一些很洋气的名字。漫漫对照着手机和她的植物,指指点点地介绍说,这是法国松,这是波士顿肾蕨,这是日本珊瑚树,这是非洲天门冬,听着像远渡重洋而来的稀客。
一些植物看着很眼熟,是我们湖南乡村记忆的一部分。我以为这是漫漫有意的选择,她却像我一样,叫不上它们的名字。
漫漫说:“我找园艺公司打理的。自己动手干了一两天,太累了。”
我说起我们的父辈进了城,不是在做保安,就是在做绿化工人。漫漫的爸爸就在张家浜河畔的九间堂别墅做绿化工人。老人和同事们共享地下车库里头的一间房子,随身携带保温杯烫冷饭冷菜吃,你要问他为什么能这么乐呵,他坦然地说,在上海很多人都是这么过的。
早前,漫漫情愿补贴她爸爸每月四千,也不想让他做这份工作。但是爸爸坚决不同意。观点大意是:“归根结底,是人需要劳动。诚实适度的劳动是符合人性的。”换句话说,如果漫漫不让爸爸参加劳动,那是反人性的行为。爸爸是不是认为漫漫在过一种反人性的生活而不自知呢?受限于表达能力,爸爸也许讲不出那番话,但是不代表他脑子里不这么思想。正是后一种考虑,让漫漫不好坚持她的孝心。
我环视了一圈漫漫的花园,翻土,种植,铺卵石,我自觉也难以完成这份工作量。我说:“我们小时候被鼓励热爱劳动,现在这劳动能力退化得可厉害了。”
漫漫笑了起来,她说:“如果发生战争,把人打回乡下,我们可怎么活呢?”
 客厅是一个二十平米左右的房间,方方正正的。左边挂着一个大电视,屏幕上跳动着彩色的波段,正在放一首英文乡村歌曲,调调洋溢着松软的热情。米色的布艺沙发上,一条坠着流苏的深色毯子像溪流一样淌到地板上,连接着一块不大的图案复杂的波斯地毯。沙发的一头,贴着窗帘立着一张白玉色的折叠桌。漫漫说,那是商学院的学生们送来的麻将桌。
客厅是一个二十平米左右的房间,方方正正的。左边挂着一个大电视,屏幕上跳动着彩色的波段,正在放一首英文乡村歌曲,调调洋溢着松软的热情。米色的布艺沙发上,一条坠着流苏的深色毯子像溪流一样淌到地板上,连接着一块不大的图案复杂的波斯地毯。沙发的一头,贴着窗帘立着一张白玉色的折叠桌。漫漫说,那是商学院的学生们送来的麻将桌。漫漫说:“上个周末,商学院来了好些人,在这儿打了一天的麻将。”
我们忽然来了灵感:“说不定,工作室可以成为一个麻将馆。”
漫漫觉得这主意不错。操作也不难。弄一个小红书账号,学着博主们包装一下,一家网红麻将馆就诞生了。入会费定多少合适呢?大家好像认真思忖起来。漫漫说,如果能覆盖每月房租八千,水电煤茶叶咖啡两千,就行了,它就光荣地自力更生了。

漫漫工作室 作者供图
漫漫看了好多房子,这套最满意,合同签了三年。所谓“满意”,不是指性价比最高,而是这房子带来的一种前所未有的奇特感受。那种感受怎么形容呢,漫漫说,“你只是个看热闹的。”
她以前待在湖南,后来离开去了北京,又来上海,才明白那是一种“边缘人”的心理感受。不过漫漫也说,就算人在北京上海,也不一定能摆脱那种自觉渺小无用、可有可无的心理感受。
也许话题有点沉重了。这时候,漫漫才笑着说起来,这套房子是一个名人故居。一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伟大教育家和他的第二任妻子曾在这里居住。教育家临终之际,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夫人奔赴来此看望过他。点开手机搜索看看,史料充分,细节有据,漫漫不是在信口开河。
我忍不住想象了一下:他可能会走进小花园,站在我们刚站的那些地方,像我们一样深沉地眺望对面别墅的阁楼彩窗,陷入了短暂的遐想。
这时,我听见漫漫的丈夫说,这里非常安全,门不上锁也不丢东西。街上有人24小时巡逻,到处都是便衣。在这样的氛围下,人很容易想起“旧时王谢堂前燕”之类的古诗。我没有这么感慨。万一漫漫并不想做一个“寻常百姓”呢?我忽然觉得自己并不了解漫漫。
我低头翻看手机。这时,百度百科跳出来说,那位伟大的教育家在这套房子里英年早逝,原因是“劳累过度”。
刚才,我们正在讨论拿这套房子开一个麻将馆。
愿他们安息。可是,寻常老百姓的生活总要打麻将的嘛。短暂的嬉笑过后,漫漫像是沉思了一会儿,拿腔捏调地说:“你们这群平庸的不肖子孙啊。”
我们愕然,她这是在模仿谁的声音呢?
 听漫漫的丈夫说,漫漫本来是一个很有事业心的人。在我听来,他想表达的更有可能是,漫漫本来是一个很有能量的人。
听漫漫的丈夫说,漫漫本来是一个很有事业心的人。在我听来,他想表达的更有可能是,漫漫本来是一个很有能量的人。这话不假。有两三年时间,她都在正式工作开始前三个小时起床看书,跳绳,是励志书上讲的“清晨5点联盟”的成员。我们面对她时,不免自惭形秽,但一想到那是漫漫,是我们这群人能够抵达的理想的标高点,又会宽宽心。
求学和就业,漫漫去的都是大名鼎鼎的好地方。这是大家看在眼里的。可是不知怎么回事,也许是好地方一点都不把漫漫当回事,长此以往,导致漫漫也不把自己当回事了。我们等着漫漫大放异彩呢,可是好些年时间过去了,我们没看到漫漫把她的能量释放出来。
我在微信上问漫漫,最近在忙什么呢。漫漫发来一个地毯的链接。我没想到一块地毯会那么贵,也没想到漫漫买一块地毯会比我买一张床还贵。她问我有没有时间陪她去实体店看一看。我陪她去了。漫漫如意选到了那条草绿色的羊毛地毯,草色很新,高度真实,上面趴着一只温顺的家养宠物似的大老虎。
老板娘夸赞漫漫的品味,漫漫一边扫码付款,一边微笑着说:“谢谢您的地毯,它把春天和动物园都送到了我家里。”
那一刻,漫漫优雅得令我震惊。
可是,这就是我们的漫漫大放异彩的方式吗?
 十年前,漫漫刚硕士毕业,举行完毕业婚礼,开始在那家全国知名的商学院做行政老师。学生都是四五十岁的企业家,男女比例差不多。这些人生活比较滋润,讲话好听,恭恭敬敬地叫漫漫老师,有时也好为人师地传授过来人经验。对老板们而言,所谓求学,要么是想拓展业务版图,要么是想了解未来行业的机会,总之是奔着交生意场上的朋友而来。
十年前,漫漫刚硕士毕业,举行完毕业婚礼,开始在那家全国知名的商学院做行政老师。学生都是四五十岁的企业家,男女比例差不多。这些人生活比较滋润,讲话好听,恭恭敬敬地叫漫漫老师,有时也好为人师地传授过来人经验。对老板们而言,所谓求学,要么是想拓展业务版图,要么是想了解未来行业的机会,总之是奔着交生意场上的朋友而来。在那样一个环境中,师生关系也不是传统学校的师生关系。回想起来,大家一起吃了好多饭,一起去了好多地方。漫漫第一次出国就是跟那些学生,去意大利买手工皮鞋,去巴黎看人体T台秀,去曼谷看情色话剧。花花世界,开了漫漫的眼界。不过,用漫漫自己的话说,她那时“整个人严丝合缝,还没有打开”。一个年轻女孩,身体刚刚脱离学校生活的规训,脑子还没有跟上,在自由的大世界面前,她愣住了。特别是和那些成熟女人比起来,她面对自由的表现,还相当的稚嫩胆怯。
漫漫在商学院工作不到两年,辞职了。一个原因是备孕不太顺利。回想起来,漫漫也不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年轻的自己,会那么想生孩子。那份渴望与其说是起源于爱,不如说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忧惧。主流社会提供了标准套餐在那,好像你不购买那个套餐,不老老实实地吃完套餐里的每样食物,你就是一个罪人。你会陷入那种阿猫阿狗也能抱着优越感对你的人生说三道四的糟糕处境。
所以,结婚、买房、生孩子,一个当代中国人的人生三件套,漫漫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标记了打勾。非常年轻的漫漫在求得标准答案的时候,还料不到年纪稍长的漫漫会对她滋生出疑虑不解的心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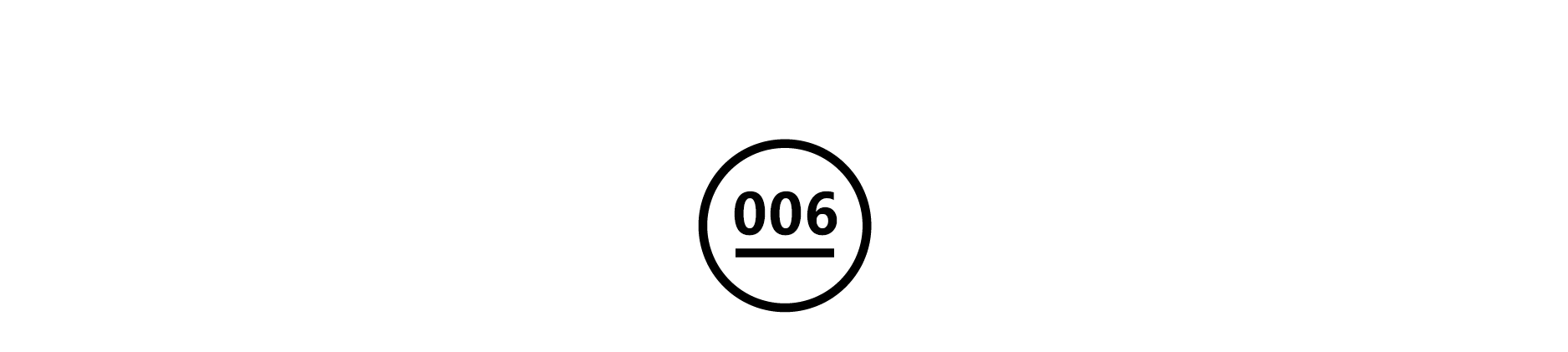 或许,备孕不顺是辞掉那份工作的一个托词。真实的原因是漫漫在那样的环境里待得不舒服。
或许,备孕不顺是辞掉那份工作的一个托词。真实的原因是漫漫在那样的环境里待得不舒服。有次在南京西路逛逛,我问漫漫:“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买奢侈品的?”
我以为是漫漫和她丈夫在2015年股指期货大涨,同时抓住区块链的机会,完成了财富积累之后。那是漫漫和她丈夫本硕七年研习的专业领域,预测行业走势的敏感性是必备素养。尽管金融界竞争激烈,“聚集了全中国最聪明最勤奋的一群人”,但是早一年,晚一年,漫漫淡定地说,她会通过这扇窄门,进入一个不受金钱围困的世界。
漫漫说:“我开始喜欢买奢侈品,是在商学院工作的时候,那时候还是一个入不敷出的状态。”
我问漫漫:“真的吗?”
漫漫笑了,认为这完全不必大惊小怪,她们宿舍的女生都是如此,即使是读书时最朴素的那个女生,毕业后进入社会也一样。她们都在上海,会定期聚餐。
漫漫说:“在那个环境里,人们会注意看你背的包,穿的衣服和鞋子的牌子。人们根据这些来评判你,至少,这些构成第一眼的印象。出去聚会的时候,你要是戴一条梵克雅宝的高仿项链,你心里会很别扭,好像等于你自己就是一个仿制品。你要是没有一个爱马仕包包,就感觉自己抬不起头。你什么都没做错,又分明什么都做错了。你犯了罪,被大家通通看在眼里。人家看待你的眼神,就好像是你误闯了那个世界,他们正在犹豫该怎么把你赶出门去。”
我一时不知怎么接话。漫漫提醒道,不要忘了,那些人是这个社会的中上层人士,在他们面前,命运一开局就不利的人,天生懂得怎么低头。也不要忘了,那时候的漫漫连城市中产都算不上。
漫漫还说,世界上居然会有那种矛盾重重的工作。它的存在,好像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是为了给工作的人心里添堵。比如,学校给的薪水很低,当漫漫看到她一个月的薪水支付不起师生一顿寻常聚餐的开销时,漫漫一度失去了平等心,平常心。
她说起那样的工作聚餐:“我除了吃吃生鱼片,跟着笑一笑,还能做什么呢?”
商学院的同事,离婚率超高。抛开诱惑不说,漫漫也不是没有遇到过打心底欣赏的男士。她用理性和隐忍压制了自己。
漫漫自嘲地说:“咱们学霸最擅长过压抑的生活。”
似乎说不清哪个原因对漫漫的离职起了决定作用,但是这个那个,糅合在一起,就造成了强烈的如坐针毡的感受。漫漫以身体缘由提了辞职。龙凤胎出生后,商学院想请漫漫回去,她拒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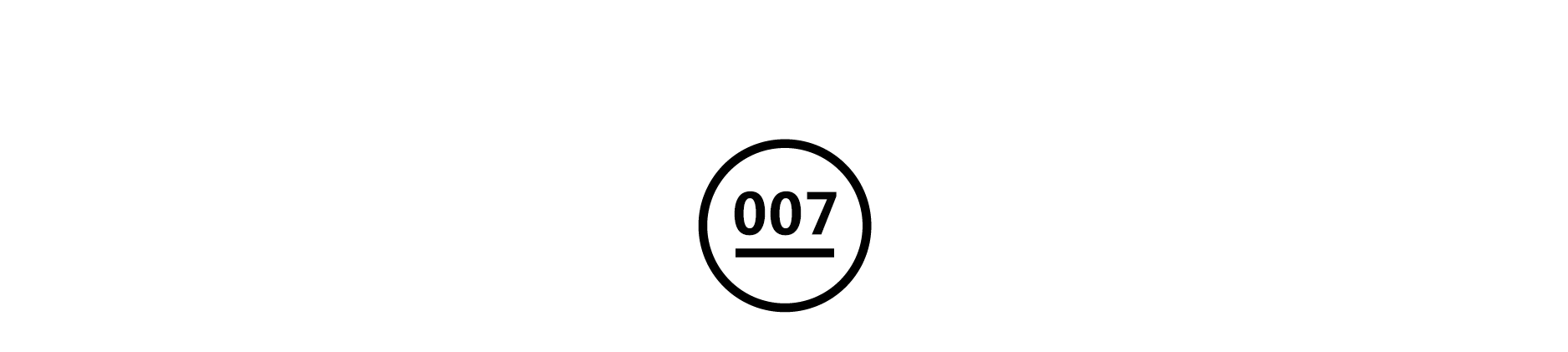 休整了一段时间,漫漫去了高校管院,做EMBA方面的行政工作。可是,上了半年班,漫漫想不起来这半年自己做了什么事。更别提有什么值得说叨的骄傲了。在她看来,人生如果活得像没有活过一样,经不起回望,就有些恐怖了。过完第一个暑假即将复工的时候,漫漫脑子里辞职的想法像脑梗一样难以挽回地复发了。
休整了一段时间,漫漫去了高校管院,做EMBA方面的行政工作。可是,上了半年班,漫漫想不起来这半年自己做了什么事。更别提有什么值得说叨的骄傲了。在她看来,人生如果活得像没有活过一样,经不起回望,就有些恐怖了。过完第一个暑假即将复工的时候,漫漫脑子里辞职的想法像脑梗一样难以挽回地复发了。从那以后,漫漫再去别的地方工作,无论是高校,还是证券公司,时间都不能待满半年。说起这些,漫漫的眼睛往低处看,打了个比方:如果你的第一第二个恋爱对象还比较不错,在主动离开他们之后,你的胆子就大了,你更加不想交付出那份自由。
等“漫漫工作室”挂牌,漫漫已经有一年没有出去工作了。
 漫漫不是相夫教子的传统女人。尽管她看重下一代的教育,家里有很多育儿书。漫漫说,明明是育儿书吧,却可以当作悬疑心理小说看。因为那些人总在教育妈妈要把快乐的心情传递给孩子。不然,如果孩子长大了,成为反社会的罪犯,或者是自残的抑郁症患者,追根溯源,都怪养育他的妈妈当初情绪不好。
漫漫不是相夫教子的传统女人。尽管她看重下一代的教育,家里有很多育儿书。漫漫说,明明是育儿书吧,却可以当作悬疑心理小说看。因为那些人总在教育妈妈要把快乐的心情传递给孩子。不然,如果孩子长大了,成为反社会的罪犯,或者是自残的抑郁症患者,追根溯源,都怪养育他的妈妈当初情绪不好。漫漫似乎很排斥做全职主妇,提这个词都令她反感。她说,全职主妇的生活会养出狭隘贫瘠的头脑,危险还不止变得愚蠢污浊这一种。如果我们几个老姐妹有谁起念做全职主妇,一定会被漫漫骂个狗血淋头。有阵子,我腻烦了东颠西跑的采访工作,打算不干了。我在脑子里盘算着退路和说辞:现在国家取消了计划生育政策,鼓励多胎呢。一个女人在新社会有很多选择,也有长路可走,不是吗?虽然我并不这么想,但我对漫漫这么说了。我说,我要回家专心培养下一代。
对此,漫漫是这么说的:“你为啥不直接回家刨祖坟呢?”
“什么意思啊?”我问漫漫。
漫漫戳着我的脑袋说:“你刨开了,钻进去,找奶奶呀。”
那时候,我奶奶还活得好好的。
这一年,漫漫一个人去了新疆、内蒙、福建和日本。她还想跑更远一点,但是盯着地球仪上的非洲南美洲遐想的时候,漫漫好像瞥见了自己灵魂里懦弱浅薄的那一面。她非常心神不宁。她会关掉智能地球仪上的照明灯,起身走开。
漫漫每次跑出去一两个星期。因为时间再长,她会受到愧疚感的折磨。漫漫说,明明她没做错什么,明明她知道人生该这么过,但是,那种犯罪的、空洞的、自视一事无成一无是处的恐慌感,像一群深夜出没的狼狗,对她穷追猛打。即使睡在美丽梦幻的北海道支笏湖畔,睡在精致高端的温泉酒店,她也会忽然惊醒,漫长的失眠随之而来。
漫漫说,她分明听见有一个声音:“我才三十多岁,难道这辈子就走到头了吗?”
某些时候,她会回答那声音:“这辈子决不能这样算了!”
然而更多的时候,她看见自己陷在某种巨大的惯性的圈套里出不来,似乎走到这个位置就到头了,没有出路了。她还说到了一种孤独无助的情感,因为她甚至找不到一个可以模仿和学习的女性典范。
 春节期间,我养了一盆小小的黄金豹蝴蝶兰,在这个春天里出落得烂漫而耀眼,可惜现在完全盛开了,呈现出即将凋败的势头。近日出差,我决定把它送到漫漫的小花园去。
春节期间,我养了一盆小小的黄金豹蝴蝶兰,在这个春天里出落得烂漫而耀眼,可惜现在完全盛开了,呈现出即将凋败的势头。近日出差,我决定把它送到漫漫的小花园去。我也惦念着漫漫,不知道她拿工作室在做什么。
我摁下密码锁,推门而入,看见漫漫工作室的装修还没弄完。看来,另辟蹊径,重建一份生活,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事。室内比上次见到时凌乱多了。我扫视着墙壁找开关,把灯打开了。漫漫穿着袜子,踩在一块什么垫子上面,脑袋伸进桌子下面正忙什么。起身往回缩时,漫漫一不留神,头磕到了桌子的边角。桌子上的玻璃杯里剩着半杯水,一下子洒出来,流得到处都是。漫漫的右边肩膀也被打湿了。她用英文骂了一句脏话。
“这就算咱们打完招呼了。”我笑道。
“随便坐。”漫漫说。她搬过我端着的那盆蝴蝶兰,又蹲到桌子下面,把花盆放进了一个黑咕隆咚的地方。
 我问她在干什么。漫漫说,她得拿些重物,压平脚下这块软墙纸的四只角,不然这玩意总是把自个儿卷起来。我这才看清地板上有一块瑜伽垫子那么大的,颜色较深的软墙纸。漫漫折起一角给我看里层,这是非洲乌檀木的木屑拼接成的。她将拿它做一面照片墙,每只图钉压进去,不担心损伤房屋的墙壁。漫漫那得来全不费力的语气,恍然带我来到了一个日常却异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一种形式与另一种形式的转换如此迅速,丢失了过程,也丢失了精神。尽管这是人人熟悉的日常生活,我却突然感到非常不安。
我问她在干什么。漫漫说,她得拿些重物,压平脚下这块软墙纸的四只角,不然这玩意总是把自个儿卷起来。我这才看清地板上有一块瑜伽垫子那么大的,颜色较深的软墙纸。漫漫折起一角给我看里层,这是非洲乌檀木的木屑拼接成的。她将拿它做一面照片墙,每只图钉压进去,不担心损伤房屋的墙壁。漫漫那得来全不费力的语气,恍然带我来到了一个日常却异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一种形式与另一种形式的转换如此迅速,丢失了过程,也丢失了精神。尽管这是人人熟悉的日常生活,我却突然感到非常不安。我很怕漫漫重新开始的地方,又变回了一个重复的守旧的昨日世界。
 漫漫问我要不要喝点什么,我说,出去吧。她锁门的时候,我突然有点不放心那盆蝴蝶兰。如果我让漫漫好好照顾它,漫漫可能说什么呢,“养砸了也没关系,咱们换一盆新的,更漂亮的。”
漫漫问我要不要喝点什么,我说,出去吧。她锁门的时候,我突然有点不放心那盆蝴蝶兰。如果我让漫漫好好照顾它,漫漫可能说什么呢,“养砸了也没关系,咱们换一盆新的,更漂亮的。”“话虽然难听点,但是你懂我。”漫漫听我这么一说,咯咯地笑了笑。
上海春天的街道很舒服,暖风吹得人浑身酥酥麻麻的。甜点的香味和路人的香水充盈在空气中,走到哪儿都一股香甜。我和漫漫挽着胳膊走得挺快,到了三四百米开外的网红街武康路,汇入人群,步子逐渐慢了下来。这一带真让人眼花缭乱。撇开建筑不说,光看人就看不完。
漫漫轻车熟路地带我走进一些店,径直来到她喜欢的物品面前,好像她不只是主顾,而是主人。比方说,我们走进一家波斯地毯商店,漫漫会说,这些非常昂贵的地毯不是产自伊朗,而是产自河南南召县。她语速飞快地说了一段话,“人生就像波斯地毯上的图案”,怎样怎样。我听着有点耳熟。漫漫指着橱窗那边说:“去瞅瞅,毛姆给他们免费写文案了。”一段引自《人性的枷锁》里的话,印在自家橱窗上,既不提作者,也不提出处。
漫漫说:“仔细看看,这里到处都是聪明优雅的强盗。”
不知为什么,漫漫似乎格外喜爱买毯子。她摸了摸五彩缤纷的手感粗糙的羊毛地毯,又摸了摸莫兰迪纯色的质地柔软的羊绒盖毯,向店员问产地,问工艺,问价格。我看见她像我们的母亲在镇上的服装批发市场一样,比对磨蹭很久。
从波斯地毯商店出来,我忍不住问漫漫,她是不是能从一块毯子那里,收获真正的快乐。
“是的,毫无疑问。”漫漫说。
“可是,它们本质上只是一块毯子呀。”
漫漫狡黠地一笑,说:“没错。但是毯子像人一样,论本质也是有区别的。你只要摸一摸三百块的毯子和三万块的毯子,自然就明白了。”
我容易被漫漫说话时确信又轻盈的语气逗笑。
为了加强她的观点,漫漫举了个例子说:“有一次,我去朋友家玩,在沙发上午睡,抱着她那条三万块的爱马仕小毯子,好舒服好舒服呀。我好像拥抱到了……幸福的本质。”她微微偏斜着脑袋,微笑着闭上眼睛,张开双臂抱住了自己,好像那条毯子从她的脑子里来到了她的怀里。
我们身后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停下她推着的轮椅,谨慎地踩了一下刹车。轮椅上坐着一个瘦得不成人形的偏瘫老人。他像一把行将报废的折叠椅,非常僵硬地折叠在轮椅之上。说不清那是她的雇主,还是她的丈夫。她弯下腰,熟练地把手臂伸进垃圾桶里,翻拣出漫漫刚扔掉的那只空瓶子,塞进挂在轮椅推手上的一只鼓鼓囊囊的黑色编织袋里。她推着病人继续往前走时,没有忘记拉紧编织袋的口子。
漫漫应该没有看见这一切。
十字路口,我们混在人群里等红绿灯的时候,漫漫示意我注意一下轮椅上的老人。绿灯亮了。我们下一站要去马路对面一家运动品牌商店。漫漫翻看了小红书,想买它家的一件绿白相间小棋盘格的文胸。她心情雀跃,拉着我脚步飞快。在斑马线的边缘,在缓慢行走的人群边缘,我们几乎跑了起来。漫漫贴上我的耳朵,喘着热气压低声音对我说:“及时行乐呀,亲爱的!再过几十年,我们也成那样啦。”
(本文配图除特别标注外,均来自《我的天才女友 第二季》剧照,实习编辑吴争对文本亦有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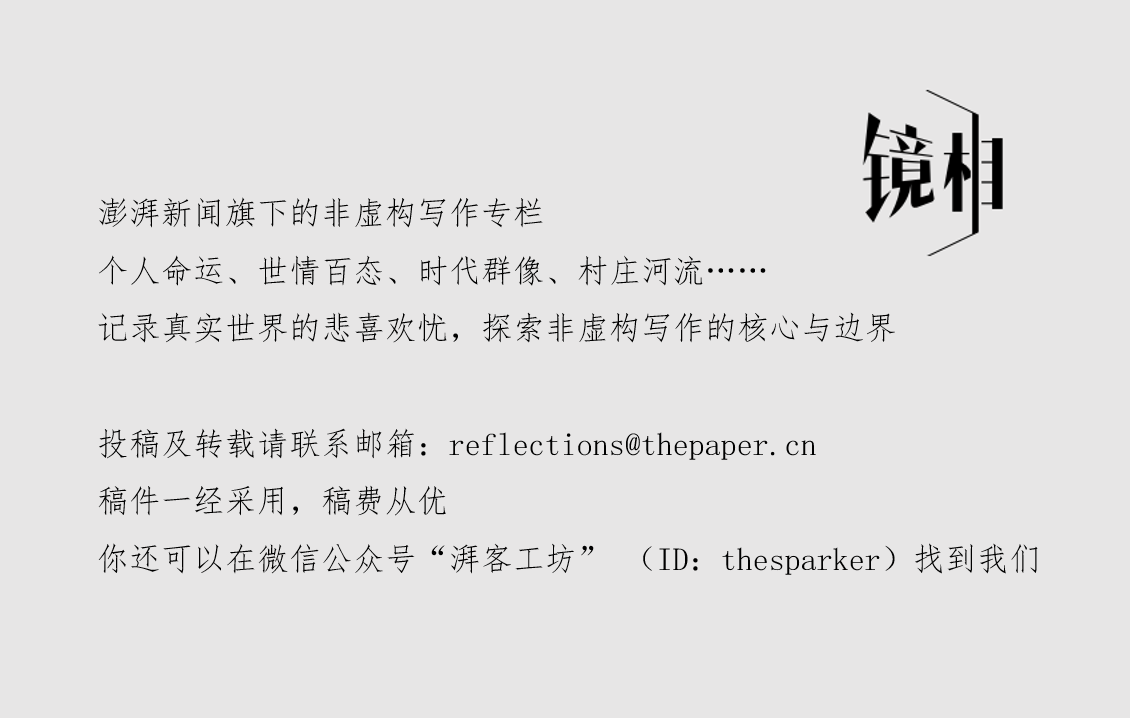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6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