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七岁就开始写作,已经写了将近70年
欢迎加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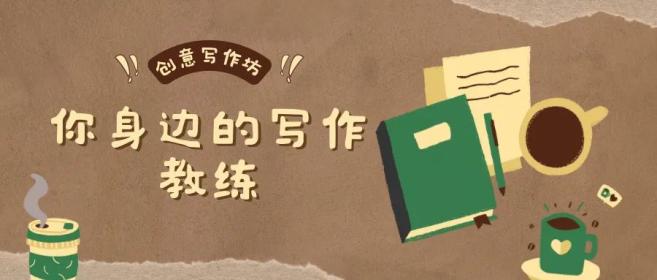
本文节选自
《文学是诗意的历险:许钧与勒克莱齐奥对话录》
勒克莱齐奥等 著
译林出版社
编者的话
2015年12月11日下午15时至17时,在南京大学鼓楼校区院士楼,让——马利·古斯塔夫·勒克莱齐奥先生在他的居所接受了好友兼其作品中译者,南京大学许钧教授的访谈。访谈法文稿由南京大学法语系研究生,勒克莱齐奥指导的博士生施雪莹根据录音加以整理并译成中文。
Q
许钧:
勒克莱齐奥先生,你1940年出生,七岁就开始写作,已经写了将近70年。对你而言,这真算得上一条漫长的追寻之路。一路走来,你进行了各种尝试,小说、随笔、诗歌、翻译、儿童文学几乎都试过了。你还写过戏剧,甚至还写了一部侦探小说。我的第一个问题便与这场追寻之旅有关:追寻的是什么?是因为写作是你唯一的存在理由,还是你确实在寻找什么东西?
A
勒克莱齐奥:
是的,我想说两者互相影响,兼而有之。写作的理由也滋养了写作的愿望。换言之,我写作是因为我热爱写作。我之所以写作,一是为了交流,二是因为写作能让问题暴露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锻炼。写作是一场冒险。那么追寻的是什么呢?我会说追寻的是未知,因为无法确定目标。我不知道这场旅途的终点在哪里,我想它大概会与我生命的终点重合。也许前者的终点会更早来临,但我希望两者能够重合。写作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附加的活动,它对我自身的存在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我通过写作去生活,又通过生活去写作,生活与写作就这样融合在了一起。而当我说不能确定目标而无法指明旅途的终点时,我想说的是,写作在我眼中并不像侦探小说那么简单。
侦探小说中,我们可以查出凶手,或者给出一个让故事变得合理的理由。然而写作的逻辑却是一点一点构建出来的,我只有在写作过程中才能逐渐了解其中的环节,却不知道最终会通向哪里。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会从“认识”走向“认可”,也许还会走向“认同”,认清构成我的以及构成世界的一切。不仅仅探讨我自身是如何构成的,还要探讨世界是如何构成的,我又是如何认识世界的。
每当这时,写作便像一道清流,让世界的粒子、世界的碎片都流动起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文学不是现实主义的。我不信什么现实主义。我觉得文学表现出来的是截然不同的东西。那是另一个世界,并不比这个世界更好,也不具有魔力,但它在虚构中真实存在,一如现实在现实世界中真实存在一样。
Q
许钧:
的确,一场近70年,对认识、认可尤其是未知的追寻,我觉得这三件事在人生中都非常重要。从已知到未知,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前进。人总想更多地认识自我、认识周遭的世界、认识他人,因此这种探索永远不会止息。而且我觉得,人与世界、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需要这种不断的探寻。现在让我们回到你的作品上来。我读过你很多作品——你已经出版了各类作品四十余部。你的第一部作品《诉讼笔录》出版于1963年。没有人知道书中的主人公从哪儿来。他可能是从哪个疯人院或兵营里逃出来的。我们也可以说,他想逃避兵营或疯人院。前者代表战争,而后者则指向疯癫。那么对你来说,写这本“逃”之书的主要动机是什么?
A
勒克莱齐奥:
这本书诞生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我是在1961年至1962年写这部作品的,书是1963年出版的,不过1962年就已经完成写作和编辑工作了,主要是在1961年写的。从我开始写到编辑给我回信表示这本书很有趣并且会出版它之间,隔了很长一段沉寂的时间。1961年正好是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我是在那时构思并写下这本书的。书中还有关于阿尔及利亚军统帅布迈丁进入提济乌祖时受到人群夹道欢迎的剪报。我把整则报道都放了进去,好让故事更好地融入时代。
那么,为什么提到疯人院和军队呢?因为当时我可能会被征召入伍。那时我还没服兵役,正在为成为士官做军事准备。有一年的时间我都在训练,使用一把不怎么样的步枪,还学了些排兵布阵的理论等。我准备好了要上战场。与此同时,我有些同学——全部是男同学,因为女孩不用打仗——为了不去打仗,就把自己弄进军队的心理诊所去。其中有个人吃了肥皂,装出口吐白沫的样子,让别人以为他得了癫痫。另一个假装自己疯了,其他人也都做出类似的举动。有些人给自己注射咖啡因,好让心跳过速。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复员。
不过我完全不想这样做,要么打仗,要么逃跑,但绝不进精神病院。所以军营和疯人院其实是一回事。这就是当时的年轻人被召集的地方,每个青年都得做出自己的选择,而我选择了军营。幸运的是,我获得了延期的机会。因为到了1962年,戴高乐的谈判结束了,谈判经历的时间很长……谈判进行了很多场,耽搁了很长时间,耗去了许多生命,因为谈判过程中,战争仍在继续。阿尔及利亚要求对撒哈拉行使主权,但戴高乐将军计划将撒哈拉用作核武器试验场,所以他肯定希望留下撒哈拉来制造核武器。最后,1962年,历经在埃维昂的激烈协谈后,终于结束了战争……这部小说就是在那个时候写的,其中的内容就可以得到解释……
Q
许钧:
所以,这部小说的创作确实与当时的历史环境紧密相连,也是对你自己生存状况的一种表达。
A
勒克莱齐奥:
是的,我和许多我们这代人一样,不是阿尔贝·加缪的孩子,而是他的弟弟,加缪就像我们的大哥。当时,加缪的言论令我们有些震惊,因为他没有表明立场。而我们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
我有个同学,当时是“行李搬运工”组织的一员。那时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资金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活动。而我那个同学,说来也挺奇怪,还是宪兵的儿子,他把钱藏在行李里面偷运过来,后来被发现了,差点判了死刑。最后他能侥幸死里逃生,仅仅因为他才18岁,人们觉得他太年轻了。不过,他还是被送到阿尔及利亚。
因此,那个时期的形势还是很严峻的。而我写这个故事时采取一种略带讽刺的方式,与它拉开一点儿距离。这或许也和我当时的情况有关,那时我在尼斯,离边境不太远,大家都清楚自己能不费什么力气就跑到国境线另一边去。战争对我们没有威胁。
比方说,我们曾成群结队去看意大利电影《阿尔及尔之战》,我记得是庞泰科沃拍的,讲述法军在阿尔及利亚的暴行。片子在法国被禁,所以我们是去边境那边的意大利城市文蒂米列看的。我们当时算是相当激进的。小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的,但我还是坚持采取一种反讽的态度拉开距离,这或许是为了减弱故事的戏剧性,抑或是为了表现那段时期的荒诞。我们无法像加缪那样严肃。
Q
许钧:
所以,这部小说是你对自己当时的真实处境的表达。但如你所言,你采用的是一种颇为奇趣的风格。即便情境本身是真实的,你的表达仍然让我们联想到新小说。你处理小说的方式几乎与传统小说截然相反。我们可以从作品中读出你刚才提到的种种特色:新闻简报、拼接,等等。那么当时你与新小说作家有来往吗?或者你那时是否读过新小说作品?
A
勒克莱齐奥:
我记得那时应该已经读过罗布——格里耶的《橡皮》,可能还有米歇尔·布托的《变》。另外还有个作家,现在已经被人遗忘了。他叫弗朗茨——安德烈·布尔盖,写过一部深受新小说启发的作品。所以我觉得自己尽管没有刻意摹仿新小说,但依然受到影响。因为越是刻意追求,反而越得不到。其实我原本是想写出与新小说在标准、原则以及风格上完全不同的东西。
顺便说一下,小说出版时,编辑从后来附加的前言中删去了一段话,我在那段话中写道:“请注意,这不是一部新小说。”不过那也不算前言,那是我附在手稿里寄给编辑的一封信。
Q
许钧:
我几乎读了你所有的作品,我发现你早期写的小说总是与逃离、放弃、无力等概念有关,如果这是反抗,那也是一种消极的反抗。比如《诉讼笔录》讲的是逃离与被社会抛弃的命运。1966年的《大洪水》说的是弗朗索瓦·贝松在13天里发生的故事。在第13天,他放弃“金钱、爱情、工作和幸福”,甚至将双眼“交由烈日灼烧”。在1969年的《逃之书》中,奥冈周游四方,却不属于任何一处,因为他没有家。《发热》则讲的是感官问题。据说我们的皮肤、眼睛、耳朵、鼻子和舌头每天都会积攒上百万种感觉,我们是真正的火山。
换句话说,面对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我们正经历着一场感官爆发。《战争》也一样:战火遍地,没人能够全身而退。我们创造的一切都与我们作对。在这场战争面前,我们无能为力。我们被自己的手扼住咽喉。总之,我觉得所有这些小说都围绕你自身的经历,围绕你的所见与你的生活。你能否谈谈你的小说、你对社会的看法、你的自身经历以及你面对这个给人的发展设下诸多障碍的世界所产生的感悟之间的联系?
A
勒克莱齐奥:
实际上,我早期写作的动机正是反抗。那是种属于年轻人的反抗,当时我很年轻,写下你提到的大部分作品时我还不到30岁。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也许今天依然如此,困难在于如何融入社会并接受社会的种种缺陷。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在于它被置于全面的干预之下。戴高乐统治下的社会非常死板,完全处于这位法国之父强有力的控制之下,有点类似毛泽东时期的中国。我父亲一直挺欣赏毛泽东,但对戴高乐却多有贬斥之词,说他欺骗法国人民,耍手段利用他们,玩弄了他们的感情,诸如此类。这个过于僵化、刻板的社会彻底地违背了年轻人渴望自由的愿望。
年轻一代还有抗议的需要,因为社会过于刻板、严苛,而年轻人需要自我表达。总之,戴高乐之所以倒台就是因为年轻一代的怒火在1968年5月爆发。这充分说明当时存在一股反抗力量,而这股反抗力量在对待戴高乐时常常有失公允。无论如何,戴高乐总统是位伟人。但这股力量需要表达却又无处宣泄,才催生出那个时期的标语、口号。这些口号在今天看来都十分幼稚,诸如“铺路石下是海滩”“禁止说禁止”等。所有这些从根本上说都很天真,不过却体现出反抗的需求以及年轻人确立自我存在感的渴望。
我觉得自己也是这场剧变的一部分。我没有参加红五月运动,那时我在墨西哥,但我记得自己参加过几场共产主义会议,我们高举拳头上街游行。还有人拍到过我在街头拳头高举的照片。当时我们还曾组织小团体,共同揭发出版业,认为书籍出版后应该分发到大街上,而不是出售。所有这些现在看起来都很天真。不过我想这是当时青年的集体力量,他们需要空气,需要自由。这一切似乎都已经很久远了,现在看来几乎有些古老。
Q
许钧:所以你的小说就表达了这些……
A
勒克莱齐奥:
是的,只是我认为自己的小说里还有别的东西。怎么说呢?当时还没有“生态”这种说法,可能连这个词都不存在。大多数年轻人的反抗都是出于政治原因,而我呢,更多是出于一种焦虑感:城市、封闭的街道、被摄像机监视的感觉,一切都过于有序、过于封闭、过于紧锁,这些都让我焦虑。而这种感觉在我与城市的切实接触中又进一步加强。听上去可能有些不可思议,但我在尼斯时法国才开始建造第一家超市。之前法国没有超市,也没有高速公路。
当时法国的生活和让——雅克·卢梭的时代没什么两样。但我眼看第一家超市建造起来,凭我的想象力,很快抓住了问题。我把这叫作“超级警察”,因为在我看来,这将是一系列连锁反应的开端,商业经济将就此压倒个人。
当时我刚读了古斯塔夫·勒庞的理论,他进行过有关下意识的研究,即说眼睛看到的东西,大脑就算没有记下来,它也知道。例如,在一段影片中,一秒播放的20帧画面里有一张展示了饮料。那么一段时间后,人们便会起来喝水。因为这张图片已经被捕捉并进入他们的意识中了。
今天看来,这些都有些天真,但在当时这是相当严肃的事,连天主教的领袖教皇都公开发表过声明谴责下意识。现在没人再提这些了,它们都已经被遗忘了。总之,反抗就产生在那样一个时期,人们反抗来自机械化世界的压迫,世界已经过于……
许钧:过于物质。
原标题:《七岁就开始写作,已经写了将近70年》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