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新书速递|两代人,一间手术室,他们用毕生弥补裂伤.......
《双生石》是一部关于双生兄弟传奇的成长故事,书写了家族命运和行医人生中的悲欢离合。出生时,他们是连体婴。相连着的除了脐带,还有充满波折的命运。成年后,他们是杰出的医生,却要不断修补各自生命里的破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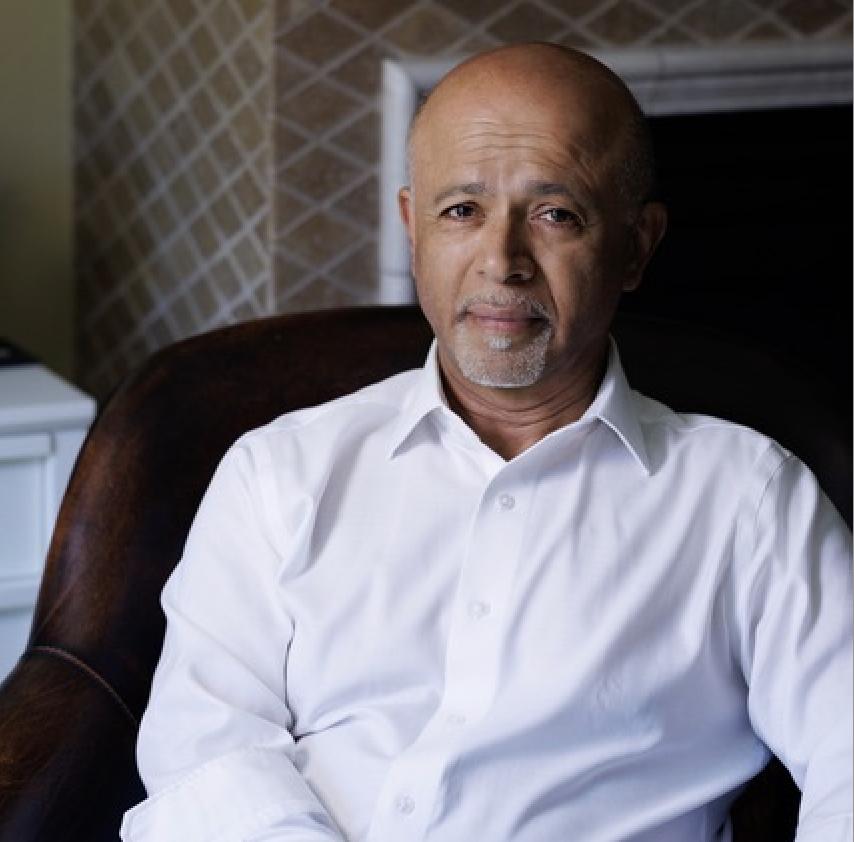
《双生石》作者亚伯拉罕・维基斯,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医学理论与实践系教授。这部作品荣获亚马逊年度最佳图书,入围都柏林国际文学奖,并获得了奥巴马夏季书单的推荐。
“维基斯有一种罕见的天赋,随着故事的发展,他以不同的方式展示笔下的角色,从悲剧到喜剧再到情节剧,结局一部分像是狄更斯,一部分像是《实习医生格蕾》。这本小说是一部家族传奇,但更多的像是给医学界的一首颂诗。”
——《娱乐周刊》
《双生石》(节选)
[美]亚伯拉罕・维基斯 著
吕玉婵 译
- 序幕・到来 -
在母亲子宫晦蒙处度过八个月之后,弟弟湿婆与我,在公元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日的傍晚,来到了人世间。于海拔两千四百米的高度,我们吸入第一口空气,吸进了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稀薄空气。
我们出世的奇迹发生在失迷医院的三号开刀房,那正是母亲玛莉·约瑟夫·普雷斯修女多数工作时间的地点,也是她最能发挥才能的地方。
我们的母亲是修女,隶属马德拉斯市主教管区的圣衣会。在那个九月的上午,当她不期然开始阵痛,埃塞俄比亚的豪雨停歇,失迷医院铁皮浪板屋顶的喋喋雨打戛然而止,好像饶舌的人话才讲到一半便打住。在阒静无声中,十字架雏菊在一夜间怒放,将亚的斯亚贝巴的山坡染为金黄。在失迷医院四周的草地,莎草克服了烂泥,如灿然的毯,一路摊展到医院的水泥门槛前,带来了比打板球、槌球或羽毛球更实在之活动的希望。
失迷医院位于翠绿的山丘上,单层与双层的石灰建筑群集错落,仿佛在造就恩托托山脉的地质活动闷响中,与山峦一同自地表隆起。槽型花圃由屋顶檐槽满溢的流水浇灌,如护城河环绕低矮房舍。赫斯特院长的蔷薇攀上了墙,绯红的花沿着每道窗框,蔓生延及至屋顶。由于土壤肥沃,院长(也就是医院睿智又明理的领袖)警告我们别光着脚踩上去,免得新的脚趾头会冒出来。
五条小径夹在肩头高的灌木丛中间,如轮辐自医院主建筑散开,通往五间几乎被杂木、树篱、野生桉树与松树掩藏的平房。这是院长的意图,她希望失迷医院像座植物园,或伦敦肯辛顿公园的一角(来非洲之前,身为年轻修女的她常在那里散步),或者人类堕落前的伊甸园。
失迷医院(Missing)其实是布道传教的使命医院(Mission Hospital),埃塞俄比亚人的舌头念这几个字会带嘶声,因此听起来像是“失迷”。卫生署一位才高中毕业的职员在执照上打了“失迷医院”,对他来说,这才是发音正确的拼法。由于一位《埃塞俄比亚先锋报》记者,拼错的用语继续沿用下去。当赫斯特院长跑去找卫生署职员修正时,他拿出原本的打字文件说:“女士,您自己看看吧!Quod erat demon strandum(拉丁语:证明完毕),是失迷医院没错。”那口气仿佛他证实了毕达哥拉斯的定理,太阳就是位居太阳系中心,地球正是球体,还有,证明了失迷医院在想象中的地球精准位置。于是乎,它叫失迷医院。
・
在酿成剧变的临盆阵痛过程中,玛莉·普雷斯修女没有迸出哭声,也不曾发出呻吟。三号开刀房隔壁的旋转门后方,有苏黎世路德教会捐赠的特大号压力锅,滚烫的蒸汽消毒了即将用在母亲身上的手术器械与毛巾,同时低声怒吼为她悲叹流泪,毕竟母亲的庇护所就在压力锅间的一角。在我们狂暴抵达之前,母亲在失迷医院待了七年,并且在不锈钢巨兽旁为自己布置了避难处,靠墙的连桌椅是从停办的教会学校抢救来的,上面有许多学生失意时的凿痕。白色开襟羊毛衫搭在椅背上,有人告诉我,她在手术与手术之间常把毛衣披在肩上。
在课桌上方的灰泥上,母亲用图钉钉了张日历图片,是贝里尼著名的雕塑:亚维拉的圣泰瑞莎。圣泰瑞莎宛如昏厥,体态软绵无力,嘴唇因销魂而张启,眼神失焦,眼皮微掩。在左右两侧,各有一群合唱团员从祈祷台俯瞰窥探。一名男童天使隐约带笑,耸立于虔诚而纵欲的修女旁,健壮的身躯与年少的脸庞相违。他以左手手指撩起遮掩她胸脯的衣缘,右手拎着箭,优雅得犹如小提琴手提着弓。

亚维拉的圣泰瑞莎雕塑|图片来源自网络
为什么放这张图片?妈妈,为什么是圣泰瑞莎呢?
四岁的我偷偷躲入无窗的房内研究图像。只凭胆量,是无法让我通过那扇重门的,只是我觉得她在里面,一心一意地想认识身为母亲的那位修女,于是产生了力气。我坐在压力锅旁,它像清醒的龙,低沉咕哝,嘶嘶作声,仿佛我咚咚的心跳唤醒了这只野兽。我坐在母亲的桌前,心情一点一滴地平静下来,感觉好像与她在沟通交流。后来我才知道,没人敢把开襟羊毛衫自椅子披挂处拿走,它是圣物。不过,对一名四岁孩童而言,样样事物都既神圣又普通。衣服有抗菌肥皂的气味,我把它拉到肩头,还用指甲绕着干涸的墨水瓶,追寻她手指曾经走过的路。如同她坐在无窗房间中一定会做的事情,我仰头凝望日历图片,那图像怔住了我。几年后,我得知圣泰瑞莎重复看见天使的幻觉被称为“穿心神迹”,字典说是灵魂因上帝之爱而“激烈燃烧”,心脏遭神的爱“穿刺”;她这份信仰的隐喻同样也被当作医学的暗喻。在四岁的年纪,我不需要“穿心神迹”这样的字眼,就可感受到图像所引发的崇敬。我没有母亲的照片可寻,情不自禁地想象着图片中的女子就是她;她受了胁迫,挥舞尖矛的男童天使即将让她心神荡漾。我总是问:“妈妈,你什么时候会来呢?”冰冷砖瓦传回我微弱声音的回声。你什么时候会来呢?
我低声回答:“上帝,让她来吧!”那句话是我唯一拥有的凭借。当我第一次闲荡到这里时,戈什医生前来找我,越过我的肩膀注视着圣泰瑞莎的图片,说出了这句断言;他用强壮的臂膀抬起我,用他那与压力锅势均力敌的嗓音说:“来了,上帝让她来了!”
・
自我呱呱落地之后,四十六又四年过去了,奇迹似的,我有机会回到那间房。我发现自己体型庞大,坐不进那张椅,开襟羊毛衫挂在肩头会像祭司的花边白麻围肩。然而,椅子、开襟羊毛衫、穿心神迹的日历图片都还存在,我——马里恩·斯通已然不同了,而其他的改变并不多。身在依然如旧的房内,时光与记忆快速往回翻动。贝里尼的圣泰瑞莎雕塑图片没有褪色,母亲以图钉固定的纸片现在装了框,存放在玻璃底下。这张图片好像提出了请求,我不得不理出生命事件的顺序,说它是从这里开始的;又因为它从这里开始,所以有了那样的一段故事,而结局就这么又衔接到了开端。于是,我在这里。
・
我们擅自来到这人世,别忘了,饥饿、苦难、早夭是普遍的命运;侥幸的话,或许能超脱命运,找到目的。我长大了,我找到了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要成为医生,与其说是要拯救世人,我的意图其实是要自我治疗。没有几个医生会这样承认,年轻一辈绝对是不会的,不过进入了这一行,我们潜意识中一定相信照料他人能治疗自己的创伤。的确可以,不过也能加深伤口。
院长是我童年与青春期中坚定不变的身影,我为了她,选择了外科专业。在我前半生最灰暗的日子中,我去找她寻求忠告。她问:“如果你尽力而为,什么是你所能做到最困难的事情?”
我局促不安。院长轻而易举便探测出追寻抱负和苟且偷安之间的距离。“为什么我非要做最困难的事情?”
“因为你是上帝的乐器,马里恩,不要让乐器留在盒子里,孩子,演奏它!好好利用乐器的每一部分,你能演奏《荣耀颂》的话,何必安于童谣《三盲鼠》呢?”
太不公平了,院长竟然提起那首昂扬的圣歌,每每听到这首曲子,我便觉得自己愣愣呆呆,与所有凡人一同站着仰望天空。我不成熟的个性,她都明白。“可是,院长,我无法幻想我能演奏巴哈的《荣耀颂》……”我压着嗓子说。我从没弹奏过弦乐器或管乐器,我看不懂乐谱。
“马里恩,我不是这个意思。”她说。温柔的凝视迎来,一双饱经风霜的粗糙手心摩挲着我的脸颊。“不是巴哈的《荣耀颂》,而是你的,存在你心里的《荣耀颂》!不去找出它,忽视上帝赋予你的可能能力,那是至深的罪恶啊!”
从性情来说,我更适合走认知相关学门,从事深入探究的领域,例如内科或精神病学。一想到手术房的景象,我便汗如雨下,想到手持手术刀,肚子就揪成一团(至今还是如此)—手术是我能想象得到最困难的事情。
于是乎,我成了外科医生。
三十年后,我不是以速度、胆大或手艺才能而出名。说我从容、说我埋头苦干、说我采用适合病人与特定情况的做法与技术,那么,我会把这些话当成重要的赞美。同事自己必须挨刀时会来找我,这一点让我信心大增,他们知道,无论是术前、术中或术后,马里恩·斯通都同样地投入时间与关注;他们知道,我不喜欢“有疑问就切除”或“能动刀就不等”之类的外科箴言,这些言论只会确实地揭露我们领域中最肤浅的人才。我的父亲拥有我最敬佩的外科医术,他说:“手术结果最为成功的,是你决定不动刀的那一项手术。”我知道何时不该开刀、何时能力不及、何时该寻求拥有父亲水平能力的外科医生协助—那样的天赋、那样的“才华”,都是自己始料未及的。
有一回病人病情危急,我求父亲动刀。他默默地站在床边,测好心跳数后,手指还在病人的脉搏上流连不去,久久不肯放开,好像需要摸着肌肤,感受动脉血管纤弱的讯号,才能归纳出结论。从他紧绷的表情中,我注意到百分百的专注,我想见他脑中的齿轮转动,幻想看到他眼中泪光闪烁。他小心翼翼地权衡不同选择的利弊,最后摇了摇头,转身走开。
我跟上前去。“斯通医生。”我用他的头衔喊他,纵然内心渴望呼喊一声“爸爸”。我说:“手术是他唯一的机会。”我心底明白,机会微乎其微,麻醉药才喷一下,或许就扼杀了他的性命。父亲把手放在我的肩头,口吻温和,就像对资浅同事而非儿子说话。“马里恩,不要忘记第十一戒,”他说,“不要在病患大限之日动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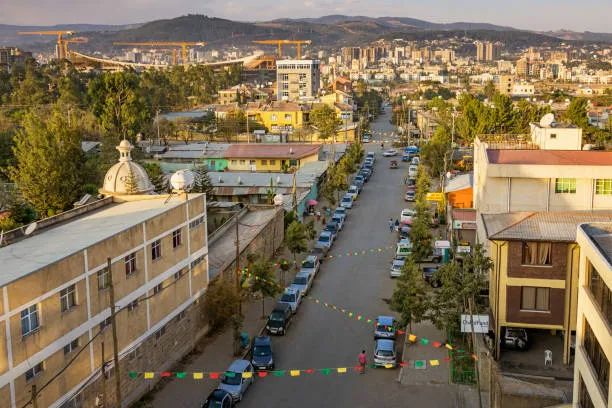
亚的斯亚贝巴|图片来源自网络
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满月时分,刀光闪耀,石头与子弹纷飞,我感觉好像站在屠宰场,而不是三号开刀房,皮肤沾了一点点的碎骨与生人的血。在这样的时分,我想起他的话。我没有忘记,可是开刀之前不见得都知道答案,开刀当下只能专注于开刀一事上。事后,在我们称之为“死亡及并发症研讨会”的闹剧上,那些妙语如珠或成为媒体名嘴的会议召集人,随随便便就能大放马后炮,宣告你的决定是对或错。生命同样也是如此,你往前走,回头才了解它,唯有驻足回首才发现卡在你车轮下的尸首。
而今,我五十岁了,见到开膛剖腹,依然一股敬意油然而生。人类彼此残害、亵渎人体的能力令我汗颜,可是这样的能力让我明白玄奥的和谐,心脏从肺脏后方窥探而出,肝脏与脾脏在横膈膜的穹窿底下彼此协商—这些让我惊讶得无言以对。我的手指“在肠道滑走”,寻找刀身或子弹造成的洞孔,闪烁微光的肠道一圈又一圈,那近乎六十厘米的长度紧密收拢在这般窄隘的空间内。在非洲的夜晚,如此这般从我指缝中滑过的肠子,至今累积的长度可能得以延展至好望角,而我还看不到这条长蛇的头在哪里。不过,我能查看藏于肌肤肋骨肌肉底下的平凡奇迹,目睹身体对主人所隐瞒的景象,人间岂有比此更为崇高的殊荣?
在这样的时刻,我不忘感谢我的孪生弟弟湿婆—湿婆·普雷斯·斯通医生。我寻寻觅觅,在两间开刀房之间的玻璃隔板上寻找他的倒影,然后点头致上谢意,因为是他让我成为今日的我,一名外科医生。
对湿婆而言,生命终究是在修补破洞。湿婆讲话不用隐喻,他要说的,就是“修补破洞”这四个字,不过,这个隐喻用在我们这一行恰如其分。然而,还有一种破洞,就是让家庭分裂的伤口。这种伤口,有在出生之际产生的,也有日后才出现的。我们都在弥补裂伤,这是毕生的任务,而许多的未竟,则留给下一代。

亚的斯亚贝巴|图片来源自网络
生于非洲,离乡背井来到美国生活,最后又重返非洲,我是“地理即命运”的实证。命运将我带回到出生的地点,不偏不倚,就在我出生的那一间手术房。我戴上手套的双手在三号开刀房的手术台上方活动,母亲与父亲的双手,也曾在这同一个空间。
有些夜晚,蟋蟀唧唧地叫,成千上万只的叫声压过了山腰上土狼的咳声和哼鸣。但霎时,天地万籁俱寂,犹似点名时间结束,时候到了,蟋蟀在阒黑中找到配偶,撤退离开。接踵而来的寂静真空中,我听见星星尖锐的嗡鸣,欣喜若狂,为自己在银河中低渺的地位感到欣慰。就是这样的时刻,我觉得自己承受了湿婆的恩惠。
身为孪生兄弟,我们同睡一张床直到十几岁,头颅相倚,两腿躯干往不同方向偏转。长大后,我们不再那样亲密,然而我依然渴望,渴望亲近他的头。当我醒来,收到又一个日出作为礼物,头一个念头是想唤醒他,告诉他:多亏有你,我才得以见到晨光。
而我亏欠湿婆最深的,是把故事说出来。这是我母亲玛莉·普雷斯修女未曾揭露的故事,是我胆大的父亲托马斯·斯通所逃避的故事,是我必须一片一片拼凑而得的故事。唯有讲述,才能愈合弟弟与我之间的裂痕。的确,对于外科手艺,我有无穷的信心,但没有哪个外科医生能修复两兄弟的分歧。精彩的故事于此出现,就从故事起头的地方开始说吧……
「相关图书」
《双生石》
[美]亚伯拉罕·维基斯 著
吕玉婵 译
中信出版·大方 2024年5月
我们的出生是一场灾难,身为修女的母亲难产而死,而医术精湛的父亲抛下我们,音信全失。尽管如此,我们仍旧继承了父亲的平凡与天才、天真与世故、热情与漠然,彼此互补也互斥。出生时被迫分割,年少时形影不离。直到发生了那件事,彷佛一把背叛的利刃,把我、弟弟湿婆和我深爱的珍妮特三人紧密的关系生生割裂。多年后我才明白,如果一味埋藏对父亲的想念和憎恨、对珍妮特未竟的情感,以及我与湿婆遭遇的波折,我将无法好好地踏出下一步。
END
编辑、排版丨雷一琴
原标题:《新书速递|两代人,一间手术室,他们用毕生弥补裂伤.......》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