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林黛玉的大雅与大俗
原创 兰藉文化

作者
何宗焕
在贾府,黛玉有两个知己,一个是宝玉,一个是凤姐。这两个人就像两面镜子,照出了黛玉人格和个性的两重性甚至多重性。
宝玉最懂黛玉。黛玉与生俱来的敏感、高贵、多愁善感和绝世才华,以及与这些品质相伴而生的“小性儿”“行动爱恼人”,贾府中人上上下下都知道,连老婆子、丫头都有体会,每每说起林姑娘,就是“心又细”“又爱刻薄人”“嘴里不肯饶人”。如此众声一词的“知道”和“体会”其实很片面。
只有贾宝玉才是真懂,因为他从心底里带着一份珍惜。大观园里群芳饯花那一回,宝玉因看见许多凤仙、石榴等各色落花,锦重重的落了一地,便想起了黛玉,要把那花兜起来送了过去,于是“登山渡水,过树穿花,一直奔了那日同林黛玉葬桃花的去处来”(二十七回)。他和黛玉一样惜花护花,他也像惜花护花一样珍惜着黛玉。正是贾宝玉这面镜子,让“世外仙姝”林黛玉,更显得纤尘不染。
黛玉又何尝不是最懂宝玉的那个人。宝玉心地澄澈,一片天真烂漫,最不喜与俗人交接,最不喜谈仕途经济,也只有黛玉能理解。因为理解而相知,因为相知而珍惜,这才是心心相印。你能说宝玉不懂宝钗吗?可是越懂越有距离,只因为宝钗并不懂宝玉。就隔那么一点点,如同窗户纸似的薄薄一层,无法捅破——在宝玉这里,他能看破却不能说破,在宝钗那边,却一直没能看破,她永远也不懂宝玉的心——两人咫尺天涯,心灵之间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宝玉是黛玉生命和感情的寄托。在曹雪芹笔下,写到贾宝玉的时候,只要与黛玉有关联,宝玉眼中、心中、口中立马就庄重起来。这是一种有意识的映衬,就是要用贾宝玉这面纯洁的镜子来照亮林黛玉的冰清玉洁。当然宝玉这面镜子也能照出薛宝钗的某些丑陋来,这是另一个话题,且按下不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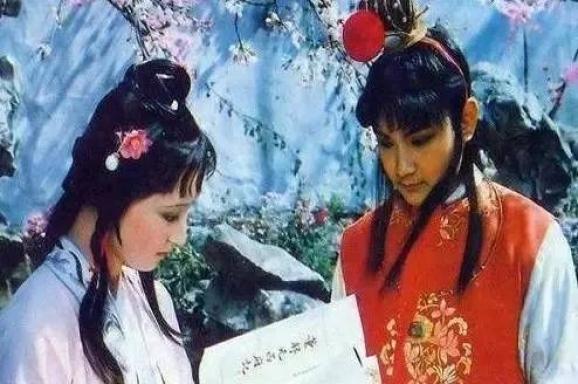
黛玉的雅,是她脱俗离群,冰清玉洁的气质,宝玉一见便说她是“神仙一样的妹妹”;她爱诗、爱花,集聪明、灵秀、高洁于一身;她还爱哭,爱流泪,常常一副泪汪汪的样子;她又多病,常要吃药,很瘦,弱不禁风。这些,都给人以不食人间烟火的印象——不是凡品,超越凡俗,已成为无数读者心中难以撼动的定论。
如果仅有雅,只是雅,或全是雅,林黛玉的形象就扁平化了。黛玉还有她的另一面,也就是——“俗”。
林黛玉的“俗”得用另一面镜子来照,这面镜子就是王熙凤。大观园是个水晶宫,那些“小龙女”一个个雪肌诗肠,是“雅”的精灵,凤姐显然进不了这个阵营,她是“俗”的代表,她以“俗”的眼光看待一切,包括林黛玉。水晶宫如果没有凤姐的保护是不能长久的,也是没有生命力的。
黛玉与凤姐能成为知己,用辩证法的观点来说,就是矛盾的对立和统一,最雅和最俗的人互相吸引,互相欣赏。看黛玉和凤姐斗嘴,每一次都如说相声一般,两人你来我往,金句不断,让人大呼精彩,这样的场面很多。
凤姐对黛玉的另一面了解得最透彻。可以说,凤姐是用自己的“俗”发现了黛玉的“俗”。凤姐最先发现了黛玉治家管家的才干,探春能帮她,但像探春这样的帮手太少,她对平儿说:“林丫头和宝姑娘他两个倒好,偏又都是亲戚,又不好管咱家务事。”(五十五回)宝钗会当家,有她和探春在大观园兴利除弊的作为为证。黛玉会治事理家凤姐是怎么发现的?且不说她弱不禁风的身子,“美人灯儿,风吹吹就坏了”,就她那种清高孤傲的个性,谁能相信她俯得下身段去做管理家政的“俗务”呢?如果你也这样看,那就大错特错了——凤姐独具慧眼,不能不说她有与世俗完全不一般的知人识人之明。

且举两例。
第二十七回,黛玉与宝玉赌气,见宝玉进来也不理他,因自己要出门,且把家里的事交待一遍,便回头对紫鹃说:
“把屋子收拾了,撂下一扇纱屉,看那大燕子回来,把帘子放下来,拿狮子倚住,烧了香,就把炉罩上。”
这几句交待,何其简捷,何其清爽,何其明白。潇湘馆是谁在管理,是谁当家作主,这不清清楚楚吗?你还以为黛玉只会见月伤怀,对花吟诗么?她交待的全是细事琐事,连燕子回巢都记得,可见平时她是多么用心经心,多么细致周详。这样的人怎么不是理家管家的好手呢?怪不得凤姐要高看她一眼。
第六十二回,黛玉对宝玉说:
“咱们家里也太花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
为贾府大家庭操心,算收支账,思前虑后,这见识,岂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管柴米油盐的深闺小姐?相比黛玉深切的忧患意识,宝玉就是只会吃安乐茶饭的贵公子了。你听他怎么回黛玉:
“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
但黛玉的“俗”毕竟不是凤姐的“俗”。凤姐不读书,胸无点墨,没有诗书的熏陶,缺少“雅”的情趣和情怀,故其“俗”在骨,是典型的俗气,其村、野、贫(嘴)和贪、酷(虐)、无赖等种种表现,很多时候让人恨,招人骂。黛玉的“俗”是由她的冰雪聪明所附带的对世俗和世事的洞烛幽微,是胸有大丘壑者的理智和清醒。若没有这种理智和清醒,要么就变成迎春,懦弱且无能,如木头一般;要么就变成妙玉,孤僻且无情,如死灰一般。
黛玉还有很多“俗”的表现,让你见识她的“不一样”。

她很会关心人,细心处、体贴处,无微不至。宝玉在薛姨妈家吃酒,回家时小丫头给他戴斗笠,老是戴不好,便不耐烦。
黛玉站在炕沿上道:“啰唆什么,过来,我瞧瞧罢。”宝玉忙就近前来,黛玉用手整理,轻轻笼住束发冠,将笠沿掖在抹额上,将那一颗核桃大的绛绒簪缨扶起,颤巍巍露于笠外。整理已毕,端相了端相,说道:“好了,披上斗篷罢。”
第八回
这个情景如果用照相机照下来,真是一幅妙不可言的豪女图:黛玉站在炕沿,拉过宝玉的头,理发整冠,完了还要端详一遍。口里说:“啰唆什么,过来,我瞧瞧。”很有震撼力和约束力,宝玉显得非常听话地任由她摆布。那派头,那架势,怎么看都像大姐姐为小弟弟细心打理行头。如此豪爽豪放的镜头,难得一见。
在宝玉面前,她敢撒野,敢骂人。宝玉偷看《西厢记》,不给她看,她便要抢,道:
“你又在我跟前弄鬼。趁早儿给我瞧,好多着呢!”
这话儿说得多带劲,多威风,宝玉只得乖乖交了出来(第二十三回)。宝玉要枕她的枕头,她脱口便骂:
“放屁!”
“放屁”是凤姐的口头禅,粗人粗话,从黛玉口中说出真如石破天惊——婉约派一变而为豪放派。
她体恤下人,解人意,懂人情。大观园里守夜的老婆子们吃酒赌博,是她最早发现的。蘅芜苑的婆子送了燕窝来,黛玉命她外头坐了吃茶。婆子笑道“不吃茶了,我还有事呢”,黛玉一听便明白是什么事。
黛玉笑道:“我也知道你们忙,如今天又凉,夜又长了,越发该会个夜局,痛赌两场了。”
四十五回
夜长天冷,守夜难熬,赌博消遣,吃酒取乐,从情理上说,黛玉是理解的。妙的是她说得那么生动幽默,又入情入理,就像自己身在其中一样。对婆子们的生活观察了解得如此细致,她那颗剔透玲珑的心,怎么那么聪明(精明)呢?无怪乎编书人要说她“心比比干多一窍”。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宝钗平日道貌岸然,正人君子,没想到为头聚赌的却是她蘅芜苑的婆子,潇湘馆可从没这样的人,也没这样的事。
吃酒赌博为害甚大,贾母王夫人等深知其情。黛玉此时看在人家送燕窝的情分上,不便说别的什么,只说“难为你,误了你发财”,还命人给她几百钱,打些酒吃,避避雨气。如此体贴暖心,便是读书人隔着书页也不免心头一热,感动得要掉下泪来。
后来宝玉在怡红院开生日派对,黛玉离桌远远的靠着靠背坐着,向李纨、探春等说道:
“你们日日说人夜聚饮博,今儿我们自己也如此,以后如何说人?”
她担心做主子的带了头,自己先犯了禁违了规,又如何禁得住下人呢?黛玉殷忧不远,后面果然出了大事。

最难得的是,她能迎合大势,在大场合并不特立独行。她的诗率真清纯,风流别致,绝不矫揉造作,从无俗语俗态,是大观园里第一流的诗人。但有两回,她写诗颂圣,出人意外。第一次,元妃归省,命宝玉和众姊妹各题一匾一诗。黛玉自己诗中末句云:“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已微露此意。后又代宝玉作《杏帘在望》:
杏帘招客饮,在望有山庄。
菱荇鹅儿水,桑榆燕子梁。
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
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种忙。
“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种忙”是典型的颂圣诗,且全无隐晦,非常直露。所谓“颂圣”就是歌颂当朝天子,有奉承、阿谀、巴结的意味。黛玉是眼里揉不进砂子的人,其人格个性独立意识很强。她为什么要向娘娘表忠心似的曲意谀词颂圣呢?是不是太俗气了?
还有一回,凹晶馆与湘云月夜联诗,湘云出上句“香新荣玉桂”,黛玉对“色健茂金萱”,湘云当即批评她,“不犯着替他们颂圣”。所谓“替他们颂圣”,就是给贾府讲好话。湘云对贾府有意见,多次尖锐批评,一点也不客气。黛玉这样明显地给他们脸上贴金,湘云看不惯。
黛玉住在贾府,寄人篱下,好在有贾母疼爱,又有宝玉知心知意,还算过得去。“色健”“金萱”都是从贾母立意,但黛玉并不是有意为之,湘云若不说“香新”“玉桂”,她也不会强对“色健”“金萱”。从写诗的角度说,也是为了铺陈得富丽一些。这是无可厚非的。
代宝玉作诗,是从宝玉的立场出发,且又是当着娘娘的面,不可不如此。古人把这种诗叫做“应制诗”,唐代大诗人李白、王维等都写过,李白的《清平调三首》,就是当面奉承唐玄宗的宠妃杨贵妃。这是大场面,须顾大局,容不得随心所欲,任意发挥。黛玉这里的“俗”,正说明她心中有分寸,知道审度大势,这与她所恪守的“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行为宗旨仍然是一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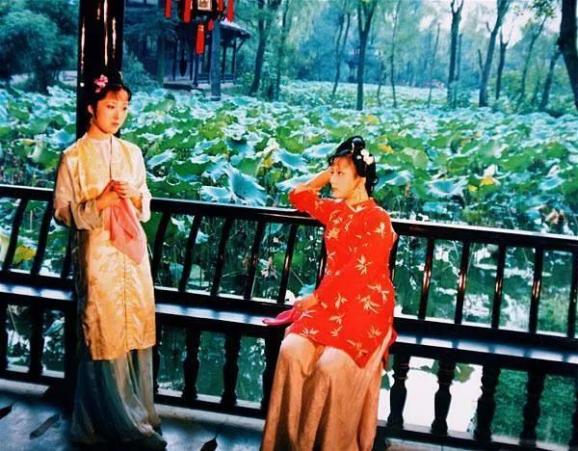
黛玉对俗有理解,有迁就,而不是一味抗拒,借用老子《道德经》“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说法,便是“大雅若俗”——俗得有格局,有特色。总结一下:一是不拘俗礼,偶显豪气;二是眼光高远,时露大气;三是世事洞明,揆情入理;四是审度大势,维护场面。
雅有品,俗有格。雅为其骨,俗为其表,雅俗互为表里。因雅而成俗,俗则有格调,不平庸,不苟且;因俗而成雅,雅则有生气,不矫情,不偏执。在雅中看到烟火色,在俗中看到精气神,则其人格自有风骨,自有奇气,而其面目自有神采,自有趣味。这就是林黛玉,大雅大俗,真率自然。太白诗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斯人之谓也。
2024.05.05
原标题:《林黛玉的大雅与大俗》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