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从徐訏到王安忆、孙甘露:审美化的革命书写潜流
编者按:本文为“启典阅新”2024上海市大学生阅读与写作大赛评论组获奖作品,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原标题为《“我是生成的鬼”——重读徐訏<鬼恋>》,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2023年11月,我与好友去孙科别墅观赏一场由上海现代人剧社改编自小说《鬼恋》的“环境戏剧”——《消失在午夜》。别墅里的氛围神秘、考究,随着剧情的推进,我们一群观众在其中四处流连,时立时坐,听徐訏于87年前写下的奇崛的对话,从三位虽未脱尽学生气但异常投入的青年演员的口中说出,内心不免激动。

《消失在午夜》剧照
《鬼恋》这一文本堪称一个令数代人陶醉与困惑的特殊存在。一方面,它问世不久便成为“现象级文本”,屡次被搬上银幕,魅力延续至今;另一方面,学者与评论家们却一直未能提出非常理想的解读方案,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块不大不小的空白。
本文以小说中“我是生成的鬼”这一表述为标题,大致有两层用意:其一,从前后两个版本的异同入手,来看如今为我们所熟悉的《鬼恋》是如何“生成”的;其二,以《鬼恋》为枢纽,推敲徐訏与鲁迅、郁达夫的隐秘关联,并提示一条从《鬼恋》蜿蜒至王安忆、孙甘露的审美化的革命书写潜流的存在。
两个版本的《鬼恋》精神如一
听起来或许有些意外:《鬼恋》的写作时间与地点,长久以来被专业研究者误会,直到《徐訏〈鬼恋〉写作时间与地点辨正》一文发表,才算完全搞清楚。写作时间,其实非常明确,作为短篇小说的《鬼恋》连载于1937年第一、二期《宇宙风》时,就有明确的落款“一九三六,七,一〇改六,一一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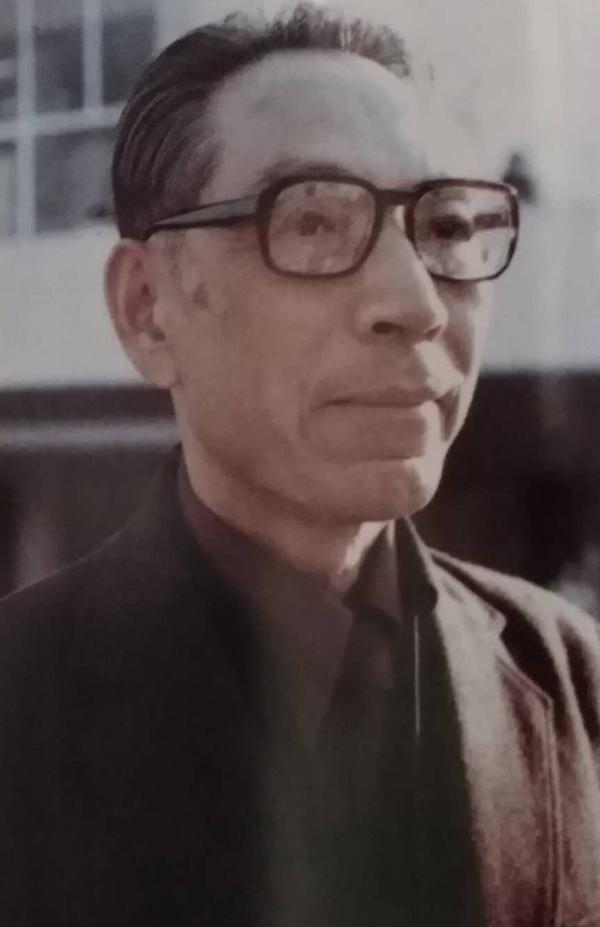
海派文学名家徐訏
难点在于写作地点,因为根据以往材料,徐訏于1936年下半年前往法国。上述文章则提供了新的证据,发现了登载于《申报》上的一则启事,证明徐訏是1936年8月离沪赴法的。也就是说,徐訏在上海写完了《鬼恋》的第一版。以上考证其实并不复杂。然而,以往绝大部分研究者却都认为《鬼恋》写于作者留法期间,并将之与徐訏在法接触了与托洛茨基有关的一些档案而转变信仰联系起来,凭借此线索来敲定《鬼恋》的主旨。

徐訏《鬼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
诚然,在确认《鬼恋》初版本的写作时间与地点后,我们可以明确地将那种以作者本人的思想观点为手术刀来解析文本的读法放在一边了。但我们不应忽视,从《宇宙风》上的“短篇小说”到作为单行本发行的“中篇小说”,《鬼恋》的文本形态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动。这一次变动具体发生的时间目前难以确认,但应当是在徐訏留法期间或回沪之后。本文具体的分析便由此展开。
读者或许会发现,“中篇版”的某些版本中有一首新诗作为献辞。
春天里我葬落花,
秋天里我再葬枯叶,
我不留一字的墓碑,
只留一声叹息。
于是我悄悄的走开,
听凭日落月坠,
千万的星星陨灭。
若还有知音人走过,
骤感到我过去的喟叹,
即是墓前的碑碣,
那他会对自己的灵魂诉说:
“那红花绿叶虽早化作了泥尘,
但坟墓里终长留着青春的痕迹,
它会在黄土里永放射生的消息。”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日夜倚枕
如果正如其本人以及诸多研究者所说,旅法期间徐訏经历了重大的思想变化,那么该诗中流露出来的回望姿态以及对“知音人”的期盼,则格外耐人寻味。且看最后一节,“坟墓”中“长留着青春的痕迹”与“永放射生的消息”,这样的表述清晰地告诉读者,自己过往的经历与信念中,存在一些难以忘怀、历久弥新的内容。由此,我们再来考虑《鬼恋》的“短篇版”(即发表在《宇宙风》上的第一版)与“中篇版”(指随后主要由“夜窗书屋”出版的各种单行本),便可大胆推测,两个版本中一以贯之的内容与精神,便是徐訏本人最为珍视的写作《鬼恋》的真实诉求、关切。所以,让我们首先自其不变者而观之。
主动生成的鬼
重要的“不变”,有时需要通过文字的改变来达成。“短篇版”开篇为“说起来该是六七年前了”;“中篇版”开篇为“说起来该是十来年前了”。考虑到“短篇版”的写作、发表时间为1936年、1937年,“中篇版”的改定时期大约是四十年代初期,我们便可发现,徐訏通过对年份的改动,执拗地将故事发生的时间指向1930年前后。
有了时间点后,再来看地点。在两版《鬼恋》中,有关“鬼”的大部分基本内容都是不变的,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点便是“龙华”。“鬼”的住处是在龙华附近的村庄。“我”第一次在白天看到扮作尼姑的“鬼”,则是在龙华寺赏桃花时。
1930年前后的龙华,发生了永远铭刻在世人心中的创伤性事件,用鲁迅的文字来说,就是“为了忘却的纪念”,就是“忍看朋辈成新鬼”。《为了忘却的纪念》最末一句是“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鬼恋》就是一部“再说他们”的作品,一方面召唤读者再次返回到那一时空中,一方面接引彼时受到创伤的革命者来到写作的此刻。由此我们发现,在前后两个版本中,故事的最高潮,即“鬼”袒露自己的革命者身份的段落,几乎一字未易,因为这就是徐訏心底里想对1930年前后的龙华说的话:
但是以后种种,一次次的失败,卖友的卖友,告密的告密,做官的做官,捕的捕,死的死,同侪中只剩我孤苦的一身!我历遍了这人世,尝遍了这人世,认识了这人心。我要做鬼,做鬼。
以往对于《鬼恋》的研究与评价,虽然具体论述思路繁多,但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认为其与时代社会脱节,是封闭的浪漫主义读物,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写作技巧上;另一类则认为其体现了作者本人经历思想转变后对革命的逃避乃至反感、排斥,是反动的,或至少是另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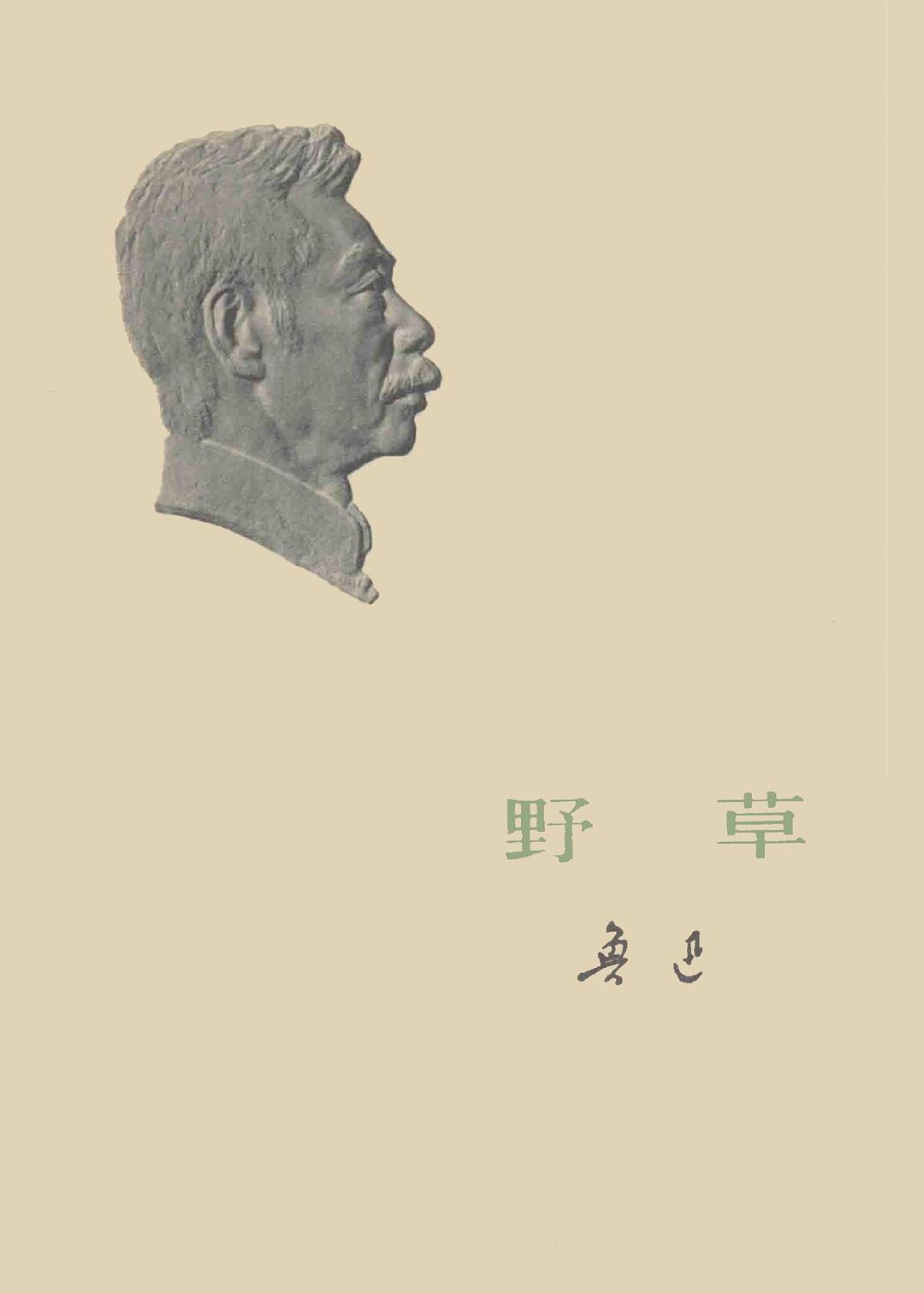
鲁迅《野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
经过上述分析,第一类说法无需再加以反驳,第二类说法尚需进一步的商榷。在小说中,“鬼”的形象其实非常复杂,且不乏深刻,她的诸多言说风格与思路,令人想到鲁迅的《野草》,如:“人终以为鬼是丑恶的,人终把吊死的溺死的死尸的样子来形容鬼的样子”“可怕的鬼相一定是丑恶吗?”“‘你以为死可以做鬼么’?她冷笑地说:‘死不过使你变成死尸’”“人,现在我什么都告诉你了,我要一个人在这世界里,以后我不希望你再来扰我,不希望你再来这里”。这些言说之要义在于,“鬼”始终通过反诘、辩驳、拒斥的方式,与黑暗混乱的人世划清界限,保持自我完整的主体性。
但是我不想死,——死会什么都没有,而我可还要冷观这人世的变化,所以我在这里扮演鬼活着。
“鬼”特别注意将自己的生存状态与“死亡”区分开来。她之为“鬼”,是主动成为的,绝非凡人所认为的“人死而成为鬼”,而是“生成的鬼”,是唯有凡人经历过“最入世的磨练”后才可以成为的“鬼”。成为这样的一个“鬼”,便不是奔向虚无,亦非逃避人世,而是在人世之外,活出一个独立的个体之“有”,鉴照人世,甚至伺机而动,影响人世。在小说中,“我”得知“鬼”的真相之后,便想要用爱情来让她重新做人,而且是“做一个享乐的人”,“鬼”虽然与“我”也有深厚的情意,但最终依旧离去,不知所终,其实便是又一次抵抗了来自人世的诱惑。
这样的一个“鬼”的形象,在气质上,颇类鲁迅笔下绍兴当地戏剧中的“女吊”,“一个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鲁迅《女吊》)。如果“女吊”值得被伊藤虎丸、汪晖等学者视为深刻而积极的力量,甚至就是鲁迅的某种自况,那么《鬼恋》中的“鬼”或许也应被视为是一个值得赞颂的、有深度的形象,而非一个沉湎于创伤不可自拔的“忧郁症患者”。
对革命的另一种真诚赞颂
以上内容讨论了两版《鬼恋》的共通之处,同时也是笔者所认为的该小说的核心所在,现在让我们自其变者而观之,有重点地来看“中篇版”修改、增添了哪些内容。
在“中篇版”里,徐訏有意识地通过增加环境描写(笔者所见1947年的《鬼恋》单行本中,数次出现了“风萧萧”、“萧萧”等表述,不知是否是其长篇《风萧萧》出版后所添加的),将“品海牌香烟”改为“Era”香烟等细节,使得故事的氛围更为空灵神秘,叙述节奏也从容了不少,整体文本结构显得婀娜。尚有一处修改,笔者至今困惑,即在“短篇版”中,“鬼”说“我是犹太人,因为我母亲是犹太人,父亲是华侨,中国恐怕都没有来过,可是现在他们都死了”,“中篇版”里该身份设定被删去。这一“犹太人”身份背后的故事,有待日后探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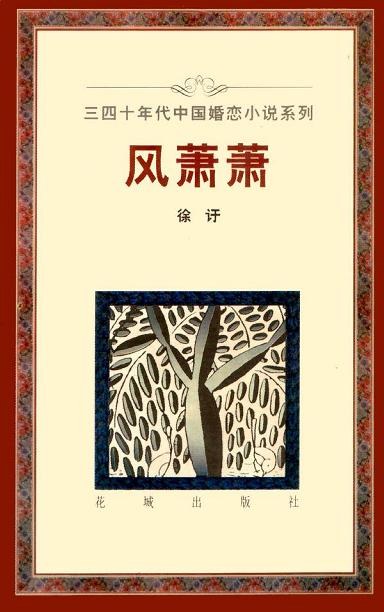
海派文学名家徐诩代表作《风萧萧》,花城出版社,1996年。
两个版本最大的区别,就是“中篇版”增加了三处情节:“我”给“鬼”讲鬼故事、“鬼”换男装扮成自己死去的丈夫、“我”入院后结识了看护小周。粗略一看,这三个情节为全篇增添了不少奇情因素,甚至显得有些通俗,仿佛作者有意迎合读者的趣味。但从风格上来看,这三处情节其实颇受郁达夫的影响。“我”所讲的鬼故事中的男主角,明明已经知道自己前夜所遇为“张氏母女之墓”中的女鬼,第二天却还要折返回墓前,想在夜间再次相会。这样一个“骸骨迷恋者”的形象,实在是接续郁达夫《十三夜》等诸篇目的小传统。小说男主角住院与女看护发生纠葛,亦是郁达夫小说中常见的设置。田晓菲指出郁达夫的《迷羊》“融合了狭邪小说与鬼怪小说两种文体”,认为其“最难得处,也是郁达夫最擅长的,在于营造一种迷离惝恍、香艳中含着诡魅与凄凉的气氛。依足了志怪小说的传统,女子一直被隐隐约约地描写为异类”,这样的一种写作取径,亦被“中篇版”《鬼恋》采用。
相较而言,“鬼”女扮男装这一设定值得进一步思考。固然,女扮男装是为了随后看护小周迷恋上扮成英俊少年的“鬼”的情节做铺垫。但我们也可以这样解读:作为革命者的“鬼”既然已经凌驾于凡人眼中“生死”的区隔之上,那么“男女”的性别区隔亦能为“鬼”所超越。这样一个具有某种超越性的革命者形象,仿佛一粒石子激起涟漪,同时以女儿身和男儿身,以深情与魅惑,扰动了“我”与看护小周的感情世界。这样一种扰动,在孜孜以求的批评家那里看来,或许是革命内容的稀释乃至浊化过程,但我并不那么觉得。“鬼”所具有的超越性,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独属于革命者的克里斯玛,用“鬼”的说法来说,便是从“最入世的磨练”中修来的“仙气”与“佛性”。虽然显得另类,但这不也是一种与言必“目的、牺牲”的思路有别的,对革命与革命者的真诚赞颂吗?
《鬼恋》真正的主角,也许是上海
在《谈话录》(王安忆、张新颖)中,有一小章节叫做“我们有没有力量审美化”,令我印象深刻。总结来说,两人的意思大概是:之所以现当代产生出来的叙事作品,总不如古典时代的那些故事、人物来得让人动心,是因为古典时代的内容都是被审美化了的。如今,面对波澜壮阔且极具浪漫色彩的中国现当代革命时期,作家所缺乏的就是审美化的能力,无法摆脱批判现实主义,走到真正的浪漫主义那里去。

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译林出版社,2019年。
在这一连串思索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关键词:审美化、革命、浪漫主义(多么神奇的三个概念,三个象)。虽然我们对其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给出明明白白的定义(或也永远无法给出),但当它们被放置在一起时,就仿佛三股难以驾驭的力量汇聚成一股,并渴望找到一个能够真正容纳自身的容器。在此种视野的关照下,我们来看《鬼恋》,会渐渐觉得它有些像是这样一个理想中的容器的一块碎片。它企图从凡人的角度来审美地看待一个另类的革命者,具有冷峻、异样的气质,却不知为何一直能够获得一般读者的偏爱,仿佛是找到了一个能够调和各种因素的配方。徐訏后来的长篇《风萧萧》获得成功其实也是水到渠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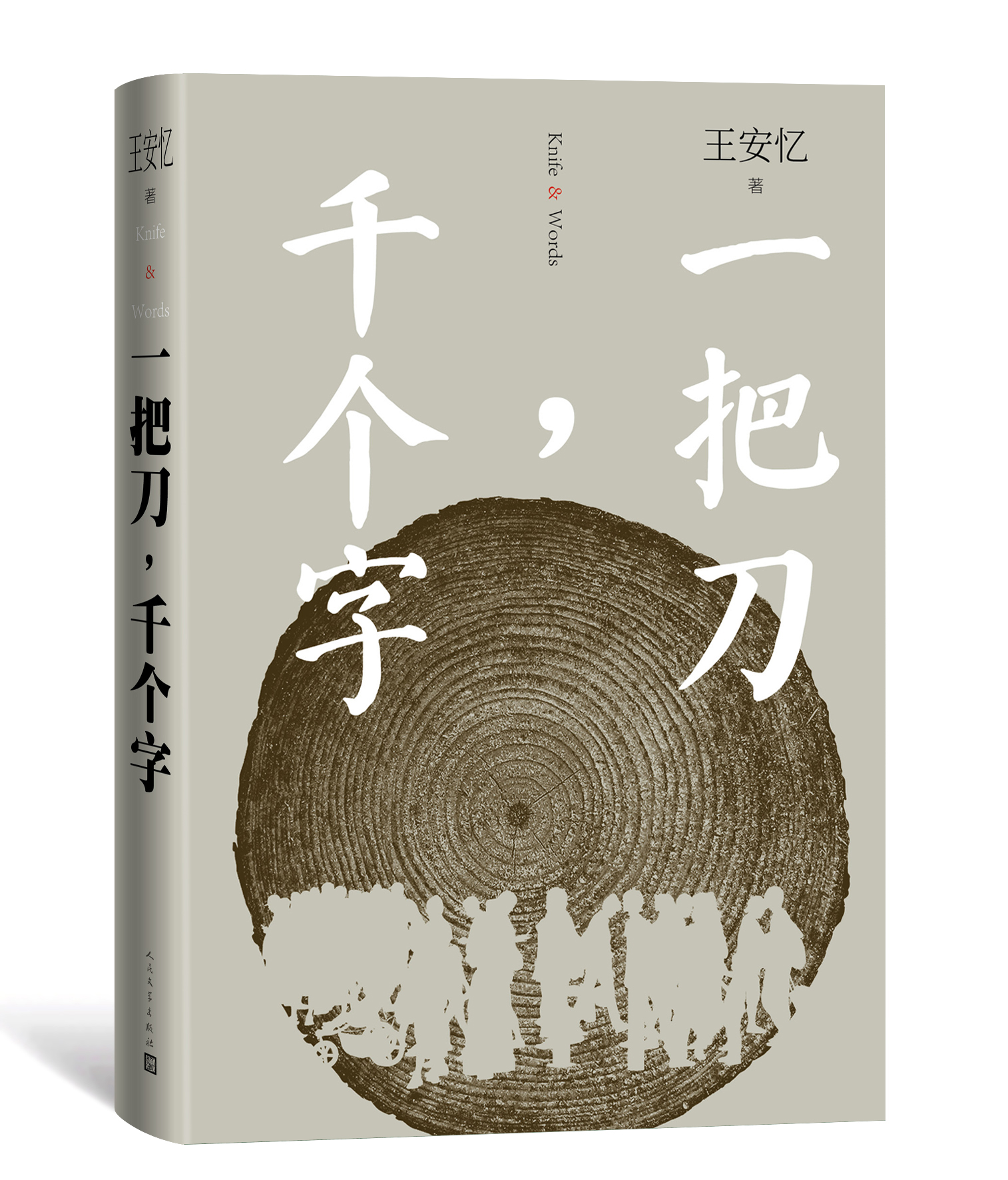
王安忆《一把刀,千个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
所以,我们不妨来看,《鬼恋》之后是否有作家作品暗地里接续了《鬼恋》的小传统,抑或发出自己的声音与《鬼恋》互为彼此的回响。我首先想到的是王蒙《青春万岁》中,苏宁的窗台上的那本《鬼恋》。当蔷云盛气凌人地问她为什么要读这种书时,苏宁说“我,病了,看别的书太累”,仿佛徐訏腕下的文字就像是邓丽君的歌声一样,具有抚慰人心的作用。多年以后,王蒙自陈: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曾经受到徐的小说的诱惑。我读起《鬼恋》、《吉卜赛的诱惑》等就放不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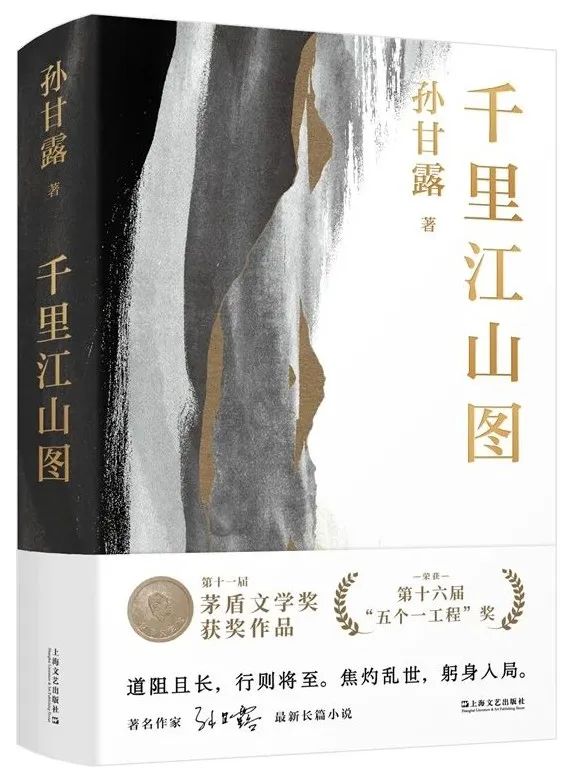
孙甘露《千里江山图》,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
我还想到王安忆的《一把刀,千个字》中那位以张志新为原型的光彩夺目的母亲,她仿佛是“鬼”的镜像,一个处在人群的顶端,一个处在鬼域的深处,却都具有一种令人神往、心碎的理想主义气质,绽放出革命最耀眼的克里斯玛。我还想到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真的就是从“霓虹灯外”的龙华写起,从《鬼恋》这里接续了创造性地将革命叙事嵌入更新后的上海都市版图的任务。
此刻也是午夜,我在离斜土路不远的大木桥路结束这篇文章。如果说以上文字仍旧带着太多翻案的意思,那么最后就自由地谈谈。
《鬼恋》全篇,最最教我难忘的还是那一句“人!请告诉我去斜土路的方向”。这一近乎于逼问的句子,在我看来,既是“鬼”道出的,也是上海这座城市,对“鬼”和“我”这两位午夜的漫游者道出的。它仿佛一道凄厉又幸福的闪电,同时击碎了两个生命内心的孤寂与苦痛。只有在上海,“鬼”才能漫无目的地去“黄浦江看月”,去寻Era香烟,并在午夜找到一个“我”,从南京路步行到斜土路(多么远的距离啊)。这是一座可以让身处不同世界的人彼此相遇的城市。所以,《鬼恋》真正的主角,也许就是上海。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