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艺术批评中“描述”的复杂性
【编者按】
《艺术批评入门:历史、策略与声音》一书系统地梳理了从批评流派缘起到2000年以来艺术批评演变的历史,并探讨了一系列与描述、解释和判断这三个主要批评活动相关的具体问题,详细论述了构成批评话语的各种力量和抉择。本文摘自该书第二章,澎湃新闻经南京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尽管批评家们在描述作品的优先顺序上存在明显的分歧,但描述一件艺术品似乎仍然是一项相对简单的活动——人们仅仅报道自己认为重要的特征。然而,在实践中,批评家们经常测试所谓描述的限度,并在此过程中对传统的描写策略提供了有趣的变体,引发了关于描述性文章本质的真正争论。
唤起式的描述
长期以来,一些批评家认为,从理论上讲,文字描述可能超越了对作品特征或效果的简单概括,通过文章和艺术品之间的意义类比,强化特征,引发效果。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尝试需要借助有唤起功能的描述语气:例如,沙龙评论家们描述场面宏大、题材严肃的历史画作时,需要相应地选用严肃和正式的词形表达。或者,类似地,18世纪的批评家、艺术史家约翰·约阿辛·温克尔曼在《古代艺术史》中对著名的《阿波罗观景台》进行了描述,这一描述后来被解读为试图通过其复杂的语气,来再现古代雕塑温和的雌雄同体之美。这就是温克尔曼的描述:“永恒的春天,就像在极乐世界快乐田野中,散发青春魅力和成熟优雅的气质;又如健硕的四肢上散发出来的细腻柔和……在这个艺术奇观前,我忘记了一切……我的胸膛充满了崇敬,恰似被圣灵所充满……因为我的肢体,亦如皮格马利翁的美丽创造,被注入了生命和动感。”
文献史学家约翰·D.罗森伯格(John D. Rosenberg)观察到,温克尔曼的语气明显是混杂的——作者似乎同时扮演了女性和男性的角色,他用一种庄重和细腻交替的声音写作。在罗森伯格看来,这一效果是阿波罗形象的巧妙反映——既蕴含着优雅的男子气概,又流露出秀美的温柔。
批评文章的描述中常常伴有对艺术作品的形式和结构的对应隐喻。在一首名为《如果我告诉格特鲁德》的著名诗中,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使用了一种碎片化的重复句子结构来尽可能地唤起读者对毕加索立体派绘画的感受,这些画作往往涉及多个观点和主题上的细微变化。斯泰因写道:“完全相似,为了完全相似,完全相似与完全相似呈现完全相似,相似得完全相似,完全与相似完全相似,完全的相似与完全相似完全相似。因为情形就是这样。因为。”斯泰因的非传统句法试图唤起毕加索某些作品的棱镜感。同样地,在20世纪70年代,阿尔林·拉文偶尔以碎片化的文风与变化的、有质感的语言写作,产生了一种与她所研究的女性艺术家的作品十分相近的非线性效果。最近,在分析本杰明·爱德华的《融合》时,杰瑞·萨尔兹通过提供一系列断音(staccato)的比较来描述绘画的主题和风格:“这座,神奇的令人产生幻觉的超级圆顶——部分似皮拉内西——部分似卡纳莱托——部分似捷森——看起来像是23世纪的休斯顿,一座来自另一个维度的巴洛克教堂,或者是电子游戏《末日》中设计的最高境界。” 这种层次感很强的比较与爱德华画作的层次感很相似,而萨尔兹的描述结构也因此微妙地引起了对其主题结构的注意。
从一个稍微不同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描述可以说是试图在读者的头脑中唤起一件作品的所谓效果。这种描述不仅与艺术品相似,也会产生类似的反应。尽管这种方法在斯泰因的诗中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但事实上,更多的是与其他时代的诗人有关。考虑到画家可以把经验和感觉转换为视觉形象,费利克斯·费尼翁和J.K.于斯曼早在19世纪80年代,先后提出要把图像经验转化为文字。随后,在20世纪50年代,一些为《艺术新闻》撰稿的文学批评家开始采用类似的描述方法,部分原因是受到杂志编辑托马斯·赫斯的鼓励——赫斯本人在自己的批评中也采用了类似的风格。例如,赫斯在1959年对德·库宁画作的描述中写道:“就像拇指、指关节和指甲在无名指后面弯曲,对着架子上风景画中静物的立面,如天使在飞翔一般,这个高贵的女人将头转向画面。他们的脸一直对着田野和山峦。”赫斯的文章颇像斯泰因的主题诗,故意表现得高深莫测,他有意将文中的意象变得富有流动性,尽力模仿德·库宁绘画抽象多变的特点。
然而,从赫斯的时代起,联想唤起式的描写一直毁誉参半。20世纪60年代,一些批评家开始质疑甚至贬低这种做法。例如,1966年,芭芭拉·罗斯嘲笑了她所说的“50年代艺术写作中的紫色段落,这些段落愚蠢地试图通过为艺术对象创造一种文学对等物来唤起读者的同感”。随后,许多批评家转而采用了一种相对直接的描述风格,这种风格并不要求唤起任何特殊的感觉,也不再声称复制艺术品的效果。最终,唤起式描写被证明是令人沮丧的,至少对一些作家来说。1974年,露西·利帕德作为已经不再使用唤起式描写的批评家之一,突然得出结论,认为她曾竭力提供传统的、可证实的描述,现在看来“是在浪费时间……我过去常常花一半的篇幅细致入微地描述作品,然而,没有亲眼见过这一作品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从语言描述中分辨出它是什么样子”。从那时起,批评家们倾向于少用联想唤起式描写,并将它与其他方法结合起来。
用语言表达视觉的困难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关于艺术批评的正确目标产生了很多争论,这一景象可以在罗斯和利帕德的评论文章中找到影子。但两个人最终都接受了一种普遍的认识,并以此指导自己的批评写作。这一普遍认识就是,书面语言根本无法真正细致地反映艺术形式。当艺术批评家们试图将视觉意象翻译成语言术语时,他们已经无数次意识到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例如,1960年,诗人、批评家詹姆斯·梅里尔承认:“人们会想象在这两种艺术之间存在一些有用的类比,但只要试着用莫奈或凡·高的方法写诗,或者告诉你的学生她的诗在左下角需要些暖色,看看你能做到什么程度(你便知道这是多么痴心妄想啊)。”
换句话说,诗和画是以不同的方式创作,也是以不同方式来欣赏的。因为当我们开始浏览一幅画时,通常在一两秒钟内了解其总体布局,然后聚焦于某些特定的细节上;作为对比,我们总是以线性的方式阅读文字,一句一句地读。因此,对一件艺术作品的文字描述永远不能与观看作品的体验完全平行,因为观看者的眼睛与阅读者的眼睛以不同的速度和方式移动。正如艺术史家迈克尔·巴克桑德尔在《艺术批评的语言》中所说的那样,“连续的、线性的(解释性的)言语说明可以与阅读行为保持一致,但不能够与看一幅画的节奏、顺序相匹配”。或者,用一种更极端的说法,追求真正意义上唤起式的批评可能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
但是,即使我们愿意放弃成功地实现唤起式批评这一目标,由于语言的限制,我们仍然面临着相当大的问题。批评家们有时会遇到大量的描述性词语,多得无法选择(一座雕塑是大的,是宏伟的,还是壮观的?一个画廊是拥挤的还是拥阻的?);有时,他们面临着无词可用的窘境。这种差异往往最终归因于更广泛的文化基因。正如巴克桑德尔所观察到的那样,西方批评在某些描述性术语上非常丰富,但在其他方面相当贫乏。例如,法国和英国的批评家很久以来就能利用复杂的词汇来描述欧几里得的几何形状(绘画中的元素可以被识别为正方形、长方形或梯形)。但是,当涉及描述艺术品的表面时,他们的可选词汇通常较少,因为没有一系列既定的关键词汇。因此,批评家们在试图描述画作表面时,常常使用外来语或依赖类比;因此,我们经常会读到将表面说成“黄油状”或“玻璃状”的文字。一方面,约鲁巴雕刻家可以使用特定的术语,如didon,表示光滑但不是光泽的表面亮度。换句话说,语言在某些方面是丰富的,而在另一些方面常是有限的,因此批评家有时不得不在大致相同的词语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或者试图想出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来描述一种性质,却没有可用词语。
长久以来,在批评中,人们经常说起描述艺术作品的努力是徒劳的,这种感慨也许是有道理的。例如,约翰·拉斯金的《现代画家》的前两卷充满了对作品的冗长(通常是艺术性的)描述,但拉斯金也一再强调,任何试图用文字描绘一幅画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例如,在第一卷的某个地方,他惊叹道,仅仅用语言来表达或解释感官对象的那些微妙的品质是多么困难。在接下来的一卷中,他介绍了丁托列托的《受难记》,并立即声明不会用语言来描述它,以免侮辱这幅奇妙的图画。一个世纪后,马克斯·科兹洛夫在《效果图》中写道:“语言和视觉形象之间并不存相互交换的市场。在这两种媒介产生的感知中,没有自然交换或客观等价物。”或者,按照杰里米·吉尔伯特罗尔夫的观点,“给视觉命名就相当于剥夺了它的视觉性,并把它寄存在语言中。视觉的对象因此脱离了事物的世界,被插入一种或另一种话语之中”。
因此,一些作家认为,有些艺术品或艺术的某些方面根本无法用语言来描述。例如,1763年《信使报》上的一则公告用了整整四页的篇幅来讨论让巴蒂斯特·德沙伊斯(Jean Baptiste Deshays)的《军人的婚姻》,然后突然声明对这一画作所有的描述都是不充分的。两年后,狄德罗在讨论画家克洛德·约瑟夫·韦尔内时得出结论:他的作品是无法描述的,必须看一看;同样,1951年,艺术史家约瑟夫·斯隆提出,“今天公众在理解大量针对抽象艺术的文章时遇到的一些困难,可能是因为作者必须用语言表达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东西”。
公平起见,一些关于描述的局限性的说法本身就可以被看作一种描述。通过论述一个作品超越或逃避描述,批评家可能试图表明其伟大或复杂。在《纽约时报》担任建筑评论家多年的艾达·路易斯·赫克斯特布尔(Ada Louis Huxtable)曾在一篇关于休斯顿的彭佐尔广场的文章中写道:“这座建筑很难描述,没有任何图片可以完全代表它。因为它是一个复杂的、非常规的三维形态,实际上从不同的视角观看,会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造型。”赫克斯特布尔认为,这座建筑的一个特点就是防止简单描述或复制。但是,关于描写的局限性的论断即使偶尔被用作比喻,仍然常常会指向这样一种感觉,正如芭芭拉·罗斯在1966年所说的那样,“视觉经验没有文学上的等价物,而这正是我们作为艺术批评家的困境的核心所在。我们的主要问题是语言问题”。
解释性描述
意识到语言是一种受限的(并且是起到限制作用的)工具,有思想的批评家也早就知道,语言描述的这种行为不可避免地涉及选择、优先权和牺牲。评论家必须选择描述什么和如何描述。因此,似乎也可以说,描述总是涉及某种程度的解释甚至评估。例如,在迈克尔·巴克桑德尔的《艺术批评语言》中,“即使最初看起来纯粹是描述性的词语,其说明的成分也要大于描述的成分——也就是说,我的目的不是描述而是指明……我在艺术品中发现的视觉趣味”。按照同样的思路,哲学家弗·爱·斯帕肖特本说过,在实践中,没有真正的批评把描述和评价分开,两者是齐头并进的。即使在原则上区分它们也不容易。很少有完全中性的描述。此外,每一种描述都必须选择引起它注意的某些特征加以描述,而这种选择很可能是根据艺术品实际体现的已经做出的评价。
因此,描述依赖于选择,而选择总是意味着解释和评价。
作为这一过程的例子,不妨考虑一下彼得·施耶达尔2002年的一篇文章中对高更《守望死亡的精神》的简短描述:“总结,一个受惊的裸女趴在床上,身后是一个怪诞的萨满形象,这幅带有讽刺意味的形象占据了画面,与奇异闪亮的色彩和错综复杂的、令人激动的笔触交相辉映。”这是一种简洁的描述,有效地勾勒出了绘画的主题,并描绘了画家的调色板、风格和笔触。同时,这种描述也为施耶达尔表明他对这幅画的特殊反应留有空间,并对某些元素进行优先性排序。他选择把女孩描述成裸体,而不是赤裸或脱光衣服,这样就悄悄地把这幅画置于一个既定的裸体形象传统中。此外,他注意到她的心理状态(恐惧,而不是忧虑或紧张),但把床仅仅当作一个支撑物。因此,施耶达尔鼓励我们仔细看女孩,而不是床。对于画面,他用“与闪亮的色彩交相辉映”加以描述,这表明了施耶达尔对这幅作品的喜爱。
因此,即使是这样一个简短的描述,也包含了依据具体优先性、假设和推断所做出的词语选择。因此,它很难是一个简单、中立的绘画记录,更多的是一个主观的叙述。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可以简单地看看其他人对这幅画的描述。例如,格里塞尔达·波洛克(Griselda Pollock)在描述这幅画时说:“画的平面上有一张巨大的床,耀眼的床单上摆着一个赤裸的身体。”这个女孩现在是赤裸的(naked),而不是裸体(nude);因此,波洛克在暗示她是脆弱的,暴露在外的。这张床,施耶达尔认为不值一提的床,现在变成了巨大的床:它在波洛克的描述中显得很重要。简而言之,描写的行为允许甚至迫使批评家强调作品的某一特定方面,并有效地传达诸如兴趣、优先性和立场等主观喜好。
可以肯定的是,并不是每一个文字描述都明确承认这一过程。但是有思想的批评家偶尔会探讨描写和解释之间的关系,或者在他们的写作中反映描述过程的复杂性。例如,马克斯·科兹洛夫在《修炼的僵局》中声称,他的众多的描述都不可避免地与解释的过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写道:“通过对作品物理特征的热情描述,我想放大我作为一个观赏者的心理感受。这些来自凝视的感受有助于解读手头的作品,使之成为一种可供分享的个人体验。”还有一些批评家隐晦地承认了这一点,例如,安德鲁·格拉汉姆迪克森(Andrew Graham-Dixon)1991年对约翰·康斯坦布尔(Constable)的《跃马》的讨论:“看看最前面的驳船左边的这些人物的形象塑造,他们只是不完整的黑影,从黑暗中树林中挣扎出来。看看那狂风肆虐的天空,甩出的颜料构成一团纷乱的云彩。看看那匹马……”这种描述有效地表明了这幅画的几个显著特征,反复使用的“看看”一词突出了批评家将读者的注意力从一个细节引导到另一个细节的过程。格拉汉姆迪克森和其他批评家一样,赋予艺术品的某些方面以优先性,并清晰地体现出排序的过程。
描述不当的代价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描述是针对可见的艺术品,有时会与解释发生重合,这样的描述就可以被看作表达了个人的判断和喜好。可以肯定的是,坚持认为任何一件艺术品都只有一个正确的描述是不公平的。如前所诉,描述是有选择性的,而且绝不会是面面俱到的。因此,有些描述可能会让一些读者或听众感到不公平、不正确或不具代表性。例如,卡罗琳·兰奇纳和威廉·鲁宾曾在一篇画展前言文章中描述了法国艺术家亨利·卢梭的几幅画,并说除了他自己独特的风格之外,其创作手法还有印象派的血脉。然而,在对画展的回顾中,莱克斯特劳·道恩斯(Rackstraw Downes)对此并不认同。其主要原因是不同意他们对画作的描述。道恩斯写道:“我对此表示严重怀疑。首先,他们对这些素描的描述是不准确的。这些素描没有表现出对印象派的吸收,太暗,没有表现出投光或碎色的概念。”通过质疑他们描述的准确性,道恩斯削弱了作者对卢梭作品所下的结论。
因此,把不令人信服的描述建立在沙子上,往往根基不牢。但是,这不一定会失去读者的信任。1982年,美国评论家凯·拉森回应桑福德·施瓦茨对美国艺术家马斯登·哈特利作品的创造性描述时说:“虽然我不同意他的描述,但我被他的描述迷住了。”但在某些情况下,对画作进行不当描述的作者可能会发现他们会使整个文章因此受到谴责。例如,1885年,《批评家》的一位匿名评论员在评价克拉拉·厄斯金·克莱门特(Clara Erskine Clement)的《雕塑概况》时指出,确实有必要对雕塑进行概述,但这本书未能满足这一需求,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本书的描述太差了。这个匿名者指出:“总的来说,很可能没有哪一本书能像这本书这样,对埃及艺术做了误导性的描述和愚蠢的评价。”因此,该文作者最后怀疑克莱门特是否亲眼见过任何一个埃及雕塑,并继续得出结论说,这本书一点价值也没有。这样粗暴的猛烈斥责在批评文章中并不多见,但它确实指出了一个没有说服力的描述所付出的代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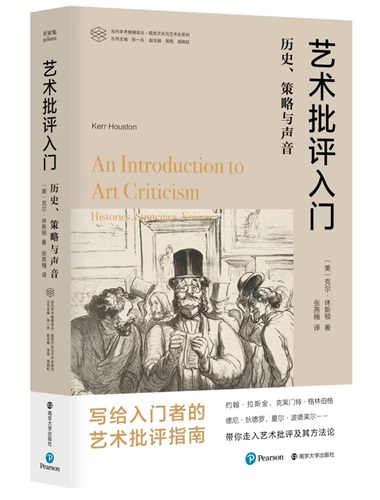
《艺术批评入门:历史、策略与声音》,[美]克尔·休斯顿著,张燕楠译,南京大学出版社·折射集2024年3月。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