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呼啸山庄》:与激情相关的恶的问题
【编者按】
文学并不清白。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巴塔耶认为,只有承认自己与恶的认识“同流合污”,文学才能进行全面而深刻的交流。在《文学与恶》一书中,巴塔耶分析了八位作家及其作品,包括艾米莉·勃朗特、波德莱尔、米什莱、威廉·布莱克、萨德、普鲁斯特、卡夫卡和热内,探讨了暴力、色情、童年、神话和僭越等主题。本文摘自讨论艾米莉·勃朗特的部分,澎湃新闻经上海人民出版社授权发布。
在所有女性中,艾米莉·勃朗特似乎是被优先诅咒的对象。她短暂的一生并不幸福。她道德的纯洁性一尘不染,但却深刻体验过恶的深渊。尽管很少有人比她更严苛、更勇敢、更正直,她还是深切认识了恶。
这是文学、想象和梦想的任务。在三十岁时结束的一生,使她远离了一切可能的事物。她出生于1818 年,几乎没有离开过约克郡的教士住宅,在乡下,在荒原,粗犷严酷的景色与爱尔兰牧师的调性不谋而合,这些只给了她严苛的教育,而缺乏母性的抚慰。她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她的两个姐姐也一样严苛。唯一的兄弟误入歧途,陷入了浪漫主义的不幸之中。我们知道,勃朗特三姐妹既生活在教士住宅的庄严肃穆中,又生活在文学创作的激荡骚动中。她们每天都亲密无间地生活在一起,但艾米莉从未停止过保持道德上的孤独,她想象的幻影在这种孤独中自由驰骋。她性格孤僻,但从表面上来看,她曾温柔、善良、积极、执着。她生活在一种沉默之中,只有文学从外部打破了这一寂静。临终的那天早晨,肺病短暂发作后的她像往常一样起床,下楼到家人中间,一言不发,她没有回到床上,就咽下了正午前最后一口气。她甚至没想过去看医生。
她留下了少数诗作,以及文学史上最美的书之一,《呼啸山庄》。
或许也是最美的、最深刻暴烈的爱情故事……
因为命运显然希望艾米莉·勃朗特即使在美的情况下,也要对爱完全不解,同时也希望她对激情有一种焦虑的认识:这种认识不仅将爱与明亮联系在一起,而且将爱与暴力和死亡联系在一起——因为死亡显然是爱的真相。正如爱也是死亡的真相一样。
直到死亡,色情也是对生命的赞许
如果我想谈论艾米莉·勃朗特的话,我必须首先做一个初始的声明。
我认为,直到死亡,色情也是对生命的赞许。性包含了死亡的意味,这不仅是指新生的延续和取代死者意义上的死亡,还因为它涉及繁衍生命的存在。繁衍就是消失,最简单的无性生命在不断繁衍的同时也在不断衰弱。它们并没有死亡,如果我们所说的死亡是指从生命到腐烂的过程的话;但是,这一曾在者,通过繁衍,不再是它曾是的样子了(因为它变成了复制品)。个体的死亡只是生命不断增殖的一个面向。有性繁殖本身只是无性繁殖承诺的生命不朽的一个最复杂的面向。是不朽,但同时也是个体的死亡。不沉溺于运动中,就没有动物可以进入有性繁殖,而这一运动最终的形式就是死亡。无论如何,性倾泻的基础是对自我孤立的否定,自我只有通过在紧拥中消除存在的孤独感,超出自我、超越自我,才能体验到晕眩。无论是纯粹的色情(爱—激情交加的),还是肉体的感官享受,只要是在存在的毁灭和死亡得以彰显的情况下,其强度就是最大的。我们所说的恶习,就源于这种对死亡的深度参与。脱离肉身的爱的酷刑更能象征着爱背后的真相,尤其是他们的死亡使他们靠近的同时,又鞭打着他们。
没有什么凡人的爱情能够比拟《呼啸山庄》的主人公凯瑟琳·欧肖和希斯克利夫的结合。没有人比艾米莉·勃朗特更有力地表达了这一真相。这并不是因为她以明晰的形式思考了它,而我却沉重地把它表达了出来。而是因为她感受到了这一点,并以致命的,且在某种意义上神性的方式表达了这点。
童年,理性和恶
《呼啸山庄》中致命的激情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我认为,如果不能详尽地探讨它所提出的问题,那么讨论就是毫无意义的。
我曾将恶习(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被普遍认为的恶的重要形式)与最纯粹的爱的酷刑相比较。这种悖论的比较会引起苦思冥想的困惑,我将尽力为它辩解。
事实上,除了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的恋情将感官享受搁置一旁之外,《呼啸山庄》还提出了与激情相关的恶的问题。仿佛恶是展露激情最有力的手段。
抛开恶习的施虐性形式不谈,勃朗特书中所体现的恶,也许是以其最完美的形式展现的。
我们不能将那些以物质利益为目的的行为视为恶的表达。这种利益,或许是利己主义的,但如果我们从中期待的是除恶本身之外的其他东西——一种好处,那么它就无足轻重。
另一方面,在施虐狂行为中,享受才是屏息凝神的毁灭,最痛苦的毁灭是人的死亡。施虐狂才是恶:如果一个人为了物质利益而杀人,这不是真正的恶,纯粹的恶,是凶手在预期的利益之外,仍享受着施暴的快感。为了更好地表现善与恶的图示,我将回到《呼啸山庄》的基本情况,回到童年,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的爱情,从完整性的角度看,正是从童年开始的。这是两个无人照管的孩子在荒郊野外追逐中度过的野性生活,他们没有受到任何约束或传统的阻碍(除了反对感官游戏的限制;但在他们的天真无邪中,两个孩子坚不可摧的爱在于另一层面)。也许,这种爱甚至可以归结为拒绝放弃野性童年的自由,不受社交规则和传统礼仪的影响。这种野性生活(世界之外)的条件是基本的。艾米莉·勃朗特使它变得可感——而这点正是诗性的条件,一种没有预谋的诗性,两个孩子都拒绝自我封闭。社会与天真烂漫的自由游戏相对立之处在于前者以利益算计为基础的理性。社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规定自己,使自己能够延续。童年的冲动活动将孩子们紧紧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共谋的感觉,如果将这种冲动的主权性强行施加于自身,社会将无法生存。社会约束会要求野性的青年放弃他们天真的主权,并要求他们屈从于成年人的理性惯习:这种理性的、精打细算的方式最终是为了集体利益。
这种对立在艾米莉·勃朗特的书中非常明显。正如雅克·布隆代尔所说,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在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的生活中,情感固定在了童年时代”。但是,如果幸运的话,孩子们是能够暂时忘却成人世界的,尽管这一世界对他们来说就在预期之内。灾难突如其来。希斯克利夫这个被捡来的孩子,被迫逃离其在荒野上与凯瑟琳肆意奔跑的美妙王国。她生性粗野,却有意否认童年的野性:她放任自己被一位年轻、富有、敏感的绅士引诱,过上富足的生活。事实上,凯瑟琳与埃德加·林顿婚姻的价值是有两面性的。这并不是真正的丧权。林顿和凯瑟琳住在呼啸山庄附近的画眉田庄,在艾米莉·勃朗特的心中,那里的世界并不是一个稳固的世界。林顿慷慨大方,他没有放弃童年的天性骄傲,而是保留了这一成分。他的主权性超越了他从中受益的物质条件,但如果不是因为与稳固的理性世界达成了深刻的一致,他也无法从中受益。希斯克利夫衣锦还乡,他有理由认为凯瑟琳背叛了童年的绝对主权王国,而她的身体和灵魂都和他一起属于这个王国。
我愚笨地去理解这个故事,这个故事里,希斯克利夫肆无忌惮的暴力在叙述者的平静朴实中得到了彰显……
这本书的主题是一个被命运驱赶出他王国的受诅咒之人的反抗,他被重新收复这一失去的王国的强烈欲望所牵制。
我不想细说这一系列情节是何等令人着迷。我只想指出,没有任何律法或力量、惯习或怜悯能让希斯克利夫暂时收敛愤怒:除了死亡本身,因为他无悔、激情地造成了凯瑟琳的疾病和死亡,而他却将她视为己有。
我将深入探讨艾米莉·勃朗特的想象和梦想产生的反抗的道德意义。
这种反抗是恶对善的反抗。
从形式上说它是非理性的。
这一希斯克利夫恶魔般的意志拒绝放弃的童年王国到底是什么呢?只能是不可能性,和死亡。面对着这个由理性主宰、以生存意志为基础的现实世界,有两种反抗的可能性。最常见的一种,也就是目前的一种,是质疑其理性。不难看出,这个现实世界的原则并不是真正的理性,而是含有任意性的理性,而任意性又源于过去的暴力或稚气的运动。这种反抗揭露了善与恶的斗争,由暴力或徒劳的运动所代表。希斯克利夫对他所反对的世界进行评判:他无法把这一世界认同为善,因为他是在与之斗争。如果说他愤怒地与之斗争,那也是出于清醒:他知道自己代表的是善与理性。他憎恨人性和善良,这激发了他的嘲讽。在故事之外——在故事的魅力之外——他的性格甚至显得不自然、矫揉造作。但他是梦想的产物,不是作者逻辑的产物。小说中没有任何一个人物能比希斯克利夫更真实、更直率地使人信服,他还体现了一个最基本的真相,那就是儿童反抗善的世界,反抗成人的世界,并且由于毫无保留的反抗,他注定要献身于恶。
在这场反抗中,没有什么律法是希斯克利夫不喜欢僭越的。他发现凯瑟琳的小姑子对他倾心,为了尽可能地伤害凯瑟琳的丈夫,他立刻就娶了伊莎贝拉。他带走了她,一和她结婚,他就嘲弄她;然后他又粗暴待她,使她陷入绝望。雅克·布隆代尔将萨德和艾米莉·布朗特的这两句话对比,不无道理。萨德借《瑞斯汀娜》(Justine)的一名行刑者之口说:“毁灭是多么令人陶醉的行为。我想不出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人心痒难耐;当你沉溺于这神性的耻辱时,没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人着迷。”艾米莉·勃朗特则借希斯克利夫之口说:“如果我出生在一个法律不那么严苛、风俗不那么讲究的国家,我愿慢慢地活剖这两个人,作为打发夜晚时光的消遣。”
艾米莉·勃朗特与僭越
对于一个道德的、缺乏经验的年轻少女来说,发明一个如此完全地献身于恶的人物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但最重要的是,这就是发明希斯克利夫令人不安的原因。
凯瑟琳·欧肖有绝对的道德感。事实上,她是如此有道德,以至于在死前都无法与她从小就深爱的男人分开。明知他内心深处充斥着恶,她还是爱他,甚至说出了如此坚决的一句话:“我就是希斯克利夫。”
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恶不仅是恶人的梦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善的梦想。死亡是这一荒谬失常的梦想所自找的惩罚,但没有什么能阻止它继续被梦想。不幸的凯瑟琳·欧肖就是如此,在同样的意义上,必须说它对于艾米莉·勃朗特来说也是如此。艾米莉·勃朗特死前经历了她所描述的状态,我们怎么能不怀疑她在某种程度上认同凯瑟琳·欧肖呢?《呼啸山庄》中有一种类似于希腊悲剧的行动,因为这部小说的主题是对律法的悲剧性僭越。悲剧的作者同意他所描述的要僭越的律法,但他的情感是建立在同情之上的,通过同情,他传达了他对僭越律法者的情感。在这两种情况下,赎罪也被卷入僭越行为之中。希斯克利夫临死前经历了一种奇特的至福,但这种至福令人畏惧,是悲剧性的。凯瑟琳爱上了希斯克利夫,即使不在肉体上,在精神上她也为违背忠贞的律法而死;凯瑟琳的死是希斯克利夫为他的暴力所承受的“永久的折磨”。
《呼啸山庄》中的律法与希腊悲剧中的律法一样,本身并没有被废止,但它所禁止的并不是人类无事可做的领域。被禁止的领域是悲剧领域,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神圣的领域。诚然,人们把它排除在外,但这是为了使它更为崇高。禁忌使得它禁止接触的东西神化。它使接触的途径从属于赎罪——死亡,但禁忌既是一种劝诱,也是一种障碍。《呼啸山庄》和希腊悲剧——甚至所有宗教——教导我们的是,其实它是一场神性的迷醉运动,算计的理性世界无法承受。这一运动是善的反面。善建立于对共同利益的担忧之上,它以一种基本的方式,涉及对未来的考虑。童年的“冲动活动”类似于神性的迷醉,它完全处在当下。在儿童教育中,对当下瞬间的偏爱定义了普遍的恶。成年人禁止必须走向“成熟”的人走入童年的神性王国。但是,为了未来而谴责当下,即便它不可避免的,哪怕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也是一种谬误。不仅要禁止人们轻易地、危险地进入瞬间的领域(童年的王国),还有必要重新找回它,而这就要求暂时僭越禁忌。
暂时的僭越更加自由,恰恰是因为被禁止的东西是捉摸不定的。因此,艾米莉·勃朗特和凯瑟琳·欧肖都彰显了僭越和赎罪,她们的行动与其说属于道德的范畴,不如说更属于超道德。《呼啸山庄》的意义是对道德的挑战,而其根源是超道德。在这里,无须借助一般性表达,雅克·布隆代尔便正确理解了这一联系,他写道:“艾米莉·勃朗特显示了她自己……能够完成这一摆脱一切伦理或社会偏见的解放。于是,多重生命像多束光线一样展开,每一束光线,如果去思考小说中主要的对立面,都诠释了对社会和道德的完全解放。这是一种与世界决裂的意愿,为了更好地拥抱生命的丰盈,在艺术创作中探索现实所弃绝之物。这是真正的觉醒,真正的展露,是意想不到的潜在性。对于每位艺术家来说,这种解放都是必要的,这不容置疑;但在那些伦理价值观根深蒂固的人中,这种解放可能被感受得更为强烈。”
《呼啸山庄》的终极意义正是这种僭越道德律和超道德的亲密耦合。另外,雅克·布隆代尔仔细描述了宗教世界,即受活跃的卫理公会记忆影响的新教,年轻的艾米莉·勃朗特就是在这样的宗教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道德的紧张和严苛紧缚着这个世界。然而,艾米莉·勃朗特在态度上的严苛与希腊悲剧所基于的严苛有所不同。悲剧属于基本宗教禁忌的层面,如谋杀或乱伦等,并不被理性所证明。艾米莉·勃朗特已经摆脱了正统观念;她远离了基督教的简朴和天真,但她仍然秉承着家族的宗教精神。特别是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善的严格忠诚,而理性奠定了善。希斯克利夫违犯的律法——并且不管是不是出于意愿,由于她爱着他,凯瑟琳·欧肖也与他一起违犯了这一律法——首先是理性的律法。至少可以说这是基督教创立的集体律法,基于原始宗教的禁忌、神圣和理性的共识。上帝,作为神圣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在更古老的时代构建神灵世界时任意的暴力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滑动已然开始:从根本上说,原始禁忌排斥的是暴力(在实践中,理性与禁忌具有相同的意义,原始禁忌本身与理性有着遥远的一致性)。在基督教中,存在着一个模糊不清的领域,介于上帝与理性之间——这种模糊不清实际上滋养了不安,这也解释了例如冉森主义的反方向努力。经历过漫长的基督教模糊状态,艾米莉·勃朗特的态度绽放出一种坚定不移的道德力量,梦想着神圣的暴力,它不会被任何妥协削弱,或与有序的社会达成任何协定。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重新找到了通往童年王国的道路——其动力来自天真和无邪。这种道路是通过对赎罪的恐惧来实现的。
爱的纯粹在其内在的真相中被重新找回,正如我所说的,这是死亡的真相。
死亡和神性迷醉的瞬间都建立在与以理性算计为基础的善的意图相对立的基础上。然而,尽管与之相对,死亡和瞬间都是最终的结局,是所有算计的出路。死亡是瞬间的标志,而在它是瞬间这一层面上,死亡放弃了对延续的算计的追求。个体生命的瞬间依赖于已逝生命的死亡。如果这些生命没有消逝,新生命就无法有位置。繁衍和死亡为生命永存的新生提供了条件,它们塑造了永远新的瞬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只能从悲剧的视角来看待生命的魅力,但也正因如此,悲剧是魅力的象征。也许这一切都被浪漫主义所预示,但在所有作品中,最具人性的莫过于较晚问世的《呼啸山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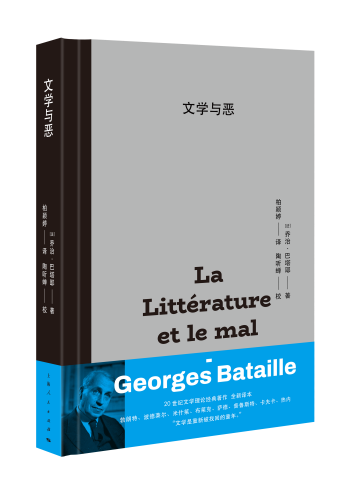
《文学与恶》,[法]乔治·巴塔耶著,柏颖婷译,陶听蝉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4月。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