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发明与发现之间:论维特根斯坦的数学观
维特根斯坦早在曼彻斯特学习航空学期间就对纯数学发生了兴趣,他细致地研习了罗素的《数学原理》和弗雷格的《算术基本规律》,还尝试去解决困扰罗素与弗雷格的“罗素悖论”。自此之后,他对逻辑和数学的哲学思考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但他的数学哲学由于受到众多逻辑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如罗素、弗雷格和图灵等)的影响而纷繁复杂,再加上他的精深思索,使他的思想更加难以得到理解和发扬。本文不求面面俱到地评述他那艰深难懂的数学哲学,而主要对其数学发明论作力求正确的理解。由于维特根斯坦的数学哲学一般可区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本文前三节将以此为顺序展开维特根斯坦的数学发明论,然后在第四节论述表明数学是居于发明与发现之间的学科。
一
前期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与数学哲学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认为,命题的意义(sense)在于它和事态的存在与否的可能性之间的符合与否。由于命题和实在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图像性关系,故命题的成分对应着实在的成分。因此,对他而言,命题是那些与实在(reality)紧密相关的经验命题。只有这样的命题才有意义,才能在该命题为真时显示出事物实际情况如何,才能算是真正命题。然而逻辑命题和数学命题与实在毫不相关,它们什么也没说。它们的真假只依赖于命题本身而不考虑实在。虽然我们常常说逻辑/数学命题是“真/假”的,但是它们并没有和真正命题一样的意义。因为“真/假”表达的是真正命题与实在之间的图像性关系。这种图像性关系具有与实在相符和不相符这两个状态。但是逻辑和数学上的“真”和“假”并不是图像性关系的这两种状态上的标签,而是逻辑或数学的必然性和不可能性这两种语义规律上的极端可能性的标签。换句话说,虽然我们在逻辑-数学语言和日常语言中都使用“真”和“假”这两个标签,但是这两种使用中所表达的意义并不相同。因此,维特根斯坦认为逻辑/数学命题都是拟命题(pseudo-propositions)。
 既然维特根斯坦认为数学命题是拟命题而非真正命题,那么:对于维特根斯坦,数学是不是跟物理和化学等经验科学一样,是发现真理的学科呢?从下面两节可知,中后期维特根斯坦认为:数学并不是一个发现真理的学科,而是一种发明;而且这种发明会导致不可判定的命题;故他主张:数学家的发明活动应当受到限制,而不能发明导致不可判定命题的无穷数学实体。但前期维特根斯坦却并未宣称数学家发明数学。而且他认为,“对数学命题进行证明的可能性,仅仅意味着:它们的正确性,不必通过将它们所表达的内容与事实进行比较来确定,就可以被认知到(perceived)”。这里的“可以认知到”意味着:数学命题的正确性可以纯粹通过句法方式来判定,不存在不可判定的命题。有些学者可能会认为,在这里维特根斯坦的注意力只在“不必……与事实比较……”,而不在于“可以被认知到”。但上述细节表明,前期维特根斯坦的数学直观是:数学命题的正确性可以只通过证明来认知到。对于数学命题是否不可判定,他并没有考虑到,甚至他很可能拒绝认为存在不可判定的数学命题。而这意味着维特根斯坦的“数学命题”概念是与“可认知到”或“判定性”概念相联系的。所以前期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因不可判定的数学命题而拒绝无穷的数学实体。
既然维特根斯坦认为数学命题是拟命题而非真正命题,那么:对于维特根斯坦,数学是不是跟物理和化学等经验科学一样,是发现真理的学科呢?从下面两节可知,中后期维特根斯坦认为:数学并不是一个发现真理的学科,而是一种发明;而且这种发明会导致不可判定的命题;故他主张:数学家的发明活动应当受到限制,而不能发明导致不可判定命题的无穷数学实体。但前期维特根斯坦却并未宣称数学家发明数学。而且他认为,“对数学命题进行证明的可能性,仅仅意味着:它们的正确性,不必通过将它们所表达的内容与事实进行比较来确定,就可以被认知到(perceived)”。这里的“可以认知到”意味着:数学命题的正确性可以纯粹通过句法方式来判定,不存在不可判定的命题。有些学者可能会认为,在这里维特根斯坦的注意力只在“不必……与事实比较……”,而不在于“可以被认知到”。但上述细节表明,前期维特根斯坦的数学直观是:数学命题的正确性可以只通过证明来认知到。对于数学命题是否不可判定,他并没有考虑到,甚至他很可能拒绝认为存在不可判定的数学命题。而这意味着维特根斯坦的“数学命题”概念是与“可认知到”或“判定性”概念相联系的。所以前期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因不可判定的数学命题而拒绝无穷的数学实体。二
中期维特根斯坦的数学发明论
(一) 数学实体和数学真理的发明
从前期到中期,维特根斯坦受布劳威尔和希尔伯特的影响,被可判定性问题所吸引,从而其数学哲学经历了一些转变而变成发明论者。他认为:数学家发明数学。他利用“质数的数量”概念的使用案例来说明为什么“数学家发明数学”。他认为,“质数”概念来自“口头语言”,而且它一直以有穷的方式被使用。比如,命题“7是一个质数”仅仅意味着“用小一点的数去除7一直有余数”。然而,一旦数学家制造出这个概念,他们就会追问“自然数中有多少个质数”这样的问题。这就像给出“这个房间里的人”这个概念之后,人们会问“这个房间里有多少人”。然后他们会定义出一个包含所有质数的集合。这个集合就像“房间”包含了所有“这个房间里的人”那样包含了所有质数。并且他们还会继续追问“是否存在有穷个质数”。虽然这些问题听起来像是“真正的问题”,但是维特根斯坦认为它们只是一些由数学家引起的、容易误导人的“错觉”。所以他得出结论,“只有在我们的口头语言中,才有数学上‘迄今为止尚未解决的问题’或‘每个数学问题的有穷可解性问题’”。简而言之,他认为,数学家首先“制造”出一些诸如“质数”“质数的集合”的数学概念,然后“制造”或追问一些关于它们的问题,最后尝试去发现一些解法。
 在此观点下,维特根斯坦自然就会有下面观点:数学演算的符号并不指称任何事物。他认为数学符号缺乏意义,它们并不是事物的代表(proxy)。他写道:“算术关心的是模式||||。——但是算术是在谈论我用铅笔画在纸上的这些线吗?——算术并不谈论这些线,它用这些线进行操作(operate)。”这意味着“算术并不谈论数,它运转(work)数”。所以,在中期维特根斯坦的观点里,数不是事物或对象,而且数学不是指称性的。
在此观点下,维特根斯坦自然就会有下面观点:数学演算的符号并不指称任何事物。他认为数学符号缺乏意义,它们并不是事物的代表(proxy)。他写道:“算术关心的是模式||||。——但是算术是在谈论我用铅笔画在纸上的这些线吗?——算术并不谈论这些线,它用这些线进行操作(operate)。”这意味着“算术并不谈论数,它运转(work)数”。所以,在中期维特根斯坦的观点里,数不是事物或对象,而且数学不是指称性的。除了对数学实体持发明论外,维特根斯坦还认为数学家并不是发现而只是发明数学真理。因为他认为数学真理并不是先在的(pre-existing),即并不是“已然在那而未被人知的”。这里“先在的”的意思就好比“一个满的盒子”里的“内容”对于研究者的调查而言是先在的。然而有一些数学家可能会说,数学真理当然是“已然在那未被人知的”数学实体间的关系。当问及他们“你的‘已然在那’之物是什么”时,他们可能回答说,“数学的可能性”。就像两点之间未画出的直线已然在那?那是什么东西呢?这里是什么在误导我们?维特根斯坦说道:“‘可能性’一词当然是误导性的,因为有人会说,现在让那些可能的变成现实的(actual)。在如此思考时,我们常会想到时间过程,并从数学与时间无关这一事实推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性(已然)是现实性。”从而“数学的可能性”就是“数学的现实性”。但“两点”间并没有“现实的线”。
(二) 数学家的发明活动应受限制
那么数学家对数学实体和数学真理的发明活动是否可以不受限制呢?中期维特根斯坦认为并非如此,他拒绝无穷的数学实体及其相关命题。
第一,无穷的数学实体是永远无法完成的,从而是无意义的发明。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用有穷数来回答“……有多少……”这样的问题。尽管我们也用与此类似的方式来使用“无穷基数”,但是我们并不是以相同的方式使用它们。维特根斯坦认为,“无穷”并不是一个像有穷数(比如5)那样的“量”,而是一种“无穷可能性”。一个无穷的类是一个递归的规则,或一个归纳。然而,用以表示有穷类的符号是一个列表。他还认为,
‘所有自然数’这个概念并不是一个有限的或受约束概念……我常常说你不能谈及所有的数,因为并没有‘所有的数’这种东西。那只是对一种感觉的表达。严格地说,……在算术中我们永远不是正在谈论所有的数。如果一个人仍然按这种方式说话,那么可以这么说,他发明了一些无意义的东西来填补算术事实。
除了无穷基数,维特根斯坦还认为,“一个无理数并不是一个无穷十进制分数的外延(extension)……它是一个法则(law)……它不是一个外延。一个实数是一个无止境地产生十进制分数的位置的算术法则”。对他而言,无理数与无穷基数一样,也是无法完成的,是数学家无意义的发明。此外,维特根斯坦还拒绝关于无穷的数学命题,即反对在无穷域上的量化。他认为,带有无穷域的命题包含了无穷的合取支,所有这些合取支无法全部枚举。有的学者会认为这是“人类的弱点”。但是由于这个序列是无止境的,故这种无能同样适用于上帝(全知的存在者),而不仅仅适用于人类。
 第二,带有无穷数学实体的命题会导致不可判定性,从而这种数学命题也是无意义的。
第二,带有无穷数学实体的命题会导致不可判定性,从而这种数学命题也是无意义的。数学命题的判定性是维特根斯坦拒绝无穷的数学实体及其相关命题的最重要的原因。就像前期维特根斯坦认为数学命题的正确性是可以被认知到的,后期维特根斯坦也认为,每个真正的数学命题都是可判定的。如果一个数学问题“在原则上是不可回答的”,那么它是“毫无用处的”且并不是“有意义的”。“只有那些具有解法的地方才有问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在找到解法之时才有问题’)。”但是为何他会认为:不可判定的数学命题是无意义的,从而是拟命题?什么是一个数学命题成为真正数学命题的必要条件?对于维特根斯坦而言,其关键是排中律。他认为,断定命题的真假不可能是先验(即逻辑)不可能的。所有真正的数学命题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的,但那些不可判定的命题貌似违反了排中律。故维特根斯坦说:“数学命题与真正命题之间共同的地方只在于它们都能够被回答……如果排中律不适用于不可判定命题,那么其他逻辑定律也不适用,因为在那些情况下我们不是在处理数学命题。”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判定性”与“排中律”概念是紧密相关的。对他而言,如果一个命题是不可判定的,那么它就违反排中律。他以一种激进的方式强调算法判定性的重要性:“在数学中,所有事物都是算法。”一个数学命题,只有在我们知道或者原则上能够找到一个它的可应用的判定程序时,才是一个真正有意义的命题。然而带有无穷数学实体的命题可能会导致不可判定性。因此,他把这种数学命题从真正的数学命题中区分出来。因此,对维特根斯坦而言,所有命题至少可以被区分为下面这三类:真正的命题(谈论实在的经验命题)、拟命题(那些真正的逻辑命题和数学命题)和带有无穷域的拟逻辑或拟数学命题(如费马最后定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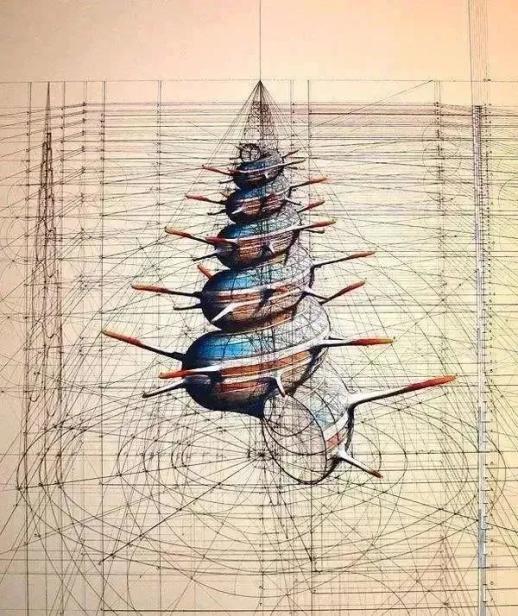 除了诉诸排中律之外,维特根斯坦将不可判定数学命题排除在真正数学命题之外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认为“每个数学命题都必定属于一个数学演算。”这意味着,每个真正的数学命题都必定在某些演算系统中是可判定的。他甚至还坚持一种激进的观点:如果一个命题和一个演算之间具有一种“联系”或“桥梁”,那么“肯定能够看到它”。这里的“看到”意味着可判定性。维特根斯坦说道:“可以这么说,不可判定性预先假定了这两边有一个秘密的联系;也预先假定了这个桥梁不能用符号建成……一个存在却不能用符号变形来表征的符号间联系是一个不可能想象的想法。”对维特根斯坦而言,这意味着不可判定性在真正的演算中是不可能的,从而所有的真命题都是可判定的。
除了诉诸排中律之外,维特根斯坦将不可判定数学命题排除在真正数学命题之外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认为“每个数学命题都必定属于一个数学演算。”这意味着,每个真正的数学命题都必定在某些演算系统中是可判定的。他甚至还坚持一种激进的观点:如果一个命题和一个演算之间具有一种“联系”或“桥梁”,那么“肯定能够看到它”。这里的“看到”意味着可判定性。维特根斯坦说道:“可以这么说,不可判定性预先假定了这两边有一个秘密的联系;也预先假定了这个桥梁不能用符号建成……一个存在却不能用符号变形来表征的符号间联系是一个不可能想象的想法。”对维特根斯坦而言,这意味着不可判定性在真正的演算中是不可能的,从而所有的真命题都是可判定的。三
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数学发明论
后期维特根斯坦仍然坚持他中期的数学发明论,即数学家“发明了”了数学。他说道:“数学家不是发现者,他是发明家。”这里的“发明”概念,并不仅仅是指“数学机器”的“发明”,还是数学真理的“发明”。换句话说,数学家不仅发明了数学实体,还发明了数学真理。
对维特根斯坦而言,有些人(如罗素和弗雷格)会提出一些误导性的数学观。这些数学观认为数学真理已然在数学实在里,就像两点间直线“已然”在“几何王国”或“欧几里得天堂(Euclidean heaven)”,即使“没人把它画出来”。在这种类比中,“数学实体”对应着几何中的点,关于“数学实体”的数学真理则对应着两点间未画直线时那条可能的直线。维特根斯坦反对这种把可能性当成现实存在性的误导性的观点。从他的观点看,当数学家在证明数学命题时,它们正是在尝试“画出”这“两个点”之间的“直线”。因此,维特根斯坦的数学实在是一个只有“点”或“数学实体”,而没有未画之“线”或未证之数学真理的数学“王国”。总的来说,他认为:数学家首先发明“无时间的(timeless)”的数学王国;然后逐个发明那些“无时间的”数学实体(这些数学实体一旦发明就被数学家放进数学王国里);最后发明关于那些数学实体的、同样是“无时间的”数学真理(但这些被发明的或被“画”的“线”并不是“已然”在这个数学王国里的)。那些“线”或数学真理并不是在数学实体被发明之后就同时被发明或“已然”在数学王国里。它们是数学家在证明或“画线”时才被发明或被“画”出来的。那么,为什么那“直线”或数学真理并不是“已然”在维特根斯坦的数学实在里呢?其实,维特根斯坦的“已然在那”概念与实在概念是紧密相关的,但是数学是一种与实在毫无关联的发明,所以数学真理不可能是“已然在那”的。
那么在发明数学实体或“画点”时,为什么那些数学真理或“直线”不是同时也被发明出来并被“放进”数学王国里?从维特根斯坦的角度看,两个特定的“点”之间那条未“画”出的“直线”或未经证明的数学命题,与数学实体是不相同的两类事物。尽管它们都是被发明之物,但是借助不同的方式:数学实体是通过定义来发明的;然而数学真理是通过证明来发明的。而且后者是“跟随”前者的定义而来的,是一种随附性。这个“跟随”或随附性意味着:一旦前者通过定义被发明出来,后者就被前者的定义所确定下来,而不能随意地“发明”,即只能依赖这些已定义数学实体的性质通过证明的方式去“发明”那些已被确定的必然性。因此,数学真理是一种介于纯粹发现(如对经验规律的发现)和纯粹发明(如数学定义、电灯泡的发明等)之间的“事物”。说它们是发明的,是在它们并非“已然”在实在之中这个意义上说的;说它是发现的,是在描述它们从未被证明到被证明出来的过程。它们就像“画两点之间的直线”那样被发明出来。
从上面的论述不难发现,维特根斯坦的“发现”“已然在那”“事实”“对象”和“实在”等概念是相互关联的。因此,对他而言:第一,数学是与实在无关的;第二,数学家发明了而不是发现了数学实体;第三,数学中不存在数学事实;第四,数学真理并不是“已然”在某处等待数学家去发现的。数学并不是像矿物学那样——是“发现”在“实在”里“存在”的“对象”及其“事实”——的学科。这也说明了为何后期维特根斯坦警告说,“把算术当成是数的自然史(矿物学),这是一种错误”。
在数学发明论的基调下,后期维特根斯坦仍然像中期一样拒绝无穷,认为数学发明应当受到限制。他说道:“数学命题中的无穷十进制小数的概念并不是序列的概念,而是序列的不受限制的扩展方法。”类似的,他依旧拒绝无穷基数。尽管我们经常像使用有穷数那样用“无穷”和“无穷多”这两个词来回答类似于“……有多少……”这样的问题,但维特根斯坦认为无穷和有穷是两类不同的技术(technique),无穷看起来似乎是非常极大的数,但它不是巨大的“外延”,甚至都不是一个“外延”。自然数集合的基数并不是一个不与任何(有穷)“外延”相对应的基数。所以他建议在数学上“避免使用‘无穷’这个词”。
除了拒绝无穷的数学实体,后期维特根斯坦通过不可判定性拒绝在无穷域上进行量化的命题。他的有穷主义和可判定性概念是紧密关联的。有些带无穷域的命题是不可判定的,从而是违反排中律的,因此他拒绝把它们归为真正的数学命题。他还认为这种不可判定性并不是人类的缺点,即使是上帝——全知的主体——也不能判定。这是因为这个域是无穷的,即使上帝也只能像我们凡人那样通过数学来确定数学问题。所以维特根斯坦说:“在数学方面我们跟上帝知道的一样多。”比如,“在圆周率π的十进制小数扩展中,‘5’总共出现了偶数次”。即使是上帝也只有那些数学规则来判定这些命题,从而在这些案例中上帝的全知并无优势。
四
发明与发现之间
上面对维特根斯坦的数学发明论进行了梳理和辨析。他的数学发明论具有三个内涵:第一,他认为数学实体是数学家所发明之物;第二,他认为数学实体间的数学真理也是数学家的发明;第三,数学家的发明活动应当受到限制,而不能发明出无穷的实体和不可判定的关于无穷的命题。这些观点颇受学界争议,大部分数学家当然不会同意这种观点,但这些观点也颇具启发性。这一节笔者将表明:数学并不全是发现,也不全是发明,而是居于发明与发现之间的事物。
数学并非完全与实在无关,而是“由于经验而被引入”,而后数学家将它“与经验独立开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用类似于“2个苹果加3个苹果等于5个苹果”这样的命题来描述事实。然后,我们也常像“2加3等于5”这样来简述上面这个命题。然后,就有一些人对后面这个表达更感兴趣,并开始扮演数学家的角色。后面这个表达式也貌似跟前一个表达式一样富含意义。但是前后二者实际上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类表达式。前者是在日常意义上使用的,而后者是在数学意义上使用的。人们常对这两类表达式不做区分,把前者当成是数学表达式,也把后者当成是日常意义上的表达式。其原因在于,这两个表达式相似的形式使得后者听起来像是一个与前者类似的、关于实在中对象的、真正的命题。进而,“2”和“3”不再是量词,而被称为数的专名。这个从量词到数的专名的身份转变是一个大的转变,也是数学家的发明。这导致两个表达式之间的差异变得非常大,它们是两个不同“语言游戏”里的表达式,却使用了类似的符号和表达形式。
类似的,我们也常使用类似于“这是圆形的物体”或“这是三角形的纸片”这样的命题。但部分具有理论兴趣的研究者常常对形状本身感兴趣,从而忽略这些形容词所描述的对象,而只关注其形状。然后在表达上只谈及特定形状,并用新名字“圆形”或“三角形”来称呼它们。自此以后,特定形状的类就用几何学里的通名来命名,这就像用真正的通名来命名实在里的类一样。如此类推,不仅数量和形状可以成为专门学科的对象,颜色和问题的困难程度等都会成为对应的专门领域(如色彩学和图灵度理论)的对象;这些领域的研究者都会对这些性质进行名词化,从而形成新的抽象实体。
一旦数学实体被发明出来后,数学家们需要一个“空间”来存放它们;就像特殊物体需要像“宇宙”或“实在”这样的“房子”“仓库”那样。于是,数学家发明了一个数学空间。这个空间是“无时间的”,它“存放”了大量同样是“无时间的”数学实体,如数、集合、平面形状和其他数学结构。当然,这个数学空间不是日常语言意义上的实在,而是一个被发明而成的拟空间。一旦发明了这个空间,我们可以定义任意的、无时间性的数学实体,并同时将它们“放进”这个空间之中。这意味着这个空间并不像实在那样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膨胀的,即还可以将新定义的数学实体添加进数学空间之中。比如,我们可以定义这样一个不足道的数学实体,即{1,2,3,边长为4的正方形},进而证明下面这个数学命题,即“在这个集合中存在一个数和一个正方形,使得这个数是那个正方形的边长的开方”。显然这个数学实体是个真正的数学实体,而且这个数学命题也是真正的数学命题。
一旦数学空间和实体被发明出来,发明者就成为真正的数学家,他们开创了一个数学学科。在这个学科里,数学家们使用特定的语言来指称和描述研究对象,这正如我们使用日常语言来描述实在中的事物那样。但对于维特根斯坦而言,数学并不是指称性的。这是因为他的“指称”与“对象”概念是密切关联的,而“对象”概念又与“实在”概念相关联。然而数学是人类的发明,数学实体都不是“实在”中的对象。所以类似于“‘13’这个符号具有指称”的命题是一种矛盾,从而是无意义的。但在数学直观中,“13”和“√1+3+5+160”这两个物理符号当然“指称”了某种东西,就像专名“珠穆朗玛峰”和摹状词“地球上最高的山”那般。那么,我们是否应当说这些数学符号具有指称呢?如果是,它们指称了什么东西?笔者认为,它们(在数学而非日常的意义上)“指称”了不与“实在”概念相关联的数学实体。因为我们常常在日常语言和数学语言中使用一些共同的符号,比如,数量词、“命题”“真/假”“实在”“发现”“指称”“性质”“关系”“多少”等,但它们在这两种语言中的角色,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同的,却在另一种意义上是相似的。在日常的意义上,数学并不是指称的,数学领域里没有对象,对象只在实在之中。然而,在数学的意义上,数学又是指称的,数学符号指称的是数学实体,这些数学实体是存在于数学实在中的拟对象,而不是实在之中的对象。那么无理数——比如√2——指称的是什么呢?维特根斯坦认为无理数并不是数,因为无理数是无法完成的。但笔者认为并非如此。√2当然是一个量的名字,从而在数学的意义上“指称”了一个数。比如,边长为单位1的正方形的对角线长度是√2。由此可见,几何学是不能没有无理数的。只不过无理数在十进制表示系统中是永远不可能完成的。数学家需要一个“空间”,使得无理数在那个“空间”里是完成的。这个“空间”就是被数学家发明的数学世界。
那么数学真理是否“已然在那”等待被发现呢?维特根斯坦的回答是否定的。但是为什么很多数学家的回答却是:数学真理在被发现之前就“已然在那”呢?“那”里又是哪里呢?实在,还是数学世界?“已然在那”这个词经常在日常意义和数学意义上被使用。当维特根斯坦否定数学真理“已然在那”时,他是在日常意义上使用“已然在那”这个短语的,而这个意义跟“实在”概念是相关联的。如果考虑这个词语在数学语言中的意义,我们可以说,一旦相关数学实体通过定义被发明出来时,数学真理就同时“已然在那”数学空间里了。当然在数学家发明数学实体时,数学家并没有同时发明这些数学真理。数学真理只是,在随附性的意义上,自己“跟随”数学实体而来,并“藏”在已被发明的数学空间里。这些数学真理就像隐藏在实在中的因果律,等待着科学家去发现。比如,一旦我们定义了集合{1,3,5,7},并把它“放进”包含5的数学空间里,那么数学真理“5属于集合{1,3,5,7}”就“跟随”这两个数学实体而“已然在那”数学空间里等待被发现了。所以,在数学的意义上,数学真理确实是“已然在那”等待被发现的。那么这个发现的过程是怎样的呢?对于这一点,笔者赞同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数学世界里的“发现”与实在中的发现是相互区别的。数学真理不是一种在日常意义的“发现”,而是一种特殊的、非日常意义的“发明”。我们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发现”数学真理,这种特殊方式就是证明。
对于带有无穷论域的数学命题,后期维特根斯坦认为:它们并不是真正的数学命题。因为他认为,带有无穷论域的命题会导致不可判定性,这意味着对排中律的违反,而真正的数学命题必然满足“排中律”。问题是:不可判定命题真的违反了排中律吗?并非如此。即使一个数学命题在本质上不可判定,它仍然是非真即假的。比如,“在圆周率π的扩展中,存在超过2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个‘7’”,这个命题当然是非真即假的。它的真值属性是数学本体论层面的性质,而它的可判定性则是数学认识论层面的性质,因此,这两种性质是相互独立的。尽管一些数学命题是不可判定的,它们仍然在数学世界里非真即假地“已然在那”“等候”被发现。这也是数学家总是把不可判定命题当成真正数学命题的原因。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第一,虽然日常语言和数学语言中使用了共同的术语,但它们都是在不同的意义上被使用的;第二,我们不仅应当知道日常语言是如何应用于实在之中的,还应当知道数学世界是如何被发明的,并且数学语言又是如何应用于数学世界的;第三,数学并不是力图发现实在中真理的经验科学,而只是研究被发明数学实体的性质和关系的学科,是一种居于发明和发现之间的学科。当然这不是说数学实体是与现实生活完全脱节的随意构造物,也不是说数学真理于现实生活毫无用处。数学的应用是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运用,是从数学的天堂下降到人间服务于人类。
来源:《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20年第4期,第15-20页。
 原标题:《发明与发现之间:论维特根斯坦的数学观》
原标题:《发明与发现之间:论维特根斯坦的数学观》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6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