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出租屋文学”里有什么?迁徙世代的家庭想象 | 涟漪效应

毕业季一向是租房旺季,这个夏天,又有一大批年轻人即将搬入自己人生的第一个出租屋,他们会在这个空间里完成自己新旧身份的转变——成为一个社会人,也将基于此地,向更广阔的城市空间进行探索。
在倡导生活美学的小红书上,出租屋改造始终是大热的词条:“楼道破,关我屋里什么事?”、“爆改30㎡老破小”、“妈妈以为我在上海出租屋过得很惨”……大量关于漂泊与租房的感受、经验和段子被批量炮制出来,形成一种独特的“出租屋文学”。租房的生活意味着脆弱、变动、漂泊、不占有,也意味着一种轻盈的力量,意味着变革与流动的可能性。脱离大家庭在异乡独自生活,在大都市的出租屋里,有着属于成年人的“后青春期”吗?从千禧年初《蜗居》《裸婚时代》《北京爱情故事》中的出租屋,到如今的“出租屋文学”,出租屋这一特殊的空间所承载的意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作为迁徙的世代,今天的我们如何理解租房这件事?
通过讨论、想象一种“租”的生活,我们期待看见更多格外的活法。
以下为文字节选,更多讨论请点击音频条收听,或【点击此处前往小宇宙App收听】,效果更佳。
【本期嘉宾】
夏周
文学编辑,播客《席地而坐》主播。
普照
文学编辑,编辑有非虚构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递》等。
【本期主播】
柳逸
澎湃新闻·镜相工作室 非虚构写作编辑
【收听指南】
08:38 精致又悬浮:上海梧桐区生活图鉴
16:08 疫情之后,我和社区的链接感更强了
20:08“妈妈以为我在老破小过得很惨”:出租屋文学在反抗什么?
26:55 爱情地狱or友谊乌托邦?出租屋寄托了千禧年初的家庭想象
32:59 萧红、鲁迅、沈从文、张爱玲......沪漂作家与黄金时代
42:15“东京8平米”如何可能?年轻人为何涌进酒店洗衣房?
48:42 706社区、定海桥互助社......生活可以是一场实验吗?
53:00 韩国的出租屋文学:“半地下”里的露馅人生
【本期福利】
欢迎在小宇宙单集评论区留言,我们将选取一位听众送出图书盲盒一份!
【本期配乐】
591——郑宜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通过小宇宙节目主页公告栏加入“涟漪效应听友群”,解锁更多福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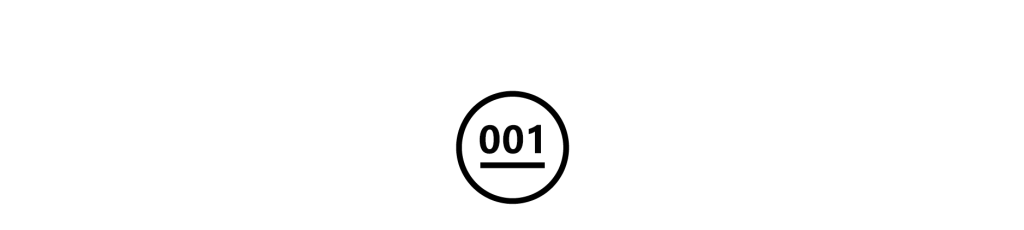
妈妈以为我在上海老破小过得很惨:“出租屋文学”在抵抗什么?
柳逸:
我自己因为用小红书特别多,经常会发现上面有大量关于出租屋的各种笔记,它已经形成了一种类似于景观的存在。所以我会给它贴一个标签,觉得这像是互联网上的“出租文学”。比如像“爆改30平米老破小”,或者是强调家里家外巨大反差的“楼道破关我屋里什么事?”“妈妈以为我在上海出租屋过得很惨”“上海月租2500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关于出租屋改造或者在出租屋里追求精致生活的各种段子正在被大量炮制出来。
我个人的观察是,千禧年初的出租屋,要么被悬浮成像《爱情公寓》里的那种非常乌托邦的存在,要么就是被污名化。在像《蜗居》这样的影视作品中,或者在《北京爱情故事》《裸婚时代》中,出租屋多少都被呈现为一种会扭曲美好的一种空间。
而在今天,我们这一代人再去谈论和表现出租屋时,很多时代的语境和情绪其实都发生了变化。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想聊聊,作为不断迁徙和流动的一代人,我们怎么看待出租屋。大家可以先聊聊自己的租房经历,有没有哪个房子让你印象特别深刻?你回忆那段经历时,觉得那个空间为什么会让你觉得特别难忘?
夏周:
我印象最深的是和朋友在上海“梧桐区”租的房子,因为客厅可以看到梧桐叶,步行还能到武康大楼。虽然那段时间因为个人生活计划的变化,很想离开上海,但回想起来,还是觉得那个区域很不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搬过去正好是2022年疫情刚结束,我除了被拉进小区群,还进了新华路街道的群。在那个群里看到了很多文化行业的从业者,周末还参加过新华社区营造中心的活动。新华路社区的居民会在那里卖咖啡、冰淇淋、可丽饼之类的,还有一些居民共创的杂志。我就在那些杂志上看到了很多平时活跃在豆瓣和微博上的ID,会让人觉得生活中文化氛围特别浓厚。
但在那样的街区,我又会有一种很强的悬浮感。一方面住在比较中心的位置,可以看到很多象征上海的符号,但另一方面总觉得自己只是暂时住在这里,谁知道一年后会发生什么变化。结果一年后我就离开上海了。
当时刚搬进去收拾房子的第二天,就发现空调插座有点问题。房东叫来了住在这栋楼里的一个比较热心的爷叔,让他帮我们清洗修理空调,他一边洗一边感叹“真的好脏”,然后又补了一句,“你们在外打工都不容易,我可怜你们。”所以我现在回想那段岁月时,感受到的是精致又悬浮。
一方面,我可以收获非常好的城市体验,而我认为除了上海之外,这样的体验很难找到,它有某种特殊性。与此同时,我也会时刻提醒自己,这样的生活其实并不真正属于我,我只是获得了一些美好而时髦的体验。所以我觉得那段岁月和生活有些悬浮,但同时也非常珍贵,尤其是现在已经离开了上海以后再回看。
普照:
我在现在的这个地方已经住了4年了,我不想搬家了,已经厌倦了搬家的生活,而且在这里甚至还建立了邻里关系。因为疫情期间,有一位上海阿姨家里的小猫没有吃的,我帮她买猫粮之类的。她那时家里发生了一些变故,情绪很低落,连去抢菜都没有力气,基本上都是我帮她去做这些事。后来她就挺照顾我的。我出去十来天,她会帮我喂猫。我想回礼,她也不要。她觉得这已经是一种很健康的邻里关系了,这在以前是没有的。我觉得如果没有疫情那种特殊的环境,我也不会和这样一位本地的阿姨有这样的往来吧。
柳逸:
确实,一些共同的经历,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都能帮助你真正获得一种社群生活,夏周也提到自己是疫情之后才被拉进街道群,好像在公共事件发生之后,才会真正有一种社区的参与感。
夏周:
那时候还有“楼长”,我经常在群里和楼长“吵架”。因为作为租客还是有很多权利无法得到保障,比如发放物资的时候,租客的物资被漏掉了,当时我非常生气,还在群里和楼长争论,我觉得作为租户,自己的权利一定要得到保障。但比较有意思的是,最后我要离开上海时,这位楼长还送了我防护服,当我见到本人的时候,我又觉得这个人似乎变得更加亲切了。
有时候我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注重这些微妙的权利。我现在住的房子其实是我买的,我的身份发生了转变,已经不再是租客了。但是我楼上的一位老爷爷,他对面的房子是租的,有时候他和我讲话时,天然带有一种房主的傲慢。他会说“对面那家常常点外卖,送餐员老是敲错门”,每次敲到他家时他都特别生气,然后他还会补上一句,“对面是租的”。哪怕现在我已经不是租客了,我还是会非常不舒服,因为我自己以前也是租客。像这样微妙的权利,以及你作为权利较低的一方的感受,都非常深刻。哪怕你住在一个很漂亮的地方,拥有很多时髦的体验,但这种权利的不对等仍然是我当时内心不安的底色。
柳逸:
所以围绕着这种“割裂感”,小红书上的网友们就生产了大量的段子。
比如标题是“妈妈以为我在上海老破小过得很惨”,内容是自己在家中非常精致的生活视频。还有比如“楼道破关我屋里什么事啊?”,大家不断地在强调,即使生活是临时性的,是租来的,但仍然要通过改造权、极致精致的生活美学,去对抗这种临时性和不稳定。
在上海租房其实就那几种建筑类型,如果你想要独居,其实你的选择非常有限。工人新村,就是大家常说的老破小,它是上海非常常见的一种生活形态。在类似这样的建筑类型中,楼道这个空间承载了大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一直到现在的生活痕迹,自然是很破败的。这就是公共空间给人的感觉。但作为租客,你在这里要开启的是自己全新的生活,于是就有了“楼道破关我屋里什么事”这样的说法。大家不断在强调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之间的巨大反差。虽然我的生活是临时性的,但我好像在这里建立了比那些拥有这个空间的人更好的一种生活。
至于“妈妈以为我在上海住老破小过得很惨”这样的梗,其实是在强调两代人对于幸福完全不同的理解。上一辈可能觉得有了房产才算有家,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出租屋中的那种幸福正在于它脱离了传统的大家庭,它是你自己可以掌控的小生活。
还有一种叫做“出租屋文学”的东西,它通常用来形容一种男女关系。比如张曼玉和黎明主演的《甜蜜蜜》,或者是《春光乍泄》这些电影中的爱情给人的感觉,甚至五条人的许多音乐也是这样,讲的是用极致的浪漫来对抗非常贫穷的生活。就像《阿珍爱上了阿强》歌词里说的,“虽然说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是爱情确实让生活更加美丽。”类似这样的出租屋文学,呈现出一种关于爱情的观点:我们的爱看起来很颓废,很贫穷,但却非常热烈。
夏周:
我自己其实也很喜欢点开类似的推文,我尝试从一个比较积极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抛开那些为了流量而取的夸张耸动的重复标题,我会理解为,这背后展现的是一种很强的生命力,是在有限条件下,热爱生活的人在努力改造自己的环境。就像我之前说的,租房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要求,但最后你会发现,必须舍弃其中一些,但你可以积极地改造,让它看起来没那么临时。
之前我听脱口秀演员Echo讲她二姐的生活,里面有一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二姐把鲜花和桌布带回了出租屋。”她的段子里,二姐的出租屋应该非常狭小和逼仄,但无论房子多么破旧,鲜花和桌布都是我们用心生活的证明。所以我觉得,“妈妈以为我在上海老破小过得很惨”,这种小红书上的叙事,其实可以看作是对主流生活的一种抵抗。
那我会想象,妈妈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下说出这样的话的。有可能她是想劝你,大城市生活不容易,所以还是回来过安稳的生活吧。因为买不起房,甚至租不到看起来体面的房子,难道你选择的生活方式就因此失去了合理性吗?所以,把外面破旧的空间温馨地改造,也会成为一种抵抗。“你以为我过得很差劲”,或者在主流社会的叙事中,好像被边缘化了,过得不幸福,但其实一点也不。实际上,很多女孩是在出租屋里获得了自由。这种生活很有可能是你小时候住的真正意义上的家,或婚姻生活,都无法给予你的。因此,我觉得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种抵抗。
柳逸:
我还有一个感受,出租屋和传统意义上的家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在于它带给你的时间感是不同的。如果你习惯了流动迁徙的生活,你可能每次搬家时都在不断舍弃一些东西。你最终会发现出租屋是一个没有过去痕迹的地方。有些人的家是他和父母从小生活的地方,他也许可以在房间里找到初中、高中等各种时期的痕迹,但出租屋就是一个没有过去、永远只有此刻和未来的空间。
由于你没有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所以在现实层面上,你并不能拥有过去,你只能不断摆脱“占有”,去过一种非常轻盈的生活。但是这样的空间给人的感觉,就是你永远可以面向未来去创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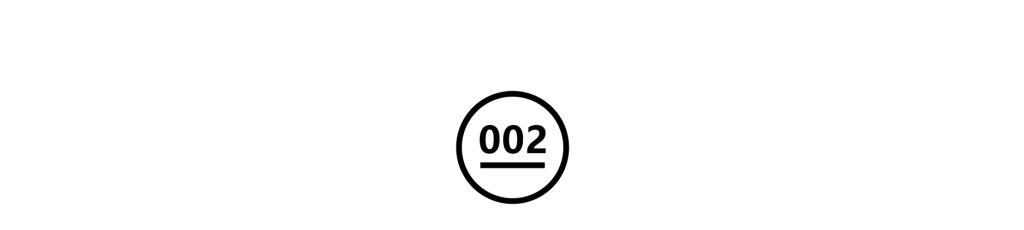
几代人的出租屋想象:从爱情地狱、友谊乌托邦到心灵家屋
柳逸:
我会觉得千禧年初关于出租屋的影视作品,其实存在两种非常极端的叙事。要么将出租屋生活描绘得特别美好,比如《粉红女郎》,以及更早的《老友记》,它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设定——因为种种原因,贫富差距很大的主人公们一起住进了一个大房子。在《粉红女郎》里,这栋大房子是一栋位于市中心的烂尾楼,是朋友的闲置资产。主人公们在屋子里过着充满友谊和幸福的生活。在《老友记》中,Monica则是继承了祖母的公寓,因为美国有租金管制政策,继承之后的租金不能涨价。总之,主人公们再一次有幸用很少的钱住进非常理想的住房,过上理想的生活。
很多基于出租屋的想象,实际上都是很失真的,要么就是非常扭曲的。像《蜗居》里的主人公海藻,她在这样的空间里生活,最终走向了堕落。甚至在她成为了别人的情人之后,那个男人还给了她一套公寓。包括像《裸婚时代》,它讨论的也是物质的匮乏最终会磨损爱情。
从当时到如今,其实关于出租屋的讨论至少变得更加切实际了。我想和大家讨论一下,你们觉得从影视作品的脉络上来看,出租屋所承载的意义有没有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普照:
这两个例子都挺极端的,一个是《老友记》,它是一部情景喜剧;另一个是朱德庸的漫画改编成的影视作品,它的体裁就已经决定了它必须是失真的,或者是有些悬浮的。我想到的是《武林外传》,它们的共同属性就是都是某种想象空间,而不是有实质的。
柳逸:
以《老友记》为典型吧,我们总是把以友谊为核心的家庭生活想象寄托在出租屋里,因为这种生活在现实层面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老友记》里Monica的公寓在现实中每月租金是4200美元,而剧情中Rachel每个月只需要付200美元租房。但通过《老友记》,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社会对于出租屋寄托了怎样的情感。
比如说2001年的911事件对《老友记》的剧情走向其实也产生了很大影响。911事件就发生在纽约,所以当时纽约是一个承受了巨大创伤的地方,似乎人人都生活在一种脆弱和不安全感当中。那时候的《老友记》正准备迎来第九季,当时整个剧组面临的困难是,我们如何在巨大的伤痛中创作喜剧。在这样的语境下,《老友记》彻底变成了乌托邦。制片人也知道这样的背景设置非常不现实,但人们非常需要这样的乌托邦,用以寄托我们对生活的想象,一种友爱、幽默、富有安全感的日常生活。那个出租屋几乎成了美国人情感上的避风港和安慰剂。
从这个意义上说,《粉红女郎》其实也很像这样一个作品,是一种悬浮的乌托邦,展现的是我们当时对一种以友情和爱情为核心的非传统家庭生活的想象。它好像也成了一个时代的寄托。
夏周:
现在,即使是现实主义题材的电视剧,其实对出租户的呈现也都挺悬浮的。其实社交平台上也有很多类似的讨论,有人说《三十而已》里的王漫妮,她租的房子是不是太夸张了?或者在《装腔启示录》里,唐影的工资是否真的租得起那个小区的房子?
如果你想了解那些真正真实、更接近普通人的租房体验,我觉得可以在脱口秀或者《一年一度喜剧大赛》这样的综艺里找到,这类内容我也很喜欢看。比如说,邱瑞最开始吐槽他自己租的奇葩户型房子,上厕所的时候都会被卡住。还有何广志,他之前分享过出租屋的段子,说自己住在上海7号线最末端,非常偏僻,他吐槽说,每次看到"禁止捕捉野生动物"的牌子都会很感动,因为觉得“这里居然也是有法的”。等到有钱以后,他租了一个比较大的房子,他又说“从客厅走到阳台就消气了”。这些感受都非常真实。
普照:
我觉得当代的很多事物都比较景观化,所以我现在都在读1949年以前的作品,我觉得还是要回到经典,他们写的东西更真实。比如萧红,大家真的以为她的“黄金时代”真的很美好吗?其实无论是在电影里,还是在她自己的笔下,在种种现实处境中,她始终是一个在城市中漂泊的写作者,一名写作的女性。她总是去鲁迅先生家拜访,经常写东西换点稿费,别人偶尔也会接济她一下。鲁迅开玩笑说,萧红在上海搬了几次家,却始终没搬出那条路,基本上一直住在那个地方。这么一个漂泊了一辈子的人,最后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远离东北老家的香港病逝。
但我读出了某种更强大的、超过我们现在讨论的“有产”“无产”概念的东西。当你更早地去了解这些人的一生,这个过程会让你对房子的执念没有那么重。无论是租房还是买房,整个看法都会有一种颠覆性的改变。所以现在我总是在想萧红,也在想沈从文。
我刚读完沈从文的全传,也知道他经历了战争时代以及后来更加混乱的岁月,他一直是租房的,从没有自己的房子,而且还拖家带口。甚至在每一个时期,他都很艰苦。但让我感动的是,无论多么艰苦,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事业。比如说,他后半生无法写作了,他就去做文物研究和整理工作。前半辈子倾注全部心血做的事业,突然换了一个轨道,是一件很艰难的事,但他似乎没有受多大影响,依然把同样的心血投入到另一件事情上。这一点很让我佩服。说到底,我觉得能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至于你在怎样的空间,独居还是其他状态,这些最终都不会影响到你。
柳逸:
我想到张爱玲。其实张爱玲和萧红,她们都是逃到上海的出租屋里的。萧红也是从北方家里逃出来的,所以上海的出租屋就成了她们的落脚点。在那种非常动荡的年代,她们给自己租来了一张书桌,然后在这里诞生了大量的作品。
我也一直在想张爱玲和鲁迅的上海漂泊经历。
比如鲁迅,他其实一直非常焦虑房租的问题。哪怕当时他已经很有名,但依旧会因为交不上房租而发愁,因此写了大量杂文。他觉得写小说赚钱太慢了,所以到后期甚至连和妻子的通信都要设法出版,其实就是因为很缺钱。
包括张爱玲,现在的她已经成为小资生活的代表,但其实你去看她的写作生涯,会发现这就是一个租客的一生。常德公寓是她诞生大部分作品的地方。那个公寓确实位于静安寺附近,现在看来是非常寸土寸金的地段。她当时和姑姑一起租住在那里,生活还算比较好,是一种比较体面的独居女性公寓生活。有管家、专门为你按电梯、打牛奶的人。但是她后来的生活就每况愈下,包括搬到美国以后,其实一直在住廉租房,经济非常拮据。为了赚钱,她去写好莱坞的烂剧本,甚至在多次搬家的过程中遗失了翻译的《海上花列传》的手稿。这些都是很让人心酸的故事。
让我特别心碎的一个细节是,张爱玲她年轻时写过一句话:“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这是她二十出头时写下的一句话。但到了晚年,她不断搬家,总觉得房子里有虱子,或者认为自己皮肤出了问题,不断去看医生。她到了晚年,几乎有一种心魔,就是觉得自己住的房子里有虫灾。我觉得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她对自己人生的一个隐喻。
她晚年的租房条件已经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单人小床,带浴室,没有炉灶,不怕虫子,无惧噪音,家里只留下纸箱和折叠床,行李随时可以丢弃。我在张爱玲写的租房条件里,其实感受到了一种离散的酸楚。这种离散不仅仅是在有产或者无产意义上的,更是一个现代人特有的离散的状态。
普照:
对,我觉得我们现在讨论的一些像《老友记》或者更当代的电视剧,它们的叙事时长大概就是几年到十年左右。但如果你把关注的时间跨度延展到一个人的一生,覆盖几十年,甚至民国时期的一百年,回过头再看,就会更明白所谓的“人如何变化”,人和房产的关系,或者说人与物的关系。
夏周:
其实说到文学作品中的租房,我想到《杀死房东太太》,张敦写过的一个小说,讲一对年轻人和房东老太太合租的故事。房东老太太非常严苛,不希望租客在房子里留下太多痕迹,也不想他们经常做饭,不希望厨房里有油烟,把灶台弄脏,于是提出各种要求。让你觉得虽然花钱购买了这个居住空间,但却无法正常使用,变得非常小心,像寄人篱下。所以这对夫妻就产生了杀死房东太太的念头。老太太在故事里真的被他们杀死了,他们把她放在了墓地里。后来他们决定不在这个房子里待了,想去戈壁。这时却发现,死去的房东老太太竟然又来找他们了,理由是:你们把我放错地方了,这不是我的墓,是别人的墓,现在我已经成了别人的租客了。
在现实生活中,活着的人需要付房租,死去的人在公墓里也可能成为租客。通过这样的反转,把租客和房东之间的权利关系展现得非常微妙。
萨利·鲁尼的小说中其实也有很多关于租房的片段和阶级的描写。比如说,《聊天记录》中的Frances出身于工人阶级,而她的好友Bobi则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在《正常人》这本小说里,康奈尔的母亲在玛丽安家做保姆。当玛丽安住进母亲提供的房子时,康奈尔还需要与别人合租,忍受窘迫的租房环境。她的第三本小说《美丽世界,你在哪里》中,主人公艾琳拥有文学硕士学位,但只能在文学杂志社拿着微薄的薪水,被姐姐称为“三十岁了还在干一份不赚钱的破工作并且住在合租房”的人。当艾琳的朋友爱丽丝因为畅销书搬进了郊区别墅时,艾琳还要面对室友长时间占用洗手间、没有热水洗澡的窘境。
读到鲁尼小说中的这些描写时,我觉得它与很多文化行业、尤其是较年轻的从业者的经历十分贴近。但这样的烦恼更像是一种隐性的压力,不像《杀死房东太太》里那种非常尖锐的矛盾、让人深陷泥潭的苦楚。
柳逸:
关于出租房相关的写作,我首先会想到韩国,因为我觉得韩国的情境可能与东亚更加贴近一些。我最先想到的是电影《寄生虫》里的那个半地下空间。《寄生虫》中有一个很经典的场景,洪水淹没了整个地下室,家里的东西都漂了起来。
围绕半地下空间,其实韩国有很多类似的表现,韩国的出租文学也展现了这样一种“半地下的人生”。
我记得金爱烂的《滔滔生活》里有一篇,讲的是一个做小生意的家庭,他们给女儿买了一架钢琴,钢琴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体面生活的象征符号,所以即使他们住在首尔的半地下,也想要在家里放一架钢琴。后来一场洪水把整个地下室都淹掉了,钢琴在洪水中被泡烂,然后我们跟随主人公一同发现,钢琴上的雕刻花纹其实只是贴皮贴上去的而已。
一个底层家庭,他们把钢琴当作一种阶级跃升的意象,但最后,这个意象在一场洪水中直接被淹没了。
半地下其实在韩国是一种特别普遍的建筑形态,在当时南北冲突的那十年间,政府规定所有建筑底层必须配备地下室。刚开始这些地下室并不是用来住人的,但后来由于租金紧张,加上地产危机爆发,很多地下室,特别是首尔的地下室,被开放出租。所以现在在首尔,有很多人都是住在半地下。《请回答1988》里面德善家就是住在半地下。
在金爱烂的“出租屋文学”中,她把暴雨作为一个很有趣的意象,雨本身是中性的,但当它落在韩国,落在首尔时,就变成了一种结构性的暴力。我们仿佛可以在其中发现某种模型,即“伪装——伪装最终被暴露”的故事模型。金爱烂的写作风格就是如此,她好像总是在书写那种夹缝中的人生。你以为自己伪装得很好,但其实最终还是会暴露。
夏周:
其实,现在买房的成本越来越高,经济下行的压力越来越大,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也不断增加。这些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无法租到好房子的人,实际上对持有房产的人也是很大的打击。你会发现,很多人在失业之后,房子就会变成法拍房。除非真的没有贷款,否则即使拥有房产的人也处于很大的不确定性中,根本无法预料未来会发生什么。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其实大家的处境都差不多?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其实租房的人和买房还贷款的人,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大区别。所有人都处于同样的不确定性中,大家都在担心自身是否会陷入困境。我们在讨论租房这个话题时,实际上是在探讨一种临时的生活状态,或者说,这种状态背后所暴露出的结构性的社会问题。我觉得,人有时候本来就是一个容易焦虑的生物,人总是在为自己的不安在买单的。
柳逸:
我们也许又可以回到那个最根本的“离散”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在读到像萧红、张爱玲、沈从文、鲁迅等人漂泊一生的经历时,会不会从中获得很大的力量?有时候我又会想,是不是因为我们作为文学读者,自带了一种文学性的滤镜,于是觉得在这种漂泊中似乎有某种巨大的能量。我想客观地讨论一下,大家是不是也像我一样,从这种漂泊的人生历程中汲取到了很多巨大的力量?
普照:
沈从文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生都在逆境中度过。他小时候就是一个看过砍头的小孩,见过很多颗人头在他身边掉落。从小就目睹这样的场面,以致后来他变成了一个充满大爱的人,我觉得是因为他很早就见证了生命的珍贵,以及死亡的近在咫尺,所以他对生命有着更强烈、更超乎常人的热情。
民国时期大家都在漂泊不定,经常过一段时间就有战争爆发,就要换地方、换城市,要随着战火的蔓延不断迁徙。其实那时候整个高校体系都是没有根基的,很多大学都是在临时租用一些地方,比如西南联大,或者其他学校。
在沈从文的观念里,是否有一个家并不重要。他觉得心里有挂念的人,有正在做的事情,再加上可以遮雨的屋顶和挡风的墙,这些就已经构成了他心中的“家”的空间。那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家,但这些事物,包括他租住的空间,构成了他心灵上的家。我觉得我们谈到家的时候,可能不只是指那样一个物质空间,不只是指它是租赁属性还是购买属性,它的整体意义其实还包含了很多心灵方面的内容。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6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