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执行和解恶意无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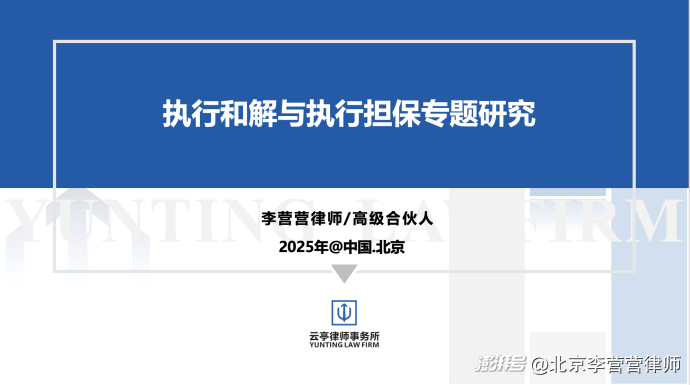
人民法院案例库:当事人恶意串通签订执行和解协议,效力如何?
和解协议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阅读提示:
当事人恶意串通签订执行和解协议,效力如何?李营营律师团队长期专注研究与执行有关业务的问题,并形成系列研究成果陆续发布。本期,我们以最高人民法院处理的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件为例,与各位读者分享法院审理类似案件的思路。
裁判要旨:
和解协议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案件简介:
1.2014年11月5日,台州某甲公司(转让人)与张某茂二人(受让人)签订《转让协议》,将其对林某铨三人(债务人)享有的债权转让给张某茂二人。约定:张某茂二人实现债权后,需代台州某甲置业公司偿还某笔债务(截至2019年2月,金额2.5亿余元)。偿还后所得余款以一定比例支付给台州某甲公司,作为债权转让对价。
2.2018年12月29日,另案判决就该笔转让债权确认:林某铨三人(债务人)应向张某茂二人(受让人)给付1.9亿余元,某乙公司就部分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3.2019年5月5日,张某茂二人(受让人)和林某铨三人(债务人)等达成《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将判决确认的应付款协商减至1.45亿元,并履行完毕。台州某甲公司(转让人)诉至浙江高院,以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为由,请求确认案涉和解协议无效。
4.2019年11月12日,浙江高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台州某甲公司请求,原告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最高法院。
5.2021年3月2日,最高法院二审判决撤销原一审判决,确认案涉和解协议无效。被告林某铨等人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
6.被告方认为,台州某甲公司不是适格原告,无权提起本案诉讼。案涉和解协议系在执行法院组织下促成的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恶意串通,应为合法有效。
7.2021年12月15日,最高法院认为,原告作为利害关系人有权提起本案诉讼,案涉债权转让对价根据张某茂二人(受让人)能够实现的债权数额确定,二人实现债权后需代原告清偿债务,二人与债务人恶意串通降低债务执行金额有损原告利益,和解协议无效,再审裁定驳回林某铨等人申请。
争议焦点:
案涉执行和解协议效力如何?
裁判要点:
一、被告林某铨等人提交的新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足以推翻原判决。
最高法院认为,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乙置业公司申请再审提交的新证据为福建省福清市公安局龙田派出所于2021年4月30日出具的《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于2021年4月25日作出的《询问笔录》《接收证据清单》及相关证据、于2021年5月3日作出的《询问笔录》、于2021年10月30日出具的《不予立案通知书》、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0日作出的(2019)京0106民初32017号民事裁定书、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1日作出的(2019)京02民辖终1101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904号判决确定的2.0019370438亿元中有7300万元涉嫌虚假诉讼,台州某甲置业公司的实际债权总额应扣除该7300万元。因此,案涉《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不存在恶意串通降低执行金额的情形。但本案审理的是张某茂、黄某与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乙置业公司于2019年5月5日签订的《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是否无效的法律关系,而非台州某甲置业公司与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故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乙置业公司提交的新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乙置业公司关于案涉《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的签订系考虑904号判决涉嫌虚假诉讼而非恶意串通降低执行金额的再审事由不能成立。
二、台州某甲置业公司作为利害关系人,有权向执行法院提起本案诉讼。
(一)台州某甲置业公司是案涉和解协议所涉执行依据中的案件当事人(第三人)。
最高法院认为,关于台州某甲置业公司是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的问题。经审查,台州某甲置业公司与张某茂、黄某于2014年11月5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台州某甲置业公司自愿将案涉上述全部《认购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和台州某乙置业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及代垫款项等往来结算对账确认函》中对于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乙置业公司、某丙公司、某丁公司所享有的包括但不限于土地使用权和股权转让款的债权本息及其他权益全部转让给张某茂、黄某;张某茂、黄某通过诉讼或非诉讼方式从林某铨等六债务人实现了债权,若张某茂、黄某实现的债权少于或等于台州某甲置业公司所欠张某官的借款本息、滞纳金,则张某茂、黄某须将实现的债权全部直接支付给张某官,以代台州某甲置业公司偿还台州某甲置业公司所欠张某官部分或全部的借款本息、滞纳金;若张某茂、黄某实现的债权超过台州某甲置业公司所欠张某官的借款本息、滞纳金,则张某茂、黄某在代台州某甲置业公司清偿台州某甲置业公司所欠张某官的借款本息、滞纳金的剩余款项中,张某茂、黄某的律师何某雄有权留取所实现债权的10%作为律师费,最后余款的50%作为张某茂、黄某收益,另50%作为债权转让款支付给台州某甲置业公司。”2015年9月10日,台州某甲置业公司与张某茂、黄某、何某瑞、李某龙签订《债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如果法院认定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乙置业公司按照《投资协议》及相关合同应付给台州某甲置业公司的土地使用权转让余款高于或等于2.6333730959亿元,则台州某甲置业公司转让给张某茂、黄某的债权本金数额确定为2.6333730959亿元,由该债权本金产生的利息等全部权益也转让给张某茂、黄某。”2018年12月29日,904号判决确认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连带给付张某茂、黄某土地使用权转让款198158473.38元,台州某乙置业公司在209860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2019年2月20日,债权人张某官以台州某甲置业公司至今仍未向其偿还分文借款本息为由向台州某甲置业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总额252120900元,其中本金118710000元,利息133350900元,其他60000元。2019年5月5日,张某茂、黄某和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乙置业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约定将904号判决确认的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及台州某乙置业公司应偿还共2.0019370438亿元减为1.45亿元,并于2019年5月6日前执行完毕《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由上述事实可知,台州某甲置业公司是904号判决所列的案件当事人(第三人),《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所涉的执行依据是904号判决。
(二)台州某甲置业公司债权转让对价系根据张某茂二人能够实现的债权数额确定。
最高法院认为,台州某甲置业公司虽将案涉债权转让给张某茂、黄某,但在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时并未明确约定转让对价,而是约定根据张某茂、黄某能够实现的债权数额来确定债权转让对价的支付及分配方式,支付的首要对象为台州某甲置业公司的债权人张某官,当有剩余款项时扣除律师费及张某茂、黄某的收益后,作为债权转让款支付给台州某甲置业公司。由此可见,案涉债权实现后的首要目的是偿还台州某甲置业公司对张某官的欠款,如实现的债权数额不足以覆盖应支付给张某官的全部欠款,则台州某甲置业公司仍需继续承担其对张某官的剩余欠付款项。
(三)台州某甲置业公司作为利害关系人,有权提起本案诉讼。
最高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关于“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和解协议无效或者应予撤销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台州某甲置业公司主张案涉《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减少了其受偿债权数额,亦影响台州某甲置业公司与张某茂、黄某、张某官的结算事宜,并主张《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存在无效情形,原判决认定台州某甲置业公司有权作为利害关系人向执行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并无不当。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乙置业公司的该项再审事由不能成立。
三、案涉和解协议签署和履行超出债权转让目的,恶意串通损害台州某甲置业公司利益,无效。
(一)张某茂二人受让债权目的系实现债权后代台州某甲置业公司清偿债务,行使权利不应超出该目的范围。
最高法院认为,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及台州某乙置业公司主张《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并未损害国家、社会及其他人的利益,符合法定程序且已履行完毕,不应确认为无效。经审查,鉴于张某茂、黄某通过《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补充协议》虽受让取得案涉债权,但根据当事人的约定,其受让债权之目的仅在于实现债权后代台州某甲置业公司清偿债务,故张某茂、黄某受让台州某甲置业公司债权后行使权利亦不应超出该债权转让目的的范围。
(二)张某茂二人降低债务执行数额,有损台州某甲置业公司利益,有违其受让债权的目的,属于恶意串通。
最高法院认为,在《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未得到台州某甲置业公司事先同意或事后追认的情况下,张某茂、黄某在履行《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中减低了债务执行数额,不仅有损台州某甲置业公司的利益,亦有违其受让债权的目的。原判决综合案涉相关事实,认定张某茂、黄某在明知债权转让目的以及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乙置业公司理应知晓其与张某茂、黄某在执行阶段签订《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关于降低债务执行数额的行为将有损台州某甲置业公司的利益,足以证明其存在主观恶意,属恶意串通,并无不当。
(三)案涉和解协议因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而无效。
最高法院认为,因案涉法律事实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原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之规定,认定案涉《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无效,亦无不当。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乙置业公司关于案涉《债权和解及担保协议》的签署和履行未超出案涉债权转让目的范畴未给国家、社会和其他人造成损害后果以及案涉《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符合法定程序且已履行完毕、被撤销或无效将使本案法律关系处于混乱状态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最高法院认为,案涉协议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而无效,再审裁定驳回被告等人申请。
案例来源:
《台州某甲置业有限公司诉张某茂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6599号],入库编号:2023-16-2-076-001
实战指南:
和解协议本质上也是合同,也存在无效或可撤销事由,“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就是其中一种典型无效事由。对于恶意串通的定义及其法律后果,想必无需赘述,依据本案,我们希望深入探讨如下问题:
一、本案当事人是如何通过签订执行和解协议损害第三人利益的?
首先,从制度背景来说,以确认给付义务的生效法律文书为执行依据,判决确认的权利人可向执行机构申请强制执行。同时,法律也允许当事人协商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对执行依据确认的债务履行方式、期限、金额等进行变更。一方面,这种制度安排体现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另一方面,如果当事人以协商和解取代强制执行,也有助于高效化解纠纷、节约执行资源。但是,执行和解协议的这一特性同样可能被恶意利用,成为当事人规避执行、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工具。
具体到本案,案涉债权转让协议涉及两个核心权利义务:第一,受让人在受让债权、实现债权后,需以债权的实际受偿金额代转让人清偿债务;第二,受让人应向转让人支付的债权转让对价,需根据债权的实际受偿金额按比例确定。据此,受让人在受让债权后,能够自债务人处获得的清偿数额,一是会影响代转让人清偿的数额,二是会影响转让人收取的对价。综合以上,受让人与债务人通过执行和解协议协商降低执行债务金额,会在减少其代转让人清偿的债务数额的同时,降低其应支付给转让人的对价金额,势必有损转让人利益。法院遂基于系列约定及具体履行行为、后果等,认定案涉执行和解协议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而无效。
二、虽然,最高法院最终支持了本案转让人诉请,确认执行和解协议无效。但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商事主体要通过“恶意串通”主张合同无效,实际并非易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和解协议具备无效或应撤销情形的,可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但是,司法实践中大量类似案例表明,商事主体依据该条规定,以恶意串通为由要求确认执行和解协议无效的,其诉讼请求往往难以获得支持。原因在于,商事主体要证明“恶意串通”事实,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程度,超过普通民事案件“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并非易事。
在此类案件中,代理人对证据的筛选、把握、统筹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由于恶意串通行为本身具有高度隐蔽性,遭受损害的商事主体与对方信息不对称,很难获取有力的直接证据。同时,这类案件对法官的审查技巧也有很高要求,代理人需要收集间接证据、尽可能完善证据链条,在此基础上展开系统的法律论证,以证明己方主张、争取法官内心确信。因此,对于意图主张恶意串通而致执行和解协议无效的商事主体而言,需充分认识到此类诉讼的证明难度,并在专业律师指导下,及早开展证据收集、固定工作。
法律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 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和解协议无效或者应予撤销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执行和解协议被确认无效或者撤销后,申请执行人可以据此申请恢复执行。
被执行人以执行和解协议无效或者应予撤销为由提起诉讼的,不影响申请执行人申请恢复执行。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 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延伸阅读:
1.当事人主张恶意串通、执行和解协议无效的,需达到“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否则需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
案例1:《邓铁云、贾正午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民事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案号: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晋民申4025号]
山西高院认为,关于实体方面,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再审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恶意串通,应适用上述“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采信标准。但申请人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亦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被申请人之间在另案中的调解协议、执行和解协议存在无效的事由,故原审认定申请人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并无不当。
2.执行和解协议符合法定情形的无效。协议能否履行并不必然影响协议效力。
案例2:《李某某、申某某民事申请再审审查民事裁定书》[案号: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3)内民申880号]
内蒙古高院认为,签订案涉《执行和解协议》时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案涉执行和解协议系双方当事人在人民法院主持下自愿签订,并不存在上述条款规定的无效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第(六)项规定,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屋不得转让。李某某在签订案涉执行和解协议时,案涉房屋未进行依法登记,李某某未领取权属证书,但上述规定是针对房地产交易过程中产生物权变动登记时所适用的管理性规定,李某某用以抵债的房屋能否交付属于合同履行问题,并不必然影响案涉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李某某关于案涉执行和解协议无效的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