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专访|羽戈:不为什么而读书
近期,青年学者、作家羽戈出版了新著《激进之踵:戊戌变法反思录》(山西人民出版社·汉唐阳光,2019年1月)和随笔集《不为什么而读书》(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10月)。前者是羽戈这些年来探索近代中国历史的成果,后者是他历年随笔文章的结集。
羽戈出生于1982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学法律出身,早年以时评成名,后来转向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写作,迄今已出版《从黄昏起飞》《穿越午夜之门:影像里的爱欲与正义》《百年孤影》《酒罢问君三语》《少年游》《岂有文章觉天下》《帝王学的迷津:杨度与近代中国》等多部著作。他的写作在同辈人中成熟较早,两本新著的语言也愈发凝练响脆。
3月24日,羽戈做客上海“星期天读书会”,与读者畅谈“如何阅读中国近代史”。在读书会后,我们和他聊了聊他的写作经历、阅读史和精神资源。

澎湃新闻:你的第一本书《从黄昏起飞》出版于2008年,其中收录了四篇读金庸的随笔。这次《不为什么而读书》的体例相似,但重写了谈曲非烟、令狐冲、张无忌的文章。你在后记里说,每年都要重读金庸,能否谈谈你眼中的金庸和金庸作品?
羽戈:金庸小说应该是一代人的共同记忆。小时候我父亲读金庸,我也跟着读。在小县城里,那是为数不多的阅读选择。
这些年来,我几乎每年都要重读金庸,重读次数最多的是《倚天屠龙记》和《笑傲江湖》。这两本书的主角,虽然结局相似,张无忌和令狐冲都选择远离江湖,退隐林下,不过他们并不是一种人,张无忌的性格温和柔弱,做事顺其自然、顺水推舟,讲究“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在令狐冲的内心,金庸刻意塑造出一种对自由的渴望与执念,自由高于门派,高于权力,不自由,毋宁死。要总结的话,张无忌的价值观是自然,令狐冲的价值观是自由。
对于金庸先生本人,很多人把他当做大侠,我不这么看。我对他的定位,乃是大商人、大媒体人。用“侠”评价他,可谓误判。侠客对应的是游民社会,商人以及商业精神,对应的是现代社会。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更需要商人精神,而不是侠客精神。
我在《少年游》里写过一个小时候的街坊,在他家里,我读到了金庸、古龙、梁羽生等人的文集。他的职业是澡堂的锅炉工,家里藏有两套正版的金庸全集,一套阅读,一套珍藏。那是1990年代,买一套金庸全集可能要花他两三个月的工资。正是从他身上,我体会到了读书的真意。那时常常在想,我们为什么而读书?为知识、为工作、为中国之崛起,总该有一个原因。我猜想他热爱武侠小说,可能是追随一种侠义的精神——我的故乡尚武成风,大有侠客横行的空间。拿这个问题问他,他的回答很直接,读书就是读书,没有为什么。当我后来开始思考读书的意义,想到“不为什么而读书”的时候,眼前便会浮现他淡定的模样。我承认“不为什么而读书”是一种理想状态,我自己很多时候也很难达到,但是难以抵达,并不代表不该追求。

澎湃新闻:在你的个人阅读史中,还有哪些关键的作品和人物?
羽戈:2002年春天我读到刘小枫先生的《拯救与逍遥》,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激烈的批判态度,所依赖的思想资源和凭借主要是西方基督教,二者对我而言都非常新鲜,正是这本书把我带入思想的大门。
影响我的第二本书,应是2003年我在重庆沙坪坝区图书馆里读到的朱大可先生的早年著作《燃烧的迷津》。那时我正处于一种迷茫、焦灼的状态,不仅思想惶惑,而且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这种惶惑,不知道该怎么写作,读完这本书后,我慢慢找到了一种写作的方法。
第三位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夏可君先生。他早年提倡心魂书写,我受他启发,意识到思想与语言的关系,开始审视汉语的变迁与出路,这构成了思想的一个基点。大学毕业前后,我一度对语言学很感兴趣,发愿写一本《汉语灾变史》,梳理20世纪汉语所遭受的种种劫难,历数汉语的“敌人”,文言、官话、党八股、欧化语体等等,还列过一个提纲,可惜此后不久,兴趣逐渐转向政治,无奈搁浅。
这之后,还得感谢止庵先生的书信集《远书》,他提出写作应该“勿渲染,勿夸饰,少少许胜多多许。”由此我开始注重追求简练、克制的语言,这也是我的写作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当然,说起对语言的锻造,最大的老师其实来自现实,来自编辑,来自审读者。他们教会我怎么使用精简、克制、隐晦的表达。

澎湃新闻:学法律出身,以时评成名,你是在什么机缘下转向历史写作?这些经历对写历史专栏有什么影响?
羽戈:我读大学期间,先后在律所、检察院实习,那些痛苦的经历,使我决心以后不去从事相关的职业。不过,生在人间,总得吃饭。机缘巧合,自大三开始,四处投稿,结识了一些媒体朋友,所以毕业前半年,我提前介入社会,在《重庆青年报》的《激动周刊》做采编,从此混迹于媒体,直到2011年夏天才彻底脱离单位,自由写作。
年轻的时候讲求博览,无书不读,这种状态大概持续到2007年中,此后有所觉悟,开始收束自己。那时一手写现实,一手写历史,主攻中国近代史,对清末预备立宪这段历史尤其感兴趣。2012年之后放弃时评写作,完全转向历史。
常有人问,你一个学法律的人,怎么去研究历史呢?我以为这二者并非风马牛不相及。我读法律专业,最大受益即司法逻辑的训练,司法逻辑比一般逻辑学更严谨,更能锻炼思维能力和证据精神。这是一种方法论,可以用来分析案件,同样可以用来研究历史,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且法学讲证据,历史学也讲证据,对证据的重视,对证据的发掘和辨析,也是法律与历史相通的一点。所以我觉得法律人研究历史,正有得天独厚的一面。大体而言,这两者的相通之处要大于迥异之处,其区别主要在于态度,法律更像工具,有些冰冷,有些严酷,历史则强调温情与敬意,了解之同情。

澎湃新闻:你在最近出版的《激进之踵》中反思戊戌变法,为什么选择这一历史事件来写?
羽戈:对于近代中国,我最想探究的是清末预备立宪这段历史。我认为从1901年到1911年,大清最后十年,可称为立宪时代。要研究预备立宪,必须往前走,回到义和团运动,回到戊戌变法,甚至甲午战争。
还有现实的刺激和考量。1990年代以后,中国迎来了“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态势,激进思潮被批,渐进思潮兴起,但激进和渐进之间是二元论的关系吗?主张激进就一定要告别渐进吗?我对此一直很怀疑。
写戊戌变法这段历史时,我最想做两件事,一是尽量回到当时的语境,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来看看康有为、谭嗣同们为什么选择了激进而非渐进的路径;二是试图证明激进和渐进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守旧。
在戊戌年间,乃至整个晚清时期,守旧派始终是庙堂之主力。只要守旧派在,激进和渐进的政治运动都不可能成功。从这个角度而言,戊戌变法是激进、也是渐进的失败。戊戌变法之后,二者显然都丧失了前进的空间,朝廷被守旧派把持,两年后爆发的义和团运动,正由守旧派所主导。
今天我们回头评判20世纪的中国,会发现一条清晰的脉络,那就是激进在1919年之后成为主流思潮。我在《激进之踵》序中引用过费正清的一段话,他在1943年9月的一封信里谈到,在当时的中国,“不激进无以成事”。我认为这七个字堪称中国近代史的最佳注脚。而激进思潮在中国近代史上导演的第一场政治运动,就是戊戌变法。如果我们要重审激进,就要回到原点,从戊戌变法谈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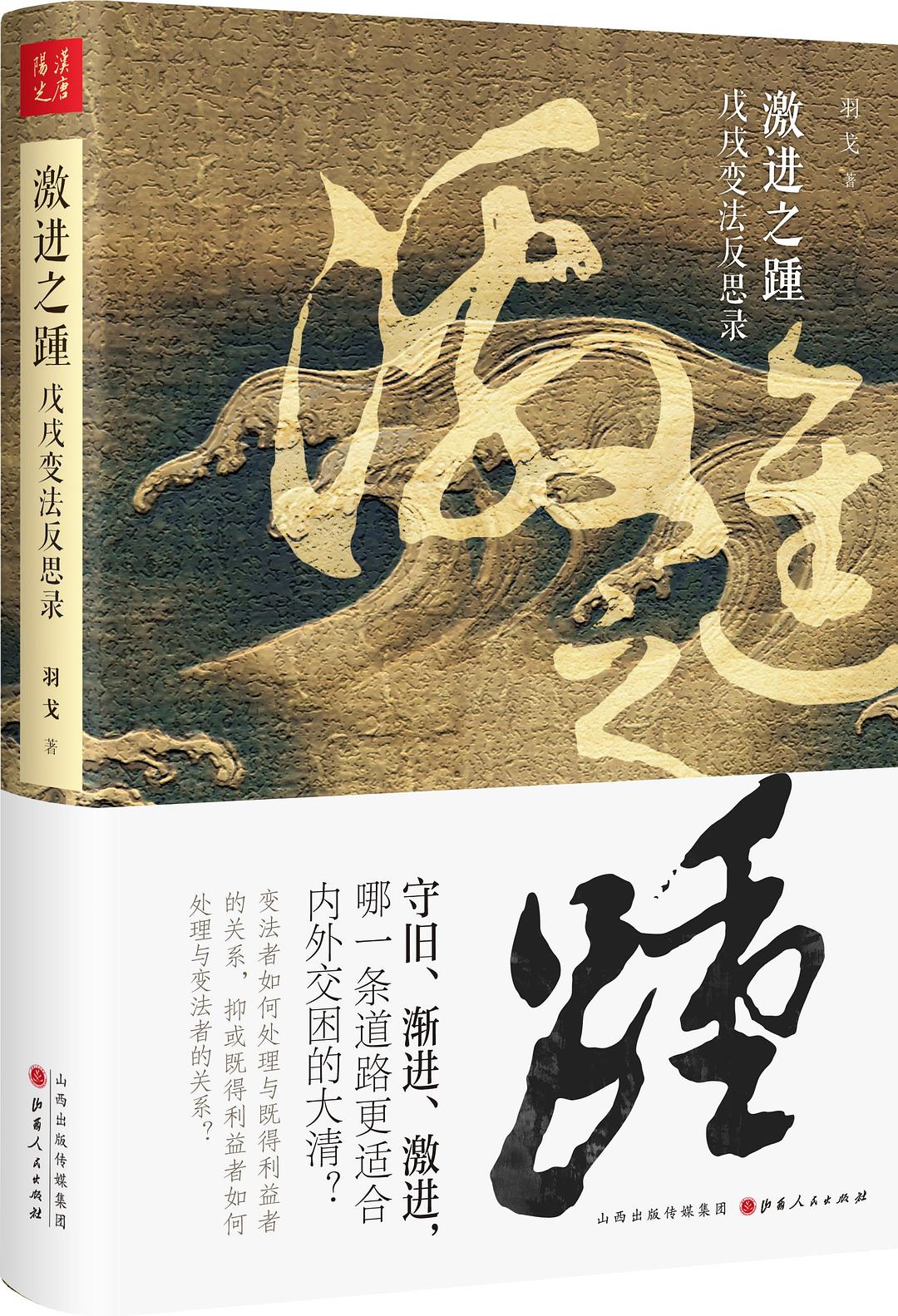
澎湃新闻:你认为过去对戊戌变法的主流叙事有哪些问题?
羽戈:一是史料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戊戌变法的研究,都把康有为、梁启超留下的文本作为最主要的证据。事实上,康有为的《我史》、《戊戌奏稿》,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等,存在不少作伪的成分,几乎每一句话都需要重审。
二是思潮的问题。现在研究戊戌变法,大都在渐进主义的主导之下,对康有为、谭嗣同持批判态度,认为他们的激进、狂热的政治手段导致了变法失败。这是原因之一,但我不认为是主要原因。
在《激进之踵》一书结尾,我谈到了戊戌变法失败的三点原因,首先在时势,改革的动力来自外界,来自列强的侵略,亡国灭种的危机刺激了变法,而不是内部所达成的政治共识,说白了,其动力是外因而非内因,内因不成熟,改革难成功;其次在力量,改革派没有形成统一的观念、组织,势孤力薄,哪怕拉上革命派合作,也不是守旧派的对手。最后才是人与方法的问题,康有为们可比庸医,所推行的“大变、全变、骤变”可比虎狼方。不过,在前两个因素的对比之下,这第三点已经不是那么重要。基于此,对于戊戌变法败于激进,败在了康有为、谭嗣同这些激进者手上的说法,我实在不敢苟同。我认为板子可以打,但没有打到点上。
其实我给自己的定位是渐进主义者,我一向推崇胡适先生,主张“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只不过,我们主张渐进,历史未必会渐进,个体的选择与历史潮流可能会存在反差。
澎湃新闻:《激进之踵》里提到这种人与时代的纠结:康有为的激进主义塑造了戊戌变法的政治气质,但激进的时代一路冲刺,反而把发起人远远抛在了起跑线上。
羽戈:是的。预备立宪前后的这段历史是很典型的情况。戊戌变法之后大环境转向守旧,出现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慈禧太后在逃亡路上幡然悔悟,启动新政。晚清新政正是一场标准的渐进主义政治运动,它的广度和深度都要胜过戊戌变法。康有为、梁启超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情,在新政期间慢慢实现了。但是,哪怕大清最后十年已经走在渐进的路上,最终还是爆发了革命,导致清朝一命呜呼。我认为这就是历史的不可逆性。激进主义可比潘多拉魔盒,打开了就停不下来。
不过需要注意,辛亥革命并不像后世的革命那样激烈,它是激进派和渐进派合作的产物,激进派点火,渐进派收割,二者以一种相当默契的方式主导了这场革命。由此愈发可见,激进与渐进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关系。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