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公元1092年:君子是怎么落入派系之争的?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92年,大宋元祐七年,大辽大安八年。
这一年,大宋哲宗皇帝虚岁17。他当年即位的时候才9岁,这一转眼已经是大小伙子了。在古代,这可就是该娶媳妇的年纪了啊。其实,早在两年前,哲宗皇帝的奶奶,就是现在垂帘听政的高太皇太后就已经开始替哲宗物色皇后了。
刚开始挑中的是狄青的孙女。狄青,是名将,也当过枢密使,家世很好。但是这个女孩子有个缺点,就是庶出,而且是由伯父养大的。这就带来一个麻烦,如果这个女孩当了皇后,将来在皇家的族谱上,皇后的父母到底该写谁呢?是写养父母,还是生父母?如果写生父母,那是写嫡母,还是生她的庶母?老太太和宰相们一商量,算了,不惹这个麻烦了,换一位。
到了这一年,高太皇太后又物色了一个女孩子,这是大将孟元的孙女。这位是嫡出,但是找人一算,又坏了,她和哲宗皇帝两个人阴阳八字不合。这一次,老太太说什么也不肯再换了,管这位孟氏八字合不合,就她了!宰相们也只能站出来背锅,说是我们几个觉得八字不合不重要的,太皇太后也是听了我们的话,才选了孟氏,外人就不要瞎嘀咕了。孟氏就这么成了哲宗的皇后。
不过,我要先预告一下,这位姓孟的女子,一生是既坎坷,又传奇,她的政治影响力一直延伸到南宋。我们《文明之旅》节目今后会多次提到她,今天暂且按下不表。
皇后选完了,哲宗皇帝随即大婚。在古代,一个男子结婚了,也就意味着他成年了。那另一个问题就出来了:皇帝什么时候能亲自执政啊?
有人试着上了一封奏疏给高太皇太后:您孙子已经结婚了,人间的事儿往前迈了一大步;今年冬至南郊大典也是他亲自祭祀了,天上的事儿他也会办了,哪儿哪儿都准备好了,老太太您这么多年也是太辛苦了,要不然把政权还给哲宗呗?结果,老太太没理他。
这个话题,暂时在宰相群体里也很难讨论起来。你想,现在的宰相,无一例外都是高太皇太后提拔的。谁都知道,只要哲宗亲政,宰相马上就会全班下岗。所以,除了沉默,他们也没得选。但是,在中层官员那里,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不站队什么时候站队?
比如,在今年冬至的南郊大典的礼仪问题上,朝廷就出现了重大分歧。有一派官员就说,不按我们的来,我们就不干了,放我走!欸?就为这点礼仪上的小事,至于的吗?当然至于。重点不在于哪种礼仪正确,而在于哪种礼仪是谁定的。高太皇太后最后定下来的礼仪,是更早的宋仁宗时代的祭祀传统,而那些撂挑子不干的官员坚持的礼仪呢?那是神宗皇帝定的规矩。看出来了吧?表面上争的是礼仪,实际上呢?表达的是对神宗皇帝生前决策的态度。
大家都心知肚明,哲宗皇帝这个时候虽然没有亲政,但小伙子可在旁边看着呢。谁对他爹神宗什么态度,一笔笔账也没准儿都在拿小本儿记着呢。果然啊,几年后哲宗亲政,马上就把这次礼仪之争中辞职的官员请来,说要重用他们。
但这毕竟都是未来的事,是天边的一朵乌云。眼下政坛正演着一场大戏,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元祐党争”。简单说就是三拨人:“蜀党”、“洛党”、“朔党”之间的大乱斗。
我们《文明之旅》节目讲过好多党争,比如宋仁宗时期的“景祐党争”、“庆历党争”,还有宋神宗以来的“新旧党争”。我们还提到过唐朝的“牛李党争”,以后我们还要讲明朝的东林党争。但是回头一看,在所有的党争中,这几年发生的“元祐党争”不是最激烈的,但确实是最奇怪的一次。
我这里只说一点:争得最厉害的两派,你能想得到吗?一派的首领是一辈子嘻嘻哈哈的,所谓“不可救药的乐天派”的苏轼苏东坡,而当时的苏轼,也不过就是一个笔杆子,手里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权力;另一派的首领就更奇怪了,是中国儒家历史上的一个响当当的大思想家,“二程”之一的程颐。那这个程颐当时的官儿有多大呢?从七品。你没听错,比七品芝麻官还小一点。
就这么两个人,就这么大的官儿,怎么还能掀起一场党争呢?那今天这一期,我就帮你捋一捋宋朝历史上这场奇怪的“元祐党争”,我们来看看这场大乱斗背后的政治逻辑到底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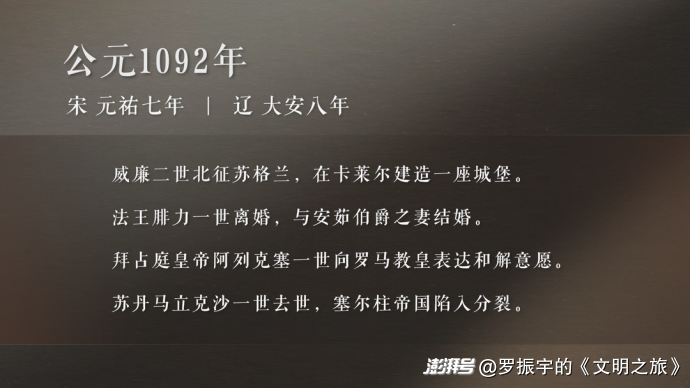
洛蜀党争
我们要把一场政治冲突叫做“党争”,那至少得有两个特点:第一,分得清楚人。两个党嘛,阵营之间,得泾渭分明。第二,分得清楚立场。党派之间总得有个政治观点的区别吧?
但是,如果你用这两条标准来衡量我们今天要讲的“元祐党争”,你会发现,面目一团模糊。所谓党争,拢共就两个字,一个“党”字,一个“争”字,而这次“元祐党争”是一个也说不清楚。
来,请你给我一点点耐心,我给你简单捋捋是怎么回事儿。
所谓“洛党”,核心人物是程颐。程颐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大师。有个著名的典故“程门立雪”,说的就是他。有两个弟子去拜见他,程颐正闭着眼睛静坐呢,两人就恭恭敬敬站在旁边等。等程颐睁眼,发现门外的积雪已经一尺深了,这俩人还没动。后来说学生求学心切,恭敬师长,就总用这个典故。
那为啥程颐叫“洛党”呢?因为程颐是洛阳人。但是请注意,追随程颐的那些学生,可不见得是洛阳人。所以,“洛党”只是一个地图炮的标签。
至于“蜀党”,就更是这样了。“蜀党”的领袖,是我们的老熟人苏轼苏东坡,他是四川眉山人嘛,所以叫“蜀党”。但是蜀党里的骨干呢?就拿其中两个名人来说,黄庭坚是江西人,秦观秦少游是江苏人,跟四川也不挨着。“蜀党”就更是一个地图炮标签。
至于第三个党“朔党”,所谓“朔”,就是北方的意思,也就是一群北方人,有河北的、有山东的。你看,这是不是实在起不出合适的名儿了,勉强叫了个“朔党”?至于“朔党”的那个旗帜性人物,叫刘挚,他在元祐时期做过台谏官,也做过宰相,你可能没听说过这个人。没关系,你知道一下有这么个人就行,他算是司马光的小弟,也是司马光政治遗产的坚定继承者。
这三个党,都有什么政治主张上的区别呢?其实谈不上,大家都是王安石新法的反对派,都同属于保守派阵营,甚至也都跟司马光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朔党的刘挚不用说了,他本来就是司马光的衣钵传人。蜀党的苏轼,也是因为司马光的举荐,这几年才一直升官,成为朝廷的第一号笔杆子。那洛党的程颐呢?其实也是司马光举荐到朝廷的。程颐虽然学问大,但是没考中过进士,本来不是官场中人。是司马光当政之后,把他推荐给年幼的哲宗当老师,这才有了一个从七品的职位。
你看,大家都是司马光这条藤上结出来的瓜,有什么了不得的恩怨要搞党争呢?
我看过很多讲“元祐党争”的论文,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程颐和苏轼,这俩人有矛盾。请注意,这跟政治路线没有啥关系,纯粹就是个人之间的恩怨。没想到吧?程颐和苏轼,两个我们印象中的正面人物,他们居然是有那么深的矛盾。那你说,谁是谁非呢?我把俩人闹矛盾的过程说给你听,您自个儿判断。
巧了,这事儿也跟司马光有关,确切地说,跟司马光的葬礼有关。司马光去世那会儿,正好赶上朝廷举办明堂大礼。文武百官只能优先顾朝廷这头,先去庆贺明堂大礼,然后再一起赶去祭奠司马光。结果,程颐不干了,说这哪儿行?明堂大礼是吉礼,吉利的吉,祭奠司马光,是丧事,属于凶礼,一个喜一个悲,这两件事怎么能同一天干呢?《论语》里不是有一句话吗?“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孔老夫子就是这样啊,一天之内哭过,就不再唱歌。
可是苏轼听了就摇头:你程颐咋能这么迂腐呢?刚哭过,马上就乐,可能不合适。但是刚乐过,没说不能哭啊?
程颐气不过,就跑去跟司马光的儿子说,大臣们来吊丧,你们都别接受啊。他们刚刚参加过吉礼,怎么能跑来吊丧呢?苏轼就讥讽程颐:哟,你是叔孙通呀!——就是当年替汉高祖刘邦制定礼仪的那个叔孙通——这么懂礼仪?不过啊,你程颐是一个低俗版、乱糟糟版的叔孙通。你想,苏轼那张嘴,那个才子性格,那种轻佻玩笑的口气,在场的人当然是哄堂大笑。程颐和苏轼之间的梁子,据说就这么结下了。
还有几个类似的故事,大致的意思差不多,都是程颐死守一些儒家礼制,而苏轼看不惯,出口讽刺,结果俩人矛盾越来越大。你想,这个时候程颐60了,苏轼也56了,都是在朝堂上有辈分、在江湖里有地位的人了。他们互相之间有点心结,很正常,但是看在他们的追随者眼里,尤其是程颐的学生眼里,自家的老大被人羞辱了,那还行?这就演化成了群体性的矛盾。程颐的学生开始对苏轼穷追猛打,上奏疏!告苏轼的状!一会说他诽谤先帝,一会说他对朝廷不忠,甚至只要是苏轼举荐的人,他们一概都要出手攻击。比如,文学史上有所谓的“苏门四学士”的说法,就是黄庭坚、秦观那几个人,听起来好风雅,能跟苏东坡在一起玩。但其实,这些人都吃了苏轼的挂落,在党争中被攻击,一辈子都仕途不顺。
那苏轼对程颐呢?苏轼曾经说,自己这辈子,“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看谁都是好人。但是对于程颐,苏轼一直不原谅。甚至还直接用一个“奸”来评价他,就是“奸臣”的那个“奸”字,可见这个梁子结得有多大。
总之,程颐和苏轼这两拨人互相斗来斗去,最后是两败俱伤。程颐原本不是给哲宗皇帝当老师吗?闹成这个样子,这老师也干不成了,朝廷安排他回洛阳老家工作;苏轼呢?也是被人骂得待不住,元祐四年,不就去杭州当知州了嘛。
所谓“元祐党争”,最核心的矛盾,也就是这么点子事儿。你看,这里面哪有什么政治观念的冲突啊?甚至连私人利益的冲突都谈不上。就是个意气之争,话不投机半句多,性格不合导致的。
还有一点:既然是“党争”,谁属于什么党,这总应该是清楚的吧?但是你看这“元祐党争”,这也是一笔糊涂账。
举个例子,大词人李清照的公公,叫赵挺之。这个人是苏轼的死对头,找机会就要骂几句。那你说他是哪个党呢?有人说,甭问啊,赵挺之的妹夫是程颐的学生啊,所以他肯定是程颐的“洛党”啊。后来又有人攻击所谓“朔党”的领袖刘挚,划拉了一个30人名单,其中也有这位赵挺之,那他又算朔党了。但其实呢?你真要看赵挺之的履历,发现他压根就不是这拨的,所谓“朔党”、“蜀党”、“洛党”,那都是保守派内部的区分,而赵挺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新法派。你看,这是把一条鱼混到一窝鸟里去了,压根就不是一个大类啊。你说乱不乱?
宋史专家王曾瑜老师专门写过一篇论文,把这个阶段的一些重要的人事纷争一条条捋出来,捋了上十条,最后的结论是,要用“洛党”、“蜀党”和“朔党”之间的党争来解释这个阶段的政治,跟史实相差太远,根本就解释不了。
你看,尴尬了不是?一个历史名词“元祐党争”硬梆梆地放在这里,但是哪儿哪儿都对不上,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也不难理解。你要是在一些大单位待过,难免听到过一些闲言碎语:谁是张总的人,谁是王主任的人,谁跟谁都是一个大学毕业的,是“某大派”,谁跟谁是老乡,这叫“某省派”。话传得多了,大家就难免真的用这些派系名词来解释人事矛盾的格局,这些所谓的派系也就半真半假在空气里飘着。而派系这种东西,一旦有了名字,生命力还挺强。为啥?因为用派系的符号解释他人的行为,甚至是用派别的帽子攻击他人,那是既省力又好使。但是你真要去跟每个人聊,会发现很少有人打内心里承认自己是哪个派系的,真实情况要复杂得多。
元祐年间的所谓的党争,可能也就是类似的情况。朝廷里的各种闲人津津乐道这个派、那个党,说得跟真的似的,但至于真相是什么,始终是在一片迷雾之中。
那怎么解释这个阶段大宋政坛的乱象呢?像苏轼这样的文坛领袖,像程颐这样的儒家宗师,怎么会被攻击得这么厉害呢?这总得有个解释啊。
直到我看到这本书,方诚峰老师写的这本《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它就提出了另外一个解释框架。
这就是读书的乐趣了:面对一堆事实,总觉得原来的解释有点说不通,突然,读到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事实还是原来那堆事实,但是马上有了新的意义,立即觉得一片天朗气清、判然有序,那一刻,真是恨不得要倒上一杯酒,遥遥跟这书的作者碰个杯。
好,咱们还是回到大宋元祐年间,这个时候的政坛大乱斗,如果不是党争,那还能是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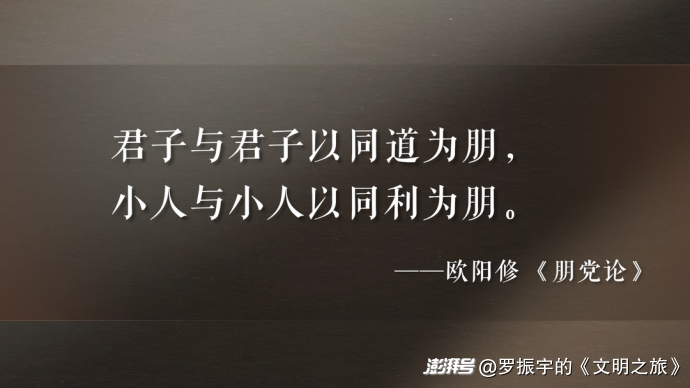
房间里的大象
大宋元祐年间,为什么苏轼和程颐这样的人饱受攻击?如果这种大乱斗不是“党争”,那又能是什么?我们先从苏轼自己的一个感受说起。
苏轼说,只要我一到朝廷的要职上,马上就有人对我穷追猛打。而我只要一离开这个职位,去当地方官,就没人搭理我了,台谏官们的攻击也消停了。你说奇怪不奇怪?对啊,如果是党争,那要斗的就是你苏轼这个人,管你在朝廷还是在地方呢?要把你斗倒斗臭,踏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再过几年,新党斗苏轼就是这样的。那才叫党争。
而这元祐年间,打击苏轼的人,好像被一个开关控制着,只要苏轼不在开封,大家马上偃旗息鼓。这一点也不像那种把人往死里整的党争啊。
那解释只有一个:大家的目标不是要把你苏轼这么样,而是你苏轼不能在这个地方待着。只要苏轼到朝廷担任什么翰林学士或六部尚书,只要他到了这个位置,当他距离宰相只差一步的时候,大家就要上前拉扯。说白了,当时有一个潜在的共识,苏轼不能当宰相。
这不是猜测啊,有人把话说得很直白:苏轼的学问高不高?高。文章好不好?好。但是,他也就是能当当笔杆子,千万不能让他当宰相。为啥?想想当年的王安石。王安石学问也好啊,但你看他当宰相之后,把国家祸祸成什么样?要引以为戒啊。方诚峰老师的这本《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梳理了这个阶段对苏轼的批评,很多都是这个论调。
其实,骂程颐的人,理由也很类似:你程颐看起来是个老百姓,但你哪是老百姓?你是一个儒家的大学者,是一个自以为掌握了圣人之学的帝王师。你看你那副自以为品行高尚,自以为真理在手,自以为毫无私心的样子。这么骂程颐,在当时的环境下,大家是一听就懂弦外之音。上一个这样的人,拿到了宰相位置,但是祸害了天下的人是谁?王安石啊。
你看,为什么是这两个人挨骂?苏轼是文章的魁首,程颐是儒学的宗师,你们这两个人都有成为下一个王安石的潜质。因为你们在士大夫中有高度的号召力、在学术上有强烈的吸引力、在性格上有鲜明的魅力。一定不能再让这样的人物介入高层政治,否则你们就会胡来。不是你苏轼、程颐本人有什么问题,而是你们一旦当权,不会安分的,也没有什么力量能控制得住你们。大宋朝已经出了一个王安石了,不能再有这样的事儿了。所以我们要严防死守。
请注意,这还不是哪一个帮派的人的说法,这是当时的一种主流的政治情绪。只要是站在新法派对立面的人,包括南宋时候的朱熹,这都隔了上百年,朱熹还说呢:当时跟着苏轼混的那帮小弟,就是秦观那帮人,轻薄无行啊。如果那帮人当了权,天下还不乱了套?你听朱熹的原话:“但教东坡作宰相时,引得秦少游、黄鲁直一队进来,坏得更猛。”你品品,这量词用的,“一队”,这是形容街头小混混的词儿啊,居然用到了苏门学士的身上。
隔了将近一千年,我们其实很难理解这种情绪。至于的吗?至于这么害怕出现第二个王安石?苏轼也好、程颐也好,在总体的政治倾向上,都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都属于你们保守派阵营啊。你们至于对自己的队友这么不宽容吗?
这个问题,我本来也觉得很困惑,但是后来我想起了一本书,才有一点恍然大悟的感觉。就是这一本:《小集团思维》,社会心理学家贾尼斯的一本名著。
作者问了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决策失败了,是因为决策者都是一帮笨蛋,那也就罢了。但是很多情况下,做决策的人都很优秀,而他们最后做的决定,往往愚蠢得不可思议,比如美国历史上珍珠港事件、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入侵古巴的猪湾事件等等。这是为什么呢?
这本书得出一个结论:很可能是因为决策群体陷入了一种“小集团思维”。只要大家觉得自己是一个小集团,找到了一种在道德上孤芳自赏的感觉,那紧接着就会有一系列的幻觉。
首先大家会认为,我们这一派是好人,对方是坏人,我们终将胜利,对方终将失败,会莫名其妙地高估自己。接下来的幻觉是:我们是有凝聚力的,我们内部是没有分歧的。没人说话,就代表一致同意。那顺理成章也就有了下一个幻觉:如果有分歧呢?谁分歧了,那谁就不是自己人啊。那就不要怪我们在集团内部做自我净化了。再接下来呢?集团内部自然会有人承担起一个责任,叫“思想卫士”,谁有不同意见,他们就会上去施加压力:你这么想是不对的。
那可想而知,在这种小集团内部,任何一个小念头,都会被放大成大家坚信不疑的真理,而且还没有纠错机制。到了最后,即使是一帮聪明人也一定会做出糊涂透顶的决策。
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说,这小集团思维说的美国那帮政客,和中国大宋元祐年间的政局有什么关系?有一点关系,那就是——元祐时代的政坛,本质上不是一个完整的执政团体,而是一个——“小集团”。
对啊,偌大的朝堂,虽然现在都是旧党保守派的天下,但是,从宰相到台谏官,大家心里都明白,自己只是一个小圈子。虽然凭借高太皇太后的力量,暂时把新党压住了,但是新党“人还在、心不死”啊。他们虽然不在场,但他们像幽灵一样存在着,他们是背景、是气氛、是隐藏变量、是天边那一朵越来越大的乌云。

我帮你简单推演一下,现在朝廷里的这些掌权者的感受:高太皇太后虽然还在垂帘听政,但老太太毕竟60了,说撒手就撒手;而另一边呢?小伙子哲宗皇帝已经17了,又刚娶了媳妇,随时可能要亲政。
所有人都知道,哲宗亲政之后会发生什么。按照当时的政治伦理,哲宗皇帝应该遵循他爹神宗皇帝的改革的政治路线,至少三年内不能变,这才符合孝道。论语上不是说吗?“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好,那等到小皇帝哲宗亲政之后,甭问啊,现在台上执政的这批保守派旧党可能全部都要倒台,甚至会被清算。政策肯定得来一个猛踩刹车、立定向后转。眼见着一场绝大的政坛风暴正在酝酿中。
这不是我们在瞎猜。其实早在元祐元年,高太皇太后刚刚掌权的时候,就有人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他说,现在我们要废除神宗皇帝的新法,满朝大臣都在观望。为啥?主要是三个原因。
第一,神宗是谁?那是先帝啊,是现在哲宗皇帝的亲爹啊。咱们把小伙子亲爹的方针给改了,将来他要是亲政,我们这帮人还不都得有罪?
第二,我们废除新法,说新法对老百姓太苛刻,搜刮得太厉害。好了,新法废了,但是国家财政支出的那些用项还在啊,钱从哪儿来呢?
还有一条,您看看您现在用的这人,司马光,又老又病,他还能干几年?这个政策连续性也不够啊?
你听听,当年的这些担心是不是都挺有道理的?尤其是第一条,哲宗皇帝将来一定会恢复新法,这是房间里的大象,不能假装看不见啊。
那问题来了:你司马光也是个大儒啊,你在小皇帝哲宗的朝廷里改先帝的既定方针,这不符合儒家伦理啊。司马光是怎么应对这个局面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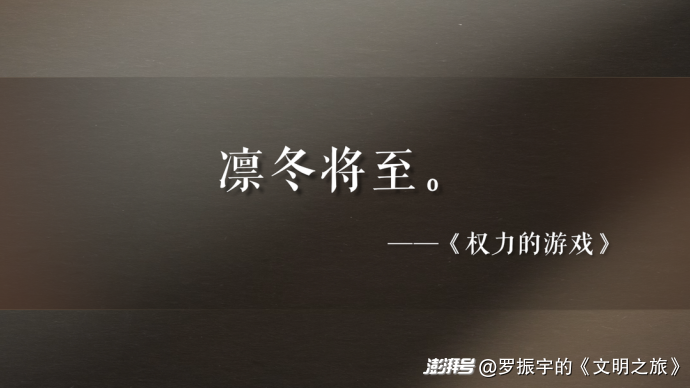
“凛冬将至”
司马光当年是这么解释的:
首先,儿子是不能改老爹的方针,但那是说于民无害、于国无损的事儿可以不改,如果是既害民又害国的事儿,咋能不改呢?
然后,如果有人拿论语里面那句“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来说事,说不用着急嘛,等三年不行吗?司马光说,不行,现在形势很危急,要改就得马上改。
再说了,司马光说,你们看看现在是谁掌权啊?是高太皇太后啊,她老人家是神宗的母亲啊。这不是儿子改父亲的路线,这是当娘的改儿子的路线啊,“以母改子”,有什么不能改的?这个角度找得巧妙,一下子就把孝道的问题给破解了。
但还有一个问题,司马光也得面对:神宗毕竟是先帝,改他的政治路线可以,但是不能否定神宗本人。这就需要非常高超的政治技术了。司马光拿起手术刀,做了两层剥离:
第一,司马光说,神宗是被蒙骗的。当年神宗确实有富国强兵的意愿,只不过他的良好愿望,被奸臣给利用了,这才有了祸国殃民的新法。
第二,神宗晚年是后悔的。宋夏战争失利以后,神宗非常后悔,只不过还没来得及行动,他就去世了。
且慢。我们要问:司马光这套说法有依据吗?其实也勉强得很。神宗是不是被奸臣蒙骗了?这个见仁见智吧。神宗晚年悔过了吗?这个得靠大家一起上阵去脑补。
比如高太皇太后就描述了一个场景,说神宗晚年非常后悔,后悔到什么程度?一个人在皇宫里面抹眼泪!深宫里的事儿,当娘的老太后都这么说了,其他人反正也无从查证。同样搞脑补的人还有苏辙,他从神宗晚年发布的一道大赦诏书中抠了四个字出来,叫“洗心自新”,你看看,神宗自己说的,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这还不是悔过的铁证吗?但你要是去看这道诏书的原文,确实有“洗心自新”这四个字,但那是神宗对被赦免的罪犯说的话,而不是说自己的。你看看,断章取义了吧?扭曲事实了吧?
咱们得体谅:司马光这一派的人也是没办法。既要走回头路,又不能违反儒家伦理;既要反对神宗路线,又不能反对神宗本人。是不是够难的?
更要命的是,不管司马光们怎么解释,大家心里也都知道,这一切都是权宜之计。又不是只有我们这帮人长着嘴,那些新党人物,什么吕惠卿、曾布、章惇、蔡确等等,都还在啊。他们都是当年神宗皇帝亲自提拔的人,他们会同意神宗是被奸臣蒙骗的吗?他们会承认神宗晚年后悔了吗?哲宗皇帝还小,现在是不会说啥,但是他将来当家做主,他会认同你司马光的这些解释吗?
当时,还真有人问了司马光这个问题:如果那帮新法派的人,将来哲宗亲政之后,就是拿父子大义来蛊惑皇帝,就是要恢复新法,那我们不就大祸临头了吗?司马光的反应是,把脸一沉,说,“不怕!如果老天爷保佑我们大宋朝,一定不会有这种事。”你听这话说的,既体现了司马光的勇气,也暴露了司马光的无奈啊:老天爷会保佑我们的!但句话你翻过来一看,就是另一行字了:最后的答案,只有天知道。司马光这句话,既是一声倔强的怒吼,也是一声悲愤的长叹啊。
今天,我们推演了元祐年间政治乱象的内在逻辑:
表面看是一场党争,实际上呢?是一个政治小集团,在巨大的外部压力下、在面对未来的焦虑中,被倒逼出来的内部清洗行动。程颐、苏轼,虽然是我们这条船上的人,但是只要他们不完美,那就要毫不留情地把他们排挤掉。
在我们后人看来,这种强烈的攻击性和过于亢奋的道德感,好像毫无必要。但是在元祐时代的政坛上,这是一种情绪上的刚需啊。
你想想大家的那个处境:海面虽然暂时平静,但是大家只要一俯身,就能看见海底的那头大鲨鱼的阴影越长越大;天气虽然暂时晴朗,但是大家只要往地平线上眺望,就能看见一场暴风雪正在缓慢而坚定地扑来。

怎么办?这个时候,大家只能调用“小集团思维”:我们是一伙的,我们是正确的,我们在道德上是完美的,我们对于有缺陷的领袖也是冷酷无情的。这样做了,大家至少会感觉到更有力量一些。现在这个处境下,好像这是唯一的安全感的来源,即使代价是小集团失去了政治弹性,也在所不惜。
有一句话说的好,要想判断一个人的格局,你看他以什么人为对手。
对一个政治集团也是这样,如果这个政治集团的对手,是制度建设的难题,是大众苍生的福祉,那他们的格局就大,如果你一个政治集团的对手,是等着上台的敌人,他们只是想逃过命中注定的这一劫。那不管他们自以为多么地正义、多么地君子,他们都会陷入一场格局狭小的乱斗。这就是小集团思维的总根源和致命伤。
当然了,这只是一个解释框架。和原来的“党争”相比,我更喜欢“小集团思维”这个解释框架。
为什么?因为“党争”是一场闹剧,里面没有好人,因此我们什么也学不到;而“小集团思维”,则是一出悲剧,它讲述的,是一群贤良君子如何因为焦虑,而沦为自身偏见的囚徒的故事。
我自己从中学到的是:如果我持有的某个观点,不是因为我有充足的事实依据,而是因为我属于某一个小群体,那我就要警惕了;如果这个观点给我带来了在小群体里的融入感和安全感,那我的警惕就要加倍;如果我发现自己居然有要把这个观点表达得更极端一些的冲动,而且居然身边没人给我踩刹车,那我就一定要停下来,再三反思。
英国哲学家罗素,有一句让我们听起来可能不太舒服的话,他说,“我不会为信仰而献身,因为我可能是错的。”我猜,他要表达的,可能也是这层意思,是担心自己陷入小集团思维。
好,这就是在公元1092年,我为你讲述的大宋政坛的故事。明年,1093年,我们再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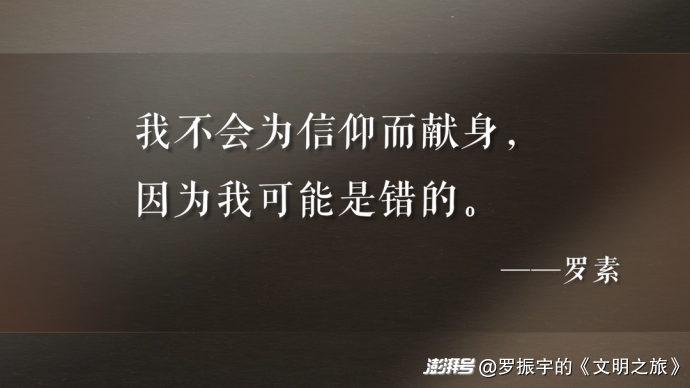
致敬
本期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一部老电影,《十二怒汉》。
这部1957年的黑白电影,讲的是12个陪审员在一间闷热的房间里,决定一个少年的生死。开场的时候,11个人都认定少年有罪,只有8号陪审员,举手说:等等,我不确定。
请注意,他不是说少年无罪,他只是说:我们是不是太快下结论了?我们能不能慢下来,再想一想?
就这么一句话,在11比1的压力下。你想想那个场面,11双眼睛盯着你,有人不耐烦,有人讥讽,有人愤怒。但8号陪审员还是说了那句话。
电影的最后,他一个人扭转了其他11个人的判断。
这部电影里有一段话,我想读给你听——
"面对这种事,要排除个人的偏见真的很难。
不论去到哪里,偏见总是遮蔽了真相。
我真的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想应该没有人知道真相是什么。
我们九个人现在觉得被告是无辜的,但我们只是在赌一个可能性,或许我们错了,或许我们会放走一个杀人犯,我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有合理的怀疑。"
你听,"偏见总是遮蔽真相","或许我们错了"。
这不就是元祐年间那些君子最缺少的声音吗?在小集团思维的笼罩下,没有人敢当那个8号陪审员。
雷金纳德·罗斯写这个剧本的时候,自己刚刚当过陪审员。正是那次经历让他意识到,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群体的压力有多么可怕,而一个人的勇气又有多么珍贵。
有意思的是,《十二怒汉》后来有多个翻拍版本,出自法律制度完全不同的印度、日本、俄罗斯美国、韩国和中国。这也说明,每一个文明内部的警醒者,都试图提醒人们,我们也许缺少一点不那么确认的勇气。
致敬《十二怒汉》,致敬那些敢于在群体压力下说"等等,我可能是错的"的人。
参考文献: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
(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宋)司马光著,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巴蜀书社,2009年。
(宋)程颢、(宋)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
(宋)孙及口述,(宋)刘延世笔录,杨倩描等点校:《孙公谈圃》,中华书局,2012年。
(宋)邵伯温撰,李剑雄等点校:《邵氏闻见录》,中华书局,1983年。
(宋)佚名撰,赵维国整理:《道山清话》,大象出版社,2019年。
(宋)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中华书局,2005年。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
(清)毕沅撰:《续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7年。
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
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
[美]欧文·贾尼斯著,张清敏等译:《小集团思维:决策及其失败的心理学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
王曾瑜:《洛、蜀、朔党争辨》,载吴荣曾主编:《尽心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朱义群:《“绍述”压力下的元祐之政——论北宋元祐年间的政治路线及其合理化论述》,《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3期。
王化雨:《从“慰反侧之诏”看元祐时期宋廷调和新旧的尝试》,《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6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