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文学之眼读钱穆
一
阅读确实是非常个人化和私密化的。思绪和目光会被牵向何处,常常自己也预想不到。
看起来如同踩西瓜皮,但比踩西瓜皮更具有目不可及的“诡异”。谁能料想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先生,晚年最感兴趣的是研究《水经注》。出发点与终点,常常南辕北辙。也许正因此种不确定因素,才使得每一次阅读,都充满了探险般的刺激和惊悚。
是不是有些夸张?且看下文。
二
遭逢特殊时期,3月最后一天晚上临离开工作室回家,顺手抓了几本最近想读的书,其中一本是钱穆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心想,既然有一段足不出户的大把时间,正好可以静下心来读闲书。笔者虽是老文青,但已经多年非必要不读小说了。不是菲薄当代小说,包括进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小说和翻译过来的外国小说都不读。这完全是个人兴趣使然。近年来游走在文史结合的非虚构写作领域,阅读的“风筝”,是被写作的“丝线”牵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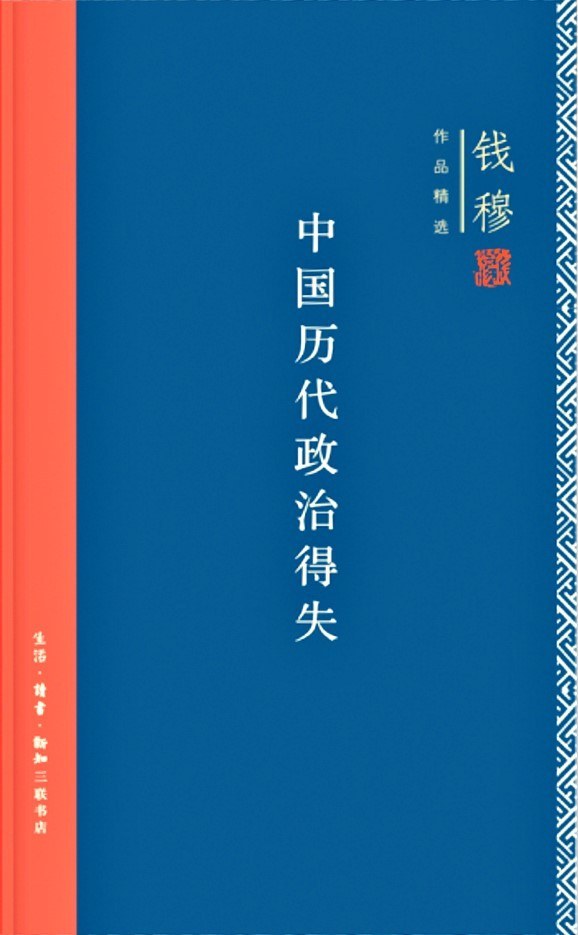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谁知风声雨声声声入耳,一心只读圣贤书也很难。从手机屏幕上迸发的各类繁杂信息撞击着大脑皮层,让人无法定神。还不时有友人转来求助信息,虽无力直接援手,也会尽力找有社会资源的其他人,看能否雪中添薪柴于一二。就这样,一本只有一百八十页的薄薄的书,居然断断续续读了半个多月。
钱穆先生的著作论述了中国古代史上五个朝代政治制度的演变和得失,包括汉、唐、宋、明、清。他认为,从这五个朝代的政治制度入手,基本可以捋清两千多年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演变的脉络。让我感到稍为不解的是,钱穆先生为何忽略了大一统时的秦朝?尽管这是一个短命的王朝。常常听到学界有一句话:两千多年中国古代史,实行的无非是秦制,虽然每个朝代都有各自的调整和变化,但本质上也还是离不开秦制的基本框架。在中国学界大多数人的概念中,中国古代政体中的专制集权属性,是从秦嬴政开始的。“秦皇汉武”,也常常被人们“捆绑”在一起论说。
钱著的自序,笔者读了数遍,未找到破解此谜的答案。
三
这是一部专题演讲文稿的汇集。阅读钱穆先生这部书,并非笔者倏然想涉足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研究;如此艰深的学术课题,想一想都让我头痛。这件事,自然有历史学专业的研究者去做。我最想了解的是这位史学大家,如何评说宋代的政治生态以及制度建设。没错,我最感兴趣的是宋代。其缘由是近年来涉足宋史,写了一组宋史随笔,还刚刚写了一部关于北宋晚期政治生态和蔡京仕宦沉浮的史传。虽然书已出版,但仍想对宋史的多个方面作进一步的探究。因此打开书迫不及待地翻到了第七十六页——“第三讲:宋代”。读完这一讲发现,孤立地了解宋代是不够的,还得上溯它各种典章制度的源头(前朝),于是倒过去看前两讲“汉、唐”,看完“汉、唐”,对宋之后的演变也很好奇,于是接着读后两讲“明、清”。这本书就是这样颠颠倒倒地读完的。
读毕此书,便对钱穆的史学理念萌发浓厚兴趣。正好家中书架上有两部涉及钱先生的多年前购入的旧著,一为钱穆本人著《国史新论》,二为余英时文论集《钱穆与中国文化》,就接着往下读。余英时是海外汉学大家,又曾是钱先生弟子。我的阅读顺序是,先读余英时,再读钱穆。边阅读,边做一些摘抄。在阅读过程中,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吾辈也算在文学圈混迹多年,但对钱先生知之甚少。一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谈起上世纪那些文化界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无非是鲁迅、胡适、蔡元培,还有在政界起起落落的陈独秀等。但我们似乎也不应忘记,类似顾颉刚、钱玄同、钱穆、陈寅恪这样的史学、学术大家,他们是另一股文脉。虽然没有浮在时代的潮头浪尖上,享受被高光追逐的声量,却在静水深流中涌动,默默为转型期的中国文化寻找新的路径。钱穆先生的文集有五十六种,摞起来超越等身之高。因此,我们的学界,与其盯着那几个被钦定的名人,挖山不止地做锦上添花乃至重复劳动的事情,不如把目光也聚焦到那些曾经被时代边缘化的巨人身上。
钱先生在谈历史人物时,曾说:“古来大伟人,其身虽死,其骨虽朽,其魂气当已散失于天壤之间,不再能抟聚凝结。然其生前之志气德行、事业文章,依然在此世间发生莫大之作用。则其人虽死如未死,其魂虽散如未散,故亦谓之神。”(余英时《一生为故国招魂》,见《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9页,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版)钱先生说的是历史上的那些巨人,当然也可以用来评价他本人,可谓夫子自道。但我觉得不必将钱先生这样的学人当作“神”,唯其著述已汇入一个民族不朽的人文精神之河,当是无可置疑的。
四
钱先生的史学之路,竟然是因为十岁时听了体育老师的一段话:“中国历史走了错路,才有‘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治乱循环。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所以中国此后应该学西方。”此话让少年钱穆如五雷轰顶,此后七十余年时间,他一直在勘察、思考,中国历史究竟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也可以说,六年后梁启超的“中国不亡论”进一步刺激他寻找答案:中国究竟靠什么才延续至今,今后又如何继续保持它的活力?(余英时《钱穆与新儒家》,见《钱穆与中国文化》第37页)
钱先生耗毕生精力,做中国历史典籍的爬梳工作,用余英时的话说:“一生为故国招魂”,那么,他招到故国之魂了吗?
且不论有什么终极答案。我最欣赏的是钱先生一生的治学态度,他曾说:“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之出发点,则实求维新。”另借用陈寅恪的话说,“一方面吸收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第3页)国内学界通常将钱先生归入“新儒家”范畴。但余英时用长篇文章论述钱先生与“新儒家”的区别,不赞成将之简单地扔进某一个筐子。诸如新儒家的代表性人物熊十力认为:“秦后二三千年,只有夷化、盗化、奴化,何足言文化?”既然如此,新儒家们为何又要从儒家前贤中寻找中国文化的核心元素,岂不是自扇耳光?钱先生觉得这样的看法是极其武断的,不符合历史的客观实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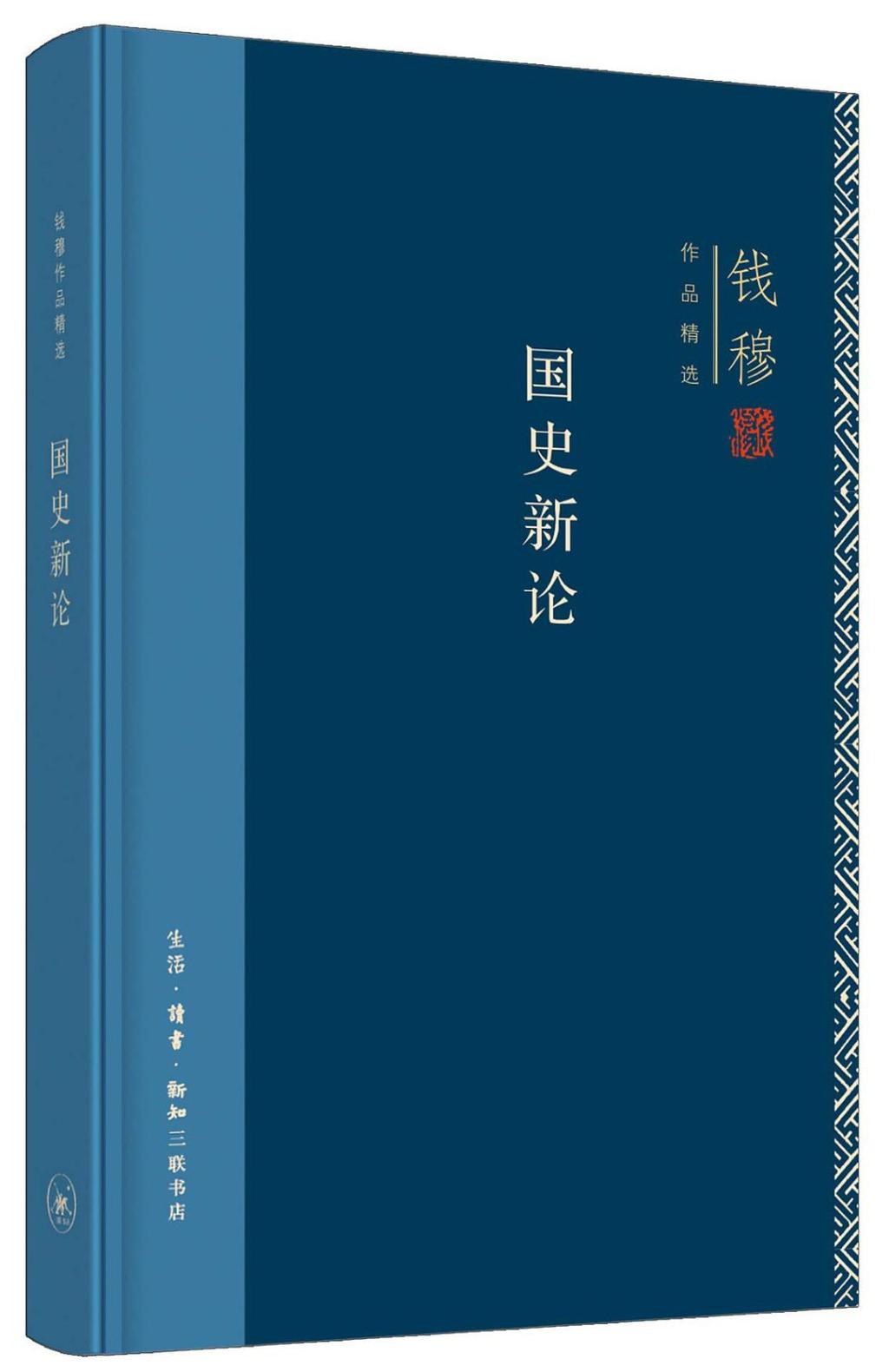
《国史新论》
钱先生既坚持自己独立的研究立场,但又不存门户之见。他对中国社会文化转型有自己独特的学术意见,也许他的想法很容易被认为是保守的。他说:“要政治清明,社会公道,把人生安定下来,则西方科学文明并不是不可能接受。而说到政治清明和社会公道本身,那就是我们内部的事,这些却不能专向外国人学。好像花盆里的花,要从根生起。不像花瓶里的花,可以随便插进就得。我们的文化前途,要用我们自己内部的力量来解救。西方新科学固然要学,可不要妨碍了我们原有的生机。不要折损了我们自己原有的活力。能这样,中国数千年文化演进的大目的,大理想,仍然可以继续求前进求实现。”(钱穆《国史新论》第37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6月版)这段话来自1941年钱先生的一次演讲,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花盆”与“花瓶”,说清楚了如何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的关系。外来文化的营养,要化为有机质,通过本民族的根须,吸收生成新的文化之花。如果像插花瓶那样,简单地插进来,其生命力是难以持续的。
我们面临的现状是,一方面,多年来做了很多持续斫丧、切断本民族文化根须的事情,另一方面,很多人面对外来文化又采取了两极化的态度,不是全盘拿来,便是全盘拒收。妄自菲薄与盲目自大相互交织,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导致族群的撕裂。凡是某国反对的该如何,凡是某国拥护的该如何,成了套用一切是非判断的公式。如何导出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并吸收世界文明的优质养料,培育出中华文化转型的新的枝叶花卉,是我们需要直面的重塑中国人文精神的重要命题。
一方面需要为故国招魂,一方面要为当下和未来铸魂。
因此居家读钱穆,首先读到的不是钱先生给我们开了什么药方,而是读出了先生面临现实问题和纷乱世界的治学态度和思维方式。
五
无论是“招魂”还是“铸魂”,都是为了推动中国文化的进步,推动中华民族向着更美好的方向转型。希冀有一天中国人在世界舞台上行走时,投射的目光既自信又谦卑,既美善、彬彬有礼又疾恶如仇,既有自己独特的生活、行事方式,又有阔大的对不同生活、行事方式的包容和气度。穿旗袍或穿比基尼各自芬芳,喝咖啡与喝茶自由切换,用筷子还是用刀叉各从所好。
纵观中国历史和世界史,从未见过通过枪炮的征服,可以赢得他人尊敬的国家。也从未见过,通过拳头和菜刀逼迫,能够让邻里成为友好的朋友。朋友是吸引来的,是通过自身良好的教养和付出获得的。古人早就说过,“道不同不相为谋”。草民也懂:“强扭的瓜不甜”。丛林法则虽然始终困扰着人类,但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就因为总有人在时时摆脱丛林法则的动物性,给更多人树立摆脱肉身驱动的标高。如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
有当代学人曾预言:“到了东方哲学该登场的时候了。”我想,甭管东方哲学在何时何地登场,首先应该让它在其诞生的土地上生长。总不能说,我这里有很好的哲学,但是我做不到,希望别人都来照着我说的去做。
品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面对社会种种匪夷所思的现象,我有一个基本心得:从古到今,从东到西,一个王朝或一个国家兴衰,无非是两个元素起决定作用——人事与制度。如果有好的人事,没有好的制度跟进,人事将很难有所作为。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的夭折与失败,就是典型的案例。如果有好的制度,没有好的人事去执行,制度就成为可以任意变通、捏塑的“橡皮泥”。如果仔细考察一下王安石变法在执行中出现的变形,就会发现:有些利民的举措,到了某些官吏辖下居然成了害民的恶政,也成了很多人反对变法的把柄。原来,出发点与终点南辕北辙,不仅仅存在于阅读生活中。
无论是“招魂”或“铸魂”,不应是高蹈的概念,而要有非常现实的针对性,才能找到几块或许有助补苍天的“石头”。
六
余英时先生认为,文化有多种定义。通常的说法是指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主要是指精神生活方面的事,如思想、学术、宗教、文学艺术之类,一切民族都有大致相同的精神生活,区别在“方式”二字上。“一旦功利、物质观念侵蚀了中国文化,整个人生都陷于不能超拔的境地,因为没有独立的精神领域可以发挥济俗的功能。”(余英时《论文化超越》,见《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43、248页)当我们看到发生在社会生活中突破法律底线的骇人事件,当我们看到“精致的利己主义”如何浸透到社会肌体的旮旮旯旯,当大多数人面对物事下意识想的都是对我有什么好处,那么这个社会雾霾的密度有多浓,是可以想象的。
偶然听到一个短视频的发布者说,有很多人,“没有享受到蔡京的福,却有蔡京的‘病’”,让我这个为蔡京写过一本书的人也惊叹,其人所道极是。蔡京其人,除了八十岁时病死于贬途中,几乎一生都在享福——出身于仕宦之家,考中进士后虽然仕途起起落落,但总还在上升的通道中。尤其是登上宰辅高位后,可以说享尽了那个时代所能获得的“酒色财气”。我童年时偶然吃到的蟹黄包子,其首创者据说就是蔡京厨房。他家中有一个由多个厨娘组成的制作蟹黄包子的流水线。而且这些厨娘个个姣美如今日“美女网红主播”。请告诉我这样的“食、色”兼容的福气,有几人享受过?什么是“蔡京病”呢?容我这里卖个关子,去看看《蔡京沉浮》便知。蔡京是一面镜子,也许会照出你自己也羞于对人言的“病灶”。
是不是扯远了?没有。我想说的是,面对人文精神缺失的窘境,首先需要倡导的是高蹈于功利之上的文化超越。前些年,很多人质疑文学有什么用。然后为文学辩护的人,便列出种种实例,说明文学是如何有用。其实际效果是,仍将文学这种精神层面的创造,降到世俗的尘土上。为何就不能大声地说出,人类也需要“为文学而文学”“为知识而知识”“为艺术而艺术”的精神追求?如果说其中有“功用”的一面,也多应诉诸精神、情感的需要。看看那些古代先贤的经典文章、诗词、歌赋,有多少是为“稻粱谋”而倒腾出来的?他们的创造为后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稻粱”,但他们创造的初衷却并非为“稻粱”。常常看到,扛着文学旗帜实际为“五斗米”而排成的滚滚长龙。愚某也不免跻身其中。
义与利的关系,是中国古代先贤早就强烈意识到的一道千古难题。甚至将之上升为君子与小人的分界线,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样的难题仍然在困扰人类。因为生存需要,人性的本能是趋利的,这一点不需要提倡和激发。解决肚子问题,是人的刚需。但是人如果仅仅为肚子活着,人就跟猪、狗没有任何区别。古人也不简单地排斥利,而是在两者之间寻求最佳平衡。需要“居利思义”,做到“非其义,不受其利”,时刻保持“门无不义之货”的警醒。为了维护最低限度的底线,西方用种种规约来限制市场经济中的不当行为,而东方则试图通过倡导商业、人的道德伦理来遏制不当行为对社会的损害。
那种为了利什么都敢干的乱象,既与传统的商业伦理和做人的伦理遭到长期的毁灭性破坏有关,也与缺少建立与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配套性规约有关。双重的缺失,使得精致的利己主义成为随处漫溢的污水;追求一夜暴富成为很多人心中的励志标识;厌恶他人贪婪,自己同样做着贪婪的美梦;问题还在于,有人虽然成了住豪宅、开豪车、吃豪餐......对钱已经没有感觉的富豪,同样找不到精神的归属和幸福感。
余英时先生所指出的“近百年来中国始终在动荡之中,文化上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共同接受的典范”(余英时《论文化超越》,见《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58页),仍然是继续寻找“魂魄”的路向。
文化超越的前提是文化共识。无共识则无方向感。
七
历史上很多社会现象,常常同时交织着人事和制度问题。诸如官员的贪腐问题,古今不绝。曾看到一篇报道,说的是某个省份的三任交通厅厅长,前后相继落马,这可以说是典型的前赴后继了。
有巨大利益诱惑的区域,几乎是公权力寻租的重灾区。
为何“肉食者”们不想想:前赴后继的动力源究竟在哪里?制衡公权力的“笼子”该如何去编织?
文学关注的是人性。因此鲁迅一生致力于改造国民性。但这一关注点其实并非他的独家创造,中国先贤们一直在致力于遏制人性中魔鬼的因子。他们薪火相传地为抑贪设置伦理警戒线。是做“人”还是“非人”,“孟子曰”具有“普世价值”,应该镌刻到所有可以“到此一游”的处所。
重塑中国人文精神,所面对的人群当然是整个社会,但重点又在握有公权力的管理者。权力既是“春药”,也是“毒药”。如果掌控不当,既害人也害己。我们常常惊骇于某贪腐官员家中堆积如山的钱钞和藏品,感叹人活百年,一睁一闭,他怎么去消受这一堆“纸”?金满箱,银满箱,转眼枷锁吃牢饭。但人性的弱点是,难以抗拒眼前诱惑,用侥幸作赌筹。阿克顿说:“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他所说的也并非绝对真理。去年我到深圳龙华书院去作一个讲座,讲题是“北宋名臣的为政之道”,其中讲了三个人的故事:蔡襄、范仲淹、王安石,都曾是北宋握有大权的重臣,但个人生活又超乎寻常地简朴节俭。他们究竟是靠什么来修身律己的?究竟是如何使用公权力的?值得我们深入地探究。老子论述的种种“圣人”品格,几乎针对的都是握有公权力的管理者。余英时说:“在传统社会中宗教和道德还多少有一些限制作用,使人不敢肆无忌惮。今天则百无禁忌了。”(余英时《论文化超越》,见《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45页)他说的是上个世纪台湾所处的社会环境。
钱穆先生不愧是一流的史学大家,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可谓四两拨千斤,用浅显畅达的文字,精细梳理了五个朝代政治制度的演变史。其中有很多观点如电光闪目,诸如他认为将中国古代历史,一概以“封建专制”来统论是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秦统一中国前,土地分封到诸侯,可以说是“封建社会”,秦统一后不再分封了,就不能称之为“封建社会”。至于“集权专制”,在他论述的各个朝代的情况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汉、唐、宋时,君权与相权是存在不同程度相互制衡作用的,到了明、清,则集权越来越严重。钱先生的论述皆有坚实的史料作支撑,自然言之有理。但笔者在读毕大著后,却也有不完全苟同的看法,即中国古代并没有形成系统性的对公权力监督的机制,就拿宋王朝来说,“相权”在很多时候,确实分解了很多“君权”,但只要“君权”处于强势状态,“相权”就会非常脆弱。在王安石第二次担任宰相后,他上奏的变法意见,能够被神宗采纳的也只有十之二三,这是王安石辞掉相位的重要原因。即便到了北宋晚期,蔡京位高权重,也有超强的执行力,但宋徽宗想把他罢免了,也是分分秒秒的事情。还有一种情况,当“君权”处于弱势,“相权”一手遮天时,谁来制衡“相权”?南宋高宗时,秦桧权势滔天,对异己大臣可以随心所欲地用“莫须有”罪名加以惩处和迫害,连官家也要置刀靴中防其害己,又有什么机制可以监督“相权”的滥用呢?
因此招什么“魂”,铸什么“魂”,仍然需要相当范畴的共识。钱先生未竟的探索,期待有更多人接力。让笔者最为厌恶的是,某些所谓精英,用一堆从历史废墟里捡来的“废铜烂铁”,来炫示祖宗的荣耀,灌输文明古国的“鸡汤”。偶然看到有网友称:幸好当年慈禧太后把贪污来的海军经费用于建颐和园,否则,银子都成了甲午海战中的炮灰,就没有每年给当下带来滚滚门票收入的颐和园了——此种骇人之语,真的要让人惊出一身冷汗!
东方哲学该登场了?我们不妨把预言转换为呼唤。且容愚某也在这里喊一嗓子:东方哲学快快登场!别再隐身于荆棘草莽深处,散漫在馆阁泛黄的故纸堆内,把头埋在厚厚的沙砾中,羞羞答答像个被遮头布蒙住高颜的娇娘......
八
敲打键盘写此文的第一天是2022年5月17日。这天夜里做了一个奇特的梦,我已经难以复盘魔幻般的记忆了。让我终身都无法忘记的是,因梦境产生的压迫感,让我猝然从床上向左侧翻滚到地板上,连带着把床头柜上的物品:书、笔筒、记事本等“咣啷啷”撒了一地。所幸的是额头未磕到柜角,身体未摔伤......
阅读果真会带来“惊悚”的体验。
重新爬上床,长长地喘了几口粗气,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老天爷对书生还算是善待的,如果胳膊腿受伤,别说深更半夜,即使大白天,到哪里求医去?
瞄一眼窗外,在沉沉夜幕下,似乎每一寸空气中都游荡着无数幽灵。

本文选自文学评论集《请拿起你的手术刀》(陈歆耕 著,作家出版社,2025年12月版)。
作者简介:陈歆耕,原籍江苏海安,现居上海。曾任《解放军报》记者部副主任,《文学报》社长、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大学非虚构写作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客座教授。著有中篇小说集《孤岛》,中短篇报告文学集《青春驿站》《海水下的冰山》,长篇报告文学《点击未来战争》《废墟上的觉醒》《赤色悲剧》《小偷回忆录》,文化批评随笔集《快语集》《谁是谋杀文学的元凶》《各打五十大板》《美人如玉剑如虹》等十多部。近十多年来致力于文史非虚构作品写作,已出版历史文化随笔集《何谈风雅》,长篇历史非虚构作品《剑魂箫韵:龚自珍传》《蔡京沉浮》《稷下先生》等。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6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