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一名资深乡村媒人的生意经
文 | 马鹏波
编辑 | 刘成硕
一
在中国西北地区,阴历十月一是传统鬼节,按照旧俗,人们在这一天傍晚都要焚纸祭祖,伴随日落西山,缭绕的烟雾很快就会笼罩四野,等烟雾散尽,北方也就进入了真正的冬季。对于北方农民而言,冬季的到来意味着蛰伏期的降临,等待与休息将成为他们未来三个月打发日子的主要方式。不过,对于从事另外一种职业的人来讲,这却是一桩好事,他们一年的等待与积累,就是为了在这最后三个月里大展身手。
老杨,乡村职业说媒人。2018年11月底,我特意前往一个叫杨村的村子,因为没有老杨的具体地址,不得不走进一家商店求助。商店老板是个健壮的中年女人,听完我的简单描述,她很快就在记忆中筛选出了我要寻找的对象,“哦,说媒的杨师!”后来我才知道,附近村子的人都称老杨为“杨师”,“说媒的”则是乡下人对“媒人”的通俗叫法,老杨很喜欢别人给他的这个称呼。
有村里人引路,我很快就在一户农家院里见到了老杨,现年62岁的他已经是远近闻名的媒人。和想象中的媒人形象稍有不同,他身材魁梧,大腹便便,全然没有中介从业者常见的那种机灵刁钻劲,简短的交谈后,我发现他也擅长伶牙俐齿的表达方式,这让我对他此前在电话里陈说的种种“业绩”不禁产生怀疑。老杨对我的到来同样深感意外,“没想到你真的找来了!”迎我进门,几杯开水,半袋瓜子,他想找一包珍藏的上好茶叶,却忘记了当初存放的具体位置,尴尬地笑笑,转而要给我展示制作好的《姻缘簿》。
这是老杨深感自豪的“独家创意“。每年鬼节一过,老杨都要花费至少一周时间,将此前整理的电话本和附近乡镇适龄男女的信息全部摆出来,花上点工夫,按照属相、年龄一一配对,最后再将配好的信息重新誊写在一本崭新的笔记本里。当然,老杨不喜欢别人用“笔记本”称呼他手上的“宝贝”,他取了一个吉祥名字——《姻缘薄》。他说“阎王手里有《生死簿》,月老手里也应该有本簿子,我就叫个《姻缘簿》吧,咱干的就是拴姻缘的事情!”
他预先在一张红纸上折出三个方框,特意请人用毛笔在方框里繁体竖排写进“姻缘簿”三个大字,剪裁过后,糊在笔记本封面,盖住了原先的英文字母。“我一年换一本,不怕麻烦,图个吉利!”
我接过老杨的《姻缘簿》,翻开,密密麻麻的男女个人信息以男左女右的格局,塞满了本子空白,老杨用了三种颜色的笔分别标注每个姓名后的关键信息,红笔写属相,蓝笔标注村子名称,黑笔则是一些具体数字,其中还有贯穿笔记本左右的铅笔线条。我想进一步搞清这些不同颜色笔记的象征意义,但老杨始终面带微笑地找理由搪塞,看得出来,他对我这个突然闯入的陌生人还有所顾忌。于是,我适时提出当天下午请他到镇上吃顿便饭,也想借此拉近我们之间的关系,以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获取更多信息。不料,老杨大手一挥,“不花这个钱。你来的巧,明天咱俩一块到县城吃顿大餐!”
二
大梦一宿,第二天上午九点,村子开始醒在雾气里。老杨把自己的一辆摩托车掀出牛棚,将一壶热水浇满油箱外部,插上钥匙,发动,递给我一副头盔,招呼我骑上后座,我们一同冲上街道,往县城驶去。
杨村距离县城仅有五公里,村子位于一片河川谷地。时间入冬,绿色的麦苗罩着一层薄雾铺展十几公里,中间散落着些许坟头。在行政区划上,杨村隶属陕西西部的陇县,这里位于黄土高原腹地,与甘肃接壤,按照政府门户网站给出的资料显示,这个面积达两千二百平方米的山区县拥有人口将近三十万人,无论如何,这都不算一个小数字,但多年来,陇县一直属于国家级贫困县,显而易见,巨大的人口资源并没创造出可观的经济数据。坐在老杨的摩托车后座,我把自己的发现和心中疑问传递给他。
“那只是户口本上的数字!“老杨大声说道,“中国人不一定都在中国,陇县人也不一定都在陇县,三十万人有三分之一在陇县干活就不错了。县里过去有煤矿,鞋厂,轧钢厂,现在啥都没了,都跑到外面去打工。”
我指着两边广阔的麦田:“看起来,留在家里种地的人也不少!“

“你要是十年前来这,麦地就不是这个样子,一行一行,整齐得很。你看现在,像不像城里的草坪。知道为啥吗?”老杨把头盔上的面罩掀上去,“过去各家壮劳力多,把庄稼当回事,现在不行了,种地的都是老年人,没那个精力,到种麦时间,把种子像给鸟喂食一样撒地里就行了。你看这麦,稠的稠,稀的稀,收成肯定不会好,麦草估计能收不少!”
老杨把陇县经济发展的滞后,归结于人口流失。媒人常年与本地人打交道的职业特征,让我有理由相信他的分析不无道理,陇县环境闭塞,年轻人选择走出大山进入城市,也是人之常情。但根据老杨的阐述,流入城市的不仅有年轻人,更多的还有过去轻易不离开乡土的中年人。为何中年人也要抛弃土地?
对于我的追问,老杨没有立即回答,他笑了笑,“等会儿吃完大餐再告诉你!”
三
我们在风里前行二十分钟后,摩托车停在了一家小餐馆门口,老杨把头盔夹在腋下,示意我跟上他的脚步。进门上楼,他推开一间包厢的红色门,掀开门帘,里面此时已经烟雾缭绕,二手烟熏得我胃里一阵难受。这是一间十平米的雅间,圆形餐桌两侧坐满了人,正对门的那个位置空着,毫无疑问,那是给老杨准备的。“一个朋友,是个作家!”老杨向已经起身站立的一圈人介绍我。
“服务员,加个凳子!”一个满脸皱纹的男子唤服务员,嗓门极大,把我让在了他的座位。
这是一场 “谢媒宴”。按照传统,如果媒人将一门亲事撮合成功,男女双方家人要在大婚之后不久专门摆酒设宴,款待媒人,以感谢他的“成人之好”。当天到场的一共有七个人,除了新婚夫妇,男女双方的家长也都来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位男方的舅舅,就是那位满脸皱纹的大嗓门男子。

老杨应付这些场面已经驾轻就熟,他径直坐在空出的上座,分别接受了双方家人的一圈敬酒后开始自斟自饮。新婚夫妇看上去极其年轻,他们似乎还不适应这种属于成年人的交际场合,一度显得局促不安,双方父母也沉默寡言,除了客套的场面话,其余时间则惜字如金。这时我才明白,为何这场两个家庭之间的聚会要邀请舅舅参加——他是专门来化解这种相顾无言的尴尬场面的。
酒菜极其丰盛,席间按照约定成俗的礼节,老杨还接受了男方赠送的一整个生猪头和一双皮鞋,有意思的是,那只刷洗得白白净净的猪头鼻孔里还插了一根大葱。然而,老杨当天在这间二手烟弥漫的雅间一直沉默不语,即使接受了对方馈赠的礼物,脸上僵硬的表情也未见软化。好在有男方舅舅,他成了当天酒席间的主角,或者还应该算上我,我的突然出现,避免了他陷入自说自话的尴尬之境。
“你们平时都写国家大事,啥时候把我们这地方也写一写。”他给我倒了一杯白酒,由于动作稍显僵硬,酒水溢出了杯口,“真的,娶个媳妇太难咧!”
就在这时,老杨抬头朝男方舅舅瞪了一眼。
我顺势追问,“说说看,说不定我回去就能写出来!”
“彩礼太贵了。一年涨两万,比城里的房价还涨的厉害。给娃娶一个媳妇还得买房买车,前前后后得花小四十万。“
“其实城市结婚也不便宜!”我接上他的话,但很快就为自己的鲁莽冲动后悔。
“城市和农村咋能比么!农村人一年到头才挣2万元。你们城里人娶媳妇不着急,到处是年轻人,连我们这地方的年轻人都跑城里去了。”
他语速很快,我没能找到插话的机会。
“农村女娃本来就少,现在更少啦,男娃不着急是假的。农村女娃能嫁到城里,城里女娃谁跑到农村?农村女娃现在就这么点,想娶媳妇就得砸锅卖铁掏大价钱。”
我猜他工作的场合肯定遍布噪音,以至于他已经习惯用超出常人许多的大嗓门发表意见,而且不知疲倦。
“你们都是文化人,你说这今后咋弄?“
鉴于之前的“教训”,这次我没有回答他的质问,只憋出了一副难堪的假笑。老杨没有再抬起他硕大的脑袋,用凌厉的眼神“瞪”视大嗓门男子,他决定做“甩手掌柜”,让我独自面对。我想,我确实挑战了他的权威,老杨在乎这个。这期间,我注意到坐在男孩旁边的姑娘一直低头不语,筷子在空碗里拨来拨去,男孩的妈妈显然看出了儿媳妇的情绪变化,试图制止男孩舅舅的发言。舅舅见状,仰头喝下一杯酒,笑了笑,“喝多了,喝多了!“随后又给我倒了一杯,笑着长长叹了一口气,我也舒了长长一口气。
这场“谢媒宴“在稍显沉闷的气氛中持续到了中午十二点,老杨把猪头挂在摩托车手把上,我帮他抱着一双皮鞋,酒足饭饱,我们又重新返回杨村。
“你今天看起来并不高兴!“
“看不起我,啥东西嘛!”他忽然变得很愤怒,“不要误会,我没有说你。今天这门亲事,是去年冬天就说成的,本来年一过就该给我把猪头和皮鞋、礼金送来。没规矩,欠了老子整整一年,给他没涨价就算便宜了。”
“礼金?啥礼金!”
“你把鞋盒打开,看看是不是塞着红包!”我打开鞋盒,一个红纸糊的信封压在鞋底。“不用数,肯定是5000元,他不敢糊弄我的!”
老杨说的礼金,也就是男女双方付给媒人的佣金,类似于中介费。在陇县的传统风俗中,媒人的佣金通常是一块猪头肉和一身新衣裳,但近些年来,由于婚姻市场的逐渐火热,陇县适龄青年中,男多女少的局面愈演愈烈,媒人的地位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佣金就由传统的实物变成了金钱,像老杨这样的资深媒人,佣金通常是彩礼价钱的百分之五左右。在某种意义上,彩礼钱越高,媒人获得的佣金也就越多,陇县地区节节攀升的彩礼钱,顺势提升了媒人的收入,也正是这样的原因,老杨在四年前毅然中断了自己贩卖牲口的生意,做起了职业说媒人。
“我干这个有优势,过去贩牲口,跑的地方广,认识人多,圈子大,能把媒说到隔壁县去。其他人,没这个本事。”老杨对自己的业务能力充满自信。
“不过最近几年这一行也不好做了,女孩子越来越少,女方家要求也越来越多,一年到头也说不成几个。今天那一对,彩礼20万,那姑娘才不到20岁,连结婚证都没领。按理说,我是不能给说媒的,违法,但没办法,那女娃有个哥哥,等着用钱结婚,这边男娃,家里的姐姐结婚不久,家里刚好有笔彩礼钱。这种事情,两家你情我愿,不给说合成,会得罪人的。你们城里人可能觉得这是婚姻买卖,没有爱情,没有感情,说实话,按我们的实际情况,这就叫缘分,钱到位,人到位,缘分也就到位了。”
“男娃家既然有了彩礼钱,何必着急呢!”我问。
“当然着急,一年涨两万呀。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他们家能拿出来的只有20万,但还要在县城买房,置办酒席,前前后后下来还欠了30万元债。正月初五结的婚,结完婚就锁上门,全家打工去了。所以,没给我把礼金及时拿来,我也不怪他们,结完婚一穷二白了,估计就留了些出门打工要用的钱,都不容易!来的路上你问我中年人为啥都要出去打工,原因就在这里:父母帮儿女还债。”
四
接下来的几天,老杨都在打电话和接电话中度过。他很擅长用手机远程处理事务,并且极有耐心,属于那种能控制场面的人物。有时候,他连续几个小时盘腿坐在炕上,把《姻缘簿》摊开,拿起铅笔,搬出一本《老黄历》,比照着在本子上勾勾画画。
“你看,像不像你们在学校里做的那种连线题!”老杨咬着一只烟,这句话说出口,他自己先笑了。“这种事情就看你咋想了。老话说,千里姻缘一线牵,这个线可以是月老手里的红线,也可以是我用铅笔画出来的这条线。”他把掉在被面上的烟灰弹到地上,吹了一口气,“不过,照我看,月老的那根红线靠不住,还是我这跟线比较灵光些!“
老杨嘴里的“月老红线”指那些通过自由恋爱,最终抵达婚姻殿堂的年轻人,“铅笔画的线”指的就是经由像他这样的媒人牵线搭桥组合的家庭。但老杨的本意不止于此,在他这里,“自由恋爱”代表着很低的彩礼钱,“铅笔画的线”则意味着高昂的彩礼。事实上,实用主义理念主导着杨村人的认知,在他们看来,“礼金多寡”才是婚姻话题的核心。
“自由恋爱当然好,但首先你硬件条件要好,要学历有学历,要模样有模样,能在城市混下去,能挣来钱,这就是自由恋爱的资本,不然,哪个女娃和你自由恋爱。但在我们这,拥有这些资本的娃,太稀缺了!”
根据老杨的提示,我检索了陇县地区近十年高中以上学龄段人数,发现2007年以前,陇县仅有1所高中,但全县境内初中多达7所,高中录取率不足百分之十五,直到2007年,新建的第二所高中开始招生,这种局面才有所改善,2008年全县初三应届毕业生多达六千余人,高中录取名额增加到800,即便如此,高中入学率依旧未能突破百分之二十。这是一个颇让人沮丧和惊讶的数据,这意味着6个初三毕业生,仅有1人能够走进高中大门,进而获得考取大学的机会。换而言之,陇县绝大多数年轻人拥有的最高学历仅为初中。
我把自己的发现告诉老杨,“一直都这样,考高中比考大学难,考上高中也不一定能考上大学,教育水平就是这个样子。初中毕业去南方工厂打工,胆子小的给人组装手表,胆子大的就去摆弄机器,被机器切掉手指、胳膊,多的很。最后都得回到农村娶媳妇,就算在外头自由恋爱,谈的也是农村打工的姑娘,彩礼肯定是跑不了的。”
“别看都在外头跑,每年这个时候都得揣着挣了一年的钱,一窝蜂回来,找我给他们牵线搭桥。今天下午会来一个小伙子,前些年打工时让机器切掉一根手指,但好歹挣了点钱。我给挑了6个适合的姑娘,下午一起去看看。”

乡村婚宴
下午三点,一辆面包车停在老杨家门口,司机是个精干的小伙子,给老杨拎了一瓶酒和一条烟。他24岁,但已有8年工龄。老杨很喜欢小伙子开的车,“有车,这个事就成了一半啦!”
按照老杨电话预约的次序,我们去的第一家距离杨村大约三公里,同属县城周边村子。老杨把小伙子领进门,介绍给女方家的父母,小伙子和姑娘留在屋里,其余人很配合地撤到了外屋。我站在他们中间,听老杨向女方父母陈说小伙子的种种“优势条件”,老杨很懂得如何在谈判过程中展现己方优势,从而把选择压力抛给对方。他明显拔高了小伙子的家境,甚至杜撰出我们已经看过其他几家姑娘、小伙子对其中两个很有兴趣的桥段,并让我给予证实。我见状只好“知趣”地点点头,然后借故上厕所,逃到了院子。我被动地成了一个“骗子”!
整个过程持续了不到半个小时,临走,小伙子给姑娘塞了50元红包,这是当地约定成俗的“见面礼”,同时也意味着小伙子和姑娘两人没有“谈拢”。小伙子说,姑娘只想找一个教师或者公务员,嫌他的工作不稳定,老杨在车上安慰,“不要紧,咱去下一家”。
汽车行驶在乡村公路上,人烟稀少。老杨希望我做他的“托”,配合他在女方家里继续“表演”。
“咱们这样算不算骗人?”我问。
“咦!这咋能叫骗人?看人下菜碟,事情就得这样子干!”
老杨的表情严肃,我只得乖乖顺从,把“骗子”继续当下去。就这样,我们马不停蹄地去了下一家,又去了下一家,到最后一家之前,老杨彻底怒了。他向小伙子吼道:“你咋回事?你要娶个七仙女?” 小伙子擦着老杨溅在他鼻梁上的唾沫星子,一脸委屈。
“我跟你讲,这几个姑娘都是我精心挑选过的,和你的八字属相特别合得来,家里条件也跟你们家相当,身体上虽然或多或少有些小问题,但都无伤大雅。你得学机灵点!”
陇县人习惯用属相计算年龄,不但如此,他们对于属相配对吉凶或者禁忌,尤其信奉。老杨当然也深谙此道,在他的《姻缘簿》上,属相信息都被他用红笔刻意勾画,那些属相配对吉利的男女名称,就被他用铅笔左右勾连起来。毫无疑问,小伙子的名字后面,一定勾连了六条铅笔线, 不过现在看来,只剩最后一道了。
老杨依旧和我互相配合,重复之前的“表演”。这次老杨没有把小伙子和姑娘单独留在屋里,而是大家共处一室,老杨选择的策略非常简单:小伙子尽量不要讲话,一切都交给他。
“很能干的小伙子,打工七八年了,在城里混的相当不错,比教师挣的多!“老杨示意小伙子把茶水倒满,小伙子照做。
女方父母面无表情地点点头,不说话,看不出来是认可还是敷衍。
“在县城跟前盖的新房,面包车也有。姑娘嫁过去吃不了亏!”老杨继续规劝,语速也越来越快,夹杂着的有些方言语调让他的谈吐变得模糊不清。
姑娘父亲继续点头说好,惜字如金,堆着一脸笑容,仿佛局外人。姑娘的母亲发话了,看得出来,她才是把持这个家庭发言权的人物,“我也不多要,22万,今年都是这个价!”
屋里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姑娘端起茶壶走向外屋,姑娘父亲也起身离场。“老姐姐,就小伙子这条件,22万,确实高了!”老杨提高嗓门,试图把价格压一压。
“你可别糊弄我,这一阵子行情都到24万了,我才要22万,在城里连半座房都买不下。”姑娘母亲虽然笑着回应,但立场鲜明,这样的人物最难搞定。我看到了小伙子和老杨脸上同样难堪的表情。老杨遇到了职业生涯最不愿遭遇的那种对手。
走出姑娘家门,天已擦黑,老杨用我听不太明白的粗鄙方言骂了姑娘母亲一路。“骂归骂,但也不是没有商量余地,你在家等消息,我回头再去走动走动,或许还有希望。”小伙子点点头,把夹在耳朵的一支烟递给老杨。“听叔一句话,不要太挑,能过日子就行了,想法太多,到头来耽搁的是自己!”

五
再见到老杨是一个礼拜以后,我在医院找到了他,他的情况看起来突然糟糕了许多。
事情是这样的。大概在九月份,本地一个大龄青年找到老杨,托他帮忙给介绍姑娘。这个青年以前有过一段精神病史,父母早亡,平时在废品收购场当装卸工。这样的条件,在相亲市场几乎没有任何机会,按照常理,大多数媒人都会借故推辞,但老杨答应了下来。
在陇县,媒人领小伙子“见”一个姑娘,不管这门亲事成不成,男方都要付给媒人200元钱,再管三顿好饭。九月属于淡季,老杨一方面想赚这笔介绍费,另一方面也有和当地其他媒人“斗气竞争”的意思——别人不敢接应的活,他敢。
但老杨很快就发现,九月时节,乡村的年轻人大都在外未归,并没有合适姑娘介绍给这位条件恶劣的大龄青年。出于维护自己口碑的考量,他既不想知难而退,也不想带这位大龄青年去见那些有头有脸的待嫁姑娘。于是,他铤而走险,以每天50元的价格从劳务市场雇来两个年轻女工,假扮未婚女子,带着大龄青年按照程序“看”了两次。相亲结果按照老杨的计划均告失败,他也顺利将一共400元的介绍费赚到了手中。
百密一疏,老杨自认为天衣无缝的计划到底还是出了问题,他忽视了来自同行的“窥视”,或者也可以称作“监督”吧。就在我们开面包车回到杨村不久,由于其他媒人给大龄青年的“指点“,老杨的“阴谋”被败漏。青年纠集了一帮江湖兄弟,在杨村通往县城的路上,把老杨从摩托车上打翻下来,老杨左脚骨折,躺进了医院。
“他妈的,他这辈子就等着打光棍吧!”老杨当着我的面咒骂起打伤他的青年,却只字未提他雇佣女工冒充姑娘的事情。他确实满腔怒火,从被子后面掏出《姻缘簿》翻阅,“看着吧,就算我躺在医院,他们照样得上门求我。冬天日子还长,有电话,就算走不了路,照样说媒!”
当天,那个断了一根手指的小伙子拎一篮水果也来看望老杨,临走塞给老杨1200元钱,那是他之前的介绍费。老杨没有推辞,也不避嫌,接过后塞进裤子口袋,笑着安慰道:“别灰心,有叔给你操心,包在我身上。你好好挣钱!”
“那就一切拜托叔!”小伙子把一颗削好的苹果递给老杨,转身告辞。
送走小伙子,我把老杨的《姻缘簿》拿过来,翻开,找出小伙子的名字。名字后面原来的六根线只剩下了一根,几粒橡皮碎屑粘在本子内侧。
“帮我把那根线也给擦了吧!“老杨眯瞪起眼睛,递给我一块橡皮。
于是,小伙子名字后面最后一根线也消失了。
镜相栏目首发独家稿件,任何媒体及个人不得未经授权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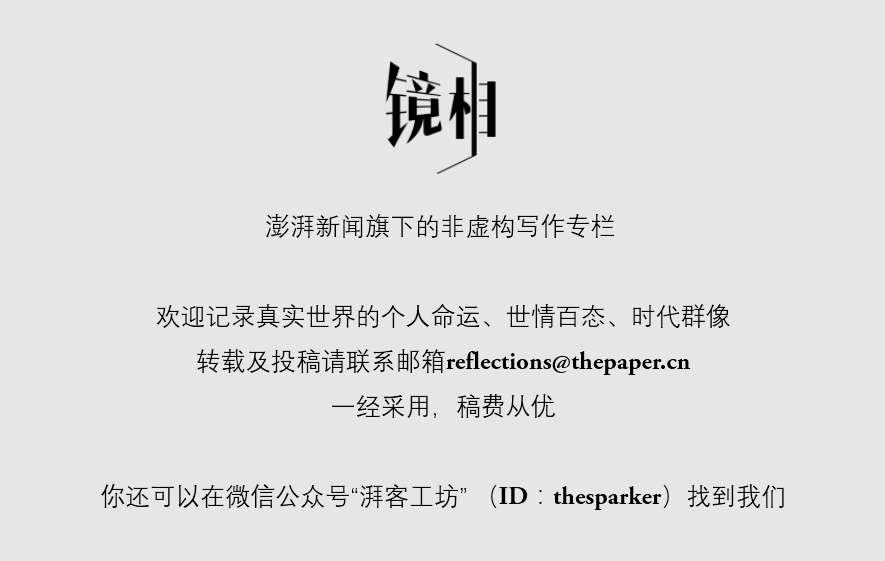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