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访谈︱刘志伟、任建敏:区域史研究的旨趣与路径
自施坚雅打破王朝国家历史叙述的范式,提出从区域的脉络解释中国历史结构的理论起,区域史研究成为学者们试图加深理解国家历史乃至全球历史的重要研究取向之一。好的区域史研究,一方面要讲好所研究区域的故事,另一方面要在故事中呈现一种“理”。这种“理”,不只是对研究者个人有效,还要能引起其他历史学家乃至其他学科学者们的共鸣。在中山大学温春来、谢晓辉两位老师的共同参与下,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任建敏对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刘志伟老师就区域史研究这一议题进行访谈,主要围绕区域史研究的当前动向与思考认识等。本文出自《区域史研究 创刊号(总第1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年6月),主编温春来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


从制度史到区域史
任建敏:您曾提到过,您1997年出版的《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一书,是在您1983年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但两者比较起来,其问题意识似乎已经有了比较大的变化。您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重点,似乎是以广东为研究区域,理解明清赋役制度的改革,而《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一书则在这一基础上,通过赋役制度改革的研究进一步探讨明清广东地方社会结构的变化。是否能谈谈,这两者之间的14年时间里,您的学术历程和理念的一些变化发展?
刘志伟:你这个问题提得好,让我有机会澄清我治学过程的一些时间点。你的问题以我毕业论文提交的1983年为起点,以后在这篇论文基础上增订成书出版的1997年为转折点。但其实,现在出版的这个书稿的基本格局,是1985年前后完成,主要是在1983年的研究生论文上增加了第五章以及第二章“盗乱”一节。书迟迟未出版,是因为我当时不觉得这是一个完整的研究成果。因此,我在接下来几年,只是把书中一些内容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并没有打算把它出版出来。后来到1994年前后交到出版社的这部书稿,其实是一本不完整的书。
我说这是一部不完整的书,意思是8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关注的问题已经很明确是在社会经济结构问题上,我认为并没有一个“问题意识的变化”的问题。我们这一代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者,都一定是把社会经济结构演变作为自己研究的核心问题,不太可能把赋役制度改革本身作为问题的。何况我一开始确定这个课题的时候,就很明确是要继续梁方仲先生的一条鞭法研究的路径,梁方仲先生从一开始做一条鞭法研究,就很明确地说出了一条鞭法包含的意义:“不仅限于田赋制度本身,其实乃代表一般社会经济状况的各方面。”沿着梁方仲先生的研究路径,我读研究生时,从户籍赋役制度着手,真正着眼的,从一开始就是明清社会经济结构。我的毕业论文的初稿,本来后面还有专门一章,讨论从户籍赋役制度演变所见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文稿已经写出来了,但我的导师汤明檖先生认为我在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讨论还很肤浅,要我撤了下来。这一章我完全丢弃了,从来没有发表。后来书中增加的第五章也不是这一章,只是连接这一章的过渡。我在1985年、1986年前后更多把眼光投向乡村社会,其实就是为了把当时老师认为我研究未深的领域深入下去。后来,深入下去就似乎走到了另一个研究领域了,以至于很多朋友以为我改变了研究方向,其实,我一直关心的,还是同一个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1985年前后是一个转折点。我在此前虽然也关注社会结构的问题,但当时还没有下到乡村去实地调查。我早期所做的,只限于接触到相关的几类材料。例如族谱,1980年我写研究生论文的时候,就考虑过研究族田,后来因为叶显恩、谭棣华老师写了非常好的论文,我就放弃了,但还是看了很多族谱。另外,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也打算做鱼鳞图册,因为我们系藏有一批鱼鳞图册,我都看过了,后来也没有做下去。我比较早也写过关于珠江三角洲沙田的论文,我印象中我第一篇发表的论文就是关于沙田的,是1981年写的,大概是1981年、1982年就发出来了。另外,关于“盗乱”的研究,是从1983年开始的,论文是1985年写的。当时我看了黄佐的《广东通志》,其中有大量关于盗乱的内容,其他方志也有一些相关的盗乱记载,很自然我就关注了“盗乱”与社会结构变迁的问题。那时,我还不懂得要从信仰和仪式去考察,在1983~1984年的时候还没有这种意识。不过我在80年代初就对社会文化问题有很多关注,这有另外一个渊源,就是中山大学的民俗学、人类学传统。我的老师中,很多是人类学学者。在当时历史系资料室二楼书库,一进门第一排书架就摆放着《民俗周刊》,而且读起来很有趣味。我那时候基本天天都待在资料室,所以1981~1982年看了很多的《民俗周刊》,这对我的学术兴趣是有直接影响的。但这个时候确实没有想到过这会成为后来我的一个研究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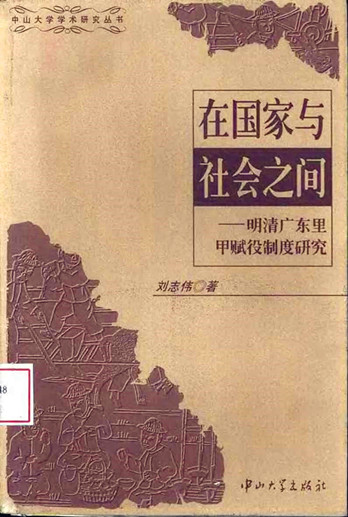
除了1986年整年在小榄的田野调查之外,从1987年到90年代初,我和萧凤霞、科大卫每年都到小榄和新会的潮连做调查,当时我们下去非常频密。除了在中山、新会做田野调查之外,从1988年开始,在科大卫的带领下,我们还到香港新界看香港学者在那里做的田野调查。记得第一次是1988年科大卫安排我们去看新界的打醮,那次我们认识了蔡志祥、张瑞威等年轻学者。虽然那次由于搞错了日期,没有看成,但是印象很深刻,收获很多。第二天蔡志祥带我们去长洲,看坟墓,讲打醮。这时我们开始对信仰、宗教有比较实际的认识。从这一年开始,一直到90年代中后期,几乎每年我都会跟着香港的学者在新界看神诞和打醮等乡村仪式。这个经验,令我对从事乡村研究,必须去看乡村的仪式和信仰有了越来越明晰的认识。1988年,科大卫还得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资助,开始了一个叫作“珠江三角洲传统乡村社会文化历史调查计划”的项目,主要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做一些乡村调查。当时科大卫和我去找几个调查点,第一个点是德庆的悦城龙母庙,是从广州坐船去的。看过悦城龙母庙之后,我们坐长途汽车去三水芦苞,芦苞有一个北帝庙。我们到那里一看,觉得很兴奋。因为科大卫之前已经对佛山有很多研究,佛山有一座北帝庙在当地历史上非常重要,我们在芦苞稍稍了解到一些情况,已经隐隐感觉到这些不同的地点可以串起来建立某种地方历史的线索。我们另外还选择了两个点,一个是番禺沙湾,另一个是南海沙头。沙湾在沙田区的边沿,沙头在桑园围。这几点在空间上的关系可以反映出珠江三角洲乡村社会历史的不同时间和阶段的情况。1989年和陈春声、戴和、萧凤霞一起在沙湾住了半年,这是此项目最长的一次田野考察了,科大卫也会经常来。

这就是我们最初几年在珠江三角洲做乡村社会研究的大概情况。经过这几年的研究经验,我的确把视线重点转移到了乡村社会,而且把更多时间放到了田野研究以及民间文献上面。旁人看起来,产生了我转移了研究方向的印象,这也很正常,但我始终认为这是我早期研究的延伸。
当然,由于这个阶段我们走进田野,是与一群对乡村社会有研究兴趣的朋友一起走的,外面看起来,我们做的是同样的研究,但其实,我们各自有不同的研究背景,也有不同的问题意识。如果说,我们逐渐形成一些共同的兴趣和意识是在1991年以后,尤其是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陈其南教授主持的华南研究计划的开展,使我们逐渐形成了更多的共识。大约1990年,萧凤霞在香港筹了一笔经费,叫李郑基金,是李兆基、郑裕彤捐了一笔钱给耶鲁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用来推动两个学校的中国研究。我们可能是最早得到这个基金资助做项目的。萧凤霞自己是筹款人,不便作为项目主持人申请,就找了陈其南教授牵头,项目主题为“华南传统中国社会文化形态研究计划”。1991年,陈其南到广州来找我,我们谈了两天两夜。第一天晚上我的印象最深,我们先在中国大酒店的餐厅谈,谈到9点半,餐厅开始有歌唱表演,很吵,我们又转去了东方宾馆继续谈。当时谈的主要话题是,这个计划究竟怎么开展。首先是邀请什么人参加,我们最后确定的人选是:广东的陈春声、戴和、罗一星和我,福建是郑振满、陈支平,香港是科大卫、蔡志祥、萧凤霞,还有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的郑力民(因为当时陈其南对徽州有兴趣)。后来,江西以梁洪生、邵鸿为主的学者也加入了。关于具体的运作方式,当时我们和科大卫、萧凤霞他们合作了虽然只有几年,但是感觉已经合作了很多年一样。我们认为我们最成功的是,我们不像别人那样共同去做一个课题,但是我们在各自研究的同时,经常进行有深度的讨论和沟通,共享想法、共享资料。这种经验,成为后来我们各种合作项目的模式。当时我和陈其南商定,“华南研究”仍然采取这种合作模式。项目参加者仍然是各做各的研究,但每两个月在一个人的田野点举办一次工作坊,每次3至5天。
第一次工作坊是1991年8月2至5日在广东新会的潮连镇,由萧凤霞主持。那时候,我、萧凤霞、科大卫三个人都在潮连做田野研究。第二次是1991年9月27至30日在广东佛山,由罗一星、科大卫主持。第三次是1992年1月3至5日在广东番禺,由我主持。第四次是1992年3月20至23日在广东澄海的樟林镇,由陈春声、蔡志祥主持。第五次是1992年7月23至29日,由陈其南主持。第六次是1992年8月12至16日在福建莆田,由郑振满、丁荷生主持。
我记得我们形成比较一致的共识,是在佛山举办的那次工作坊上。我们那一次讨论提出要有一些共同的方法和主题,以及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大家觉得神明的祭祀与信仰可以作为我们的主题。这里所说的神明崇拜也包括了祖先崇拜,祠堂、宗族的研究也可以纳入这一主题之内。当然,这样的兴趣,并不是新的想法,科大卫、蔡志祥在香港新界,以及我与萧凤霞在中山小榄进行的研究,例如她后来写的菊花会的文章,都与仪式有关。不过,作为这个计划的一种共识,是在佛山那次工作坊确立的。后来我们去了广东潮州、福建莆田考察,更确信这是我们这个计划的核心关怀。尤其是到了郑振满的田野点之后,这种认识更为明确了。当时,他的博士论文刚刚出来,讲的是宗族,但跑到莆田,他整天带我们去看庙,我们就和他说:“你要带我们看宗族。”一天早上,郑振满说:“好!我带你们去看宗族。”车子开到一个庙面前,我们下来一看还是庙,然后我们问,宗族呢?他指着庙里一块很大的碑,说宗族在这里。碑里的捐款名字确确实实是一个家族的系统,我们发觉,他们的宗族原来是在庙里面。第二次我们再到莆田,到了东岳庙,我们突然悟出:莆田的历史是从宋代开始的,宋代本地的士大夫塑造了当地的传统,把地方神提升到国家认可的高度,以神明的方式把地方拉进了王朝体系。科大卫和我们研究的珠江三角洲的历史,是从明代开始,他们更多用的是宗族的语言。于是我们就形成了一种带有理论意味的认识。这个认识现在看起来很简单,但在当时,我们觉得对我们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历史时间、制度、文化规范、空间,以及在田野中看到的各种文化形态,都可以打通来思考了。
我本来是要把我们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走过路程的时间脉络交代一下,有点扯远了。你刚才提问里面提到的14年是怎么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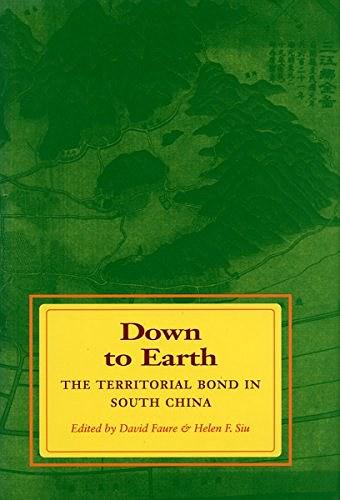
刘志伟:这14年是从文本发表出来看到的时间,其实并没有意义。真正有意义的转折不是我的书的出版,因为那本小书从完稿到出版,中间隔了12年时间,是我的拖拉造成的。刚才说了,对我们研究的进展来说,比较重要的时间点是1985年和1991年,再后来,1995年也是很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那时,我们已经走了很远很远了,所以出书的1997年,并不是一个转变的时间点。
1995年我们在牛津大学开了一个会,这是一个带有总结性的会议。当时,科大卫在牛津大学,我也到了他那里访问,蔡志祥当时也在爱丁堡。趁着我在牛津大学,科大卫把丁荷生、郑振满、陈春声、廖迪生等请到牛津,我们开了五天的会,议题集中在珠江三角洲、莆田平原和韩江三角洲,每天讨论一个地方。在会上我们对大家的研究有很多讨论,在很多问题上都争论得很厉害。在争论中,我们对过去的研究形成了比较清晰的想法,大家现在在这个领域看到我们讲的东西,当时已经有比较系统性的理解,后来只是陆续发表出来,实际上在认识上已经没有太多的进步。
1995年还有另外一件比较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那一年,我们以参加AAS(亚洲研究协会)年会的一个小组报告为基础,由科大卫和萧凤霞合作主编出版了Down to Earth(《植根乡土》,1995)这本书,这本书导论和结论可以说比较系统地把我们的研究旨趣表达了出来。几年后,科大卫写出了Emperor and Ancestor(《皇帝与祖宗》,2007),这是一本很重要的带有总结性的著作。
可以说,1995年出版的Down to Earth和此后科大卫开始写作的Emperor and Ancestor,都表明这一年在我们的研究道路上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时间点。

刘志伟:你提到的1991年这个时间点是有意义的,正是前面我提到的“华南传统中国社会文化形态研究计划”。但不是说到1992年才扩展到这些领域。我刚才已经提到,我第一篇文章就是讲沙田的,1984年前后我已经有一篇讲宗族问题的文章,族群与盗乱是我1983至1984年研究的重点。那时的研究最后写到书里只有一句话,但这是在我研究经历中花的时间最多才写下来的一句话。你看一回我的这句话就明白了,这句话原文是:“所谓的‘蛮夷’,不仅是一个血统的范畴,更是一个文化和社会的范畴,他们不仅在文化上属于‘魋结卉服之民’,在社会身份上更是区别于‘良民’‘编户’‘齐民’,属于所谓的‘化外之民。’”在我的毕业论文完成之后,我花了很多时间想去把广东的族群问题研究清楚,这些所谓的族群,在文献中叫作“獠”“猺”“獞”等。我关注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在研究广东明代的户籍赋役制度问题时,感觉到当时广东的社会变动,与这些族群在文献中呈现出来的活动有直接的关联,我要真正理解户籍赋役制度改革的社会意义,尤其是落实到本地的社会脉络,不能不了解当时的族群问题。我当时是看了好多这类的资料,也包括当代民族学者的调查。不过我当时得到的认识是,明代广东的各种族群,文献中记录其实是很混乱的。明代文献中记录,当时大部分的非汉族群是“獠”,但到了明代后期以后,似乎就没有了,很多资料都没有提到。后来研究瑶族的李默先生是讲从“獠俚”到“猺獞”的转变过程,但我当时觉得,这个说不清楚的问题,其实反映了明代很多族群都在当时的社会变动中改变了身份的事实。
温春来:刘老师,马克思好像对您产生了很大影响。之前您多少提到过这一问题,但是没有听您细讲。
刘志伟:我们这代人,年轻时候读过的书,最重要的当然是马克思的著作。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没有什么书可读,能读的有思想深度的书都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我们的学术思维是从马克思那里学的。我16岁中学毕业,那是1972年。中学毕业之后,我有一段工作的经历,当时毛主席要我们读马列原著,其中有6本书是毛主席要大家读的,就是《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我最早阅读的具有思想深度的著作,当时我读后觉得最有收获的是辩证思维,因为我们少年时已经读《实践论》和《矛盾论》,后来又读过艾思奇的哲学教材,我觉得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思维是不太一样的。当时希望从辩证法里找思想资源,解开疑惑。到大学读书之后,又读了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列宁的《哲学笔记》等。后来我们上蔡鸿生老师的课,要读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农民战争》以及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再后来又读《人类学笔记》。到读研究生时,还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我觉得读这些著作对辩证思维的训练很重要。我那时候对哲学比较有兴趣。真正让我们着迷的还是辩证法,读《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头脑里都是辩证法的思维,再读黑格尔就更是如此。这个与我们那时候的政治关怀和时代的感观有关系。这种阅读是希望能够解开我们那个时代的困惑。所以,我相信年轻时候真正影响我们形成辩证的学术思维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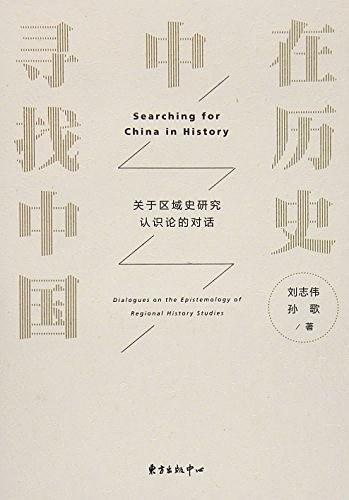
刘志伟:我近年来比较多写(谈)些议论性的思考性的文字,第一个原因是自己老了,时日无多了,觉得过去阅读和研究过程中思考过的问题和产生的想法,还是要赶快用笔记录下来,留下一点想法,这是比较正面的动力。
第二个是比较负面的动力,就是越来越觉得自己做不了什么专门的实证的研究了。要为自己找借口,可以找出很多客观原因的,如费很多精力要去管理各种各样的项目,我都是要承担“管家”的角色,再加上多年来从事行政工作,虽然没有离开读书和研究,但专精深入的研究逐渐少了。除了这个借口以外,更重要的是,我原来主要做明代的研究,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能看的明代历史文献很少,尤其是明人的文集,基本文献大致能仔细研读。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过去看不到的明代文献大量被影印出版。最早是把《四库全书》里面的明人文集单独影印出来。现在的人可能把这套书忘了,但当时这套书出来之后,我一看,就知道麻烦了。我以前做研究的时候,看得到的只有收入《四部丛刊》的那几本,现在一下子可以看到那么多。继这一套书之后,《四库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系列也陆续出来了。还有过去只能从《天下郡国利病书》中看到明代方志的片段,也大量影印出版了。于是,一方面我们能看到的明代文献呈数以百倍的规模增加,另一方面自己能用于研究的时间越来越少。以前我们做研究要求能掌握基本史料,但当时在中山大学,连《诸司职掌》《大明令》这些典籍都看不到,甚至《明会典》在中山大学图书馆也缺藏,所以有一种能掌握基本史料的自信。但90年代以后,大量明代文献涌到自己面前的时候,一下子产生了畏惧感,从此,我越来越相信自己剩下的时间做不了多少研究了。
第三个原因是在我重版书的后记里面提到的,我当年期望继续深入做下去的主要问题,最近十多年来,有越来越多人关注了,尤其是年轻学者们,他们找到的材料也越来越丰富,研究的专精和细致,都比我做得好。我觉得我已经落伍了,更没有信心了!
这些也许是我近年比较多发议论而少做专题研究的原因吧。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