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荷兰人在日本的经验:“欧洲崛起”并非所向披靡
本文选摘自《公司与将军:荷兰人与德川时代日本的相遇》,[英]亚当·克卢洛著,朱新屋、董丽琼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5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标题为编者所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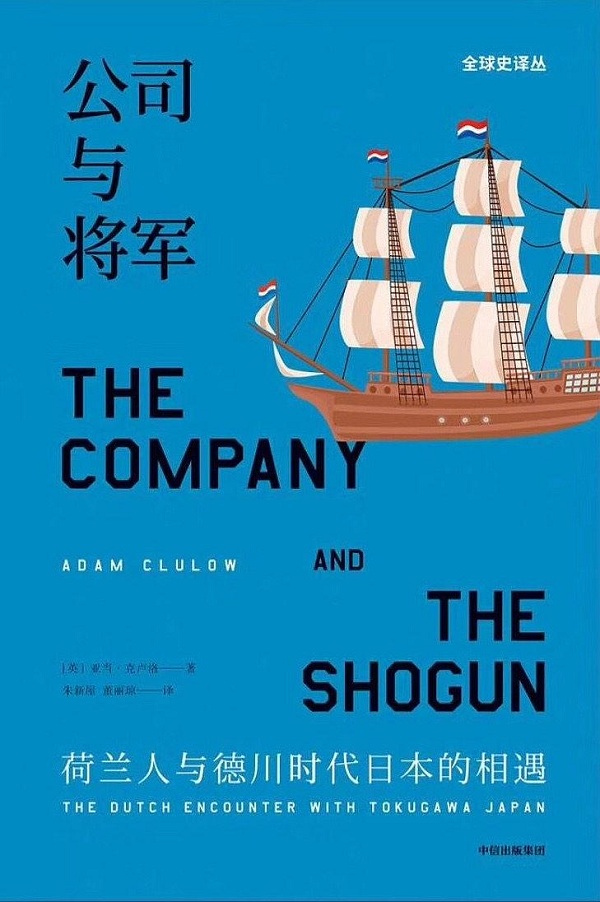
以上两种关系类型中的一种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这种关系中逐渐积累权力,直到它能够决定双方订约的条件,以此来获得更具主导性的地位。这种类型主要包括印度尼西亚的政权,如马塔兰、万丹和望加锡,它们都在17世纪开始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强大竞争对手,但最终以一种从属地位被纳入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帝国中。韦纽斯和芬克的著作显示,尽管在这一过程中荷兰东印度公司遭受到频繁的(有时是毁灭性的)挫折,但在整个侵略性扩张的漫长时期,不论是在马塔兰、万丹,还是在望加锡,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地位仍然成功地不断上升。荷兰东印度公司与爪哇中部的马塔兰君主的关系——在前面的章节已有简单讨论——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权力的缓慢增长提供了典型例子。马塔兰在阿贡苏丹(Sultan Agung,1613—1646在位)统治时期,几乎要征服巴达维亚,后来却被迫变成一个越来越从属的角色,到1677年唯有依靠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军事支持才平定了内部叛乱。同一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另一个竞争对手——万丹港口的政权影响力与日俱增,后者最终于1684年被迫签署一个单方面的条约,承认荷兰总督的权威。
巴达维亚与位于南苏拉威西(South Sulawesi)的戈瓦(Gowa)苏丹或望加锡苏丹之间的往来有着相似的轨迹。16世纪晚期,苏丹作为一支商业和新兴的军事力量崛起;至17 世纪上半叶,苏丹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最持久的对手,它有能力召集成千上万的军队,把望加锡城变成了一个日益繁荣的中心,其规模之宏大,堪比欧洲的都会城市。160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望加锡开办了一个工厂,但双方关系却迅速恶化。虽然荷兰人被迫于1615年撤退,但是随后的冲突断断续续地持续了五十多年,双方争夺的焦点主要是对贸易的控制。荷兰东印度公司曾勇敢地尝试通过为包括葡萄牙人在内的外来贸易者提供庇护所,来建立起对珍稀香料的垄断权;望加锡正是在规避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这种限制的过程中才繁荣起来的。事实上,望加锡的统治者曾大肆抗议:“真主安拉创造了大地和海洋。他在人们中间分割大地,海洋为大家所共有。从未听说过任何人可以禁止通航。”
巴达维亚充分利用武器优势,尤其是通过强势的外交部署和军事设施,来回应苏丹的挑战。为获得贸易控制权,荷兰东印度公司曾通过一系列的信件和派遣使节,与继任的苏丹建立了双边关系,这些苏丹把荷兰总督看作是一个拥有自身权利的独立政治行动者,而且同时作为“所有土地与堡垒、大大小小的船只,以及所有荷兰臣民都在其庇护之下”的统治者。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劝说未能产生效果,于是很快诉诸武力,正如它在日本的行动一样,派出船只袭击在望加锡海域的葡萄牙船只,随后又于1653年、1660年和1666年发动了对苏丹的一系列战争。最后一次战争最具决定性,1667年哈山努丁苏丹(Sultan Hasanuddin,1653—1669 在任)被迫签署《本加亚条约》(the treaty of Bungaya),实际上把望加锡变成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属臣。
在为掌控关系主动权而发动的三次战争期间,荷兰东印度公司逐渐施加压力,直到它能够对其曾经的对手实施绝对的影响力。然而,这种类型的关系远非标准模式,因为在其他类型的关系中——荷兰东印度公司被迫做出让步,甚至处于更危险的境地——也有着数不清的例子。后一种情况涉及的对象十分广泛,包括了早期近代亚洲一些最重要的政权,如中国的明朝和随后的清朝、印度的莫卧儿帝国、波斯的萨非王朝,以及暹罗的大城王国,所有这些政权都动用了远远超过荷兰东印度公司所能聚集的军事力量,而荷兰东印度公司只能甘拜下风。毫不意外,巴达维亚和这些政权之间所发展的关系也就随之改变。比如最明显的差异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某些情况下能成功地建立起持续性联系,而与一些政权的关系则更多是断断续续的。
例如,在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关系是间歇性的,从未成功地建立起一种持续性关系。事实上,它想要在中国统治边缘巩固自己地位的两次尝试都以军事败退告终——1624年荷兰人被一支明朝舰队从澎湖列岛击退,1662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旗帜被郑成功的军队在台湾推倒。中国有着如此大的规模和威力,即使在其国内动乱频繁和内部政权瓦解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也从未处于一种拥有决定性话语权的地位,但它总是利用大宪章第35 条中授予的使用武力的权力,扬言进行某种出其不意的袭击。因此,如前所述,162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对中国宣战,决心利用其船坚炮利来迫使明朝官员开放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殖民占领澎湖列岛之间的贸易。尽管这些策略在东南亚十分有效,但是在恐吓中国官员时却远没有那么有用。荷兰人意识到中国官员打算显示其势不可挡的军事力量。事实上,巴达维亚战役的结果之一是吸引了中国沿海官员的全部注意力,他们陆续召集军队准备驱逐澎湖列岛上的荷兰人。因此,公司第一次与中国明朝建立联系不是以落脚台湾而是从台湾撤退为结局。
明朝覆灭以后,荷兰东印度公司面临着一个更为复杂的政治环境,它不得不处理与两个相互竞争的中国政权——一个已控制绝大部分中国大陆的清政权,以及一个实际上在郑成功治下的海上政权——的关系。处理与前者的关系,公司的首选工具是官方使团,多个荷兰使团被派往北京,带着荷兰总督的信件和礼物,希望结成军事联盟以期获得商业让步。正在此时,荷兰东印度公司面临着来自郑成功的日益严峻的威胁。郑成功正致力于将台湾变成一个反清战争的基地。转折点来临时,就如1624年一样,中国统治者——在当时情况下指的是郑成功,决定不再容忍荷兰人的存在,聚集了大批军队将他们从大员的坚固阵地中驱逐出去。结果,荷兰东印度公司又一次遭到溃败,尽管它从未在中国军队的袭击中占据过优势地位,但是这一次从事实上结束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中国海岸的存在。
暹罗的情况恰恰相反,荷兰东印度公司成功地建立起了与大城王国(1351—1767)的持久关系。从1608年在暹罗开设工厂,到1765年的150多年时间里,虽然有过偶尔的间断,但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持续在那里开展活动。这种关系的长期存在主要取决于与大城朝廷的相对良好的关系,大城朝廷很热情地与荷兰人往来。巴哈旺?栾斯尔皮(Bhawan Ruangsilp)的论著,是对荷兰人在暹罗的最好研究之一。她认为巴达维亚和暹罗国王之间发展出了一种伙伴关系,尽管她也谨慎地指出这种关系一直是有条件的。处在这种关系中心的是双方频繁的外交往来,首先是暹罗君主与奥兰治亲王,然后是与巴达维亚,使团定期往来于荷兰东印度公司总部与大城首都之间。荷兰东印度公司不仅被看作一个商业和外交伙伴,而且被当成一个有价值的军事同盟;正因为这样,荷兰东印度公司利用外交的能力也得到提高。实际上,暹罗国王在与敌人或叛乱下属的各种战役中,曾多次向荷兰官员寻求军舰协助。
与在中国的情况一样,荷兰东印度公司从未能够对暹罗发号施令,其雇员将暹罗描述成一个“著名的强大的王国”,但是它打算采取强势行动,并利用必要的工具来迫使大城对一些关键问题的政策有所转变。最明显的是1663年,巴达维亚认为——引用栾斯尔皮的话——一系列“荷兰东印度公司和暹罗国王之间累积的问题,都应按照它的条件得到解决”。为此公司选择了一种老掉牙的策略——军舰封锁。从1663年11月到1664年2月,公司的船只封锁了湄南河,抓获暹罗帆船,直到国王对巴达维亚的要求做出让步。双方签订了一个条约,根据当时荷兰人的报道,“ 出于对荷兰东印度公司威力和武器的惧怕与敬畏”,才为荷兰东印度公司赢得了一系列的重要让步。这一短暂却十分有效的战役,其总的影响是将荷兰东印度公司与暹罗的关系重新调整到一个对巴达维亚更为有利的位置。

上述简略讨论把我们拉回到日本,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日本的经验的问题。当然,巴达维亚与德川日本之间维持了两个多世纪的持久联系,与它在中国所发生的间歇性交往有着明显的不同。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暹罗也成功建立了一种持久性的存在,但出人意料的是,日本的例子与和大城王国所建立的关系也几乎毫无相同之处。最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日本几乎很少看到栾斯尔皮所描述的有条件的伙伴关系的证据。相反,这是一种绝对的不平等关系,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其中被迫处于一种一贯的从属地位。尽管这部分是因为德川幕府相对强大的力量,它是早期近代亚洲强大的政权之一,但只是指出这一事实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事情会发展成它们所呈现的那样。通过关注在17世纪——也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强势扩张阶段,荷兰东印度公司和德川政权之间发生的所有一系列冲突,本研究试图为此提出解释。
1609年抵达日本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就是一个带有企业和政府双重属性的混合组织。因此它来日本时不仅带着船只和商品,还带着一种源自大宪章并且决心要予以执行的统治权。荷兰东印度公司随后对外交、暴力以及主权的权利维护,引发了与幕府的一连串冲突。在这些冲突中,诸如荷兰东印度公司是否能与幕府将军建立高层次的外交关系,是否有权在日本海域或针对日本贸易伙伴实施海上暴力,以及是否有权在大员宣示绝对主权等,荷兰东印度公司与幕府将军之间的关系,我已经表示过,大体上是确定的。虽然是以不同的方式,但在每种情况下都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而非德川政权被迫放弃立场,从其对应有权利和统治特权的坚持上做出退让。这个过程一旦完成,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失去了它在亚洲其他地区理所当然采取的手段。
在暹罗,比如1663年发生在湄南河的事情,一个阵容强大的使团或精心策划的海上战役就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创造了有利的机会,然而这种调整性的武器在日本是不存在的。1632 年的例子很明显,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决定采取非常措施,为了恢复与日本的关系,将一位高级官员彼得?奴易兹引渡到日本。荷兰官员在这一时期的许多评论也能证明这点。例如,1638年12月,荷兰总督明确解释了公司在日本的策略:“切勿惹恼日本人。若想要得到一些东西,你必须等待适当的时机与机会,并且必须抱有极大的耐心。他们不喜欢被人反驳。因此我们将自己变得越不重要,假装成卑微、低下和谦逊的商人,只为他们的愿望而存在,我们就能在他们的土地上获得越多的喜爱与尊重。这是我们从长期的经验中得来的……在日本,再怎么谦逊都不为过。”
在荷兰联合省,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也支持同样的观点。在著名的1650年通令中,十七先生谈到日本问题时,认为“除了使这个傲慢、宏大和严谨的国家在各方面都满意之外,我们给官员们没有其他训令”。董事们坚持,荷兰东印度公司官员应该“带着谦逊、卑微、礼貌和友谊”,绝不能去命令德川政权,而是应该一直服从它的愿望。
荷兰东印度公司为此失去了使用它在亚洲其他地区所依靠的有效工具的机会。但是事情绝不仅仅这么简单。在日本的荷兰人以某种方式融入日本的内部体系,这与大城的例子截然不同。去观察巴达维亚在两次不同的军事行动中向暹罗国王和后来的德川将军提供的支持,就可以看出这种区别的意义。从1633 年开始,暹罗的巴萨通(Prasatthong)国王(1629—1656年在任),通过许诺有利可图的贸易特权来换取军舰支持,试图引诱荷兰人加入反对其臣属国帕塔尼的战争中。这些请求最终奏效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634年派出一支小型舰队参加了军事行动。尽管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参与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巴达维亚愿意提供援助,为荷兰人赢得了一系列新的特权,极大地改善了他们在暹罗的处境。三年之后的岛原战役,其情形则完全不同。荷兰人并非因为许诺回报被卷入战争,而是受制于他们自己的言辞与过去的承诺,不得不自愿作为幕府将军的国内属臣参与镇压叛乱。
两次战役的差异说明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与幕府将军的关系其性质截然不同。在日本,荷兰东印度公司被驯服,受限于一个自我设定的属臣角色,承担了一系列的附带责任。不论是省督还是总督,荷兰人尽管有着明显的异域性,却放弃了他们代表一个强势的外部力量的权利,转变成了国内属臣。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代表们作为日本国内属臣的一部分,服从于一种量身定制版本的参勤交代制度;被要求承担军事服务(直接地或以提供情报的形式);在接受幕府将军的法律权威(至少与某些犯罪有关)时,被迫放弃一些关键权利(最明显的是与实行海上暴力有关);像其他属臣一样,被迫在呈递炫耀性展示品时扮演自己的角色。这是一个将会变得越发熟悉的角色,年复一年地扮演这一角色,直到表演与现实的边界变得十分模糊。至于荷兰人是否是真正的属臣,抑或只是扮演着属臣的角色,这些问题基本上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行动事实上已经像是幕府将军忠实的仆人,构成为幕府将军服务(hōkō)的单独组成部分——正如在《通航一览》中所显示的那样,在德川幕府的秩序中,荷兰人拥有与众不同的身份。
这项研究并不是要记录荷兰人在日本的历史,而是要关注在这段历史中产生的一系列冲突,旨在追踪一个社会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荷兰人被迫去适应并在德川秩序中找到一席之地。这些冲突几乎毫无例外地是在有利于日本的情况下得到解决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与德川将军的关系不完全是典型性的,这一点应该很清楚;但是它也并没有脱离欧洲人在亚洲更为普遍的经验,它不应当被看作一个在日本范围之外的无甚相关的历史局外人。尽管存在这样一种理解趋势,即关注直接殖民化发生的地方,或者欧洲在其中产生最大影响的关系,比如荷兰东印度公司与马塔兰、万丹或者望加锡之间的关系,但这些并非常态,更常见的剧目是欧洲人在其中努力掌握他们与亚洲打交道的主动权。毫无疑问,没有什么可以比荷兰人在德川日本的遭遇更好地证明这一点。
如果我们跟随彭慕兰、王国斌等人的著作,接受在早期近代时期亚洲政权的持久权力这一事实,那么很明显,更好地去记述欧洲人被纳入亚洲秩序这一长期的融合过程,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荷兰人在日本的经验表明,欧洲在亚洲的立足点并非一贯是从孤立的贸易商栈转变成城堡基地,最后变成完全的殖民地。事实恰恰相反,强大的亚洲政权的存在,意味着即使是最强大的欧洲组织也会被一个它们无法逃脱的牢笼所限制。日本给在亚洲的欧洲企业制造了一个象征性的死结,一个完全受到遏制的场所,因此为那些认为“欧洲崛起”始于1492年或1497年的探险远航,并在随后几个世纪里伴随着无休止的战鼓所向披靡的研究,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对比。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6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