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韩柳文研究法》:翻译家林纾的另外一面
林纾最家喻户晓的成就是翻译,但是他一生著述宏富,尤致力于古文的评点与写作。唐代韩愈与柳宗元提倡古文运动,在文学史上影响深远,其文章被后世奉为典范。林纾所著《韩柳文研究法》,遴选韩柳佳作一百四十余篇,逐篇剖解其文理与技巧,集中呈现了他在民国初年尖锐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宁为新近整理出版之《韩柳文研究法校注》(低音·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11月)所写的序言,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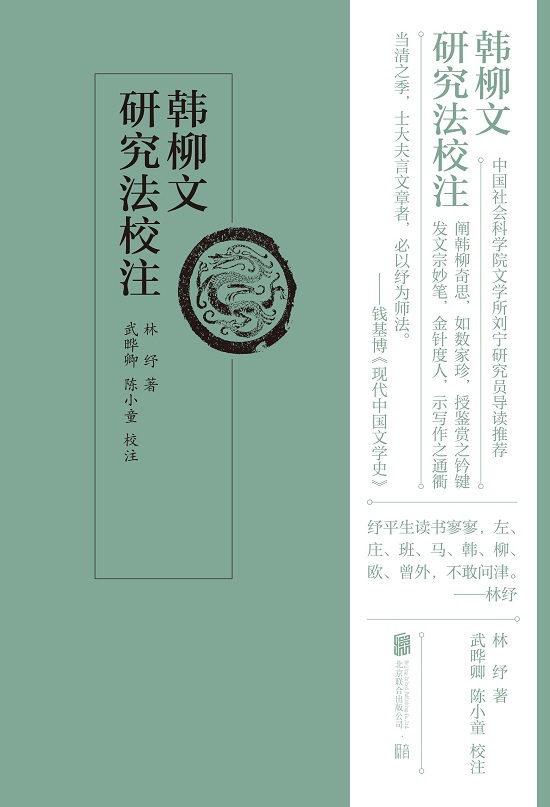
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林纾最家喻户晓的成就,是翻译二百多种外国小说,风行海内;然而在近代文化史上,他还有许多重要的建树,其中作为古文家,在新旧文化转关之际,为延续和发展古文传统所做的一系列努力,尤其值得关注。对于古文艺术,他既有抉发文理的理论思考,又有体悟文心的篇章点评,前者的代表作是《春觉斋论文》《文微》等著述,后者的代表作则是《韩柳文研究法》和《左传撷华》。韩柳古文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历代品评者众,林纾这部《韩柳文研究法》自出手眼,对理解韩柳古文极有裨益,因此自问世至今,一直是阅读韩柳古文难以绕开的津梁。
韩愈是古文宗师,林纾对韩文极为推重。在《左传撷华》中,他说:“天下文章,能变化陆离不可方物者,只有三家:一左、一马、一韩而已。”对于韩文,他沉潜钻研,倾注了极大的心力,在《答甘大文书》中,他回忆自己的学韩经历:“仆治韩文四十年,其始得一名篇,书而黏诸案,幂之。日必启读,读后复幂,积数月始易一篇。四十年中,韩之全集凡十数周矣。”林纾晚年曾反复劝勉后学,读古人书要“神与古会”,要“涵而泳之”,“泳如池沼澄碧,鱼凫上下,自在悠游于中;涵如以巾承露,浸渍全幅使透”,又说“读文须细细咀嚼,方能识辨其中甘辛”(《春觉斋论文》)。他对于韩文的研读,显然就是如此全身心地沉浸浓郁。
由于寝馈甚深,林纾自己的古文创作也被韩文潜移默化。1901年,他以文名被聘为北京金台书院讲席,从此由闽入京定居。不久又任五城中学堂国文总教习,其间与桐城古文大家吴汝纶结识。吴称赞林纾的古文“是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气者”(林纾《赠马通伯先生序》)。这一评语非常接近北宋苏洵对韩愈文章的评价:“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可见,在吴汝纶看来,林文深有得于韩文之精髓。
这部《韩柳文研究法》初版于1914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印行,林纾此时已六十二岁,刚从北京大学去职。全书选评韩文60余篇、柳文70余篇,应是在其北京大学授课讲义的基础上整理而成,当时京师大学堂的课程,多以某某研究法命名,此书的命名应该是受此影响。书中具体的选评方式,继承了古文的评点传统,但内容则多有独到的思考,不仅反映了林纾数十年沉潜韩柳文的所得,也体现了入京后复杂文化学术冲突对他的触发和影响。林纾早年即醉心古文,他博览群书,中年后对以韩愈为主的八家之文以及《左传》《史记》《汉书》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和桐城派的古文旨趣颇为接近,但林纾并未有传续桐城派的自觉意识。入京后,他与桐城派吴汝纶、马其昶、姚永概等代表人物颇为亲近,他甚至向吴汝纶表达了希望能居门下受业的愿望。1906年他受聘任教于京师大学堂,与当时同在大学堂任教的章太炎产生矛盾,钱基博提到当时“大抵崇魏晋者,称太炎为大师,而取唐宋,则推林纾为宗盟”(《林纾的古文》)。由于章太炎一派的排挤,林纾不得不于1913年从北京大学去职。无论是与桐城古文家的亲密,还是与章太炎一派的矛盾,都强化了林纾对桐城派所主张的以唐宋古文为核心的文章传统的认识。虽然他一直不认为自己是“桐城派”,而且明确主张“桐城无派”,反对用狭隘的派别来框定桐城诸子的成就,但桐城派对其古文思考的影响,在入京之后无疑是日趋深刻的。这部《韩柳文研究法》就体现出这种影响。
桐城派主张“文道合一”,“桐城三祖”之一的方苞重“义法”、讲“雅洁”。所谓“义法”,方苞认为“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意谓文章内容要合乎儒家之义理,行文要讲求法度。所谓“雅洁”,就是为文以儒家伦理之道为本,立意雅正,语言也不能芜杂枝蔓。这些文章宗旨,都鲜明地体现在林纾对韩柳文的解读之中。北宋秦观称赞韩文“钩庄列,挟苏张,摭迁固,猎屈宋,折之以孔氏”,林纾认为此语颇为不妥:“韩文之摭迁固,容或有之;至钩庄列,挟苏张,可决其必无。昌黎学术极正,辟老矣,胡至乎钩庄列?且方以正道匡俗,又焉肯拾苏张之余唾?”林纾认为秦观被韩文的“海涵地负之才,英华秾郁之色”所炫惑,没有看到韩文“信道笃、读书多、析理精”;因此,林纾论韩文,始终坚持以儒为本。
在艺术上,林纾高度赞同北宋苏洵对韩文“抑绝蔽掩,不使自露”的评价,认为“蔽掩,昌黎之长技也。不善学者,往往因蔽而晦,累掩而涩……能于蔽掩中有‘渊然之光、苍然之色’,所以成为昌黎耳。”在林纾看来,韩文的汪洋纵恣,并不表现为外在的驳杂,而是内在的丰富,因此韩文的创作一定是经历了深入的锤炼淘洗,绝非率然的随兴所至,他说:“吾思昌黎下笔之先,必唾弃无数不应言与言之似是而非者,则神志已空定如山岳,然后随其所出,移步换形,只在此山之中,而幽窈曲折,使入者迷惘;而按之实理,又在在具有主脑。”
林纾对韩文的解读,正是用力于揭示韩文抑遏蔽掩、淘洗锤炼中的光芒;而其诠评的入手处,则是分析韩文的法度,其中又尤其关注韩文文体的特点。他论韩愈《原道》不仅“理足于中”,而且“造语复衷之法律”。行文有法,可使学者“循其途轨而进”。又论《进学解》,认为此文“本于东方《客难》、扬雄《解嘲》”,孙樵以其行文奇警而将其与卢仝《月蚀诗》相提并论,是不恰当的。又如《张中丞传后叙》是“盖仿史公传后论体”。这些都体现了辨体的努力。林纾对古文文体特点多有精妙的论述,如论“赠序”之特点:“愚尝谓验人文字之有意境与机轴,当先读其赠送序。序不是论,却句句是论,不惟造语宜敛,即制局亦宜变。”又论“祭文体本以用韵者为正格,若不驾驭以散文之法,终觉直致”。这些文体之论,都颇为新警深刻。
在此基础上,林纾进一步观察到韩文法度中的新意,规矩中的千变万化,如论韩愈之书信:“一篇之成必有一篇之结构,未尝有信手挥洒之文字。熟读不已,可悟无数法门。”又论韩之“赠序”如“飞行绝技”,无人可以企及。《韩柳文研究法》最吸引人的地方,正在于对这些无法之法的解读。他或言韩文语言之妙,“在浓淡疏密相间错而成文”,又论《说马》之“马之千里者”五字,是于行文几无余地可以转旋之处,忽然叫起,“似从甚败之中,挺出一生力之军”;论《画记》“文心之妙,能举不相偶之事对举成偶,真匪夷所思”;论《重答张籍书》“辩驳处无激烈之词,自信中含冲和之气”;《送齐暤下第序》则是“篇法、字法、笔法,如神龙变化,东云出鳞,西云露爪,不可方物”。
这些精妙的体悟,是林纾继承桐城而又更为丰富开阔之处。他对桐城“义法”,从“性情”和“意境”两个方面加以拓展,认为“义”要融会为一种作家内在的精神人格,形成丰富的精神性情,这种“性情”是文章的根本——“文章为性情之华”“性情端,斯出辞气重厚”。对于 “义法”之“法”,他没有将其泥定为具体的起承点画,而是从“意境”的角度加以阐发。在《春觉斋论文》中,他标举为文“应知八则”,皆文法纲领,首揭者即为“意境”,提出“文章唯能立意,方能造境。境者,意中之境也”;“不能造境,安有体制到恰好地位”。义法之法,即是“意中之境”,“境”的形成当然要综合多种因素,而其所以形成之本又在于“意”。这就为悟入古文妙境,寻绎文章无法之法,打开更丰富的空间。“桐城三祖”中的刘大櫆和姚鼐,从推重音调和艺术风格的角度来丰富对文法的认识,而林纾对文法的讨论,则综合了这些传统而更为丰富灵活。
《韩柳文研究法》另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特点,是韩柳并论。柳宗元虽名列八家之一,但后世古文家对柳文颇多争议,特别是桐城派如方苞等人,论文取法韩欧,多有抑柳之论。林纾并未受此束缚,他自述精研“韩柳欧三氏之文,楮叶汗渍近四十年矣”(《答徐敏书》),力主柳宗元“为昌黎配飨之人”。
林纾虽然突破了桐城派对柳文的偏见,但他解读柳文的视角,还是与他解读韩文一样,渊源于桐城的文法传统。唐代刘禹锡论柳文:“端而曼,苦而腴,佶然以生,癯然以清。”古来论柳文者众,林纾独以此语为知言,甚至说“虽柳州自道,不能违心而他逸”。对于柳文的语言,他认为“用字稍新特,未尝近纤;选材至恢富,未尝近滥;丽而能古,博而能精”。从思想上讲,柳宗元精通佛理,林纾对此有意加以忽略,“集中六、七两卷均和尚碑,不佞昧于禅理,不能尽解,故特阙而不论”,又“柳州集中有‘序隐遁道儒释’一门,制词命意固有工者,然终不如昌黎之变化。且释氏之文逾半,从略可也”。可见,无论从艺术上,还是思想上,林纾论柳都渗透了桐城的“雅洁”旨趣。
林纾对柳文艺术的诠评,就其方法,与评韩并无二致,也很善于揭示柳文文体特色,发抉其篇法、章法、字法之妙,如对《封建论》开篇立一“势”字的分析,对《段太尉逸事状》“气壮而语醇,力伟而光敛”的讨论,对永州山水记用字精微的品味,都值得细细体会。
林纾读柳文,最值得关注的,是对韩柳文命笔异同的对比,例如“昌黎《碑》适是学《尚书》,子厚《雅》适是学《大雅》,两臻极地”“(韩愈《柳州罗池庙碑》)幽峭颇近柳州,如‘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则非人’,此三语,纯乎柳州矣。柳州勍峭,每于短句见长技,用字为人人意中所有,用意乃为人人笔下所无,昌黎则长短皆宜。自‘民业有经’起,‘出相弟长,入相慈孝’,纯用四言,积叠而下,文气未尝喘促,此亦昌黎平日所长”。这些看法,也都很值得细细体会。
马其昶为《韩柳文研究法》作序,称林纾将自己平生对古文的甘苦所得,“倾囷竭廪,唯恐其言之不尽”。在此书出版数年后,林纾就卷入了与“五四”新文化人的论战,为延续古文命脉而大声疾呼。1917年2月8日,他在《民国日报》上发表《论古文之不当废》,称“夫马、班、韩、柳之文,虽不协于时用,固文字之祖也。嗜者学之,……必有一二巨子出肩其统,则中国之元气尚有存者”。这部《韩柳文研究法》集中呈现了他在民国初年尖锐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对作为中国文字之祖的韩柳文的深入认识。在古文的文化艺术价值重新引发关注的百年后的今天,这部书值得给予更充分的关注和探讨。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6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