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魏斌:江南名山背后的王朝政治地理因素
山岳最初都是自然性的山体,文化属性是后起的。在山岳的文化属性中,山神信仰的传统最为久远。原始性的山神信仰往往会进一步形象化和人格化,《山海经》所记述的就是这种过渡形态的山岳祭祀。而在一定的契机下,有些山岳又会被纳入官方祭祀系统,汉代以来的五岳祭祀体系,就是最显著的例子。
江南地区的山神祭祀,同样有久远的传统。《山经》中的《南山经》《中次十二经》,记述江南山岳和神祇不少,如《中次十二经》记洞庭等山,“其神状皆鸟身而龙首”。楚辞《九歌·山鬼》中,山鬼的形象则是“乘赤豹兮从文狸”的女性。这些神祇中有一些受到楚国的特别重视,包山、葛陵等地出土的战国楚简中,就有峗山、五山等祭名。《越绝书》中亦记有几处与巫有关的山岳,如吴之虞山、越之巫山。
秦灭六国后,“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制定了一个新的山岳祭祀体系,其中“自殽以东,名山五”,即太室(嵩高)山、恒山、泰山、会稽山、湘山。这个新定的名山祭祀体系,以关中诸山为重心的色彩很突出。“自殽以东”名山五所,北方的嵩高山、恒山、泰山后来均位列五岳,但并不包括后来的南岳。
会稽山、湘山为何会受到始皇帝的重视,已难确知。不过,两山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均与圣王传说有关。湘山之神,传说是“尧女,舜之妻,而葬此”。与之相关的是始皇帝望祀过的另一座江南名山——九嶷山,传说是虞舜葬地。马王堆出土西汉初期长沙国地图中,九嶷山地区亦明确标有“帝舜”二字和可能表示祭祀的柱状图案。会稽山则是大禹葬地,“上有禹冢、禹井”。这就让人想到楚、越两国的政治影响。如王明珂所说,对华夏圣王传说的地理附会,表达的应当是华夏边缘政权的文化诉求。圣王传说的附会和认同,取决于传说中可资附会的知识资源。虞舜南征葬于苍梧之野、大禹涂山之会,为此提供了基础素材。越、楚虽然灭国,江南的舜、禹遗迹却流传下来,秦汉之际得到广泛认同。湘山、会稽山、九嶷山的重要性,应当从这一点来理解。
“名山”是一个文化符号,背后是王朝政治地理的影响。楚、越灭国之后,王朝政治重心位于北方,江南地区在政治、文化上均被边缘化,“名山”的地位也逐渐弱化。湘山、会稽山、九嶷山在两汉国家祭祀中的地位,远不能与位于长江以北的五岳相比。
江南再次出现独立政权是在六朝时期。相应地,江南山岳祭祀在以首都建康为重心的政治地理格局下,也出现了独特的文化面貌。孙皓时期的国山祭祀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这次颇受讥刺的祭祀活动,折射出江南政权的一个政治文化难题。国山祭祀并非完整的封禅活动,而是“先行禅礼”。《史记》卷28《封禅书》引管仲之说:历来“封”均在泰山,“禅”的位置则多所变更。此说为江南政权举行“禅”提供了依据,但“封”的问题无法解决。国山祭祀之后,梁武帝时又有人提议“封会稽、禅国山”,一度引起梁武帝的兴趣,但最终遭到学士反对而作罢。这个封禅难题体现出汉代政治文化传统与江南地方政权的矛盾性。秦汉时期形成的五岳,是以北方为重心的祭祀体系。孙吴、东晋到南朝,江南政权对于五岳祭祀一直兴趣不大,或许就是由于这一尴尬。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钟山之神”即蒋子文信仰,受到江南政权崇重。淝水之战前,会稽王司马道子“以威仪鼓吹求助于钟山之神,奉以相国之号”,刘宋时更加爵“位至相国、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加殊礼,钟山王”。沈约《赛蒋山庙文》有“仰惟大王,年逾二百,世兼四代”之辞。蒋子文生前不过是一位“嗜酒好色”的秣陵尉,为何会受到如此重视?《隋书》卷6《礼仪志一》说:
至(天监)十六年,有事北郊,帝复下其议。于是八座奏省四望、松江、浙江、五湖等座。其钟山、白石,既土地所在,并留如故。
这里提到保留钟山、白石的原因,是“土地所在”。蒋子文曾自称:“我当为此土地之神,以福尔下民耳,尔可宣告百姓,为我立祠,当有瑞应也。不尔,将有大咎。”白石山是建康西北的军事要地,其神白石郎,见于《神弦歌》,同样也是“土地神”性质。这些“土地所在”的小山被列入朝廷祭祀正是始于东晋。《宋书》卷16《礼志三》提到:“江南诸小山,盖江左所立,犹如汉西京关中小水,皆有祭秩也。”“江南诸小山”与汉代长安“关中小水”相比,所云正是建康政权与“土地所在”的关系。刘宋孝武帝时重修蒋山祠,“所在山川,渐皆修复”,明帝时“立九州庙于鸡笼山,大聚群神”,这些举措也可以置于“土地所在”的背景下理解。
这一点很值得注意。虽然说“山无大小,皆有神灵”,但秦汉时期,由于江南地区处于文化边缘,很少进入主流历史记述,江南山神绝大多数并不知名。这种情况随着江南政权的建立而发生了变化,“土地所在”的江南神祇越来越多地见诸文献记述,受到关注。除了蒋子文、白石郎,孙皓祭祀过的石印山“下有祠屋,巫祝言石印神有三郎”。最显著的例子是位于庐山山南的宫亭神。六朝立国江南后,由于庐山地处都城建康通往岭南的交通要道,在《异苑》《幽明录》等书中留下了多条传说,并成为佛教叙述中的感化对象。茅山白鹤庙,首见于《真诰》和《茅君内传》记述,由于茅山道教的影响,一直到唐代仍受到崇重。这些江南神祇应当早已存在,但直到六朝时期才载于文献。
“土地所在”的影响,同样也体现在神仙道教领域。在《抱朴子内篇·金丹》中,葛洪引《仙经》,详细列举“可以精思合作仙药”的山岳:
华山、泰山、霍山、恒山、嵩山、少室山、长山、太白山、终南山、女几山、地肺山、王屋山、抱犊山、安丘山、潜山、青城山、娥眉山、山、云台山、罗浮山、阳驾山、黄金山、鳖祖山、大小天台山、四望山、盖竹山、括苍山。
分析这个名单可知,首先是五岳,其次按照地域分列诸名山,太行山脉及其周边、关中、巴蜀、会稽、岭南地区均有分布。葛洪接下来指出,这些山岳,“皆是正神在其山中,其中或有地仙之人。上皆生芝草,可以避大兵大难,不但于中以合药也。若有道者登之,则此山神必助之为福,药必成”。但在葛洪心目中,“上国名山”亦即中原地区的名山,修道环境明显要优于南方名山。如他回答“江南山谷之间,多诸毒恶”问题时说:“中州高原,土气清和,上国名山,了无此辈。今吴楚之野,暑湿郁蒸,虽衡霍正岳,犹多毒也。”只是永嘉之乱后“中国名山不可得至”,修道者只能选择会稽名山和岛屿。
由于“中国名山不可得至”,江南名山获得了发展的契机。《真诰》卷14《稽神枢第四》条列有五岳名山中“一年之得道人”事迹,分别是:(1)霍山:邓伯元、王玄甫(时间不详);(2)华阴山:尹虔子、张石生、李方回(“并晋武帝时人”);(3)衡山:张礼正(汉末入山)、冶明期(魏末入山);(4)庐江潜山:郑景世、张重华(晋初受口诀入山);(5)括苍山:平仲节(“大胡乱中国时渡江”);(6)剡小白山:赵广信(魏末渡江);(7)海中狼五山:虞翁生(吴时隐此山);(8)赤水山:朱孺子(吴末入山)。上列修道者集中于汉末至西晋,所修道之山多位于“吴楚之野”的庐江和江南地区。真人之诰降示于江南地区,这种神仙地理叙述也让人想到“土地所在”的影响。

这一点更显著地体现在洞天福地体系之中。唐前期司马承祯编录的《天地宫府图》,是洞天福地最早的体系化记载。从地域分布来看,江南特别是吴越名山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如十大洞天有五所位于吴越地区(另外五所中,岭南、蜀地各有一所;两所为传说之山,地点不明;北方地区比较明确的仅有王屋山一所);三十六小洞天中江南名山有二十五所,吴越地区占十三所。洞天福地体系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东晋中期仍只有三十六洞天之说,而且只有位列前十的洞天有明确记载。《真诰》卷11《稽神枢第一》:“大地之内有地中之洞天三十六所。其第八是句曲山之洞,周回一百五十里,名曰金坛华阳之天。”东晋中期出现的《茅君传》记有三十六洞天中前十位的名称,与司马承祯《天地宫府图》所载十大洞天一致,即王屋、委羽、西城、西玄、青城、赤城、罗浮、句曲、林屋、括苍。由此来说,山中神仙洞府想象和洞天的具体化,应当是道教神仙说在江南地区的新发展。由于“土地所在”的原因,江南山岳被赋予了重要的神圣性。
无论是孙皓的国山禅礼,还是道士对江南名山的寻访,背后其实有一个共同的逻辑起点,即葛洪所说的“中国名山不可得至”,换言之,最初只是作为“上国名山”的替代。这种文化心理当然与楚、越之后江南长期成为文化边缘之地有关,同时也说明“上国”的文化正统性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意识。如何摆脱这种边地意识,将“土地所在”的江南地方性融入侨寓政权的文化认同之中,是东晋南朝时期面临的一个文化难题。国家祭祀层面上对蒋子文神的崇重,知识领域内庐山宫亭神传说的广泛传播,道教领域内以江南名山为主体的洞天体系的形成,都出现于这一背景之下。
(本文节选自魏斌著《“山中”的六朝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8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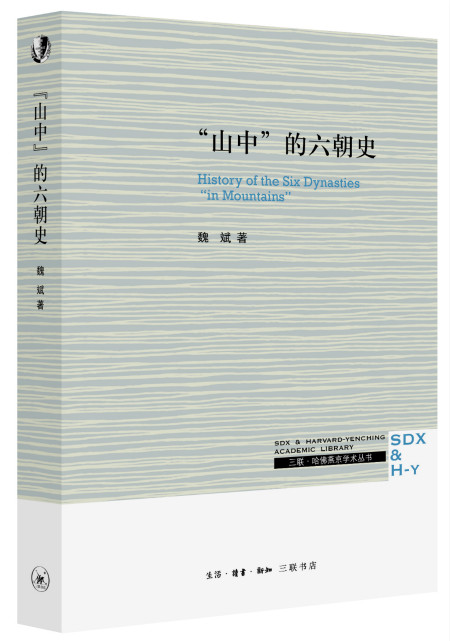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