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书城大家 | 袁筱一:雨果、《悲惨世界》和浪漫主义
思 想 | 文 化 | 艺 术

维克多·雨果(1876)
即便在中国,雨果也是一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作家。十九世纪群星璀璨,用流派的概念来说,有浪漫主义,之后又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能够数出来的经典作家除了雨果之外,浪漫派的有夏多布里昂、维尼、拉马丁,乃至后来的波德莱尔,如果说到浪漫派女作家,那就还要添上乔治·桑、斯塔尔夫人等;现实主义的有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再到自然主义的左拉。抛开流派的概念不谈,十九世纪对于法国文学来说,的确是个分水岭, 这个分水岭最为醒目的标志就是文学的世俗化。
世俗化当然不是个坏词,它就是一个事实而已。法国文学在十七世纪或者十八世纪,即我们所谓的古典主义时代和启蒙时代,是由少数精英主导的,尽管我们也会在这些精英的身上发现他们所谓“深入生活”的痕迹,例如莫里哀主动宣布放弃贵族头衔的世袭等,但是文盲的比例出乎意料地高,这是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十七、十八世纪文学的主流形式是戏剧或者诗歌,这些固然更能够被诵读,免去不识字的读者难以进入文字之苦,但作者的受众人群仍限于少数接受过教育的人。在革命发生之前,是贵族的教育或者神学院的教育,在革命发生之后,受到教育的也只是少数不那么贫穷的人。如果我们用所谓的小说人口学的统计方式,借助《悲惨世界》来看一下主要人物受教育的情况,就一目了然了。例如主人公冉·阿让,童年悲苦,是个树木修剪工,做些粗活,直到因为偷了面包去土伦服刑的时候,“无知兄弟会办了一所囚犯学校”,于是冉·阿让“四十岁入学,学习认字、写字、计算”。再例如第一部里的芳汀,她是个女工,可能能认几个字,但是在小说里谈到芳汀不幸身世以及她和其他三个女子被四个大学生骗的时候,也说过其中的一个名叫“大丽”的姑娘是四人中唯一会写字的,而且还写不周全,例如把“清早出去好快活”写成“快活出去好清早”。到了第二代的珂赛特,她受教育是因为冉·阿让带着她住在修道院里,她和修女一起受的教育。而马吕斯有个经商的外公,他爸爸是拿破仑麾下的军官,就像雨果的爸爸一样,所以他才能一直上到大学,做了律师。
文学世俗化最明显的表现是文学主流形式的改变。借助文学杂志和报纸的兴起,小说一跃成为文学中最具影响力的类型。如果说雨果的一生是典型的“斜杠青年”的一生,诗歌、戏剧、小说均有涉猎,甚至诗歌成就要高于——至少不亚于——小说,但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是,现实主义的一代人更以小说家立身。小说的兴起也是为了满足大众阅读的需要。仔细读过《悲惨世界》的人可能还会记得,小说最初写到德纳第一家,就是芳汀寄养小珂赛特的那家恶人,形容德纳第太太的时候,一方面说她“直立起来”,有着“铁塔一般的个头儿”,却又讽刺道:“她看了几部香艳小说,就有一种沉思的情态:女不女,男不男,一副忸怩作态的样子。页面破损的旧小说,对小客栈老板娘的想象力,往往会产生这种影响。”随后雨果提到小说的品位在不断下降,他还继续写道:“小说……越来越庸俗,从斯居德黎小姐降至巴特勒米·哈托夫人,从拉法耶特夫人降至布尔农-马拉姆夫人,这类小说点燃了巴黎女门房的欲火,甚至殃及郊区。德纳第太太恰好有足够的智力看这类小说,从中吸取营养,从中浸润自己那点脑子。”雨果对小说的看法我们之后再谈,但是,德纳第太太都能够阅读小说,可见得,雨果自己所说的“为了人民的文学”已经不远了。

《悲惨世界》(1862)插图中的珂赛特
世俗化的前提包含着一个有趣的矛盾,一方面,摆脱精英主义,摆脱少数人,摆脱过于限制性的陈规旧俗,这是浪漫主义得以产生的前提,它和启蒙思想联系在一起,是文学民主化的表现之一;但另一方面,浪漫主义恰恰将重点放在了个体与整个世俗化社会的抗争上。这是浪漫主义一个非常有趣的表现:呈现这个社会,是为了更好地与之抗争。后来阎连科在他的《发现小说》里称之为“浪漫现实主义”。标签或许并不重要,但今天看来,《悲惨世界》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例证。的确,雨果拒绝了出版商让他缩减其中某些章节的要求,坚信这“必将是其创作的高峰”,“虽然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细节显得有些长,但都是最后到来的结局的准备”。和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的众多作品中通过人物来呈现人世万象不同,雨果要在一部《悲惨世界》里,通过一个人对抗“悲惨社会”,并在这个过程中蜕变成完人的故事写尽人世间的一切。
在法国的二十世纪文学中,浪漫主义在某种程度上遭到了坚决的狙击。浪漫主义式的英雄人物,浪漫主义中蕴含的理想社会——无论这理想社会是在过去还是未来。残酷的现实让我们与十九世纪文学渐行渐远,什么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听起来仿佛是很古老的事情。有趣的是,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五日巴黎圣母院的一场火灾,仿佛又把一个已经远去的文学时代送到我们面前。我们突然间发现,至少是从盛大的浪漫主义文学开始,文学虽然是有国别的,也有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但它之所以是文学,就是因为它永远都是跨越边界和时间的存在。因而,我们有必要在今天从二十世纪的法国文学倒回去,重新认识一下雨果和他的作品,重新认识一下从浪漫主义开始创设的“文学国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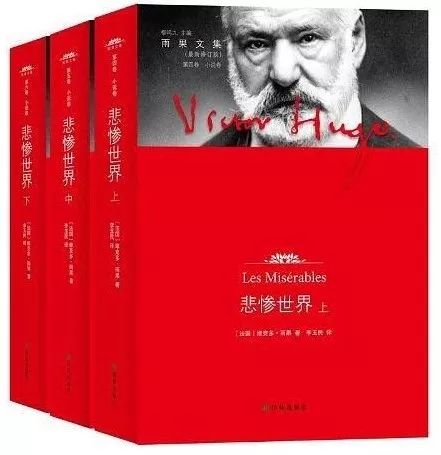
《悲惨世界》
[法]维克多·雨果著
李玉民译
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
一、雨果与雨果的时代
今天,任何一部法国文学史都不能略去维克多·雨果。一个事实足以解释这一切——雨果去世的时候,举行国葬,迎进先贤祠。
雨果出生于一八〇二年,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分别大他四岁和两岁。如果去查文学史的资料,会发现雨果出生于法国一个叫贝桑松的小城。贝桑松在法国东部,离瑞士、意大利都很近,有风景也有历史,最古老的遗迹是古罗马帝国留下的。但对于雨果来说,这些都是暂时的。因为就在他出生后不久,全家就离开了贝桑松。雨果的父亲是拿破仑手下的军人,倘若我们相信《雨果传》里的描写,他“是一个凭本能行事的人,脸红红的,举止粗鲁,和所有士兵一样,喜欢女人”。出于各种原因,雨果的父母长时间处于分离状态。雨果的童年忍受的不仅仅是父母在地理概念上的分离,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分离,在若干次努力未果之后,父母在三个儿子—尤其是两个相对来说比较小的—的抚养权上陷入了诉讼。十九岁那年,雨果失去了相对来说更加亲爱的母亲。

少年雨果(1818)
童年的痛苦是雨果天才的内心的源泉吗?也许有关系,但是当然并非全部。雨果有可能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是个特例。在十四岁时,小维克多就写下了那句著名的话:“我要么成为夏多布里昂,要么就什么都不是。”如果从弗洛伊德的角度去解释,在少年时代的天才成长中,哥哥欧仁给他带来的竞争,对母爱、对邻家女孩阿黛尔的争夺也可能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兄弟俩都喜欢写写弄弄,在一八一九年,维克多和欧仁都参加了图卢兹花神学院的诗歌竞赛,也是那一次,他完胜了他的哥哥欧仁,他的《重建亨利四世雕像》受到了评选委员会的一致赞许,得到了金百合奖。评委之一著名诗人亚历山大·苏眉不吝将颂词送给这位十七岁的天才少年,他说:“自从收到您的颂歌以来,周围的人都在谈论您的天赋以及您为我们的文学带来的神奇的希望……而您只有十七岁,这令您的欣赏者简直难以置信。您对我们来说像诗歌谜,是缪斯的秘密……”而且,据说在金百合奖最后的遴选中,雨果战胜了大他十二岁的拉马丁!
天才,从少年时代开始就已经得到的文学上的荣耀足以证明。十八岁,他再次获得图卢兹花神学院颁出的金百合奖,十九岁出版了《颂歌集》,还得到路易十八每年一千法郎的补贴,二十一岁出版了第一部小说《汉·伊斯兰特》等。但只用“天才”这两个字也过于轻飘了,因为如果没有一生的勤劳坚持,甚至没有一生的漂荡起伏,没有经历过丧女的哀恸,雨果也不可能成为今天我们人人熟知的雨果。更何况天才雨果与十九世纪法国的相遇或许也是恰逢其时。我们相信,每一个作家都是在他的时代和语言中写作,虽然他的作品的价值有可能超越他的时代和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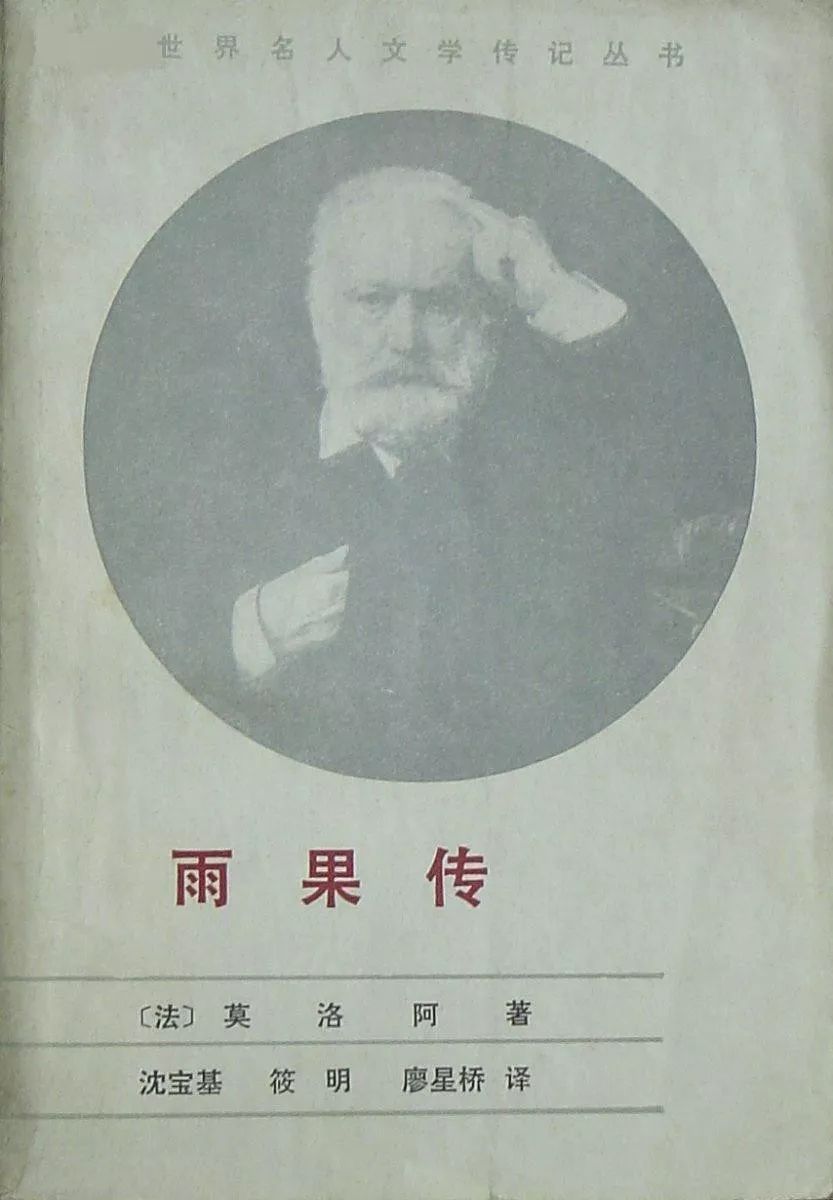
《雨果传》
[法]莫洛阿著
沈宝基等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雨果的一生几乎贯穿了整个十九世纪,而十九世纪的法国是怎样的状况呢?大革命的硝烟尚未散去,法国国内的形势尤为复杂,雨果荣耀而动荡的一生与此不无干系。所谓越荣耀越动荡,越动荡也就越荣耀。甚至在他的童年,父母之间的纷争也掺杂了复杂的政治因素。父亲是拿破仑麾下的军人,并且在拿破仑时代升至将级军官,秉持共和思想;而母亲是相对保守的保王党人,与母亲关系极为密切的雨果的教父就在拿破仑时期遭到逮捕,被执行了死刑。雨果在青少年时期与母亲更加亲近,自然也相应地倾向于更为保守的保王党。然而在复辟期间,对波旁王朝的失望又使他渐渐地站到了共和的一边。他曾经鼎力支持路易·波拿巴,但“小拿破仑”发动政变后,雨果却因为反对开始了长达十九年的流亡。从君主制,到帝国,到君主立宪,再到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试图推翻立宪制度,之后普法战争爆发,巴黎公社失败——雨果当选议员后坚决主张赦免巴黎公社的革命者,等等,大革命之后的一个世纪,法国一直处在飘摇不定中,革命伴随着暴力,共和也仍然脱离不了对专制政体的留恋。不是简单的两派——革命派与反革命派,或者共和派与保王党——的斗争,而是无法定义,时刻在变化着的各种主张之间的冲突、对峙和撕扯。
雨果在很多小说中都写到过一七九三年,《悲惨世界》里也有。如果我们梳理一下法国大革命的这条线,我们可以标记出几个富有重要意义的时间点。
第一个时间点当然是一七八九年,那年巴黎的民众在七月十四日攻占了巴士底狱。但这不是动荡的结束,而是动荡的开始。路易十六的统治本来就极不稳定,宣布召开三级会议后,发现没有办法从市民那里弄到钱,就宣布解散议会。于是民众在激愤之下攻占了巴士底狱,因为那里关押过启蒙理念的倡导者。
第二个时间点是一七九三年,至少在雨果的标记中是个重要年份,因为这一年处死了路易十六和他的王后。雅各宾派掌权,实行恐怖政策,革命变得空前暴力。在《世界小史》中,作者恩斯特·贡布里希这样写道:“雅各宾党人——所谓最狂野的党——要消灭的不光是贵族,还有那些和他们意见相左的人也不能幸免。他们要消灭谁,就将他的头砍下来。一种专门的机器——断头台——被发明后,砍头变得又简单又快速。他们自己成立了一个‘革命法庭’,每天都要宣判死刑,然后被宣判的人就死在了巴黎广场的断头台上。”一七九三年,雨果尚未出生,但是他对这段白色恐怖的历史却不能忘却,不仅写了专门的历史小说《九三年》,在《悲惨世界》中,他借米里哀主教之口,也写到了断头台:
断头台,竖立在那里,确实有一种威慑之力。只要还没有亲眼目睹过断头台,就可能对死刑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不置可否,决不表示赞成还是反对;然而,一旦撞见一个,那震动就十分剧烈……断头台一出现,将人的灵魂投入噩梦中,就显得狰狞可骇,并参与了它的所作所为。断头台是刽子手的同谋,它吞噬,它吃人肉,喝人血。断头台是法官和木工合造的一种魔怪,是一个幽灵,似乎以它制造的死亡而生存,过着一种令人闻风丧胆的生活。(李玉民译)
在写下《悲惨世界》的时候,雨果早已与父亲和解,立场也渐渐趋向共和。但是,早先对共和的革命所持有的畏惧,仍然浓缩在对断头台的描写中。
第三个时间点是一七九九年,拿破仑执政。对于雨果来说,父亲的命运、擢升就是在拿破仑执政时期。一八〇四年,拿破仑称帝,于是有了第一帝国时期。
一八一四年拿破仑第一次兵败退位,波旁王朝复辟。但一八一五年拿破仑在兵败滑铁卢之前,还曾经重新登陆法国,有过一番挣扎,最终再次失败。波旁王朝二次复辟。对于滑铁卢战役,《悲惨世界》的第二部第一卷就叫作“滑铁卢”,着实让雨果过了一把历史小说的瘾。当然他写滑铁卢,是为了引出德纳第和马吕斯父亲之间的关系—那是个笑话,我们留到下文再表。
再之后的时间点就是一八四八年的第二共和国。路易·波拿巴,即“小拿破仑”,先是被选为总统,当时雨果还是支持他的,但他随即发动政变,解散议会,开始独裁,雨果正是因为反对而遭到了流放,在外流亡前后两次加起来长达十九年。直到共和制确立,第三共和国成立,才彻底回到法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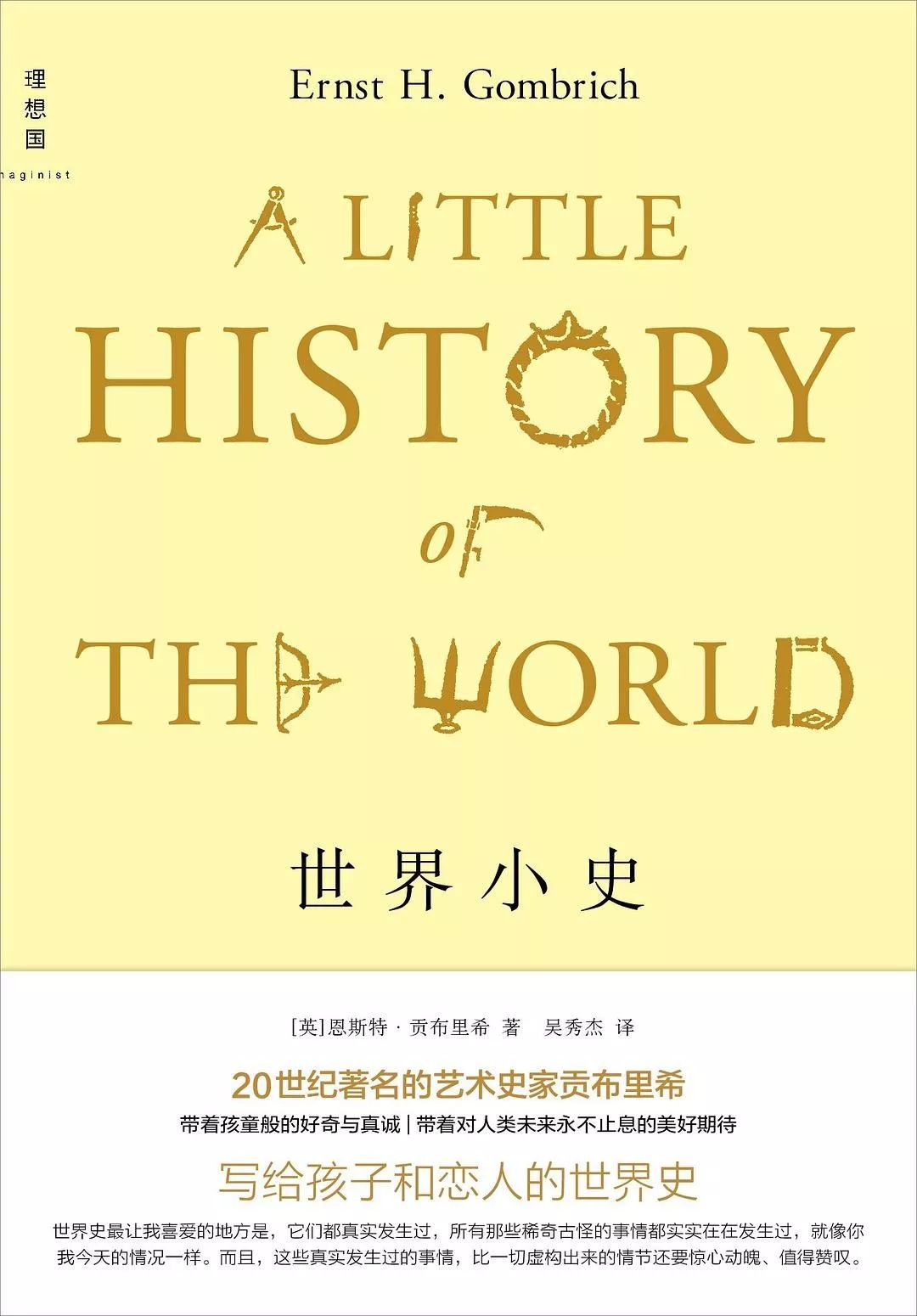
《世界小史》
[英]恩斯特·贡布里希著
吴秀杰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雨果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在不断的流放和回归中,在跌宕起伏的荣耀与低潮中,在对法国的挚爱和期待中,完成了包括《东方集》《秋叶集》《惩罚集》《沉思集》在内的二十多卷诗歌,包括《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笑面人》《海上劳工》在内的二十多卷小说,包括《欧纳尼》《克伦威尔》在内的十数卷上演或未能上演的剧本,还有不计其数的随笔。
二、从《巴黎圣母院》到《悲惨世界》:雨果的浪漫主义
《悲惨世界》,我们都知道,写于雨果六十岁的时候。那时,他已经经历了人生的大部分荣耀(文学上的声名,成为法国浪漫派的领袖,甚至虽然改朝换代,但历朝历代的政治人物都对他尊重有加,小波拿巴数度请他回去,都是雨果自己拒绝的,主动在外流放)和悲痛,例如爱女在一八五二年离世。写于六十岁的《悲惨世界》与写于二十九岁的《巴黎圣母院》自然是不一样的。

《九三年》
[法]雨果著
叶尊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
当然,二十九岁的时候,《巴黎圣母院》中已经有盛大的浪漫主义存在了。今天我们理解浪漫主义,或许更多是将它当作一种文学和艺术的流派来理解。的确,流派是一种简单、易操作的概念,带有一劳永逸的意味。以相同的观点、相同的主张,团结在某一个或者几个领袖的周围,形成文学社(cenacle)这样的小圈子。《欧纳尼》上演的时候与古典学院派展开了一场混战,这些都可以让我们承认流派的存在。但浪漫主义不仅如此。尤其到了十九世纪的法国,在纷繁的政治局势下,它脱胎于启蒙时期的“文人”这个群体迅速地从人群中分离出来,形成一股特殊的势力,从浪漫主义开始,不仅文学艺术的布局、方法发生了改变,文学艺术的使命也发生了改变。文人既不是简单的政客,也不是简单服务于——像古典主义时期的剧作家们那样——国王和王室,在精神娱乐的大前提下追求语言、文学艺术形式的完美。在《〈克伦威尔〉序》和《〈欧纳尼〉序》中,雨果的立场再清楚不过了,他说:“人民,只有广大的人民才能让作品不朽。”的确,至少是在法国,经过浪漫主义一代持续的、充满激情的努力,文学艺术不再是少数沙龙里精英的游戏,而是为了法国四千万的大众。
而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浪漫主义更是可以被晋升为一场重塑西方价值观的思想革命,而且是世界性的。是从浪漫主义开始,认知中心从外部世界转向了人。放在浪漫主义文学的身上,就是描述人的心灵,讲述人的欲望(合理的或者不合理的,美好的或者不美好的),为人争取自由的权利,物质的或者精神的。连康德都说,要倾听“人内心的声音”。我们突然发现,也许支配这个世界的,并不是客观世界的自然法则,而是人类的精神、意识,或是浪漫主义文学热衷于展现的人类的创造和情感。
雨果并非哲学家,也非社会学家。但雨果对于文学,尤其是对于“为了人民的文学”的最大贡献,其中之一是塑造了真善美的人物,创设了伟大的自我,成为开始阅读文学的大众的标杆。他笔下的人物,永远都是在一个价值观重塑的时代,在历史与社会的动荡中,在旧的价值体系崩塌的前提下,遭逢善与恶的撕扯,从而做出自己的选择。我们大约不会怀疑,每一个人物的身上,也都有雨果自己的挣扎、选择与野心。《悲惨世界》里的米里哀主教的所有思考,冉·阿让临终前的大喜大悲,又何尝没有雨果自己的身影。什么是浪漫主义人物呢?借用彼得·沃森对德国浪漫主义起源的总结来说,是“在巨大的困难面前勇敢捍卫自己信仰的殉道者和悲剧式英雄”。
在浪漫主义的人设上,善恶两元因而也是小说家经常采用的模式,善者至善,恶者至恶。米里哀主教的善与德纳第夫妇的恶依然像卡西莫多的善与弗罗洛主教的恶一样对比鲜明。但是作为一个浪漫主义巅峰时期的小说家,雨果已经不会浅薄地把他的英雄塑造成所谓的“完人”,因为这样一来,浪漫主义定义的崇高不可避免的悲剧性的一面就会大打折扣。和我们对于浪漫主义——或许这和翻译有关——的想象略有出入的是,浪漫主义并不回避人性的弱点,在浪漫主义看来,人与其自身弱点相抗争的过程恰恰是英雄行为的一部分。浪漫主义不仅要展现虚构的至善至美,同时也要挖掘心灵的幽深处所埋藏着的恶,考察这恶在怎样的环境下发芽生长。弗罗洛主教的恶不是个人意义上的虚伪,而是对人内心深处那个“黑洞”的挖掘,在那里,埋藏着情欲、仇恨、迎合社会的虚荣等一切非理性的表达。待到波德莱尔以及波德莱尔之后的一代把这一“第二自我”发展到极致,二十世纪的法国文学就彻底走上了黑暗的不归途。
与《巴黎圣母院》将叙事时间定格在十五世纪路易十一治下不同,《悲惨世界》的叙事时间是雨果真正的“当下”,他从一八一五年写起,主要的叙事时间延伸至一八三二年巴黎起义—当然叙事者还跳出了人物的时间限制,你时不时地都会看到叙事者跳出来,站在一八六一年前后发表上一段对于历史或是现实的感言。一八一五年,米里哀主教在迪涅地区任主教,而冉·阿让刑满释放,走进迪涅城。作者虽然没有太在这个时间上耽搁,但是他在第一部第三卷起始的一八一七年,不经意地写了这么一句:“一八一七年这一年,路易十八以君王的坚定口气,不无自豪地宣称他在位二十二年了。”和我们前面看过的历史时期对照起来,我们很清楚地知道,这是拿破仑退位,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而一八一五年需要等到第二部“珂赛特”的第一卷“滑铁卢”,才发现决定人物命运的这个年份是怎样的。在“滑铁卢”中,雨果先是戏谑了一番拿破仑命运不济,“如果下几滴雨”,那么滑铁卢战役的胜负可能还未可知,这当然是玩笑话,但是调笑完,他自己如此陈述历史之于他的小说的作用:
当然,我们无意在这里撰写滑铁卢战役史;我们所讲述的故事中,一个有伏线的场面与这场战役紧密相关;而这段历史并不是我们的主题;况且,这段历史已经撰写完了,洋洋洒洒,鸿篇巨制,一方面,由拿破仑本人的作为,另一方面,出自史界七贤的手笔。……在我们看来,滑铁卢的双方将领,都受到一系列偶然事件的支配;而对命运这个神秘的被告,我们也像天真的审判官——民众那样进行审判。(李玉民译)
这一小段文字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小说家的历史是受到一系列偶然事件的支配完成的,一如他自己虚构的小说本身。作者在其中所说的伏线我们应该都清楚,雨果从拿破仑的滑铁卢写到乌果蒙的果园,从“反革命无意中成为自由派,拿破仑也同样无意中成为革命者”的历史感慨写到他的人物德纳第“将近半夜,奥安凹路那边……匍匐爬行……被死尸的气味吸引过去,以盗窃为胜利,要抢劫滑铁卢”的行径。他扒拉出了一个级别相当高的军官,在抢他财物的时候无意间救了他的命,而这个军官就是小说后半部主人公之一马吕斯的父亲,在战场上被拿破仑口封为“男爵”的乔治·彭迈西。

《巴黎圣母院》
[法]雨果著
陈敬容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
倒不一定要用浪漫主义去定义,虽然浪漫主义从总体上来说与小说是相连的。至少经过三十多年,小说在《悲惨世界》里发展出了一个成熟、澎湃的模式。《悲惨世界》很好地体现了十九世纪小说的四个要素:情节、语言、人物和主题——虽然这些在二十世纪基本上都得到了消解。和《巴黎圣母院》六个月的叙事时间相比,《悲惨世界》的叙事时间显然更长,从而在情节的跳跃、伏笔的埋藏上更加得心应手。例如米里哀主教家唯一的奢侈品银质餐具与之后冉·阿让的良心苏醒;例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德纳第和马吕斯之间的关系;还有用所谓孩子去敲诈马吕斯外公的马侬姑娘实际上被德纳第的两个儿子取代,又再一次缔结了冉·阿让和所谓坏穷人德纳第一家之间的关系等。
伏笔这个东西当然不是浪漫派小说的首创,倒是更接近于小说起源时的传奇,当然也和小说兴起的时候连载相关。而到了浪漫主义的时代,在小说崛起为主流的文学形式之后,小说在叙事上的日趋精致化当然就成了浪漫派小说的任务之一。虚构如何来源于生活,同时又要在道德力量上高于生活,就成了浪漫主义小说前行的目标。
三、小说真正的主人公:正义?
《悲惨世界》是从一八一五年的米里哀主教写起。只是米里哀主教并非只扮演圣人的角色,矗立在冉·阿让的人生路口,让他得以顿悟。事实上,在第一部第一卷的“正义者”中,雨果借米里哀主教之口,讨论了正义的问题。社会的动荡被浓缩在了对米里哀主教非常简短的介绍中。米里哀主教的青春是在“交际场和情场中”度过的,“爆发革命,事态急遽变化,法袍贵族家庭遭到摧残、驱逐和追捕,都四处逃散了。革命刚一爆发,查理·米里哀先生便流亡到意大利。他妻子长期患肺病,死在异国他乡,没有留下一儿半女。此后,米里哀先生命运又如何呢?法国旧社会崩溃了,他的家庭也破败了,一七九三年发生一系列的悲惨事件,在远方的流亡者看来,也许倍加恐怖和可怕,凡此种种,是否使他万念俱灰,萌生了出事的念头呢?一个人在天下动乱中,罹难重重,家道衰败,还可能处变不惊,然而在无忧无虑的温馨生活中,突然遭到神秘而可怕的打击,往往就会心死而一蹶不振吧?谁也说不清楚,只知道从意大利回国,就已经当上了教士”。雨果当然志不在此,更不想以政治或者历史的角度评论大革命,他只是想要告诉读者,历史的正义性和与人的正义性无关。第一卷的大部分时间里,雨果都在陈述正义在这位主教的身上是如何体现的:例如“劫富”济贫;让渡出自己宽敞的主教府,供医院使用;拿出自己的所有财产和俸禄,用在教区的穷人身上。在雨果的笔下,这是一位“又严肃又慈祥”,擅长打比喻,“话虽不多,但是非常形象化”,持有“耶稣基督的雄辩”能力,“自信不疑又能服人”的人,“绝不义正词严地唱高调,也不像嫉恶如仇的正人君子那样横眉立目,而是朗声宣传一种教义”,这种教义的主旨大概是“人有肉体,这对于人来说,既是负担又是诱惑。人拖着肉体,又屈从于肉体。人必须监视、约束、抑制肉体,不到万不得已,决不屈从。……成为圣贤,那是极其特殊的;做个正义者,倒是为人的准则。你们尽可徘徊,怯懦,尽可犯错误,但是要做正义者。尽量少犯错误,这也是为人的准绳。不出一点差错,这是天使的梦想。生在尘世,就难免有错。过错就是一种地心引力”。于是,这样一种富有“地心引力”的教义改变了《悲惨世界》主人公冉·阿让的命运,使得他从一个苦役犯走上了正义者的道路。

卡佩拉尼电影作品《悲惨世界》海报
正义者,这可能是已近暮年的雨果对自己的要求,而社会则看上去是站在正义者的反面的——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是谁统治的社会。和米里哀主教一样,雨果总是满怀同情地看着“忍受人类社会重压的妇女和穷人”,认为“女人、孩子、仆役、弱者、穷人和愚昧的人有过失,那就是丈夫、父亲、主人、强者、夫人和学者的过错”,而看到了断头台行刑之后,雨果也借助米里哀主教之口抨击了社会的法律:“专心致力于上天的法则,而不再理睬人间的法律,这是错误的。生死予夺的大权只属于上帝,人有什么权利染指这件陌生的事物?”《悲惨世界》里的这一开局,倒还真的和《巴黎圣母院》一下子就区分开来。《巴黎圣母院》里是穷得高尚自由与为富不仁的腹黑的对峙,是个人与这社会的对抗,是自我挣脱社会一切规定的绝唱,是在现有的秩序之外对更合理、更公平、更美好的无条件的追求。而《悲惨世界》里,则是倾听、理解、包容、共情和蜕变,这一切都可以被包容在“正义”这个模糊的词汇里。米里哀主教曾经去看望一个名为G的国民公会代表,雨果这样描绘他:“一个国民公会代表,好家伙,您想象得出吗?那是以‘你’和‘公民’相称呼的年代里存在过的。那人简直就是个怪物。虽说他没有投票赞成处死国王,但也相去不远了。他近乎是个弑君者,曾是无比残暴的人。”主教在G临死之时去探望他,开始也和普通的民众一般,是带着谴责去的,但是G说,他投票结束暴君的统治,却没有投票赞同处决暴君,他投票结束封建王朝是奔着“结束女人卖淫,男人为奴,结束儿童的黑夜”去的。这让主教陷入了思考:自己把年薪几乎全部用在穷苦百姓的身上,将相对豪华的住所改建成医院,生活中竭尽简朴,但是一己之力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女人卖淫、男人为奴、儿童的黑夜统统没有结束。善与恶仍然是相对的。G主张的国民公会没能迎来一个人人为善的时代,主教的信仰也是一样。
写作《悲惨世界》的雨果已经是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了。母亲和教父对于他的影响已经在现实中渐渐淡去。因为维护共和,他与小拿破仑决裂,最终遭到流放,并且在能够回到祖国的时候,仍然选择继续流放。《悲惨世界》出版的时候,共和制已经在法国得到了确立,此后再也没有回头。然而,共和是否能够解决一切,显然此时的雨果并没有给出让人欢欣鼓舞的答案。和面对G时的主教一样,雨果相信,如果说,制度的改变是基础,但从制度的改变到梦想中的公平和人道社会的实现,道路还很漫长。于是,我们可以理解《悲惨世界》里,竟然出现了既不能用“善”,亦不能用“恶”来定义的沙威。在小说的最后,马吕斯终于明白,沙威并非死于冉·阿让之手,沙威背后的法律也远不是正义的代名词。而真正的正义来自个体在面对另外的个体时所做出的牺牲与包容。
浪漫主义小说最为坚持的主题或许就是这样的:进步(革命是为了进步)、正义、普天下的爱以及与启蒙接轨的对蒙昧的憎恶、对科学的诚挚信仰。说一千道一万,还是可以回到《悲惨世界》的“作者序”中的那句话:“只要本世纪的三大问题:男人因穷困而道德败坏,女人因饥饿而生活堕落,儿童因黑暗而身体羸弱,还不能全部解决;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愚昧和穷困,那么,这一类书籍就不是虚设无用的。”
本文系作者在上海明珠美术馆“维克多·雨果:天才的内心”展览特设“雨果上海七日行”主题系列讲座上的演讲,刊发时经作者修订

原刊于《书城》2019年12月号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6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