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迟子建:当你与世界的痛苦感同身受
当一个作家和世界的痛能够感同身受的时候,可能就会真正触及文学的一些本质的东西了。——迟子建
当你与世界的痛苦感同身受
口述|迟子建
采访、整理|孙若茜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写了30多年了。如果一定要在我的写作里找一道分水岭,那就是2002年,尽管我多么不愿提及。我爱人因车祸离世对我的迎头痛击,毁掉了我的俗世幸福,却对我的文学成长,起到了一种催生作用。
2003年和2004年,对于我的写作是非常重要的两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额尔古纳河右岸》,还有短篇《一匹马两个人》等,都写于这个时期。长篇、中篇、短篇都有,从作品的数量上来讲是够大的,从质量来讲,不管我未来是否会写出更加令自己满意的作品,我必须承认这些作品的气质,在我个人的创作史中,是不会被自己忽视和遗忘的。这些作品里,有一个人和世界的关系,有一个人对待死亡的态度,有一个作家应该懂得的生命的重量该是什么。
我的出生地,包括我现在常回去的地方,至今仍然是中国的边疆,经济欠发达,但自然无比壮阔。命运让我出生在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四季如此分明,能够感受漫长冬天的地方,使我从小就会有一种特别感伤的东西。
生命作为生命体单纯存在的时候,总会渴望美好的、恬静的事物。可是在那里,我感受到的却恰恰相反,很早就看到永别,有大自然中生命的永别,也有人的永别。小时候我去山上拉烧柴,采野果采蘑菇,在跟大自然的生机相逢的时候,看到的死亡也比比皆是。花落了,草枯了,蝴蝶死了,再寻常不过。有时还会看到鸟儿残缺的翅膀,它可能被天敌吃掉了,但它的羽毛还在林地,跟着秋叶在风中瑟瑟发抖。有时猎人在森林里设圈套,结果自己都忘了,被捕猎的动物就死在了套里,被老鹰等食腐动物吃掉,剩下干枯的头颅和肮脏腐烂的皮毛。我至今都能想起那样的画面,那种无言的苍凉。在诗情画意的地方,你也随时有可能和死亡相逢。也许你正站在一片野花丛中,但看到聚堆的绿豆蝇发出强烈的嗡嗡声,便明白它们身下可能就是一只死狍子或者死兔子。
慢慢地,你会用渐长的生命了解到,大自然的永别,那冬天时看上去完全死寂的大地,第二年还会有生机。可是人呢?为什么去了另一世界就不再苏醒了呢?你从少年时代,就会朦朦胧胧追问人的去处。而我耳闻的神话故事,似乎告诉了我们人死后所去的地方,但这又难以说服人,那么人之死是什么?是生命的终结还是诞生?从最初的作品到现在,我始终在探讨。它不是哲学意义上对死的解析,也不是宗教对灵魂归属的指向,不是对死亡的一种温情的消解,而是一个作家在童年就开始感知死亡,发现死亡与炊烟一样生生不息后,从生中望见死,也从死里看到生。
我过去住的小镇大概100户人家,那时多子多女,三代同堂的也多,差不多就有近千人,几乎每一户人家彼此都认识。死亡的事件经常发生,一年四季,你会眼见这个人家支起灵棚哭丧了,那个人家的棺材又被老人用上了。一些突然暴病离世的人,会仓促打棺材,小镇回荡着木匠打棺材的声音,而没成年的孩子夭折,连棺材都不会有,就在山上找个地方埋掉了。
我看到的这些死亡及后来父亲在盛年去世,都让人格外悲痛。可是直到2002年,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人突然离去,才让我觉得死亡一直潜在地跟随,在用各种方式提醒着我它的存在,让我不得不真正地去思考和面对,人是什么,死亡是怎么到来的,人在一生当中究竟该做什么,甚至于写作,哪些东西是你真正应该写的,哪些东西本来是轻的被你写重了,哪些东西本该是重的被你无意化解了。那个瞬间,一个世界在我的文学天地里重新洗牌了。
我爱人是那一年5月去世的,5月底料理完丧事,我从大兴安岭回到哈尔滨,眼里是没有春天的。当一个人陷在悲伤、孤独、绝望中的时候,过的就是冬天。我那时候不出门,甚至连书也不想看。我觉得特别委屈,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循规蹈矩的女人,一个如此热爱生活又喜欢家庭的人,还没给爱人做够饭呢,还没听够他对我做的饭的赞美呢,上帝为什么这样对待我?
直到6月份,黑龙江发生了一起很大的矿难,死了100多人,我开始关注这个事件。当我看到电视画面中遇难者家属那种无泪的绝望的眼神,真是痛心。那种眼神很难描绘,像冬天苍茫的天空,聚集了很沉很沉的浓云,却没有一道闪电,能让浓云得到释放沉闷。
遇难的那100多人都是男人,会有多少人一夜之间变成寡妇?她们面临着矿难赔偿的官司,一轮一轮的谈判,得有多揪心?之后要面对多少生计的问题?老人孩子怎么办?未来的生活怎么办?我那时正在写《越过云层的晴朗》,一个知识分子至少还可以用一支笔寄托哀思,而她们呢?我突然觉得我的痛苦和这些人相比要轻得多。
我很自然地开始向自己发问。为什么一定要夸大自己的痛苦?为什么觉得命运对自己不公?在死亡面前没有一个人有豁免权,为什么他不可能是你的挚爱亲人?为什么当死亡降临到别人身上的时候,不会问询不公?一个人,尤其一个作家,不要觉得自己是上帝的宠儿,生来就是吃蛋糕的。不,作家不是,作家可能生来就要去学会承受自身以及社会的种种苦难,并把它跟你的笔联系在一起,去探讨生之意义,以及如何摆脱、净化对死亡的恐惧感。我觉得,当一个作家和世界的痛能够感同身受的时候,可能就会真正触及文学的一些本质的东西了。
2002年之前,我去过那样的煤矿,那时候叫深入生活采访。记忆当中有一座煤矿,所在地的城市里都不能穿白衬衫,他们打的伞永远都是黑伞。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充满了丧葬气息的地方,很自然地就把它拉入《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里,而小说中的煤矿叫乌塘。那时候,超过10人的矿难,如果上报,无论是矿主还是各级领导都会受到相应的处分。于是,就有了种种隐藏矿难的罪恶,包括隐匿尸体。所以我当时虚构了一笔,一个人把矿难尸体藏在冰柜里。过去我也写死亡,但可能写得不是那么水乳交融,而这时候的死亡变得跟我休戚相关,写时能与心灵共振。
除了《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额尔古纳河右岸》之外,我的其他一些作品也探讨了死亡,它们中有的是以一种更文学的方式在介入死亡。比如《群山之巅》,写的是一个经历过战争,没有当过逃兵却被人说成是逃兵的人。他遭人唾弃地活着,成为一个小镇的笑料,直到生命最后结束,火化他时发现骨灰中残留的弹片,他仿佛复活了。而他活着的时候,与死是一样的,没人在意他的存在,他以生的面目死着。
再比如我的新作《候鸟的勇敢》,里面也涉及死亡。这种死亡回到了我们刚刚谈到的,在山林的美好当中经常看到的那种动物的死亡。一对东方白鹳,其中一只因为被树枝上人为的超强力粘鸟胶粘住,腿折掉了。它被救助后没能及时地在该迁徙的时段飞走,另一只白鹳对它放心不下,回来搭救,两只鸟在共同迁徙的途中,最终遭遇暴风雪双双陨灭。它们的死亡暴露的是整个社会的腐烂和人心不古。
从一个人的痛看到众生的痛以后,你的世界、文学的天窗一下子就开得很大很大,那些在生命的过往里,被忽略过的很多东西,它们的色彩、厚度、质地一下子就不一样了。我开始很自然地愿意触摸这些痛,也有意识地往文学更深处开掘。当然,前提是我坚持了一些东西。
改革开放这40年,文学的思潮实在太多了。20世纪80年代,我在鲁迅文学院学习的时候,就有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等,我所在的作家班当时有很多现在大名鼎鼎的人物,像莫言、余华、刘震云,还有那时很有名的徐星、洪峰,每个人的写作都不一样。那时候也有一波波的阅读热潮,比如一个时期大家都去读米兰·昆德拉,另一个时期都在读纳博科夫,再一个时期都读马尔克斯,接下来劳伦斯的东西又风靡了。这些我也都会去看,有些东西喜欢,但真正影响我的不是思潮当中的这些作家。
1990年我回到黑龙江以后,脱离了喧闹的环境,所有的声音都好像静止了。我开始选择重读一些经典作家,像托尔斯泰、雨果。近些年,一些小语种作家的作品,像捷克作家博胡米尔·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南斯拉夫作家伊沃·安德里奇的《德里纳河的桥》、匈牙利作家马洛伊·山多尔的《一个市民的自白》等让我获得了更多营养,这些作家的作品不仅独特,而且和他们的民族历史血脉相连。
我的写作不属于任何思潮,不属于任何主义。山川河流、普罗大众、神仙鬼怪、炊烟云朵,都在我的文学版图里,它们是我文学边疆的徽标,孤独孤绝,难以入流。任何思潮的宠儿,在获得侧目和关注的同时,也难免沾染泡沫。所以判断今天的文学哪些是金子,应该是半个世纪后的事情。我觉得一个作家如果做了思潮的俘虏,写作的船就会触礁。而我的这条船在我文学版图的山河间划行了30年,还没有被潮头淹没,也没有因小磕小碰而伤筋动骨,依然能够在一颗越来越沧桑的心的驱动下,不惧寒流和黑夜地航行,这是最让我庆幸的。
——本文选自《光荣与道路:中国大时代的精英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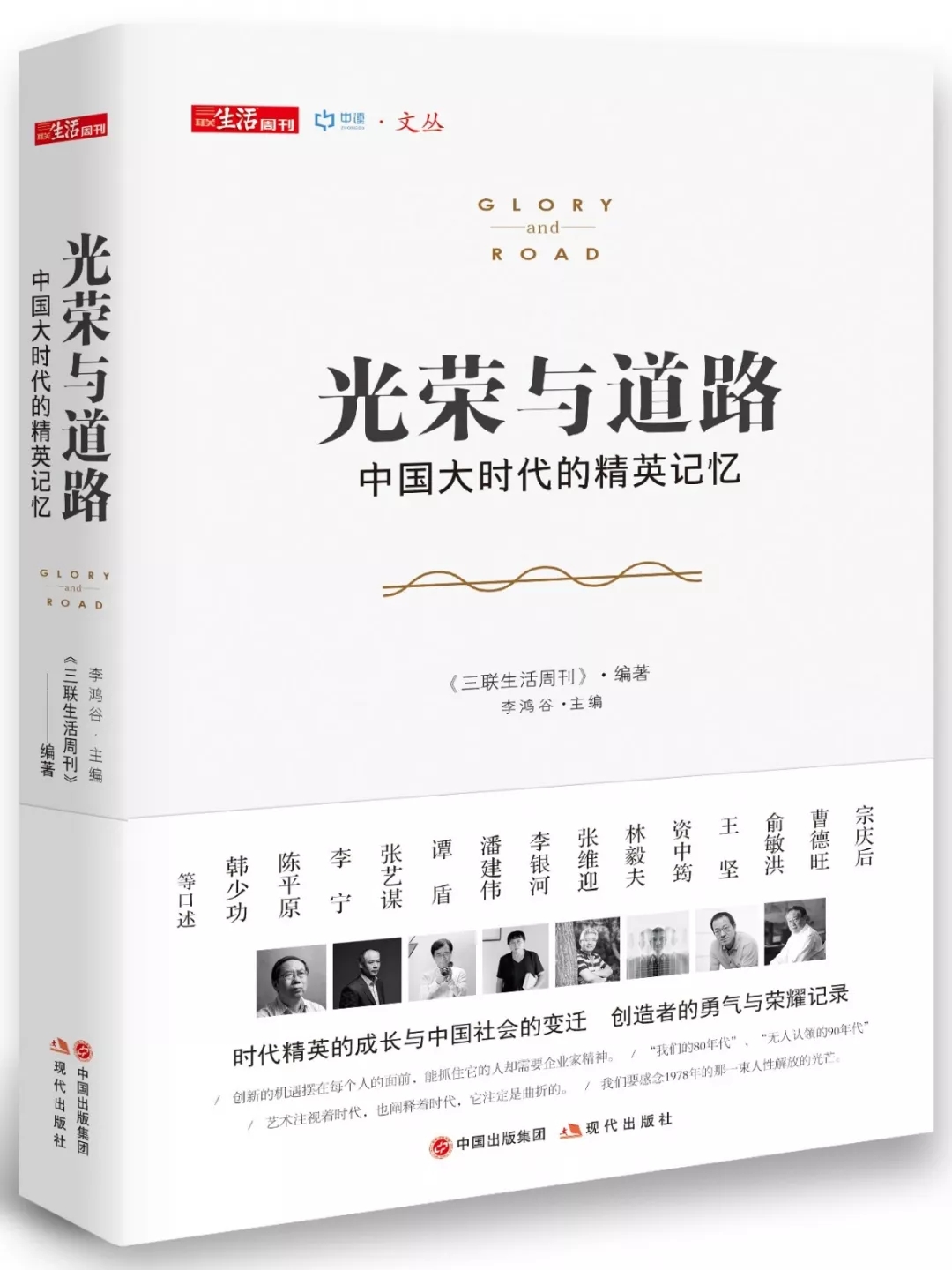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