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帝国野心与神秘主义的交织:寻找恒河之源
1772年,当第一任印度总督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抵达加尔各答时,印度正值多事之秋。议会委员会指责英属东印度公司“滥用职权,恶行昭著,玷污了民治政府之名”。一切都直指这家著名公司的诸位官员有疯狂掠夺、中饱私囊之嫌。而印度,犹如敞开的店铺,架上货物只等被洗劫一空。“比起秘鲁的西班牙人,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政治家、作家贺拉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说,“无论贪欲多么罪恶,至少他们还是那种有宗教原则的屠夫。”
黑斯廷斯到任后,一切重新开始。要统治一个国家,难道没有责任去了解它吗?他努力学习印地语和乌尔都语。那时不只是一个帝国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启蒙时代,虽然有时两者之间很难划清界限。很快,像黑斯廷斯这样的人名声大噪,因为他们愿意弄清英制下所有东西的规格、重量和价值。他们搜集情报,以便能从征服的土地中攫取财富,他们更需要了解潜在对手的力量、地理方位和性格。但同时,他们也是严肃的宗教学者、梵文文学的推动者、历史学家、地质学家、语言学家、考古学家、古文物研究者。1784年,东方学者的代表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创立了孟加拉亚洲学会。为此,他写道:“亚洲学会预期的研究对象是人和自然——无论人们如何行事,无论自然赋予什么——以印度为中心,亚洲地理范围内的人和自然。”

在黑斯廷斯治下的所有学科中,最重要的是制图学。如果想要了解治下的国家,那么第一要务就是绘制它的版图,而印度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是未知领域,特别是北方无法逾越的冰岩巨垒。探索它的最重要意义正在于它关乎恒河之源。作为创世神话的发祥地之一,东方学者对此并不陌生,但在18世纪绘制的地图上,有关恒河上游的渲染可能也不过是标上“龙地”而已。制图者所知的细节仅仅是来自旅行家之口的一些故事和奇闻轶事,而非来自科学研究或者一线观察——托勒密(Ptolemy)时代以来,1500年间这种情况一直存在。
托勒密曾参考早期希腊和罗马作家的记载绘制过一份地图,图中东南流向的恒河从喜马拉雅山脉一直流入大海。他区分了河东区和河西区,恒河流域内的印度和恒河流域外的印度。人们一致认为,无论是多瑙河还是尼罗河,都不宜采用这种划分方法。老普林尼(Pling the Elder)转述道,恒河“发于山泉,喷涌而出,其声滔滔”。在恒河的下游还有一个大湖。此外,他写道,这条大河宽从未小于8英里,深也从不小于20 噚。3世纪时的诗人狄奥尼修斯(Dionysius)大概是对这条河流的物质属性和精神意义加以评论的第一人,他说:“神圣的土地因恒河不舍昼夜的奔流而光荣,恒河则是这片大地的奇妙景观。”
7世纪的玄奘是众多中国朝圣者之一。当时,他们历经磨难,前往印度佛教圣地,求取经书和圣物。名录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鹿野苑(Sarnath), 距瓦拉纳西6至7英里,佛陀曾在那里第一次讲经说法,而两种伟大的宗教——佛教和印度教也是在那里分道扬镳,沿着不同的路径各自演进,一个宁静沉思,另一个喧嚣争鸣,充盈着神话和史诗故事。在克什米尔度过两年后,玄奘来到了恒河。“它的河水碧蓝,就像海洋一样,它波澜壮阔,同样像海洋一样,无边无际。”他写道。他还记载了河岸上进行的葬礼仪式,将这一场景描述为:“这是宗教的功德之河,它涤荡了无数的罪恶。那些厌倦生命的人,如果能够在河水中结束自己的生命,那么就会飞升天堂,获得无上幸福。”
从11世纪开始,随着莫卧儿入侵者横扫中亚,将北印度纳入自己的刀剑之下,数以千计的寺庙被夷为平地,穆斯林旅行家也纷至沓来。阿尔-比鲁尼(Al-Biruni)综合了印度经文中有关“天堂之河”的叙述,伊本·白图泰则记述了来自恒河的圣水如何从陆地历经40天被运到德里的苏丹面前。后来,给安拉阿巴德命名的穆斯林君主阿克巴(Akbar)特命仆人用精美的铜罐将河水从圣城哈瑞多瓦一直送到他位于阿格拉的宫廷。后来,他的长孙沙·贾汗(Shah Jahan)在那儿建造了泰姬陵。
17世纪阿克巴当政。有关他高度重视“永生之河”的记载源于约同期赴印度的第一位欧洲作家。而英国人尼古拉斯·威辛顿(Nicholas Withington),很可能是将科学的好奇心放进当时大量反复论述恒河宗教性文献的第一人。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恒河的水“即便储存很久也不会变质,不会有害虫滋生”。“考虑到河中不断被投入的尸体的数量”,法国人让-巴蒂斯特·塔韦尼耶(Jean-Baptiste Tavernier)对此深表怀疑。1896年,阿格拉的主任医师E. 汉伯里·汉金(E.Hanbury Hankin)博士对这一现象充满疑惑,当时,位于巴黎的巴斯德(Pasteur)研究所公布了他的调查结果。汉金记述了他在瓦拉纳西是如何收集被霍乱病毒感染的尸体被扔进河里的案例的,最终发现接触过水的微生物在几个小时内会死亡。
东方学者们绘制地图的第一次伟大尝试是由孟加拉总测量师詹姆斯·伦内尔(James Rennell)少校完成的。他所绘制的《孟加拉地图集和印度地图》(A Bengal Atlas and Map of Hindostan )于1781年出版,对哈瑞多瓦以南的恒河做出了精确的描述。但对于北方的山区,他和所有其他人一样一无所知。他所能做的就是参阅经文,神话和传闻。巴吉拉蒂国王站过千年的岩石在哪里?当女神从天堂射中湿婆的长发辫时,湿婆立身何处?地图的这部分读来让人一头雾水。

又比如,传统观念坚持认为恒河确定是从湿婆位于喜马拉雅的驻地——凯拉什山(也称冈仁波齐山)或者它的周边而来。矗立于西藏西部的冈仁波齐像是一块高达2.2万英尺的巨大的金字塔形黑石板。藏传佛教徒也将这座山神化。在与第一批来到这个神秘国度的欧洲传教士的对话中,他们就曾着重讲述了这个传说。喇嘛们说,也许这条河并不是发源于这座大山,而是源自冈仁波齐附近的“觉悟之湖”玛旁雍错(Mansarovar),或者相邻的更小的拉昂错(Rakshastal)。伦内尔采用了玛旁雍错一说,但同时补充了一个有趣的细节描写:
此时,这一巨大的水体从喜马拉雅群山的山脊间冲出一条河道,它侵蚀着群山的基础,穿过一处洞穴后,在山脚岩石上被水穿凿出的巨盆上沉淀。这样,在漫不经心的观察者们面前,恒河就好像发源于山中泉水:人们把洞口想象成牛头的形状,而牛是印度人敬奉的动物,印度人对牛的崇拜的程度就像古埃及敬奉公牛神阿比斯(Apis)一般。
对于一代英国探险家来说,洞穴和牛头这个细节就像寻宝过程中的第一条线索,让他们欲罢不能。
1808年,军事测绘师、才华横溢的水彩画家罗伯特·科尔布鲁克(Robert Colebrooke)计划了他首次正式的探险,希望能找到恒河之源。然而,在他的团队即将出发时,他不幸染病离世。但威廉·韦伯(William Webb)上尉和运气不佳的威廉·雷珀(William Raper)上尉继承了他的遗志。他们穿过哈瑞多瓦,又横穿旷野,到达了已成废墟的小镇乌塔卡西(Uttarkashi),五年前这里遭受过大地震的破坏。在那里,他们记下了当地的民风民俗和农耕方法。他们运用三角测量法计算山脉的高度,并向河流上游奋力行进了20英里或更长的路。设备繁多,非常累人。如果丢弃帐篷会怎样呢?完全行不通,因为春天的天气变化多端。行程每一天都变得更加缓慢,更为艰苦也更加危险。最后,他们经一个名叫萨朗(Salang)的小村穿过河流,行至距离甘戈特里还有五六天路程的地方,决定放弃这次远征。
但是,他们说服了在当地找来的向导继续独自前进。他们给了这位向导一个指南针并教他如何使用。在他的帮助下,最终成功绘制出了地图,这幅地图追踪了恒河另外30英里左右的流程,避免了半途而废:甘戈特里这个词在一些模糊的等高线上徘徊,指示着“喜马拉雅山脉或雪山山脉”,在紧邻北部的某个地方,称摩诃提婆·卡·林迦(Mahádéva ca linga),与冈仁波齐山形成参照。
在加尔各答亚洲研究学会发表的报告中,韦伯和雷珀质疑了伦内尔有关那个形状奇特的洞穴的说法。韦伯写道:“是的,恒河通过了一条秘密河道或与牛嘴相似的洞穴。每个描述都认可恒河源头是……事实并非如此,尽管与之相关。”雷珀也认为:“关于牛嘴,我们现在有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能够证实其存在完全是神话传说,即其只能在印度教的宗教文献中找得到。”
终于在1815年第一个欧洲人到达了甘戈特里,他就是勇敢的苏格兰画家和旅行作家詹姆斯·贝利·弗雷泽(James Baillie Fraser),也是苏格兰雷利格(Reelig)第十五代男爵。他沿途创作了一系列绘画和尘蚀铜版画,让那些身在加尔各答和伦敦的画派首次兴趣盎然地欣赏到了来自巴吉拉蒂河上游景观的灵感,尤其是画家以其最浪漫的方式巧妙地提升了蕴含其中的美感:群峰总是比它们实际的面貌更陡峭更锐利,峡谷变得更幽深更黑暗,激流更奔放更喧嚣,多姿多彩的原住民看起来就像从《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Ali Baba and the Forty Thieves )中走出来的一样。弗雷泽也听过牛嘴的故事。“对这个寓言的起源虽然有过调查,”他写道,“但甘戈特里神庙里的一个祭司曾经郑重其事地向我们保证过那纯属无稽之谈。”毫无疑问,就像雷珀找过很多证人一样,为了摆脱外国人,拒绝他们亵渎神灵,祭司有各种理由这么说。
到了1817年,有两件事情发生了变化。经过两年的战争,不屈的廓尔喀人(Gurkhas)获得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英国人接管了山区,拥有直接统治权。随之而来的是结束了只有当地王公才能无偿征用脚夫的神授垄断地位。游客和探险家充分利用了这一变化,如果廓尔喀脚夫提出异议,公认的惩罚之一就是把马桶扣到他头上。
1817年5月31日,约翰·霍奇森(John Hodgson)和詹姆斯·赫伯特(James Herbert)终于支持了牛嘴一说并非寓言。他们到甘戈特里后,又不辞辛苦向冰川西端行走了5天,在那里,他们发现,巴吉拉蒂河从低矮的拱洞中涌出,周围有令人生畏的雪峰环绕。霍奇森拿出了他的测链测算,溪流宽27英尺,深达18 英寸。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恒河源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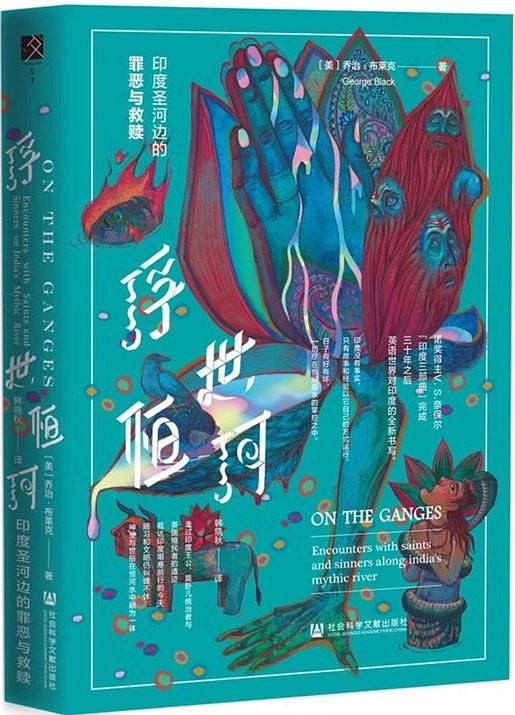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