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348年黑死病期间,薄伽丘的花园故事
罗伯特•哈里森 三联书店三联书情
微信ID:sanlianshutong
『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薄伽丘绝非一位道德说教家。他并不特别关注人性的本恶或人类获得救赎的前景。如果说他在前言里为《十日谈》确立的道德目标终究是极为平常的,那是因为人之为人本来就是件平平常常的事。那场瘟疫也证实了这一点。做人意味着无法免遭不幸与灾难,意味着时而感到自己需要援助、慰藉、消遣或启迪。这种援助有着许多平平常常的形式,尤其是借助风趣的谈吐、得体的举止、故事的魅力,通过谦恭礼让、对话交流、同伴之情和社交生活促使人类交往的领域更加愉快。给生活增添快乐而不是增加痛苦,这就是薄伽丘人文主义的首要原则。
那群年轻人从一个瘟疫横行、道德沦丧的佛罗伦萨一时逃脱,并没有对所谓“现实”产生任何直接影响。在临界地带的园林佳境里度过两周后,故事的十位讲述者又回到了一度置于身后的惨象之中。然而与此同时,《十日谈》里的故事,如同为讲故事提供环境的花园,毕竟还是干预了现实,哪怕此举仅仅在于见证形式的幻化之力。一个个故事用各种叙事形态重塑了现实,让原本被现实那无形无度的流程所遮掩的事物得以有形有致地显现于世,宛如花园将目光引至园中景物之间的审美联系。这是花园与故事兼有的幻术:它们幻化了现实,尽管看上去未曾给后者带来丝毫改观。
*文章节选自《花园:谈人之为人》([美]罗伯特•波格•哈里森 著 三联书店2020-1)。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

John William Waterhouse
薄伽丘的花园故事(节选)
文 | [美]罗伯特•哈里森
人类文化起源于故事,人类文化的历史从不间断地讲述着故事。我们能否想象人间没有故事?没有讲故事的艺术?没有故事来组织事件,给时间设立结构?假如你问我家在何方,昨晚的聚会上发生了什么,我的朋友为何心烦意乱,要回答你的问题,我多半得给你讲个小故事。不论形式正规与否,讲故事是人际交往的最基本的方式之一。生活被编入故事,故事又编织成了生活,所以说交谈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叙事艺术的掌握。不让这门艺术日复一日地作用于我们的人际关系,实为一桩憾事。
说得不错,你答道,可是讲故事同花园有什么关系呢?这个问题我们该去问西方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故事作家——《十日谈》的作者乔瓦尼·薄伽丘。除了《十日谈》,他还著有大量品质毫不次要的所谓次要作品。
薄伽丘的《十日谈》(1350年)以极为雅致的、非教条的方式体现了真正的近代式伊壁鸠鲁主义。据该书引言所述,在1348年的黑死病高峰期间,七位女郎和三个小伙子决定离开备遭瘟疫蹂躏的佛罗伦萨,退隐到周围山间的别墅里;在那儿,他们打算以交谈、漫步、跳舞、讲故事、取乐等方式度过两星期,同时恪守行为规范,不让女士们的尊严受损。与瘟疫肆虐的佛罗伦萨的惨象形成最大反差的,莫过于等待他们的田园诗般的乡间园林(《十日谈》里的故事大都是由这十位年轻人在一处处园林中讲述的)。在城里,市政秩序已沦为混乱无序,邻里之爱已转为邻里之惧(邻人如今代表传染的威胁),亲情的天然法则已让位于人人为己的准则(许多人撇下患病的亲人逃之夭夭,让后者孤立无援地面对临终的苦痛),原先谦恭礼让、温文尔雅的地方如今罪恶猖獗、神志癫狂。

这群青年男女表示,他们的目标是把怡人的田园景致带给他们的快乐(piacere)增至最大限度。我们已经注意到,伊壁鸠鲁式的享乐主义远非解除自律或满足欲望,而是一种需经培养方能形成的生活方式;有如一个花园,它的繁荣离不开秩序和规矩。“第一日”的“女王”潘比妮娅的话证实了这一点,出行后头一天,她对同伴们这么说:“让我们尽量欢乐吧——因为我们从苦难中逃出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呀。不过凡百样事要是缺了明确的形式,就不会长久。”(薄伽丘,《十日谈》,第25页)接着,她把秩序和快乐这两个概念联系了起来:她希望“大伙儿愿意在一起多久,就会过多久秩序井然、快快乐乐、没有耻辱的生活”。
在潘比妮娅的倡议下,这群青年人给他们愉快的活动设立了一个井井有条的结构。每天都有一位成员充当当日的“国王”或“女王”,负责作出用餐、午休、散步、唱歌、过安息日等方面的安排。最重要的是,国王或女王需指定当天故事的主题。根据计划,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乡居期间,大家总共讲一百个故事。由于逗留时间恰为两周,每周各有两天因为过安息日的缘故不讲故事,所以讲故事的天数共计十天(《十日谈》由此得名)。就这样,大家给这两星期的生活注入了一个“明确的形式”,这一秩序不仅确保了他们乡居期间的快乐,而且为《十日谈》一书的艺术构造奠定了基础。
欲使快乐之感社会化,关键在于给它注入形式;欲使快乐之感持续稳定,关键在于让它社会化。这一社会化过程驯化了无拘无束、自我中心的个人冲动,但并不要求人们压制或舍弃自己的欲念(《十日谈》里的故事大都与禁欲原则格格不入);正相反,它意味着让快乐在社群秩序之中得到全面实现。在薄伽丘笔下,快乐无条件地带有社会性,也毫不因此变得不“自然”。自然与社会并非势不两立,正相反,两者是人的幸福事业中富于创意的盟友。一旦快乐既成全了自然本性的愿望,又满足了社会性要求,人的幸福事业便如意大利式园林一般昌盛。《十日谈》里的花园之所以是十位青年人共享愉悦生活的理想场所,原因之一就在此。那一座座花园以优雅的方式将自然与形式融为一体,成了远不止一种意义上的“快乐之园”。让我们来探究一下此种融合。

Franz Xavier Winterhalter
从薄伽丘的描写可以看出,《十日谈》里的花园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园林艺术仿佛共有某种审美特征,哪怕这仅仅意味着两者同享某一渊源,或有传承关系。后者在16、17世纪的意大利中南部兴盛起来,过去几百年中,不少优秀学者已对这门园林艺术作了深入精彩的探讨。我不至于认为自己另有发现,而只想说在薄伽丘笔下的花园中,那些学者一定会认出自己研究的园林的某些典型特征,也就是这么一种造园风格:在这里,艺术既不支配自然(像凡尔赛宫园林那样),也不刻意突出自然(一如盛行于18世纪英国的自然风景园),而是与大自然携手共创一个既高度形式化又完全“自然”的富于人情味的空间——换言之,艺术以非正式的方式展示大自然的款款风物。
在此我想援引一位洞见精辟的评论家——伊迪丝·华顿,她撰写的《意大利别墅与别墅园林》(Italian Villas and Their Gardens)一书至今仍是这一领域的一部经典。在题为《意大利园林幻术》的序言中,华顿写道:“一天”,一位文艺复兴时代的园林设计师从他的别墅露台放眼望去,发现“环抱四周的风景被自然而然地包含在了他的花园里,两者构成了同一款构图的一部分”。如果说这一发现是杰出的意大利园林艺术的“第一步”,如华顿所言,那么“设计师的第二步是设法将自然与艺术在他的图景中融为一体”。她接着评论道:
无论其他因素如何有助于引发迷人的总体印象,如果把这些因素逐个消除,在脑海中一一隐去那丛花卉、那片阳光、岁月赋予的那组丰富色调,便会发现在这一切背后潜藏着更深的和谐构思,独立于任何偶然效果而存在。这并不意味着一座意大利式园林的设计方案同园林本身一样优美。构成园林的各种相对恒久的材料——如石工石艺,常青树木,湍泻的水流或静止的水面,尤其是自然风景的线条——都是艺术构思的一部分。但是这些风物在每一季节均以同样优雅的面貌出现;不过,即便这些也只是基本方案的配饰。园林本身固有的美在于不同部分间的组合方式——在于那些相会一处的悠长栎树小道的线条,在于阳光普照的场地与林间清幽的树荫之间的交替,在于露台和草坪的相对面积,或是一堵墙的高度同一条小径的宽度之间的比例。在文艺复兴时代的园林设计师看来,这些细节一处也不容忽视:他仔细考虑如何分配阳光与暗影,如何协调石砌建筑的直线外形与树木起伏有致的曲线轮廓,正如他反复斟酌自己的整体构图与周边景致应持有何种关系。(华顿,Italian Villas and Their Gardens,第8页)
如果细细品读薄伽丘在“第三日”的引言中对一座花园的描写(见附录一),我们会发现他的文字朝着两个相反的方向展开。一方面,作者在场景中安置了如此之多的动植物,致使花园被赋予了一种超乎写实尺度的伊甸园特性。而另一方面,这段描写称颂了被华顿视为“意大利园林幻术”之精髓的那种“不同部分间的组合方式”与“和谐构思”,两者的并列使花园的伊甸园特性成了假象。薄伽丘的文字强调花园巧妙的人为设计,这表明这座花园是人的作品,它的各种魅力源于人的匠心,它所处的环境始终受制于自然规律,无法免于衰老、灾难和死亡。同样在这里——尤其是在这里——瘟疫越过将花园像庙宇般隔离于世的墙垣,投下了它那长长的阴影。

Salvatore Postiglione
尽管这一花园囿于墙内,在《十日谈》的读者眼中,它仍不失为书中呈现的精心照料下的乡间景致之精华。薄伽丘笔下的别墅、凉廊、花园、草地、湖泊和树林组成了一种始终受制于人为设计构思的园林总汇(托斯卡纳的风景至今依然大体如此)。我们若是不信一座花园的围墙总是可以穿透的,不妨一88读“第三日”的第一篇故事(见附录一)。这篇故事把粗朴的马塞多像十足的自然力那般送入了一所女修道院的高墙之内,在此,这位装聋作哑的园丁将乐融融地去满足九位修女的情色之欲。不论被围在其中的是人还是花园,围墙无法排斥自然,至多只能让自然归顺于人的调理。
马塞多无疑是一种自然力,不过我们可不能(像修女们那样)被他摆出的那副粗陋的笨汉姿态给哄骗了。他的性欲多半是绝对“自然”、直截了当的,但他的行为和策略却颇具匠心。其实,可以说他在诸多方面都对应于故事讲述者所处的那座花园的设计师。也就是说,他深谋远虑,制订方略,按部就班地付诸实施,而整套计划则服务于自然本性。如此行事的马塞多也像预先播种、日后采摘劳动果实的园丁。
尽管马塞多的出现给修道院的精神生活与情色生活带来了不小的改观,他的闯入却并未导致无规无矩的混乱局面。正相反,在故事末了,修道院中的“力比多”能量得到了适度调控与合理分配,于是,这些能量既发挥作用,又不影响修道院原有的机构秩序。这篇故事最终颂扬了主人公们在给快乐注入“明确的形式”一事上表现出的足智多谋。从这个角度看,修道院的女院长与马塞多一样堪称英雄(依照薄伽丘眼里的英雄主义标准),那项皆大欢喜的协议,正是马塞多与女院长共同达成的。
如果说在基督教象征体系中,女修道院是修女与基督举行神秘婚典的地方,那么马塞多的到来使得修道院花园重新尘世化,它回归了大地,向自然的欲求再度敞开。在此我们免不了注意到薄伽丘特有的精妙文思:“第三日”——《十日谈》中最为“色情”的一日——开篇便影射但丁的《炼狱篇》(“太阳才从东方升起来,把鲜红的朝霞映照成一片金黄”[《十日谈》,第227页]),而《炼狱篇》的高潮就发生在伊甸园中。薄伽丘对《炼狱篇》的影射无疑是隐伏的,它贯穿了整个“第三日”,起先便有马塞多的故事在数字“九”上做的文章。在但丁眼里,“九”是最神圣的数字(三重“三位一体”位于一体)。我说薄伽丘将修道院花园再度尘世化,并不是在简单地宣称他以《玫瑰传奇》那种性爱寓言的方式把花园变成了声色的乐园,而是说他将修道院的情欲生活置于人的督管之下。繁盛的花园给修道院那获得解放却又循规蹈矩的性爱生活提供了贴切的写照:在人的督管下,大自然的繁衍力得以兴旺(修女们生下了不少“小修女和小修士”),尽管这一切都是在精心指导和控制下发生的。

Salvatore Postiglione
故事的讲述者所在的花园归功于人为设计,从这个意义上说,那处花园不啻为讲故事提供了场景。事实上,在《十日谈》里,花园与故事艺术之间存在一种更深更广的相似性,因为从总体上看,薄伽丘的叙事艺术和文艺复兴园林艺术依据了颇为相近的审美原则。我所指的不仅是《十日谈》那精致的整体建构,比如它的叙述框架,一系列彼此呼应的主题,多种多样的语声,以及不同视角之间持久的互动。我所指的还有故事与花园之间的类似。一篇故事毕竟有如一座花园:它形态独特,节奏明确,曲径通幽,远景连绵,奥妙重重,惊奇迭起,阴影朦胧,变幻无常,且与假想的边界以外那“真实世界”相通相及。在薄伽丘看来,尤为重要的是,故事倘若编得好又讲得好,它会令人愉悦。
不妨以马塞多的故事为例。一种毫不张扬的匠心贯穿着它的直白风格,譬如,故事情节发展得有条不紊,诙谐的文风毫无避讳却从不流于粗俗,基督教象征主义频频闪现,典雅爱情(特别是严禁引诱修女的戒律)得到幽默的讽刺,圣奥古斯丁关于人类言语起源的学说受到戏仿(他认为言语源自未满足的欲望,而马塞多因满足过头才开口说话),婚姻与园艺的双关语屡屡回响。一旦注意到上述特色,我们便会发现这一切把文学工事和自然主义融为一体,正如意大利式园林——依照华顿和许多其他学者的观点——融合了大自然与人为构思。甚至应当说,薄伽丘那常被人言过其实的“自然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宣称自然本性统驭人类行为与动机的学说,不如说是一种独到的叙事风格。薄伽丘著称的、也理当以之著称的那种精致却不做作的风格——一种既明畅又复杂、既大胆又细腻、既通俗又博雅的风格——是把叙事艺术高度形式化的结果,而这一形式化的目的却在于让艺术归化于自然。

Paul Falconer Poole
……
薄伽丘绝非一位道德说教家。他不是改革者,也无意充当先知。他并不特别关注人性的本恶或人类获得救赎的前景。他从未以布道者的姿态训斥读者,向他们灌输自己的道德、政治或宗教信念。如果说他在前言里为《十日谈》确立的道德目标终究是极为平常的(作者希望借助他的故事为有需要的人消愁解闷),那是因为人之为人本来就是件平平常常的事。那场瘟疫也证实了这一点。做人意味着无法免遭不幸与灾难,意味着时而感到自己需要援助、慰藉、消遣或启迪。我们的状况多半是平凡的,不是非凡的;依照薄伽丘的人文主义观点,我们对他人负有的最低限度的道义责任,不在于为他指点救赎之道,而在于帮助他走完一天的路。这种援助有着许多平平常常的形式,尤其是借助风趣的谈吐、得体的举止、故事的魅力,通过谦恭礼让、对话交流、同伴之情和社交生活促使人类交往的领域更加愉快。给生活增添快乐而不是增加痛苦,这就是薄伽丘人文主义的首要原则。它不是后世流行的那种“人定胜天”的人文主义(后者将自力更生的人类视为万物之荣耀),而是以关爱他人为核心的民众人文主(civil humanism)。(《十日谈》的前言以“人”字开头,并非偶然:“人之常情,是对不幸的人寄予同情。”[Umana cosa èaver compassione degli afflitti.])
值得重申的是,那群年轻人从一个瘟疫横行、道德沦丧的佛罗伦萨一时逃脱,并没有对所谓“现实”产生任何直接影响。在临界地带的园林佳境里度过两周后,故事的十位讲述者又回到了一度置于身后的惨象之中。然而与此同时,《十日谈》里的故事,如同为讲故事提供环境的花园,毕竟还是干预了现实,哪怕此举仅仅在于见证形式的幻化之力。一个个故事用各种叙事形态重塑了现实,让原本被现实那无形无度的流程所遮掩的事物得以有形有致地显现于世,宛如花园将目光引至园中景物之间的审美联系(见第五章)。这是花园与故事兼有的幻术:它们幻化了现实,尽管看上去未曾给后者带来丝毫改观。
如果说薄伽丘的故事艺术和他的人文主义伦理观都与意大利园林设计美学相对应,那么,应当说他的“政治立场”也同样与这一美学密切相关。虽然《十日谈》一再颂扬给事物注入形式这一举(不论此举针对自我、言行,还是人际关系),但是该书也毫不留情地痛斥了那些欲对自然或下属实施专制的暴君。在唐克雷迪(“第四日”第一篇故事)和瓜尔蒂耶里(“第十日”第十篇故事)这两个人物中,我们目睹了暴政之欲的两个最生动的化身。如果说理想的花园是自然在艺术的督管下欣欣向荣的地方,那么暴君则是欲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自然,从而征服和统治自然的人。从政治角度看,薄伽丘对专制政权的厌弃表现为他对佛罗伦萨的共和传统毕生的忠诚,这些传统让自由与市政秩序并存。出于同样的原因,那些由急于扼杀公民自由的区区暴君统治的意大利城邦令他深恶痛绝。他的友人彼特拉克力图取悦于某些傲慢的君王,屡屡寄居他们的宫中,而薄伽丘则一贯拒绝权贵的捧场,始终忠实于共和式自由的理想。此种意义上的忠诚在《十日谈》里处处可见,但它从不张扬,从不炫耀。应当说,《十日谈》的字里行间带给读者的愉悦中,它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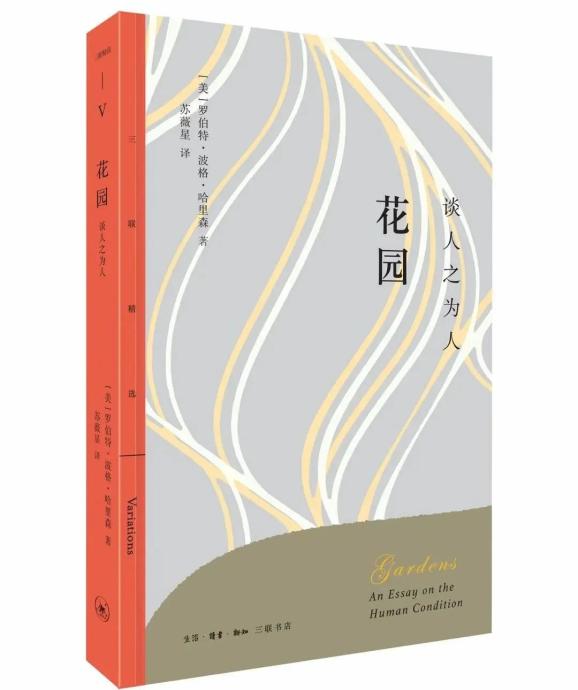
[美]罗伯特•波格•哈里森 著 苏薇星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1
ISBN:9787108066305 定价:45.00元

[美]罗伯特·波格·哈里森著 梁永安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1
ISBN:9787108060426 定价:36.00元
━━━━━
原标题:《1348年黑死病期间,薄伽丘的花园故事》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6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