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何欢欢︱“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至恶与至善
作者按:“纵使至恶,最终也必须为至善腾出空间”是现任荷兰莱顿大学佛学教授司空竺(Jonathan A. Silk)著《印度佛教中的善与恶:现报之五逆罪》一文的结语。这篇论文原题“Good and Evil in Indian Buddhism: The Five Sins of Immediate Retribution”,刊载于顶尖学术期刊《印度哲学》(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vol. 35-3,2007)。2019年初,浙江大学哲学系大二在读的上官嘉琪同学译出此文,后在浙江大学佛教资源与研究中心Lunch Talk发表了汉译兼评述的口头报告。
“一切无常,纵使至恶,最终也必须为至善腾出空间。”这句话是司空竺教授撰长文《印度佛教中的善与恶:现报之五逆罪》的结束语,原英文是:“Nothing lasts forever, and even the worst evil will, inevitably, make room for the very highest good, in the end.”这一听起来充满西方哲学式思辨味道的英语,换用通俗的中国话来说,就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从“屠”到“佛”是一个生动而深刻的过程,浓缩着现代学术界常说的“佛教中国化”或者“佛教汉化”的历史。转“屠”成“佛”则是最不可思议的弹指一刹那,蕴含着跳出轮回、顿悟正觉的甚深微妙法门。
首先想到的,也许只是一个有趣的巧合。佛教初传汉地时,梵语“Buddha”最早被记音为“浮屠”,但人们很快意识到,“屠”的宰杀意思有悖于“不杀生”的基本理念。“人如其名”可能会带来不协调甚至讽刺的心理反应与社会意识,于是“浮屠”被新造的音译词“佛陀”取代,而前者现只见于《后汉纪·孝明皇帝纪》和《后汉书·楚王英传》等古书(季羡林先生著有《浮屠与佛》《再谈“浮屠”与“佛”》两篇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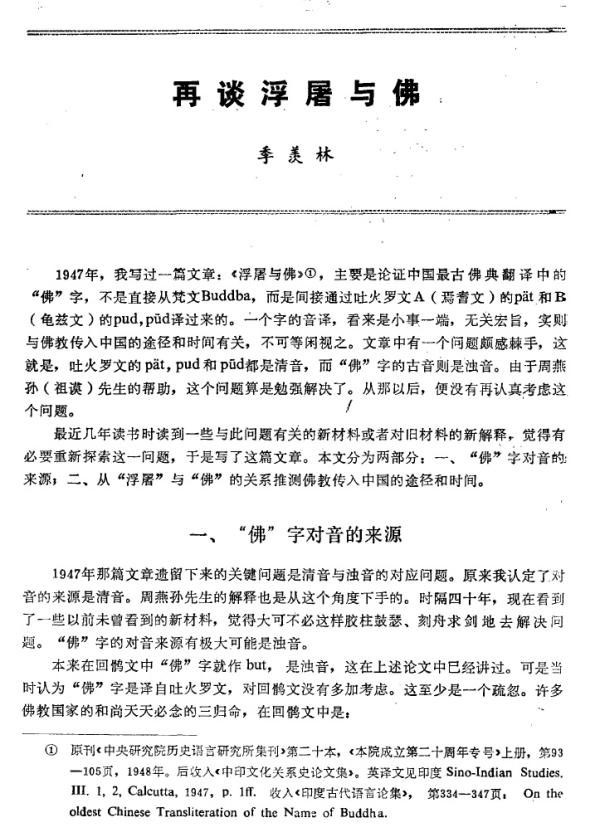
印度佛教中最著名的屠夫是“央掘魔罗”(意译“指鬘”)。央掘魔罗出生于古印度的武士阶级(刹帝利种姓),幼年到婆罗门处学习,被师母勾引不成诬以凌辱之罪。老师知道自己不是身强力壮的学生的对手就设计借刀杀人,故意教授邪门歪道的升天秘法,即杀死一千人并把他们的手指骨串成项链(“指鬘”一名的来源),死后就可以上升到梵天。当央掘魔罗正准备挥刀杀第一千个人——自己的生母时,得到释迦牟尼的教化,幡然醒悟,“放下屠刀”出家为僧,最终转凡成圣,证得阿罗汉果。这个故事共有七个版本(细节略有不同),不仅被传颂于《杂阿含》《增一阿含》等早期佛教经典(竺法护译《佛说鸯掘摩经》和法炬译《佛说鸯崛髻经》是阿含本的异译);同样的叙事素材还被大乘如来藏系经典《央掘魔罗经》(求那跋陀罗译,四卷)用来阐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等思想。

中国佛教中最幸运的屠夫应该是遇到净土宗二祖善导大师(613-681)的那位西安人。宋代僧人志磐在《佛祖统纪·净土立教志》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善导大师劝教长安城的老百姓念佛吃素,有一位京姓屠夫眼看着肉铺没了生意就持刀闯入寺院要杀和尚,善导大师开示他西方净土和念佛往生的法门,屠夫“即回心发愿,上高树念佛,堕树而终”,这时,围观群众都看到阿弥陀佛亲自前来接引,屠夫的神识从其顶门出来随着阿弥陀佛往西方极乐世界去了。顺便说一下,“净土”这一宗派名称的确立始于志磐的这一名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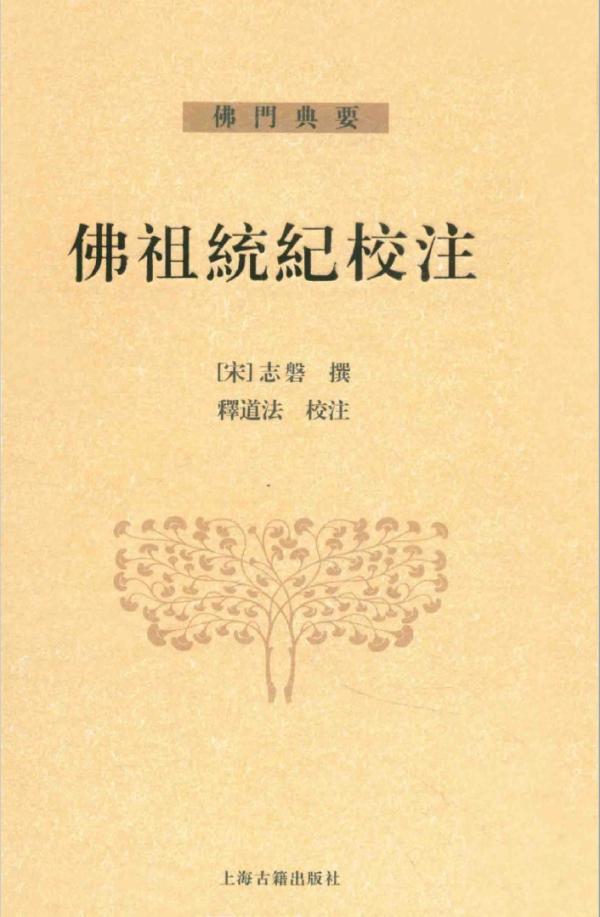
把两个故事放在一起读,不难发现很多有趣的异同点,这些往往正是佛教“中国化”的细节所在,反映了这一过程中符合汉人需求或愿景的理想佛教模型。比如,被邪师蛊惑成为杀人狂的央掘魔罗受到佛陀教导后,“放下屠刀”成为佛弟子,再经过出家修行,最终证得声闻乘的最高果位;京姓卖肉商人受到善导大师劝化后,“放下屠刀”上树念佛,(很快)堕树而亡,在众目睽睽之下,其神识由阿弥陀佛化现接引,顿获解脱。也就是说,婆罗门教的杀人屠夫在闻法当下先成了佛教修行僧,经过长时间精进才最终超出三界、涅槃解脱;中国的宰猪屠夫则当众应验了净土信仰的神迹,实现了“屠”与“佛”的“立地”(立刻)转换,完美诠释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字面意思。
当然,在大多数语境中,“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都被当做譬喻来用,即“屠刀”被广义解释为包括屠杀在内的一切言行之恶乃至痛苦烦恼,而不仅仅是真实的杀生刀刃;“立地成佛”则指立即皈依佛门,开始走上行善成佛之路,尽管距离最终获证佛果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即使该词最可能的直接源语“广额正是个杀人不眨眼底汉,飏下屠刀,立地成佛”(《五灯会元》),也多被理解为喻指禅宗顿悟成佛之迅速,而不会就字面来演说神通垂迹。所以,虽然有央掘魔罗这一印度典出的实例为借鉴,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却是一句以中国佛教为背景、以汉地撰述文献为佐释的俗谚或歇后语,亦常用在非佛教的语境中,劝人改过自新、弃恶从善,而与真正的“成佛”理论无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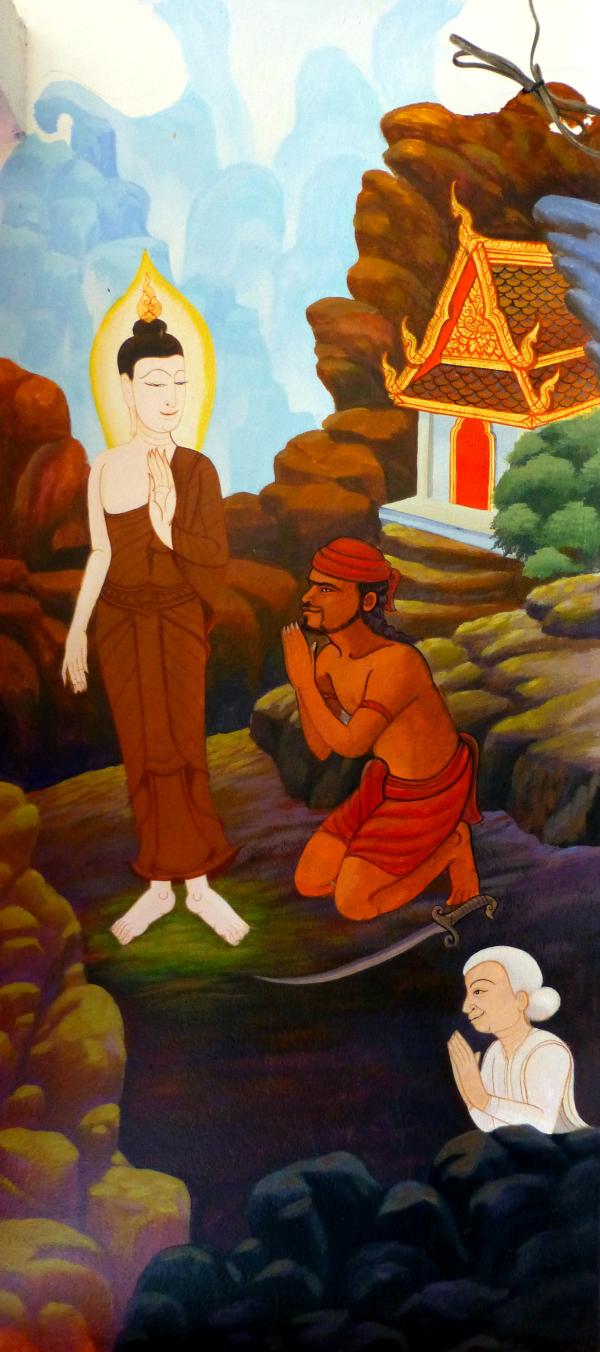
再回到《印度佛教中的善与恶》这篇颇具启发性的学术论文。实际上,司空竺的思路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毫不相干,其文如副标题“现报之五逆罪”所示,讨论的是“五逆罪”为主的善恶因果业报等印度佛教的伦理问题。
司空竺发现小乘佛教主要流派在列举“五逆罪”时有着不同的排列顺序,按从轻到重,上座部系统的《增支部》列“杀母、杀父、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僧”,说一切有部的《俱舍论》则调换了“杀母”与“杀父”的顺序。早期佛典里有很多关于这两项罪之轻重排序的争议,有的体现了女人在古印度的特殊社会地位,有的侧重于平等考察父母的道德品行。以《虚空藏菩萨经》为例,大乘佛教则把“五逆罪”归为统治者的五大根本重罪之一,这被认为是教内伦理的扩展和普遍化,也是佛教僧团在世俗社会捍卫自治的表现。司空竺细致比较了多种类型的佛典所描述的不同罪行范畴与现报形式,指出虽然犯“五逆罪”者死后都将即刻堕入地狱,但最终都能获得救赎,因为“报应非恒有”,罪行会随其业果的显现而消失,唯一可能的例外只有拒信佛教、诽谤正法的“一阐提”(梵语“icchantika”的音译,原意为“正有欲求之人”,即断绝一切善根者)。关于“一阐提”能否成佛,虽有不同意见,但很多印度佛教经典明确表示“一阐提”永住轮回、不得解脱;而犯下极严重的“五逆罪”者尽管必遭地狱恶报,但不会永世无法超生,《法句经》等讲述的大目犍连(“目连救母”的主角原型)与强盗的故事恰恰说明了佛教不会拒绝救赎弑母杀父之人。

从梵巴汉藏多语资料的整理与耙梳来看,这篇文章相当丰富精彩。然而,司空竺似乎停留在了描述印度佛教中几种代表性“五逆罪”的阶段,虽然得出了结论“即使犯五逆罪也能且终将得到救赎,表明了佛教伦理压倒性的积极本质”,却并未说明这一不完全符合普世道德价值,甚至存在内部矛盾的佛教伦理如何自圆其说并广为信奉。换句话说,司空竺简单地以“罪行会随其业果的显现而消失”这一因果报应理论为解释,实际上没有回答甚至没有考虑,为什么“杀母”等五项“至恶”(the worst evil)最终必须为成佛这一“至善”(the very highest good)腾出空间这个在我看来至关重要的问题。虽然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慈悲的佛陀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冥冥众生,但这看似理所当然的信条并非明智的学理注脚。所以,从这一层次讲,司空竺的论文没有触及佛教的哲学内核,对“印度佛教中的善与恶”的理解也就遗憾地止步于“语文学”框架下的描摹与叙述。

众所周知,佛教是弃恶扬善的宗教与哲学;少为人知的是,早期佛教没有对善恶概念的明确定义而只有具体的举例说明。日本学者藤田宏达在《原始佛教的善恶问题》(《原始仏教における善悪の問題》,《印度学仏教学研究》,1974年)一文中指出,“十善”与“十不善”(十恶)基本都是从行为实践的角度制定的善恶标准,而且都是世俗的立场,即具有在家的性格,与《摩奴法典》《摩诃婆罗多》等古印度传统经典所说的善恶标准类似;部派佛教萌发对善恶的定义与分类,由此发展而来的“八正道”与“八邪道”等既符合世间的道德轨范,也具有出世间的立场和追求。也就是说,早期佛教确立的“十善”“十恶”等教义源于或同质于当时印度一般社会的伦理准则,普遍遵循“善因乐果恶因苦果”的报应规律,只不过佛教内部对这一传统的善恶体系进行了重新编排整理。司空竺一文讨论的“五逆罪”实际上就是从“十恶”提炼出来的五种极端化的罪行,可称为“世间罪”或称“世俗恶”。
同时,从初期奥义书到数论、胜论等成熟的婆罗门教各支派,古印度的智者还设计了另一套善恶标准,即以“解脱”为唯一的至善,也就是超越了世间的“出世善”或称“胜义善”(世俗与胜义合称“二谛”)。几乎所有宗教都宣称自己的祖师发现了宇宙的根本真理,如“梵”“神我”“句义”等等,并且只有学会了本派的法门才能获得解脱——“升天”或“至福”。佛教也主张“智慧解脱”,即依靠“般若”体证释迦牟尼所悟之“缘起”而趣入涅槃。同时,佛教还强调在世间行善去恶可以获得天人果报(相当于婆罗门教的解脱状态),但仍处于轮回之中;“成佛”则是要在终极意义上(胜义谛)消除包括善恶在内的一切对立和分别,放下对轮回果报的追求与执着,从“不二”体悟空性,证得涅槃。如《坛经》说:“善恶虽殊,本性无二,无二之性,名为实性。于实性中,不染善恶,此名圆满报身佛。”

因此,从终极解脱的角度讲,“成佛”这一胜义谛的至善与世俗谛的善恶无关。如犯“五逆罪”者以所受地狱之苦抵消所犯恶行后,并不能“立地成佛”,而是要继续流转于轮回。甚至可以说,善恶不仅不能导向“成佛”,反而使人不断沉沦于“六道”,因为善恶实际上只是业感运动的一种表现,业(业力)才是宇宙唯一的存在、牵引轮回的动力。有情众生是业的相续,只要有一息业力尚存,就可感召新的果报,环环相扣、无尽轮转。这也是为什么道生(355-434)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反对世人乐于信仰的、带有浓厚宿命论色彩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倡导“善不受报”的原因。“善不受报”不是说行善没有好报,而是说行善不一定有好报。同时还可以加一句“恶不受报”,即作恶也不一定有坏报。这个“不一定”包含了佛教最根本的“缘起”思想——一切事物都由因缘和合而生起,即“空性”,故常合称“缘起性空”。所以,作为“因”的善恶行为与作为“果”的好坏报应并不构成必然的对称关系。佛教既反对胜论派的“因中无果”论,也批判数论派的“因中有果”说,主张的是“缘起因果”,即龙树菩萨在《中论·观因果品》中反复阐释的道理。

如此说来,佛陀自己追求无善恶分别为特征之一的涅槃,但劝世人行善岂不是成了“伪善”?当然不是,包括佛教在内的古印度宗教都认为,“世俗善”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众生对世间的贪著,清净梵行有利于走向究竟解脱,所以是正确的行为。涅槃要跳出轮回,就必须超越善恶等的一切“分别”,但超越不是泯灭好坏,而是要认识到“缘起性空”或说“一切皆空”。《心经》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是要教人放下对善恶果报、烦恼分别的执着,以此减少轮回中的牵引业力。极端地讲,从“行善”到“涅槃”的飞跃不会比从“屠夫”到“成佛”的转变来得容易,因为“行善”和“屠夫”都是世间此岸之物,与彼岸的涅槃成佛之间横亘着几乎难以逾越的苦海。从此岸到彼岸的摆渡人只有佛陀,不管是菩萨的大船还是声闻的小舟,只有修持正法之人才能顺利渡脱生死。

最后提一下,强调善恶报应之对称性的其实是中国本土的思想,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易传》),“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尚书》)。印度佛教自始至终都更加注重作为“因”的善恶,也就是常说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佛教定义的前半句;行为之后莫管结果回报、无所执着,即“自净其意”,才真正“是诸佛教”。除涅槃以外的果报再好也只是轮回中的短暂喜乐。后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上加了一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以更好地适应“好人没好报、坏人无恶报”的残酷现实,则显然是受了印度佛教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等思想的影响,如《大般涅槃经》说:“深思行业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三世因果,循环不失,此生空过,后悔无追。”
由此看来,司空竺用因果业报来理解印度佛教的善恶,就根本理念来说有悖于“缘起”思想。虽说“一切无常”最终也可通向“缘起”,但其论文中一次也没有出现“缘起”或“空”等词,不得不说司空竺在考虑印度佛教的善恶问题时遗漏了释迦牟尼最重要的说法。“一切无常”只是世人轮回的无奈,“缘起性空”才是菩提树下的证悟。
简言之,善恶旨归于“缘起”,表征于“二谛”,从“屠”到“佛”不是什么宇宙之谜,而是“空性”的必然呈现。《金刚经》道:“所言善法者,如来说非善法,是名善法。”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6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