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义海情天:费城第六街区黑人小伙们的在逃人生
爱丽丝·戈夫曼的《在逃——一个美国城市中的逃亡生活》总是令我想到自己十多年前完成的豫北盗区田野调查的当地语言,她的“盗区”在费城的第六街区,它又代指帮(gang)。她用“街上的”(street)和“干净的人”(decent)来区别有犯罪记录在逃的黑小子们和过着正常生活不和警察、看守所的司法系统打交道同样生活在盗区的普通人,而豫北语言的称呼是“横鬼”和“主儿人家”。追随一幕幕“在逃”场景,发生在1930年代的豫北匪患往事又浮现在眼前。他们逃,当官兵追捕到“沙滩柳林”时,他们的身影消失了。斯科特的“左米亚”(zomia)概念创造出来后,为匪患滋生、剿匪不力增加了生态解释,但是相较于坚壁清野的社会控制手段,逃跑艺术残存的浪漫主义终会荡然无存。爱丽丝以逃跑、警察追捕、警察破门而入等“在逃”场景的统计语言来量化第六街区不断上升的在逃人数以及抓捕警力投入的上涨。在大数据的信息社会,社会控制的技术支持系统已经远远超出了物理、地理性质的警力布控和人力摸排所能达到的力度和范围,可以说,人的生理存在、行踪轨迹以及通话记录等任何“有迹可查”已经转化为信息录入计算机,生活在抓捕阴霾下的第六街区的黑小子们,永远洗不干净的犯罪履历,在逃、被抓、服刑出狱、在逃……清零的停滞状态——爱丽丝用清晰的统计语言和法律程序一样冷酷的医疗语言揭示了第六街区碾转于绝望与失望之间的生活世界——它是有血有肉的生命在司法系统滥用暴力、威胁、离间等手段将爱与信任撕裂得粉碎的冷酷现实面前的挣扎和继续。爱丽丝穿梭于盗区和学术世界,在她应该属于的世界等待恐惧和惊吓在她身体中的反应慢慢消逝,近似“创伤后应激障碍”,在精神上,她已经和第六街区无法分离。

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所谓针对黑人的瞄准式拘押不仅造成“大众收监”,数以百万计的黑人年轻人远离了学校、工作和家庭生活,被捕入狱,被定重罪,之后再遣返社会,而且掀开了美国种族压迫的一个新篇章,它是伴随零容忍犯罪高压政策的信息技术升级。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统计比照系统”开始跟踪各种案件的进展,费城警署的每一个侦查部门都有了自己的担保局,以搜查令去定位以及确认人的技术得到了改进,凭借一纸担保,“分分钟找出一个人的名字成为可能”,不仅如此,担保局还使用了一种成熟的电脑定位系统来搜查有污点的人,据说是受到东德秘密警察的启发。警察们还可以通过追踪手机来实时跟踪受到通缉的人。
控制技术升级,而逃避控制的技巧与手段也在进步。麦克、卓克、阿里克斯、安东尼、史蒂夫是第六街区小分队的核心成员。其中,管麦克叫“大佬”的小弟尼克跟随左右,卓克的两个弟弟雷尼、提姆也是其中一员。他们卖毒品或偷车,从事肮脏的营生。他们不敢申请身份证明,也不敢使用身份证明,就靠买假证来满足他们的需求。到了2000年中旬,警察改用个人的照片身份号码,这个号码和一个人的首次被捕关联在一起——假证不好用了。于是他们向拥有合法身份的人付钱,把一些东西归在那个人名下,例如麦克住在朋友名下的公寓,两辆车分别在两个女人名下,手机以他孩子的母亲的名义购买,这大大增加了警察搜寻他们的难度。
探监的家属常常会带大麻给犯人,有些人还以此为赚钱来源,有偿为其他犯人带大麻,珊达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她把大麻叠进钞票里,递给犯人。手部毒品扫描仪的出现很容易把触碰过大麻的手检测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她把小包裹放在内裤的夹层里,而且多次洗手,依然能够把包裹带入监狱,尽管这样做风险重重。
麦克他们常常要在假释期间接受尿检,如果呈阳性,很有可能作为吸毒证据收回假释。为了逃避尿检,开照相馆的拉基姆从借尿到正式卖尿,开发了赚钱之道。一开始用咖啡机加热没有经验,“尿太烫”,灼伤了买尿的人大腿内侧的皮肤,拉基姆通过调试温度,加上纱布绷带的保护,解决了问题,拉基姆的尿液生意风生水起。
第六街区不仅创造了一个满足法律边缘人群各种需求、逃过愈加严密的社会控制的黑市,而且还有来自警务人员从内部为犯人开后门而创造的“刑法经济”。例如作为中转站的狱警接受犯人一晚上一百美元的贿赂,放他们出去过夜,因为中转站一个房间二十个床铺,条件恶劣,犯人们在里面打架,不堪忍受。对于这一做法,狱警在接受爱丽丝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他们记得有这个美好的夜晚,我也就聊以慰籍。”而司法工作人员在她的工作职责之内将她认识的当事人的缓释时间延后了一年,接受了一笔钱作为报答。可以说,零容忍的司法高压从内部创造的“刑法经济”,其性质已经和1936年怀特在《街角社会》所描述的纽约警局腐败截然不同,后者是在赌场等违法经营和警察共谋的前提下对那些较真的个别警察的集体抵制和小心翼翼,而共谋则是依靠收保护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片警对卖酒、赌博等非法活动的默许(威廉·怀特:《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贫民区的社会结构》,黄育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费城第六街区在内的担保局等专业机构在司法系统内部开通的 “地下铁道”,表面上是为犯人行方便,实际上是司法“敛财”合法化的一个渠道,和暴力执法有着相通之处,“监狱扮演了一种在美国社会中生产不平等群体的角色”(第15页)。

二、暴力执法
第六街区充斥着暴力,当街火拼、抢劫、放火频繁发生,压抑和愤怒随处可见。正如大卫·哈维在《希望的空间》所说的,贫困的阶层已经自发成为一个“危险的阶级”:城市囚禁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并把他们推向广阔社会的边缘(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擦枪走火、吃枪子儿是麦克他们大多数人都不稀罕的经历,警察入室搜查往往是冲着私藏枪支和毒品去的。生活在监控和追捕的司法阴霾之下,他们的受伤大多是来自逃跑过程中:不是摔伤了腿就是跌断了胳膊,这时他们寻求的是地下医疗。因为医院是诱捕之地,就像阿里克斯,宁肯忍受一只眼几近失明的痛苦,也抵死不去医院接受治疗,因为一旦假释泡汤,他便永无抽身之日。爱丽丝所描写的地下治疗是医院人员为满足法律边缘人的医疗需求而在家完成的包扎和简易手术,这些治疗办法简单、粗暴而有效,她在旁边看到那个妇女“将两根针扔进锅里的沸水中,然后用它们缝合裂开的皮肤,艾迪无声地哭泣着”(第209页),护士“在厨房的桌子上取出了罗尼的子弹,罗尼的祖母塞了一块洗碗布到他的嘴里,打开音乐掩盖他的尖叫声”(第21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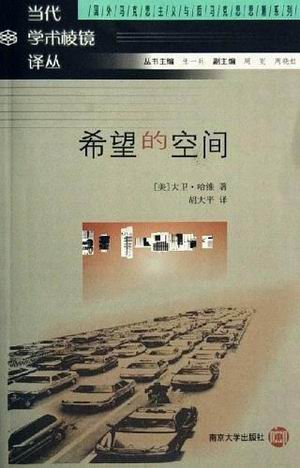
三、义字当头
生活在第六街区的黑人年轻人们在逃跑之余过着不上进的生活,他们以逮捕令为借口拒绝工作,因为就像史蒂夫所说:“他们会在工作场合把我抓起来”,六年来他没有找过工作,他们吸毒卖毒品,抢劫或者被抢劫,遭遇盗窃时不敢报警而私自寻仇,招惹更大的麻烦。卓克的母亲吸毒,家里弄得一团糟,卓克、雷吉和提姆兄弟三人就生活在这个“垃圾场”里,有麻烦了躲到车里睡觉也要“逍遥法外”。第六街区的黑人年轻人们已经丧失了米切尔·邓乃尔所描述的纽约第六大街的黑人们依靠捡“破烂”卖书刊杂志自食其力、努力工作、值得过上更好生活的生活奔头。不仅如此,他们的家庭责任感也是如此糟糕,生活在被抓的风险中,他们不敢到医院陪老婆待产,有了孩子也无法稳定地陪伴左右,他们就连探视权也要在假释官批准和监视下进行,而且他们在做了父亲的情况下,还有其他女朋友,在逃的两性关系极其脆弱。当逃跑与藏匿成为全部的目的和手段时,爱与信任几乎被折磨得只零破碎,然而在沉重的堕落意志中,爱丽丝仍旧触摸到一种与黑人拾荒群体自食其力、努力工作截然不同的价值和品质,那就是义气。
尽管卓克的母亲琳达是卓克三兄弟走上犯罪道路的肇始:卓克卖毒品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他母亲不为吸毒做出更离谱的事,她吊儿郎当,还偷拿卓克他们的钱,但是在警察的威逼利诱之下,她却不象其他女人一样轻易地告密,她是不折不扣的游侠(rider)。在暴力面前,她表现出了惊人的镇静和智慧,她不能让警察把她的儿子带走。游侠在当地享有令人尊敬的名声,包括那些在警察追捕之时给麦克他们行方便之门的邻居。
相较于游侠,更具侠义精神的是在逃的黑小伙们把危险承担在自己身上、保护想要保护的人不置于危险之中的承诺和牺牲。爱丽丝言道:保护某人免于被逮捕恰恰被认为是一种承诺和有情有义的行为(第176页)。冒着撞见警察的风险参与孩子的降生仪式,冒着被抓的风险参加被枪杀的好友的葬礼,甚至挺身而出为他人顶罪,“以这种方式,人们通过逼近的监狱的威胁,寻找机会来表示保护和牺牲而构建了一个道德世界,从而将自我与他人联结在了一起”(第173页)。而那种为保全自己将他人置于危险之中的疏忽则被看作自私,就像安东尼跑到琳达家,把警察引到琳达家的时候,琳达叫喊道:“你做过什么正经的事吗!那就是你该得的,黑鬼!这就是你他妈的该得的!”
与在逃的状态紧密相关,给予以及接受法律的风险成了在第六街区附近的人评估他们的关系的一种途径,保护所爱之人不被警察抓走,或者为他们冒被逮捕的风险,犹如礼物馈赠,将人们团结在一起。正如没有始终如一的忠诚,就连义气在条件的变动下其意义也会发生变质,取决于受惠者如何定义,正是遭遇法律的道德模糊性,施惠者所做出的牺牲往往又会被解读为别有用心,反过来被利用,遭到嘲讽甚至羞辱。因此爱丽丝将义气转变为道德说辞,它给予了人们自我解释的道德表述空间。更进一步,义气构成一个有意义的道德框架,年轻人由此获得他们的身份认同、展示他们的情感以及判断彼此的品性(第188页),当然,它是和刑事司法系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浪漫,也丝毫没有美化成分可言。
四、社会戏剧
欧文·戈夫曼对社会学理论的最大贡献是在他1959年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现》一书开始的戏剧透视法的符号互动论研究,他说生活犹如剧场,人们的社会行为就是社会表演,人们在互动过程中按一定的常规程序(即剧本)扮演自己的多种角色,为了给别人留下更好印象,人们运用一些手段(外部设施和个人的装扮)装点门面。要看到在装扮的空间背后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即后台真实。

五、义海情天
雪莉·奥特娜在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视角中引入“惩罚性统治”:政府针对其公民的暴力形式激增,具体表现为“监狱的激增”现象。她将美国描绘为“监狱国家”,认为“惩罚性治理是新自由主义的真正文化逻辑”(雪莉·奥特娜:《晦暗的人类学极其他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理论》,王正宇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第5页)。虽然她提及“囚犯中的大部分是承受贫穷与种族双重折磨的非洲裔美国人”,不过展开的是监狱增长、监狱国家与监狱审美之间的关联,而《在逃》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悲惨底层的最佳诊断”,呈现的是惩罚性治理如何演变为黑人种族隔离政策在当下的延续。如果说马林诺夫斯基在一战前后以文化自决理论支持南非种族隔离政策是现代人类学理论付诸应用的开始(Isak Niehaus. Anthropology at the dawn of apartheid: Radcliffe-Brown and Malinowski' South African engagements, 1919-1934. Journal of Global and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2017, 77, pp. 103-117),那么2000年开始“大众收监”政策将成千上百万的黑人以各种过失、罪名投入监狱的举措,黑人公民权的剥夺和丧失是否意味着白人市民权权利和利益的增加?显然并不能做这样简单的联系,但爱丽丝毫不犹豫地指出:我们或许把美国贫民区理解成这个时代最后的专制体制之一(第279页)。
正如卓克的爷爷,琳达的父亲——乔治先生对爱丽丝所言,“我不想生儿子,要儿子有什么用,本应该毕业、工作、结婚、生子的年纪,但是他们却抓了又放,跑了又抓,反反复复在牢狱内外打转,在这期间,你还要供养他,给他付帐单,给他擦屁股,在他坐牢的时候,为他祈祷,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思?!”这种停滞不前的生活状态,虽然使麦克他们羡慕拉马尔等“干净的人”拥有合法的身份、不和警察打交道、履行做人子人父的家庭责任感,但是所谓“干净的人”也仅仅是在身份合法维度与之区分,他们的少年梦想早早夭折,进入社会从事平庸或专业的工作,开始按部就班的生活,经历中年失业、老年失独的灰色人生。第六街区黑小伙子们的在逃生活蔓延到“干净的”黑人群体之上是失望、失败与麻木的生活状态,贫穷、暴力与种族混合在一起,在司法高压政策的作用下,演变为真正的贫穷、暴力与种族问题。
如果以找出“害群之马”的方式将吸毒等犯罪事实归结到个人身上,显然错过了对这个控制体系的发问。如果放过对制度的追问,显然是放过了罪与罚的噩梦——用花费大量财力、物力、人力去监控、拘捕,而不是帮助黑人走出困境,造成“种族隔阂”越来越深。《在逃》越是对处境描写得感同身受,越是激发人对制度的反思,追问监狱政治燃烧的动力和驱动力来自哪里?当这架机器瘫痪时,什么样的努力可以一点一滴地改变贫困与暴力。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怀特在1936年《街角社会》中的意大利贫民窟的帮派分子活动的观察中尚有社会工作者介入社区并组织俱乐部活动,然而2002年的费城第六街区却毫无教会、社会工作者等福利机构的干预,改良性社会措施全然缺席。
如果这个社会没有自我修复的能力,那么它的“坐以待毙”的心情就是把人推向失望与犯罪相互交替的“停滞”状态,它不是格尔茨所说的“什么事也没发生(nothing happened)”的经济停滞,而是“一切清零”的逃亡生活的写照:一直挣扎却无法前进(第269页)。
监狱政治越是以消灭的方式对待只有模糊面目的匪患,就越容易混淆黑白、殃及池鱼。“在逃”传达了一个核心理念:当有罪的人逃避法律制裁之时,一张逮捕令或假释判决会扩增到数张逮捕令或法院拘票,这种在逃的不归路来自于社会控制系统中族群的空间宰制,“反社会”不过是相反相成之意,宰制甚至暗示其鼓励或诱发受怀疑族群成为/变为社会控制定义中的暴徒、匪众。这一深刻的思想通过爱丽丝对费城第六街区的人们所置身的司法系统展现出来,其支撑性细节是枪支的离散、审讯的技术、信息控制网络、地面和地上包围结合等。对于在逃的黑小伙们和他们的家人、伴侣、朋友、邻居以及黑市交易者,任何熟人社会都有可能成为警察的信息提供者,为了个人利益出卖朋友,为了保全自己和儿女而供出自己的男人,屡见不鲜、层出不穷。然而在逃的环境,也培植了游侠和义气。面对威胁,个体如何反应,如何选择,一念之间,体现出了保护他人不置于危险的侠义品质。因为这重牺牲与承诺,生命既关联在一起又不相连累,它或许没有与监狱政治抗衡的力量,或许连被保护者都不认账,或者被保护的人随时随地跳将出来反咬一口“卖主求荣”,无论它被背叛的命运有多惨烈,它在困厄之中散发出来的微弱光亮可视为人性的荣耀而不被泯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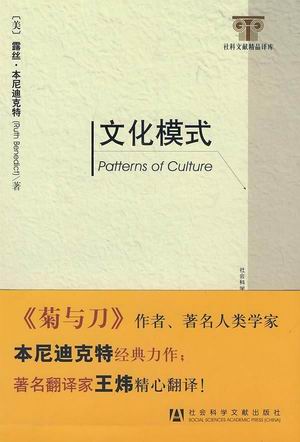
世事变迁,豫北“沙滩柳林”早已不再,而关于侠盗的传说却仍在曾经的盗区传唱。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6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