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维舟:怎样的机制才能有效促进文化生产?
文 / 维舟
网络文学算是“文学”吗?提出这个问题,可能会让很多人觉得好笑和多余:“网络文学”虽然也被冠以“文学”的名义,但那些玄幻、修仙、宫斗之类毫无文学价值的文字,也能算是“文学”吗?
类似的问题,其实早在数十年前就有人注意到了——当时,金庸、古龙等武侠小说名家发现,在很多文学批评家眼里,“武侠小说”与其说是“小说”,倒不如说更像是某种用过即弃的快消品。然而时至今日,金庸小说历经近二三十年的经典化后,在新一代年轻人心目中已经差不多变成了“严肃文学”。
这些都表明,在世人的心目中,对“文学”的界定其实一直是游移不定的,即便很多人对“文学”的认知差不多等同于“严肃文学”或“纯文学”,但问题是,雅俗的边界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试想想,《诗经》中的三百篇,最初也都只是民间歌谣而已,而我们现在奉为经典的“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在前人看来大抵也只是不入流的俗文学。当时坊间传唱的词曲一如当下的流行歌曲,也很少被人认真对待,要不然2016年鲍勃 · 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不会引发轩然大波了。
由此来看,“网络文学”作为一个历史现象也呈现出全然不同的意味:在通俗文化市场上,已经不可能只依靠少数知识精英的创作,庞大的市场需求势必催生出能够大规模生产这类文化产品的机制。在近年来的中国,正是网络顺应了这一需求,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2017年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显示,中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累计超过1,600万部(种),驻站创作者1,400万人,网络文学出版纸质图书共6,942部,改编电影、电视剧、游戏、动漫分别达1,195部、1,232部、605部、712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这是另一个“世界工厂”,一个文学的“梦工厂”,标志着中国的文化生产也进入了工业化规模。
 不难想见,这样一种全新的机制,势必会对原有的创作理念、社会意识乃至法律框架产生深远的冲击。其主要表征就是层出不穷的针对网络文学的“抄袭”指控,这典型地体现出人们对新事物性质的模糊认知:那些相似的设定究竟是否构成侵权?为何还有人不断为此辩护?这究竟算是“法制观念薄弱”,还是全新的观念,以至于新到法律框架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不难想见,这样一种全新的机制,势必会对原有的创作理念、社会意识乃至法律框架产生深远的冲击。其主要表征就是层出不穷的针对网络文学的“抄袭”指控,这典型地体现出人们对新事物性质的模糊认知:那些相似的设定究竟是否构成侵权?为何还有人不断为此辩护?这究竟算是“法制观念薄弱”,还是全新的观念,以至于新到法律框架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这些问题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似乎只能是一个彼此往对方身上扔泥巴的僵局,很难找到答案。因此,社会学者储卉娟在《说书人与梦工厂:技术、法律与网络文学生产》一书中讨论网络文学所遇到的上述问题时,首先做的便是去追溯现代知识产权下的著作权意识是怎么来的。因为法律意义上的“抄袭”指控正是这种现代理念的结果,正如没有护照等一系列出入境管理制度之前,也没有“偷渡”的概念一样。追根溯源,这些基本原则的奠定其实相当晚近:它是18世纪英国书商之间垄断与反垄断利益博弈的结果,最终确定了以作者为权利主体的保护模式,而这本身其实与个人主义、财产私有的现代理念密不可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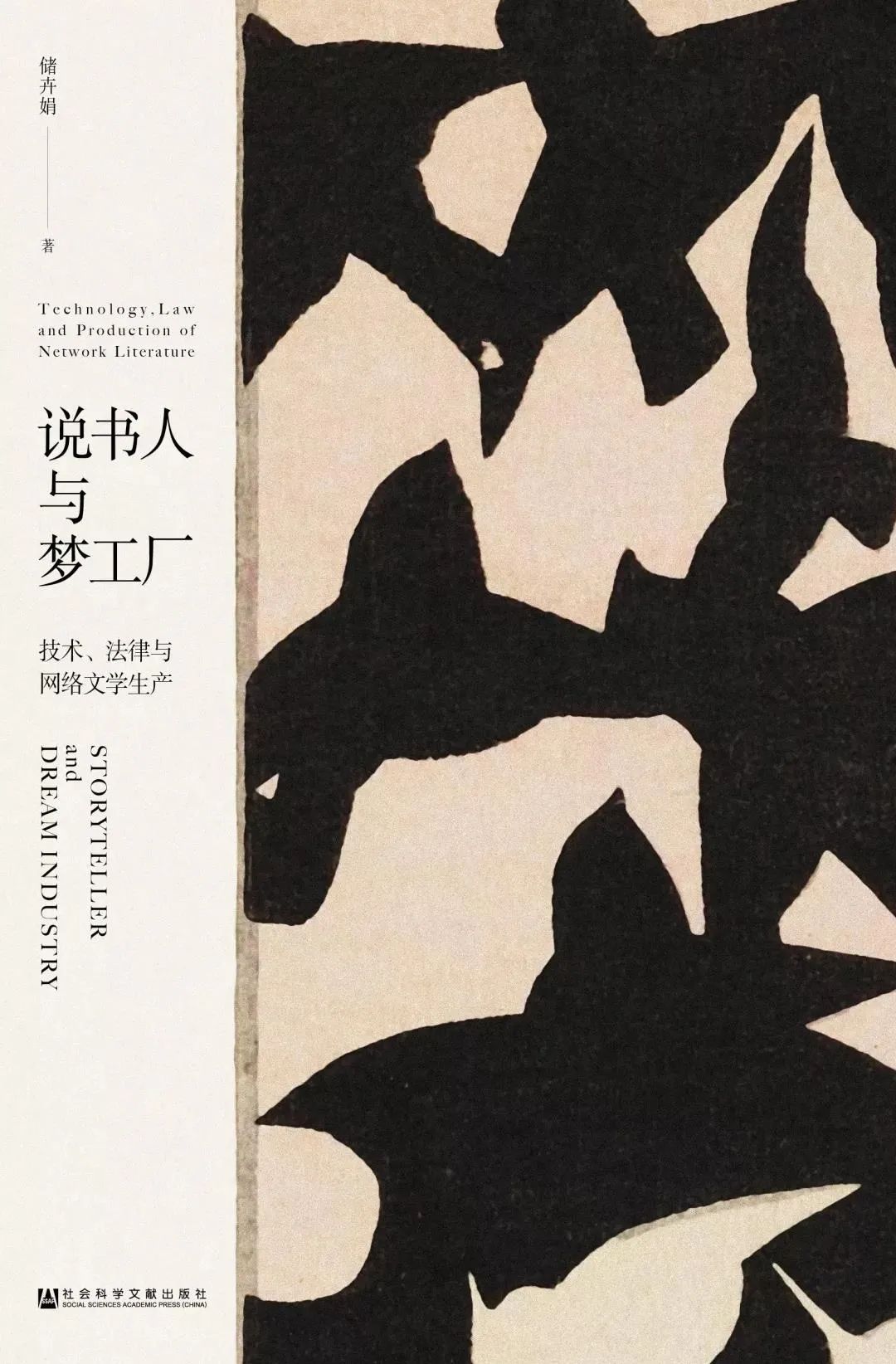
说书人与梦工厂:技术、法律与网络文学生产
储卉娟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06
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无论在哪个国家,最初都只有一种“神圣性作者观”,在这种意识下,歌谣、传说、史诗归属于所有人,人人皆可传唱、改编,而不是任何个人独立完成的作品;直到社会渐渐发展成熟,才开始出现一种“所有权作者观”,即相信每一作品都是个体天赋和努力的结晶。龚鹏程在《文化符号学》一书中解释了后一种观念的特定内涵:“每一作品均有一位单一的作者,成了我们对作品的基本了解;探寻作品之原貌、追问作者之原意、确认某一作品之作者与写作时间,亦已成为诠释及阅读作品的基本课题。通过这些工作,读者努力地去贴近作者,以了解作者所欲言之意,想见其为人,以与作者沟通。”[1]
在对经典进行文学诠释时,这些几乎是不可动摇的常识,尽管我们也难免遇到问题(所谓“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意味着对“作者原意” 几乎很难达成共识),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网络文学中这并不是读者关注的重点。很多时候人们甚至并不怎么在意作者是谁、本意又是如何,与其说他们想与作者沟通,倒不如说更在意文本所构筑的那个世界是否能让他们沉浸进去。
不仅如此,他们还会在网络上对作品加以评论、延伸,这些七嘴八舌的二次文本生产有时甚至比原文更有意思,它们与原作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虚拟世界。
借用罗兰 · 巴特那句著名的断言,这是一个“作者已死”的世界。但消解了作者之后,这个去中心化的网络呈现出了更纷繁复杂的活力:读者不再是被动的“受众”,他们不仅决定文本的意义,甚至还按捺不住参与进来互动。正如《说书人与梦工厂》中所言,在这种情况下,“作品的核心位置被取消,类型取代文本成为写作和阅读的聚焦处。作家的神圣性和个人主义色彩被取消,写作者一网络一阅读者的三位一体取代了‘作者’,成为整个网络文学生产的内容发动机。”[2]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储卉娟将网络文学的创作者比喻为“说书人”,因为在传统时代,“说书人”正是这样一个“集体创作”的角色,其并不将作品视为个人独有,常常毫不介意地传唱民间流传的故事。这意味着承认作品是一种社会产物,而不能归功于某一个人。实际上,近代早期的手艺、技术也无不如此,它们都不由个人独据,而是集体合作拥有或相互分享的。凭空出现的独家天才设想是极难的,绝大部分创造发明其实都是在原有共享知识基础上的改进。《枪的合众国》一书中强调,如果没有先驱模型为参考,即使专家也很难构想出独特新颖的设计,因而每一次“创意”其实都是在现有基础上的微小改动,但每一次都可能带来巨大突破,“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同一个创意,也很可能会有多个发明者竞相申请专利,就像麦克维尔的《白鲸》一样,当时有很多人声称著作权归自己所有”[3]。

白鲸
[美] 赫尔曼·麦尔维尔 / 著
马永波 /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0-03
在这方面,颇具参照意义的是美国的西部文学。其最初奠基于神枪手和亡命之徒的民间传说,进入20世纪后,内容越来越多、题材越来越广,而其真实起源却往往无从考证。这些在当时被认为曲折动人但毫无文学价值的西部故事由纽约等大城市的“文字工厂”生产,很多作者在简陋的出版商办公室里“每天像机器一样不停地进行机械创作廉价文学”[4]。1902年,一位西部小说作者曾说,写这类廉价小说只需要三样东西——丰富的想象力、戏剧天分和不知疲惫的手。研究这种类型小说的学者迈克尔 · 丹宁(Michael Denning)总结道,廉价小说中的情节和角色个性都是可以相互置换的,即使匿名作家也可以拼凑出来。
哪怕最强调“创意”和“独特卖点”的现代广告业,其实也是如此——美国广告大师詹姆斯· 韦伯 · 杨(James Webb Young)早就说过,创意的本质乃是“旧元素的新组合”,完全凭空而来的创新即便不是没有,也是极难的。但这样说来,“借鉴”和“抄袭”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如果说古代的说书人确实在传颂某种无法追溯源头的“公共知识财产”,那么网络文学中的那些故事框架和情节设定,最初难道不是某个创作者的独特表现吗?——它并不仅仅是“正在生成的集体想象”而已。
这不只是一个伦理问题,而且涉及什么样的机制才能最有效地保护并促进文化生产。的确,著作权法不保护作品“构思”,认为这不应由某个作者垄断,否则将阻碍文化发展,但它有必要保护“表达”,否则也会损害创作者的权益,打击其创作的动力。即便现在网络文学的读者在意文本多过作者,并且自己也参与到创作互动中来,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由此产生的收益却是属于作者和平台的。因此,这并不只是一个抽象的伦理道德问题,更是权责边界和利益分配的问题。
把这些网络文学作者称为“说书人”,最多只是隐喻意义上的,他们并不是简单地回归前现代的社会现象,这两者之间有明显的差异。按吉姆· 麦克盖根(Jim McGuigan)在《文化民粹主义》一书中的说法,最显著的后现代场景之一,就是“界限模糊,准则混同,高雅与通俗文化掺和在一起,完全是一派喜气洋洋的严肃”[5],这意味着要厘清权责边界比以前更困难了。但同时也要警惕的是,国内的诸多现象乍看是“后现代”的,其实却是“前现代”的:大规模的“洗稿”、抄袭,在很多时候确实只是知识产权意识淡漠而已。这就是我们时代的两难处境:为了推动文化生产,既需要贯彻法制观念,又需要适时调整原有的制度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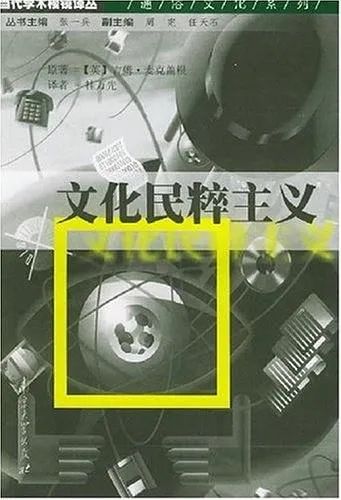
文化民粹主义
[英] 吉姆· 麦克盖根 / 著
桂万先 /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01

现代历史表明,无论在哪一个国家,文化的繁荣都必定倚赖于一个成熟的大众消费市场,以及由此催生出来的文化领域细分和公共批评。如果说早先的作者观是精英式的,聚焦于少数天才的原创,那么在这样的大规模文化生产下,势必可能呈现出大工厂生产式的泥沙俱下。尽管很多人痛心于现在很多作品、翻译的粗制滥造,但倒退回早先那种作坊式的“慢工出细活”不是出路,真正的演进道路应该是市场的自我规范。最终,即便是在看起来很差的领域,在大量垃圾的基础上,也能涌现出1%的精品。
如今文学的圣杯仍然由严肃文学作家和批评家所看守,网络文学的“文学价值”在他们眼里仍是可疑的。虽然网络文学“名分”未定,但它的崛起已经造成文学领域的分裂:在大众消费兴起之后,传统纯文学期刊在事实上已被边缘化,甚至“纯文学”本身也面临着重新界定,它不再被视为大众层面的文学样式,而“降格”为一种面向特定读者群的小众趣味。这一演变也折射出“市场”的巨大威力:如今,每种细分的文学门类都必须找到自己的受众群体,并在他们的心中占据一个具有差异性的独特位置。
在此也能看出中国通俗文化市场的特殊道路:1997年前后出现的网络类型小说,无论是武侠、玄幻、修仙、宫斗甚至穿越,大多都带有浓厚的传统文化色彩。而武侠、玄幻、言情这些类型,起初都是由港台输入的,在内地不同的市场环境中,其整个生态很快就朝着更加复杂分化的方向演进。
夏志清曾说,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未必有文学价值,但它可以表明“民国时期的中国读者喜欢做的究竟是哪几种白日梦”[6]。如果按此理解,那么网络文学所折射出的,也正是这个时代中国读者的白日梦——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既是文化快消品,又是减压阀,为人们提供了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满足感。这本身也符合网络这个虚拟空间的属性:人人都知道这些是虚构的故事,又都钟爱“虚构中的真实”,就像谁也不认为自己能穿越回清朝,但“种田文”[7]却务必将所有细节落实,因为那种小人物奋斗的灰姑娘之梦正是属于每一个读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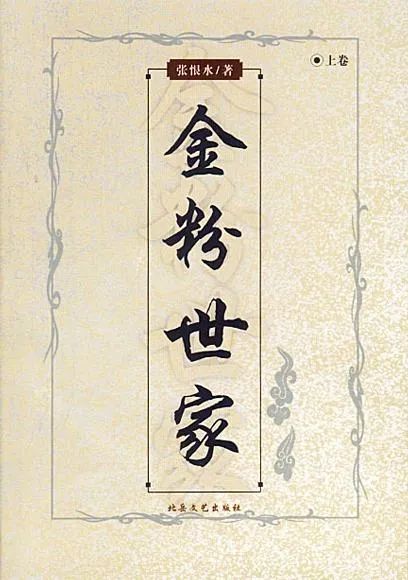
金粉世家
张恨水 /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0-01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中国的这些穿越小说乃至宫斗剧中,很多设想都是“按计划进行的”,很少出现蝴蝶效应式的不可预见的结果,这本身暴露出中国社会的一种特殊心态,那就是偏好在一个封闭系统之下的适应。所谓“种田流”,其基本设想都是一步步稳扎稳打,在一个危机四伏的环境中逐个克服困难与障碍,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这实际上是中国式的小人物的成功之路:结果是确定的、必须实现的,问题只是如何打通关。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它尤其像白日梦。
除了穿越、宫斗之外,《说书人与梦工厂》几乎没谈及太多的女性文学、同人小说和耽美故事;但更为重要的是,书中也没有解释为何是这几种类型占据了上风。在日本和欧美都极为流行的科幻、推理,在中国的网络文学板块中却不算突出。也许是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也许是遗漏,又或觉得人所共知,作者在这方面并未多做交代,但我们应当清楚地意识到一点:这远不是一个自我分化独立的市场,而是受政治和资本双重力量挤压的市场,并由此才进化发育出特殊的文化类型。

步步惊心
桐华 / 著
民族出版社, 2006-06
由于将视线聚焦在理解网络文学这一现象本身上,在阅读中我有时不免感觉作者的论述缺乏对网络文学及其模式的批判:她似乎惊叹于网络文学生产的规模(“量”),而对其“质”避而不谈。当然,那或许是文学评论家而非社会学家需要关心的事。另外,在我看来,作者对网络文学所开辟出来的市场模式也过于肯定,她将传统的出版模式视为落伍,甚至是阻碍。这并不能算是持平之论,因为在文学生产中,恰恰正是编辑、批评家等职业担负起了把关人的角色——本来就发育不全的中国文学批评,再遭此打击,从长远而言很难说是好消息。
2002年VIP收费模式兴起,以点击量作为读者付费和作者获得报酬的标准,意味着作者必须不断生产出读者有兴趣阅读的网络文学产品。这的确取消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中介模式,编辑、审稿、版权代理、出版社等,统统被颠覆,似乎算法就能解析读者的需求,自动精确匹配并推荐。但要说“从此之后,网络文学生产进入了读者消费行为直接引导的生产模式”,就未免太过乐观了。既然作者也意识到互联网本身便起源于“控制论”,控制论的主要动机不是消除控制,而是要发现更好的控制方法;那么,为什么又相信在中国的网络文学生产中,那些“有形之手”并不在场?
公平地说,《说书人与梦工厂》的结论也并未完全忽视这些外部力量,因而强调“如果政府和法律完全放弃了对网络空间的控制,就等于将塑造/摧毁自由的力量完全交给可以影响代码模式的互联网商业公司”[8];但网络文学也不仅仅是一场“没有英雄的群众运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读者行为就能直接引导网络文学生产”这样的认知,其实是一个尚未实现的乌托邦理想,因为无论是国家还是资本力量,都不会放弃引导读者行为本身。说到底,读者行为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由读者自己决定。
注 释
[1] 龚鹏程. 文化符号学:中国社会的肌理与文化法则[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43.
[2] 储卉娟. 说书人与梦工厂:技术、法律与网络文学生产[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15.
[3] 帕梅拉 · 哈格. 枪的合众国[M]. 李小龙,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44.
[4] 同上,216—217.
[5] 吉姆 · 麦克盖根. 文化民粹主义[M]. 桂万先,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67.
[6] 夏志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0.
[7] 种田文,在策略类游戏中,指在特定环境下稳扎稳打地扩大自己地盘势力;在穿越小说中,指“学习做一个古代人”、适应环境并步步成功的类型。
[8] 同[2],253—254.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6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