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对于海外中国学,我们所知有限:由汪荣祖教授新文引发的思考
最近,著名学者汪荣祖先生在《国际汉学》2020年第2期发表了《海外中国史研究值得警惕的六大问题》一文(以下简称“汪文”),从个案出发,犀利指陈海外中国史研究中“离谱的误读”“严重的曲解”“荒唐的扭曲”“不自觉的偏差”“颠倒黑白的传记”“居心叵测的翻案”六大问题,一时引发热议。其中的第一大问题——“严重的曲解”,汪文以执教于耶鲁大学、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为例,指出其著作中的种种硬伤。如史景迁在著作中将张岱原文中的“仕女”解作“年轻男女”、将“星星自散”解作“天上的星星散去了”、将“岳王坟”解作“古代越王们的墓”、将“莫逆”解作“平定叛逆”,等等,多是不应有的错误。关于史景迁著作中的此类问题,汪文此前已在《梦忆里的梦呓:评Jonathan D. Spence, 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 Memories of a Late Ming Man》(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5期,2009年9月;《上海书评》第65期,2009年11月)一文中指出,读者自可参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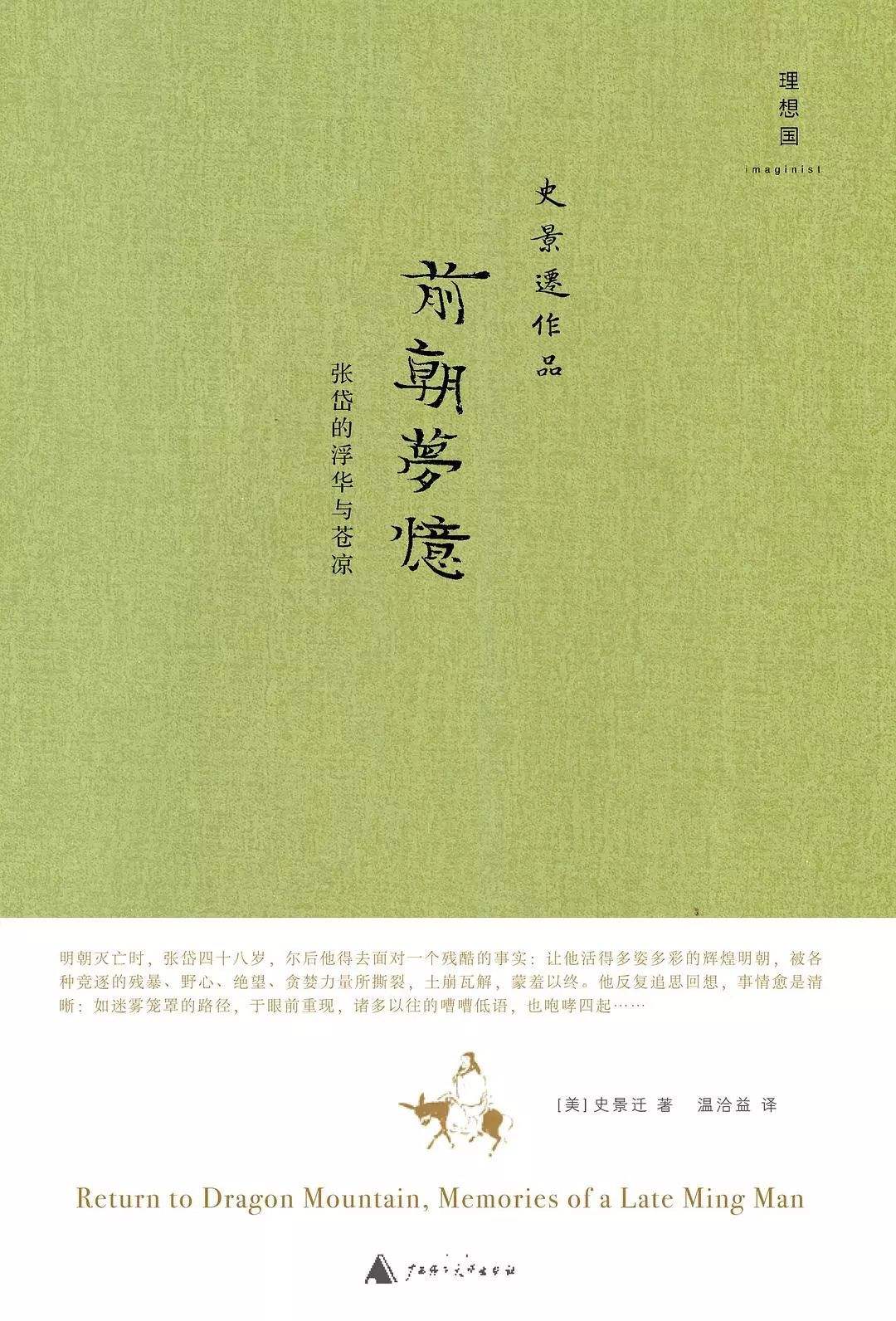
此外,诸如“新清史”等问题,汪先生此前亦多有批评,因此汪文相当于一次全面的总结与反思。汪文所指出的问题的确存在,但也要注意,汪文在指出问题的同时,也肯定海外中国史研究的贡献。鉴于汪文有可能会给读者造成误会,甚至会引发一些读者抵触海外中国学(汉学)的情绪,笔者试谈谈个人的粗浅认识,以就教于方家。
一、文本解读与语言根柢
汪文指出:
研究历史,文本为要;读懂文本,才会有正确的研究成果。中外文字之间的鸿沟较大,学习不易。美国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大多进研究所后才学中文,已经错过学习外语的最佳岁月,以至于往往一知半解,对晚清之前所用的古文,尤有扞格。当今西方汉学研究者几乎已无人能用汉文著书立说,且他们也无此需要,因英文已成学术霸权语言,用他们自己的文字写,似更有权威。
历史研究,自然以文本为要。不过汉学研究者并非不重视文本的解读,与中国学者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研究中国古典的汉学研究者而言,注译古书与文本细读都是基本的工作,往往抠得很细。尤其是日本学者,在文本解读方面极费心力。笔者在以色列希伯来大学访学期间,曾参与过东亚系的《左传》研读课程,对此有所体会。
至于汉学研究者的汉语水平以及解读古文的水平究竟如何,不可一概而论,往往受到研究方向、教育背景、年龄层次等因素的制约。通常来说,研究中国古典的汉学研究者,古文水平胜于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学者;一些日韩学者,对古文的理解与感受可能更接近中国学者;相对年轻的汉学研究者,与老一辈学者相比,由于有更多来华学习、访学的机会,汉语的运用一般也会更加娴熟。
而过去老一辈的汉学研究者,则可能存在精通古文却不谙现代汉语的情况。美国学者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在一次访谈中指出:“我的老师倪德卫(David S. Nivison)古代汉语水平很高,但一句汉语都不会说。不光是他,那个时代很多汉学家都是这样,研究做得很好,但不会说。”德国学者鲁道夫·瓦格纳(Rudolf G. Wagner)在《王弼〈老子注〉研究》中文版(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的序言中写道:
20世纪60年代初,我在德国和法国学习期间,我关注的是古代汉语。那个时候很多研究古希腊的学者在学习古典的希腊文,但连在现代希腊的雅典餐馆叫来一杯水这样的事情也压根儿无法做到。我那时既没有学习现代的白话文,也没有看到这样做有什么必要。那时候,社会主义阵营外的世界,与中国大陆没有任何实质的学术交流,而少数在台湾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学者讲的都是英语。直到1979年,我年近40的时候,我才学会了第一个普通话的单词。
此种情况类似于:研究梵文的中国学者,可能无法在当代印度用印地语与当地人顺畅交流。但这似乎并不影响汉学研究者对中国古典的研读,如瓦格纳先生对王弼《老子注》的文本分析便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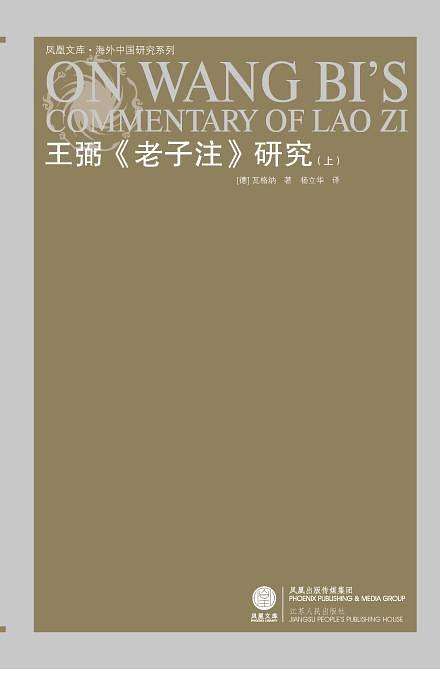
相比接触汉语较迟的汉学研究者,自幼浸淫于中国语言与文化情境的华人学者,无疑有天然的优势。这种基于母语的感受力,很难通过后天的学习来弥补。在我翻看英文的正式出版物时,便会时常遭遇汉字的误用情况,当出于西方学者对汉字不甚敏感之故。正是不同的语言环境和学术环境,造就了海外中国学与国内学术之间的分野。二者的立场、问题域与学术范式皆不尽相同,甚至反差巨大。对于二者的差异,我们应抱以“理解之同情”,求同存异,彼此尊重与理解。
譬如,除了夏含夷等少数学者能直接以中文撰文(夏含夷先生称“我常常觉得与自己有沟通问题的不是中国学者,而更多的是西方汉学家”),大多数西方汉学研究者的著作主要以英文、法文、德文等语文撰写。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汉学研究者的中文水平不足,事实上,能以汉语流畅沟通且能以中文撰写文章的汉学研究者并不在少数。即便是一些生长在中国、后执教于欧美的华人学者,也以外文著述为主。这是学术环境不同使然。
再如,史景迁著作中的硬伤,主要体现在对张岱著述的翻译上,汉学研究者写文章吃亏或麻烦之处便在于,他们引述古文需要悉数翻译成外文。这就决定了他们对于每个实词与虚词,都不能轻易糊弄,不像有些中国学者那样复制粘贴引文即可。我想,如果中国学者写文章也需要将每段古文翻译成现代汉语,错误可能未必会比汉学研究者少。最近我正在写一篇英文文章,引述青铜铭文的材料时,争议字词需要有所交代,而不能像写中文论文那样含混带过。
二、三个误区
在笔者看来,中国学者在认识汉学研究者的成果时,往往存在以下误区:
第一个误区:片面看待汉学研究者的研究。
所谓的“汉学家”,成分比较复杂。既有同属于东亚文化圈的日韩学者,也有所谓“西方”学者,还有数量不少的华人学者,他们的学术范式并不完全相同,宜加区分。汪文所举的例子,主要针对美国的非华人学者。
而且,汉学研究者的观点并不是铁板一块、千人一面的。我们不宜以某种观点或刻板印象强加到所有汉学研究者的头上,并人为制造中外对立。譬如,中国考古学界和史学界基本认为夏朝的存在并无问题,但一些汉学研究者则持谨慎意见,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汉学研究者都否认夏朝。再如一些汉学研究者对近年购藏简牍的合法性心存疑虑,但我们也要注意到越来越多的汉学研究者投入这些简牍的研究之中。再如清华简、安大简的新材料为《诗经》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最近夏含夷与柯马丁(Martin Kern)两位学者都在中文重要刊物发表文章,正如许多人所知道的,他们对《诗经》文本的早期形态与形成年代有着迥然不同的认识。
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其优劣不可一概而论;不同国家、不同研究机构、不同学者的研究方向与重心亦不尽相同;具体到某位学者、某本著作,水平有高下,更要作具体分析。日韩汉学与欧美汉学也不宜混同,譬如,由于日韩学者对经学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因此日韩的经学传统仍延续至今,欧美学者则不甚重视经学研究。就目前日本的早期中国研究而言,日本学者长于汉简文书学和思想史的研究,在甲骨文、金文、战国竹简等方面则显得后劲不足。反观国内,由于中国学者有长时期的积累,并延续了传统小学的治学方式与旨趣,故在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方面有绝对优势。总之,汉学研究在不同时代、不同领域的表现并不均衡,其得失不宜笼统视之。汪文所举例子,主要是明清以及现代;由于笔者的研究方向主要在早期中国,故本文所举的例子以早期中国为主。
第二个误区:过度抬高汉学研究者。
近年来,诸如史景迁、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柯马丁、夏含夷、艾兰(Sarah Allan)、罗森夫人(Jessica Rawson)等汉学研究者在中国享有盛名,他们的著作广为传诵与称引。汉学研究者作为提升“国际研讨会”格调的标配,成为座上客甚至“吉祥物”。在追求“国际化”的浪潮下,一些著名高校的教员在参评长聘副教授与教授时,需要得到国外同行的肯定,文史学科亦不能免俗。但国内外学者之间实质性的对话并不多,很多时候,国内学者并不真正关心汉学研究者到底研究了什么。
正如罗森夫人在2017年接受采访时指出的:
从中国的标准看,北大已经给予了我足够的礼遇:考古文博学院的教授坐在台下全程聆听我的演讲,文物局的官员、考古界学者与我进行对话。然而在我看来,无论我走到哪里,都被当作一只“金丝雀”(trophy bird)来展示,而没有专业深入的交流。尽管观众热情极高,但很多学者和观众提出的问题往往并不基于我的研究领域,而只是由研究内容的佐证申发出的一些无关主旨的细节性、技术性问题。从一个西方学者的视角看,没有针锋相对的交流,这是另一种不尊重。

对于汉学研究者,我们有必要以更加理性的态度来看待。既没必要妄自菲薄,也没必要一味盲从、乃至于言必称洋学者。真正的互相尊重,莫过于真正平等的交流与对话。
第三个误区,无视汉学研究者的研究。
有的中国学者认为,汉学研究者的成果存在缺陷,并无足观,没有参考的必要,则不免因噎废食了。以色列学者尤锐(Yuri Pines)曾在李若晖《久旷大仪:汉代儒学政制研究》(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一书的序言中指出:
可惜的是李先生并没有涉及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著作。比如,鲁威仪(Mark E. Lewis)对中国早期思想史的重要研究就儒家对汉朝政治体制的影响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设想。……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可谓汗牛充犊栋,如鲁惟一(Michael Loewe)、柯马丁(Martin Kern)、金鹏程(Paul R.Goldin)、叶翰(Hans Van Ess)、戴梅可(Michael Nylan)等,这仅仅是其中一例,我认为这些研究都应当在《久旷大仪》一书中有所涉猎。我相信,现在正是中国同仁以西方汉学界关注中国本土学者同样的严肃性和彻底性来关注西方汉学发展的时候了。唯其如此,我们才可能在国内外学者间建立一种有意义的对话方式。
如若局限于中文世界,而忽略了汉学研究者在相关领域的已有研究,不免是令人遗憾的。对于汉学研究者而言,他们很难回避以中文撰写的著述;但对中国学者而言,外文著述往往被轻易忽视,即便引用,通常也是点缀,而缺乏真正深入的了解。
汉学研究者的“他者”视角未必都合理,但我们身在此山中,有时的确会容易被习焉不察的观念与情绪所遮蔽。当我们借助“他者”之眼“跳出三界外”,或许会有全新的收获与启迪。
三、基于学术的对话
1992年,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成立,李学勤先生首次提出将“国际汉学”或“汉学史”作为一个学科来开拓。目前国际汉学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与成熟,大体来自两个领域:一是外语专业的学者,注重译介与学术史的研究;二是某一领域的专门学者,就本领域的相关学者与著作加以讨论。后者的研究力量较为分散,且缺乏“国际汉学”的学科意识,但由于他们对具体研究对象有更深入的理解,故更有可能与汉学研究者展开平等的对话,而不是流于皮相之论。
尽管某些汉学研究者受到极力推崇,国际汉学的研究也得到积极的推动,但总体来讲,国内学者对海外的研究成果仍普遍缺乏实际的了解。近年来,葛兆光和张西平两位学者都强调“批评的中国学”的研究,认为我们对于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成果不应盲目跟风,并提出以平等的姿态进行批评与对话。而批评与对话的展开,或者说“批评的中国学”,应当是建立在学理与专业知识的基础之上的。
除了对话,更实际的相互促进是合作。至少在简帛学研究领域,国内外学者的合作是相对密切且有成效的。国内学者在海外高校深造者不在少数,汉学研究者在国内访问甚至就职的也不乏其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任职于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的德国学者陶安(Arnd H. Hafner)主持了《岳麓书院藏秦简》第三卷的整理、研究工作,是该卷的直接负责人。
不过目前来看,国内外学者的对话与合作仍有待深入。从事学术研究者,都知道文献综述与学术史回顾的重要性,但不少研究者显然对海外的研究成果缺乏关注。正如前文所引尤锐先生的序言,汉学研究者既然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完全无视不但是视野问题,还涉及学术规范与伦理。当然,这些海外研究成果质量如何、值不值得参考,又是另一回事了。
国内学者对海外研究成果了解不足,个中有信息不对称的原因。许多重要的汉学刊物,很少有国内的高校或研究机构订阅,研究者接触到海外最新研究成果的机会并不多。加上国内外文献数字化的发展程度不同,也制约了文献的流通。除了客观的因素,一些国内学者在主观上也并无借鉴海外研究成果的意识。
国内学者对海外研究成果的了解,基本上限于已被译为中文的著作。著作被介绍到国内越多的汉学研究者,也越容易获得极高的声誉。这便有可能造成一种反常的现象:在中国红极一时的汉学研究者,在海外可能并没有那么高的地位;在海外极为重要的学者,可能在中国并没什么影响。举例而言,美国学者杜润德(Stephen W. Durant)在《史记》和《左传》方面有精深的研究,影响很大,但他的著作并没有被介绍到国内,乃至于国人对其知之甚少,不免令人遗憾。事实上,近年国外学者对中国史学史研究有一系列突破,这些学者包括而不限于杜润德、史嘉柏(David C. Schaberg)、尤锐,但国内对他们的研究成果关注无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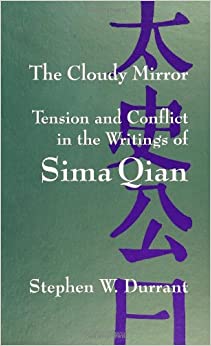
造成目前中外学术研究隔阂的一大障碍是语言。对于汉学研究者而言,娴熟掌握中文与英文自不待言,此外他们还需要研习日文、法文、德文等语文。反观中国学者,多仅限于中文阅读与写作。这便造成了中外学者之间信息的不对等——汉学研究者对中国研究成果的了解远比中国学者对海外汉学的了解来得多。柯马丁先生曾在《学术月刊》2017年第12期发表《超越本土主义:早期中国研究的方法与伦理》一文,对中国以及国外的早期中国研究提出方法论的反思,他指出:
一些学者竭力寻求在纯粹中国层面上所定义的绝对可信的文化身份认同,他们不愿接纳包括中国及其邻邦和其他古典文明在内的丰富图景,也不愿重视来自国外的学术研究,而更愿意频繁施展如下三种策略举动:其一,对国外学术迫不得已说些应酬话,实际上却几乎不予任何阅读;其二,拒绝学习任何外语;其三,对其他早期文化或是关于这些文化极具启发性的研究都不感兴趣。其结果就是形成一种防守性的、本土主义的、自我边缘化的、单语主义以及单一文化主义的学术。放眼未来,我认为这种学术是难以为继的,连下一代学人都不会接受。
柯氏所说的“单语主义”(monolingualism),意在批评一些中国学者只关注单一语言(即汉语)的研究,而忽视其他语言的研究成果。据柯氏所说,他要求自己的学生能够至少关注以中文、日文、英文、德文、法文等文字撰写的相关论著,不能因为无法直接阅读而忽视可资借鉴的前人成果。而柯氏所主编的国际权威汉学期刊《通报》(T’oung Pao),西方学者如若忽视中文和日文的参考文献、中国学者如若忽视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其文章便不可能会被采用。
中国学者自然不一定人人都要掌握多门外语,但对海外研究成果多一分了解,自然也便多一分知己知彼的成竹在胸。一方面,国际汉学研究很热闹;另一方面,我们对海外中国学的了解并非太多,而是太少。学问本无分东西,尽管中外学术范式存在差异,但如若彼此增进了解与对话,同声自可相应,异调亦可互为激荡。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6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