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四个子女眼中的一代宗师潘懋元

作为中国高教界的一代宗师,潘懋元先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桃李满天;作为子女的第一任老师,潘老先生也有建树,培养了四个合格的学生。
今年已是百岁华诞的潘老先生仍然坚持在带研究生,40年来,他一共培养出326名博士研究生和759名硕士研究生,先后走进233所大学,出席报告会331场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463篇,编著66部。
四个子女在不同领域取得的杰出成就,也是潘老先生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最佳诠释。老大潘凯伦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曾任厦门化工厂技术副厂长,是当年厦门化工系统两名高级工程师之一;老二潘世墨,毕业于厦门大学哲学系,曾任教育部三个专家委员会委员和福建省人民政府顾问,原厦门大学常务副校长;老三潘世平,毕业于厦门师范专科学校,曾任集美师范专科学校党委书记和厦门城市学院党委书记兼常务副校长;老四潘世建,曾任厦门路桥建设投资总公司总经理,省劳模,厦门市副市长、政协副主席。
在潘老先生百岁华诞之际,老二潘世墨自己动手撰写了一篇题为“儿女心目中的‘先生’”的文章,文中回忆了潘老先生的教子之道,很多言传身教在今天仍然适用。
原厦门大学常务副校长 潘世墨
我的父亲潘懋元先生百岁华诞之际,他的众多学生纷纷提笔,写出一篇篇“我和潘先生的故事”。每一个故事的细枝末节,每一位学生的真情流露,都深深地打动了我,多少往事涌上心头 ……
01 被“弄错”的一件事:子女与学生的关系

潘世墨与潘老先生。
在父亲的学生中间,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潘先生对待学生像子女,对待子女像学生”(后来有不同的表述,但是意思一样)。这句话源于1980年代。有一年除夕,父亲听说高教所有几位学生留校没回家,就邀他们到家里,一块围炉吃年饭。晚辈私下有微词,除夕应该是自家人的大团聚呀?我很理解父亲想法,上个世纪40年代初,父亲在內迁闽西长汀的厦门大学求学。家乡汕头沦陷,孤身一人,有家难归。老人家特别理解年轻人过年不能回家与亲人团聚的心情。在他心里,学生就像自己的子女一样。我这么一说,大家不觉点头称是。说完之后,我一闪念,那对待子女呢?就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爸爸对待子女就像学生一样。我们四姐弟更是深有同感。
“对待学生像子女,对待子女像学生” —— 30多年前的一句非常普通的话,流传开来,长久不息,足见其说得恰如其分,很得人心。
02 家庭教育的“秘诀”:“行不言之教”
今年,父亲整整一百岁,依然身体安康、思维敏捷、精神矍铄、谈吐自如。“古稀之年”的我们,在“期颐之年”的父亲面前,依然是孝顺的儿女,聆听教诲的学生。父亲总是说,自己的家庭教育没有什么秘诀,这并非谦虚,或者秘而不发。我的切身体会是,父亲的家教,如老子云:“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身教重于言教,言教言简意赅、有的放矢。“不言之教”这个道理,人所皆知,但是真正做到、做好,则非易事。

在1980年代之前,我们家庭的经济条件并不好。虽然父亲的工资比较高,但是一家6口,加上负担广东的祖父和江西的外婆,尤其母亲常年生病,病退后沉重的医疗费用,家庭日子过得十分拮据。我们从小就知道,每逢新学年开学,四个孩子的学杂费、课本费,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父亲想尽办法,向约稿单位预支稿费,或向同事借,不让子女被老师催缴而难堪。19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有一年临到年关,包括购买过年供应的肉票、鱼票的钱还没有着落,为难关头收到一笔讲课费18元,大家才松一口气。
当时国家照顾老讲师以上的知识分子,有个中灶食堂,午餐供应三五角钱一份的荤菜,也就是青菜带上几片猪肉、几块炸鱼等。父亲从来不在食堂用餐,而是让我们买回来,拌在大锅菜里全家共享。在我记忆中,我们从小就懂事,生活简朴。我们打小几乎全年打赤脚出门,我们的衣服多数是打过补丁的。我初中三年的数理化课本,都是姐姐用过的,虽然旧一点,也不错,提前知道课文重点、习题的答案。我做数学作业的草稿纸,是买印刷厂论斤称重裁剪下来的下脚料。艰苦朴素就是这样从小培养起来的。
平时,父亲相信孩子会努力读书,很少过问我们的学习情况,期末成绩册家长签名时,会做一个评价。他倒是经常检查每个月给各人的三五元零用钱是怎样花的。开始,我拿到钱,买零食没几天就花光了。父亲没有直接批评,而是提起他上小学时,家境贫困,中午饿肚子,省下午饭钱买书,落下胃病。现在三餐有保证,有没有比吃零食更应该花钱的地方?这让我们从小养成计划用钱的习惯。
有一回,我答应星期天帮助家里大扫除,出门后忘了,回家有点不好意思,却也无所谓。当时父亲没有说什么。过后,父亲给大家讲一个成语:轻诺寡信。这个成语至今不忘,更是牢记做人要讲信用的道理。
1977年年初,我在山区武平工作,登记结婚,分了喜糖,单位为我们开茶话会。回到厦门,父亲和我商量,我弟弟刚结婚办过酒席,我们在单位也举行过茶话会,是否不一定办酒席吧。我和爱人理解父亲,同意了。全家高高兴兴地围一大桌,有美酒,有佳肴,庆祝新成员加入。父亲送我爱人一块“上海牌”手表,还有200元大红包。
父亲给我们的另一个深刻印象就是勤奋上进、自爱自律。打从小看见他总是在忙,白天一早骑自行车上班的身影,深夜灯下伏案的背影。时至今日,仍然如此。这两三年父亲出门少了,在家里不外是三种状态,在书房看书报、写文章,在客厅与客人、学生交谈,在寝室小憩、闭目养神。
早年,父亲长期超负荷工作,有了知识分子的“职业病”,如神经衰弱、胃病,也与茶、烟、酒交上朋友。他迄今保持潮汕人的品茶嗜好,当然年纪越大喝得越寡淡。80岁过后,他抽烟频率递减,90岁过后,基本戒了,偶尔陪弟子吸一两支。早年家里备有酒,父亲习惯晚上工作疲劳时,独自小酌。后来不太喝了,怕影响工作。我曾问他,过去喝酒有没有喝醉过?父亲十分认真地回答,喝了多少年的酒,但是非常节制,从未喝醉过。此话一出口,我们默然无语,“从未喝醉过”,有几个人敢说?我们兄弟也喜杯中之物,通常都能控制酒量,但总有喝高的记录。饮酒而从不贪杯,多么强大的自制力啊!
邬大光教授是父亲的大弟子,与父亲共事多年,他总结先生的“保留节目”:“几十年如一日不论刮风下雨乃至台风不停课,学生交上来的作业或毕业论文字字修改包括标点符号,参加学术会议从不提前离席,听别人作报告永远做笔记,…… 这些保留节目的日积月累,则逐渐形成了不成文的家规、师规、院规,一位大家的做人育人文化”。
这种“不成文的家规”就是“不言之教”,它远远胜于喋喋不休、长篇大论的说教。
03 难忘的“记一件有意义的事”
1962年,我是厦门五中初中二年级学生。语文课布置一道命题作文:“记一件有意义的事”。我写的是除夕全家围炉吃年饭,那年,三年困难时期刚过,难得备有一桌丰盛的年饭。我们议论道,要是天天都过年就好了。父亲听后说,虽然现在物资供应紧张,很多东西凭票供应,只有过年过节才有,但比起解放前,好多了。父亲讲述旧社会穷苦人家过年如过鬼门关,很多人外出躲债,别说过年团聚吃饭了。我的班主任看了这篇作文,认为很有教育意义,就邀请父亲到学校,在小礼堂给初二年级7个班级全体学生做了一场关于新旧社会对比、忆苦思甜的报告。虽然差不多60年前的事情,当时礼堂的场景和自己的感受,我记忆犹新。这对于青少年的我,影响非常大。
父亲从小家境困难,生活窘迫,求学艰难,十个兄弟姐妹,七个因病早逝。他13岁时就在汕头《市民日报》发表文学作品赚取稿费,15岁时就走上讲台代兄上课。大学时代在当地中学兼职教书补贴生活。我陆陆续续了解父亲的身世之后,逐渐有了自己的奋斗方向。要像父亲那样,生活艰苦朴素,读书刻苦上进。我的中学时代每天上学,往返七、八公里路,都是步行,既锻炼身体,又省下的公交车费,主要用于购买课外书。每个学期的成绩单,基本都是5分。我在初二年级被评为全校三好学生,初三年级加入共青团。
青年时代的父亲,忧国忧民,富有正义感。七七事变之后,积极投身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青抗会”的抗日活动。新中国成立后,拥护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于1956年光荣加入共产党,是一位6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在父亲的影响、教育下,我们姐弟四人都能自觉要求进步,都是具有40年以上的党龄的共产党员,几十年来,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04 传承中华民族的美德:“兼爱”“尚贤”
父亲在平常谈话中,在他的《口述史》记载里,回顾自己成长的历程,无不得到贵人相助,感恩之情,溢于言表。上个世纪30年代,汕头时中中学杨雪立校长热心肠,当他了解到父亲学习成绩优异,家境困难,特批他从时中中学附小直升中学,学费减半,使父亲得以顺利完成学业。父亲经常给我们讲述陈嘉庚校主“毁家兴学”、萨本栋校长“舍身办校”、王亚南校长“广纳贤才”的故事。这些故事深深地打动我们,铭刻于心。

父亲在“指引我人生道路的教育系李培囿主任”一文中,深情地回忆恩师如何推荐他在长汀中学兼职兼课,既增长了实践经验,又提高了生活水平。以后又引荐他返母校任教兼厦大附小校长。我们还记得1950年代,逢年过节,父亲会带我们到大生里教工宿舍,给我们称呼为“李公公”的李培囿老人拜年。李老教授逝世后,父亲每年还都会登门看望师母丁老师。
“文革”后期,有一次,我陪父亲到鼓浪屿看望他亦师亦友的大学问家虞愚先生。虞老赋闲居家,食量大却消瘦得很,身体状况堪忧。堂堂一位蜚声海内外的大学者,却求医无门,查不出病因。父亲说,恐怕是甲亢,因为我们的一位邻居就是这个症状。后来,找医生一问,果然如此,对症下药,很快就好转了。父亲也常常登门拜访汪德耀、陈诗启等老先生。同样,春节过年,他会给退休的工友潮汕阿婆包个红包,老阿婆也会送我们一大块家乡年糕。教务处职员杨铮因交通事故不幸去世,时任教务处处长的父亲专门在校报《新厦大》写纪念文章,称赞他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在一块硕大的黑板上做好全校课程表的编排工作。
父亲在耄耋之年,几次到闽西武平访问,因为那是当年我们兄弟上山下乡的县城。有一回率领一大家子,翻山越岭几十公里,走进我们插队落户的山村邓坑,拜访村民,看看我们兄弟当年生活的地方。当年一家六口分别在四个地方,他特别挂记我们当知青能否过得了生活关、劳动关,总是来信鼓励我们,也有泼“冷水”。我下乡时买了一些常用的药剂,还有一本厚厚的《农村医生手册》,希望自学成才当个“赤脚医生”。有一次,一个村民的小孩半夜发高烧抽筋,他们敲门求我,我顾不了许多,给小孩打了一针退烧药,烧退没事了。村民感谢不尽,我也洋洋得意。父亲得悉后,来信告之,你不是医生,不可以随便给别人打针吃药。
父亲非常推崇墨子“兼爱”、“尚贤”的思想。“兼爱”的意义就是要求人们对别人的爱与对自己亲人的爱一视同仁,“尚贤”就是要尊重有德有才的人。他认为,这是做人的道理。故此,我出生时,他给我取名:“世墨”。“墨子”还伴随我走出国门:1988至1989年,我在前苏联莫斯科师范学院哲学所访问期间,我的指导老师阿.玛诺娃教授介绍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逻辑,顺带提到古印度逻辑(因明学)。我说还有古代中国逻辑,她却一无所知。为此,我写了一篇“略论古代中国逻辑”,主要介绍墨子的逻辑思想—墨辩逻辑。她看了以后,把这篇文章推荐在《哲学科学》(1991年11期)上发表,并收入她主编的《逻辑手册》里面。这部词典里的“墨辩逻辑”词条的下注:作者潘世墨。
我珍惜父亲给我所取的这个名字,这是我唯一的名字,且不说改名,连个别名、笔名都免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应当像父亲那样,身体力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的文化传统。
05 “周末学术沙龙”的魅力:师生平等交流
30年延绵不断,举办近800次的“周末学术沙龙”,曾获得教育部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这是父亲的研究生教育教学的模式,深受学生的欢迎,成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一道风景,一种风范。它最大的亮点是形成一个“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的学习环境,创造一个“相互学习,共同受益”教学效果。更加可贵的是,大家庭的温馨,学术的智慧,平等交流,心灵沟通。尤其是师长尊重学生,认真听取学生的意见。“周末学术沙龙”的魅力在于,不论从学识上还是从做人上,要平等待人的理念。“周末学术沙龙”演绎中国传统文化——“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韩愈语),并且与时俱进,赋予其新时代的内涵。
父亲在与子女在讨论一些理论问题时,也是平等的。有一回,在饭桌上,他忽然向我发问:“哲学的‘规律’概念是如何界定的?” 当年,作为哲学专业二年级学生的我,倒是立马背出来:“规律是事物之间的、内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联系,…… ”。显然,父亲不满足,又追问:“‘内在’就一定是‘内部’的吗?”我根据教科书的定义,坚持“‘内在的’当然就是‘内部的’。父亲有不同看法,但是没有直接反驳。过后,我了解,父亲提出“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理论,受到有些学者的质疑:“内在”就是在内部,那有“外部”的规律?为此,父亲在在进一步研究、思考中,广泛征求意见,包括刚刚接触哲学领域的儿子。之后,他认为,规律都是“内在的”,有本质与本质之间两种,一是本质,是“内部的”;一是两个本质,即本质之间,是 “外部的”。不要把“内在的”与“内部的”混在一起。规律是“内在的”,但是“内在的”可以是在“外部的”。这样就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理论得到学界的广泛的认可。前几天(7月13日),这个旧话重提。我认为,从哲学的视角看,相对于不同系统而言,“外部的”概念是相对的。父亲不同意这种说法,坚持“外部的”的也是“内在的”。父亲进一步发挥说,根据系统论的观点,系统与系统之间,要不断交流信息,才能发展,如果封闭起来,就发展不了。可能是对概念、范畴的理解有差异,也可能强调侧重点不同,我们保留各自的意见吧。
06 父亲的“金句”:“如果有来生,还是愿意做一名教师”
父亲热爱教育事业,热爱教师职业,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表达:“我一生最欣慰的是,我的名字排在教师的行列里”,“如果有来生,还是愿意做一名教师”,的确如此。父亲自15岁走上讲台,代兄上课始,八十五年如一日,一辈子躬耕在学校 —— 小学、中学到大学 —— 以教书育人为天职,以教师职业为最高荣誉。
1930年代中期,中学毕业后正式在家乡的乡村小学任教,1940年代初期,大学读书时在县城中学做兼课老师。新中国成立之初,父亲在厦门大学教育系讲授“教育概论”“中国教育史”“教育政策法令”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等课程。1950年代末期,在中文系、经济系开设“逻辑学”公共课, 1978年给恢复高考首届哲学系本科生讲授“形式逻辑”专业课。
在这里,说个“题外话”。我正是这个班级的学生,聆听父亲讲授“形式逻辑”,引发我对这门课程的兴趣。适逢1979年,全国掀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哲学命题的大讨论,我和几位同学凭借初学的哲学和逻辑学知识,积极参与讨论,而后形成一篇论文”试论在检验真理过程中逻辑证明与实践证明的辩证关系“,由系主任赵民老师推荐,发表在《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79年第1期)。大二学生能在学校顶级刊物发表论文,对我的激励是不言而喻的,从此与逻辑学终身“结缘”。
父亲在80年代中期逐步退出学校领导岗位,开始新的长征,专心致志、全身心地投入到高等教育学的教学、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之中。60岁至100岁的四十年里,作为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40年来,父亲一共培养(含间接培养)326名博士研究生和759名硕士研究生,弟子遍布全国各地。他先后走进233所大学,参加报告会331场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463篇,编著66部,不遗余力地为“高等教育学”鼓与呼。2001年至2019年的近20年,他以耄耋之年,亲力亲为,十余次带领博士团队,赴全国几十所大学实地调研、考察,帮助学校解决教育与教学上存在的问题。父亲在百岁生日临近之时,在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主持的“师说课改”公益讲坛的“云课堂”上开讲,做首场报告,与超过三万名的全国各地师生通过网络进行互动交流。如果没有坚定的目标、坚强的信念和坚韧的毅力,要做出这些成就,是难以想象的。
几十年来,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润物无声,我以父亲为榜样,在学系、学校担任教育管理工作的同时,始终坚持逻辑学的教学、研究工作,始终坚持给本科生上课,培养13名逻辑学、科学哲学的博士生和18名硕士生。
再说一个“题外话”。1952年9月,正在北师大读研究生二年级的父亲接到王亚南校长来信,希望他回到学校担负起教学和课程改革的重任,父亲欣然服从,中断学习返校。我有与父亲相似的经历。1996年,我担任校长助理时考取武汉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师从张巨青教授。我挤出时间,刻苦学习,完成全部课程,还获得武汉大学“李达奖学金”一等奖。2002年是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期限,我担任学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职务,还有本科生、研究生教学任务,职责所在,实在不能请假专心准备,又不想应付过关,只好放弃申请博士学位资格。
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首届大学生,毕业时父亲送我的贺礼是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逻辑学(黑格尔)》。他在扉页上写着“送给世墨:作为学习知识,毕业了;作为研究学问,刚开始。爸爸1982年1月”。我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
作为先生的弟子,吴岩在《我和潘先生的故事》中满怀深情地说:“我眼中的潘懋元先生:对国家来讲,他是一位杰出的当代社会科学家!对教育来讲,他是一位享誉世界的当代教育家!对我本人讲,他是影响我一生的经师人师恩师!”
作为先生的儿子,我在《我和潘先生的故事》中同样满怀激情地说:“父亲恩重如山,大爱无言!他是我们儿女终身受益的严父、良友、导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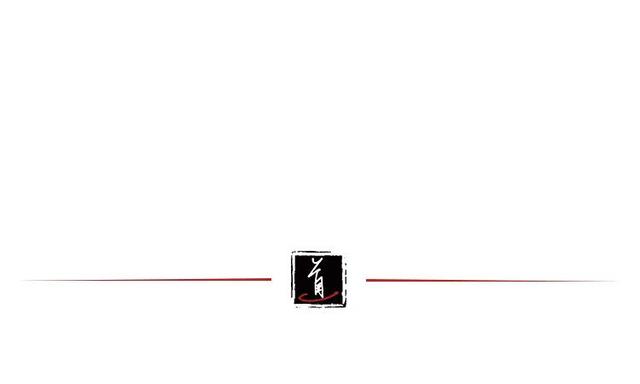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