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奇约录 | 华工禁令(上):三百年海禁里的黄皮肤“苦力”
文 | 江隐龙
作为世界上容纳度最高的语言之一,英语中向来不乏源于法语、德语甚至希腊语的舶来词。语言史背后是文化史,文化史背后是民族史,每当一种语言多一个舶来词,势必都会牵扯出两个甚至多个民族的交融与碰撞——语种的“血缘”越远、彼此渗入的舶来词越难以归化,民族之间的历史也往往越惨烈。
而“Coolie(苦力)”一词,无疑便是这种惨烈历史的代表。除了“Coolie”之外,苦力在英文中有多种拼写方式: Cooly、Kuli、Quli、Koelie……虽然这一单词因为其林林总总的拼写方式而漫漶了起源,但其含义却有着清晰的指向性,那便是以劳动来维持生活的廉价劳动力。“Coolie”很可能来自于汉语,就算抛开极其雷同的读音不谈,同一时代英语中也的确爆发式的出现了一批汉语的舶来词,如Kowtow(磕头)、Yamun(衙门)、Wonton(云吞)等。不过也有学者提出“Coolie”最早是德国博物学家恩格尔贝特·坎普弗尔用于形容日本码头工人的,而这位博物学家在抵达日本之前只去过波斯及印度而非中国。无论是那种说法,“Coolie”一词所代表的廉价劳动力都具有强烈的时间与地域属性:大航海时代之后逐渐被殖民、半殖民化的远东。
而中国人——或者说是清帝国的子民,无疑占据了苦力中的最大多数。在中国历史的语境上,它还有一个相对正式也相对中性的名称:Chinese Workers(华工)。毕竟,苦力一词难以登上大雅之堂,无论是清帝国,还是与强行与清帝国签订条约的列强均不愿意将苦力一词不加修饰地写在条文之中,正如在条约中,鸦片不会是“鸦片”而是“洋药”一样。
不过华工却不是一开始便如苦力一样带有贬义色彩的。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华工不仅代表了先进的技术、雄厚的实力以及高素质的人口,而且还真的在东南亚一带叱咤风云,甚至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事迹曾在梁启超所著的《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中被浓墨重彩地提及,在此且先按下不表;因为早在华工占据历史主流之前,从日本海到印度洋的广阔海域间还存在着另一强大的华人群体,那便是华人海盗集团。
如果说苦力的发展史要从华工身上寻找源头,那华工嬗变史便必须要从华人海盗史开始讲起。明清时代,除了多次海禁之外,对外贸易尽数为“钦定贸易”模式,其利润也完全由朝廷支配。但是,中国物产在海外需求量极大,尤其是丝绸、茶叶、火药等物利润极高,于是明清帝国东南沿海一带走私盛行。朝廷压制取缔益紧,走私商人便自行武装横行海上,成为海盗。走私产生巨大的收益给予了这些海盗强有力的经济支撑,于是一些海盗得以屯殖一方甚至建国称王。当时的中国代表着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生产力,这一批批华人海盗所谱写的海上史诗,足以与维京海盗或是加勒比海盗相媲美。
嘉靖年间(1522年至1566年),盘踞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的华人海盗渐渐分成徽州帮与福建帮,并最终被号称“五峰旗主”的汪直所统一。在汪直统治的全盛时期,整个东亚、东南亚海域的商船不悬挂“五峰旗”几乎不敢行驶——如果嘉靖帝是中华文化圈的大陆皇帝,那汪直便堪称海洋皇帝,甚至于日后成为明朝大患的“倭寇”,也多为汪直所率领的华人海盗,反倒是日本人占了少数。
明清易代之时,华人海盗势力逐渐衰落,相反东南沿海地区商业性的移民则逐渐增多,这其中客家人移民之风尤甚。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罗芳伯率领百余客家人移民至加里曼丹岛,不久便发展出了繁荣的殖民区。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罗芳伯取其与同族陈兰伯之名建立兰芳公司,次年建立兰芳共和国——这便是《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中提到的那个华人殖民共和国。
18世纪的华人以“殖民者”的身姿进入东南亚并不奇怪。虽然清朝中期已经渐显疲态,但清帝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在整个中华文化圈更具有着不可撼动的统治力。那时的华人如同古代日本的渡来人一般给落后的东南亚带来了先进文明的火种,华工一词自然也流露出浓浓的自豪感。那时称雄于东南亚的华人自然不会想到,仅仅一个世纪之后“华工”会与“苦力”二字混同,并成为“奴隶”富有东方特色的同义词。

明信片中的清朝苦力
海禁国策:新时代来临之前的华人殖民史
明朝与清朝前期,华人的确在东南亚地区叱咤风云,但这在安土重迁的中国人中毕竟不是主流。在传统的宗藩体系下,远离中原的东南亚介乎于外藩与化外之地之间,以至于出现了乾隆十八年(1753年)苏禄国向清廷上《请奉纳版图表文》请求并入中国版图而遭到乾隆帝拒绝的历史事件。一国之君尚且如此,其臣民轻视海外之心便可想而知了。
华人在海外的“开疆拓土”并未改变明朝清朝前期海禁政策的大趋势,如果不是欧美列强强行以战争打开了清帝国的海防,或许这个“天朝上国”的海外贸易会永远停留在广州十三行统治的时代。
陈仁锡所辑《皇明世法录》的卷七十五中详载,凡大明子民未经许可不得前往外洋各地;运货物出洋者将予以严惩;若走私牲畜铁器于军事用途、或运铜钱丝棉等物“接济外洋”者更要处以一百重杖……与此同时,有明一朝对于负责海禁之官员的立法也极为严苛,甚至禁止民间建造三桅以上的大型船只,由此也能了解华人海盗以及兰芳共和国的出现在中国历史上是多么小概率的事件了。
兴起于关外的清朝对海禁之事基本延续了明朝的律法,并有所增益。顺治十三年(1658年),尚未在中原立稳脚跟的顺治帝迅速下了一道海禁诏令:“凡有商民船只私自下海或盗寇通盗者,斩。货物充公,家产给奸告之人。该管文武官不能查获,俱革职从重治罪。”这道禁令看似针对于民间的走私活动,其实也是时局使然:当时南明小朝廷尚未完全灭亡,反清复明的势力以东南沿海为最盛,故在清廷眼中海禁是关乎国家存亡的大政方针,万万马虎不得。

苏禄国方位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收复台湾后立刻严禁闽粤二省人移民,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帝更进一步下旨“凡出洋久留者,该督行文外国,将留下之人,令其解回立斩”。雍正、乾隆年间,清廷或下令不允许这些“出洋久留者”回国,或直接将其视为“无赖流氓之民”,这一系列冷酷政策发展至极便是“红溪之役”。
乾隆五年(1740年),荷兰人于雅加达大肆屠杀华人,上万名华人在此役中罹难是为“红溪之役”。面对此惨案,时任两广总督的庆复居然如此上奏:“此类侨商乃违旨不听召回甘心久住之辈,在天朝本应正法,其在外生事被害,孽由自取。”朝廷视海外华人如弃子,海外华人又如何将大清视为母国?
在如此严苛的律令下,海外移民本应逐渐减少,为何在海禁最为严厉的乾隆时期却偏偏能出现包括兰芳共和国在内的一大批海外华人组织?因为朝廷律法在求生本能面前,从来都不是赢家。清朝前期,东南沿海地区屡遭战事,又兼天灾,百姓生计问题尚不能解决,自然甘于冒险至移民海外以解决温饱问题。对于东南亚地区来说,华人及华工能够带来先进的文明技术,故同样受到当地人的欢迎。随着岁月的流逝,移民于海外的华人积少成多,并渐渐在东南亚的政界商界占据了优势地位——如果不是鸦片战争之后世界局势逆转,东南亚在百年经营之后完全可能演变成另一个“小中华”,甚至可以在海外与清廷分庭抗礼。
然而东西方的碰撞终究还是来了,“红溪之役”只是这一历史碰撞微不足道的开场白而已。大航海时代将世界边成一体,以荷兰人为先驱的西方文明终于对远东地区祭起了屠刀。如果此时清帝国可以与海外华人合众一心,东西方的终极战争未必便会在几十年之后呈一边倒的态势。可惜在清廷眼中,这些“弃子”的价值甚至还不如荷兰商人,于是在西方殖民者与清廷的双重绞杀下,中国古代的海外移民终于消融于即将到来的血色时代。
也正是由此开始,“华工”一词风光不在,跟随着沉沦的清帝国渐渐成为苦力的同义词。可悲,可叹,当清帝国强大时,移民于海外的华人从未借到祖国的光;当清帝国衰亡时,这些华人却要共同背负祖国遭受的苦难。只是,历史不会给人留下太多喟叹的机会,新的时代开始了,曾经不被清迁认可的华工,终于出现在了清帝国正式的法律文件上。这一份文件,便是1860年签订的《外国招工章程十二条》。

乾隆接待英国使团
北京条约:打破华工出洋禁令的潘多拉魔盒
后世历史学家在审视晚清开华工出洋之禁时,大多以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为肇始。这两份《北京条约》均签订于咸丰十年(1860年)十月,其实在几个月前,时任两广总督的劳崇光便已经出具了一份《准许各国招工出洋照会》,同意欧美列强在广州城内外设公所招华工出洋,一个月后,又将招工地区拓展到了潮州。在潮州发布告示时,劳崇光也说明了开放招工的缘由:
“惟本部堂所属潮州府汕头妈屿一带地方,查得内地拐匪甚多,诱骗良民,私行贩卖。亦有外国船只,接受被拐华民,私运出洋之事。潮州现已经开港贸易,所有税饷,已派税务司在彼帮同办理……”
不难看出,劳崇光开放招工并非源于对海外贸易的肯定与支持,而是面对“内地拐匪甚多,诱骗良民,私行贩卖”现象的无奈之举。既然无力制止私招华工,那便不如将其合法化并通过律法加以限制。曾经居于宗藩体系金字塔顶端的天朝,曾经宁可放弃海外华工也不愿意开放海禁的清帝国,曾经雄踞整个西太平洋海域的华人海盗,在劳崇光做出这一份照会之时都已经成过眼云烟——自道光二十年(1840年)以来,中华文明的衰落已经不可避免,而“华工”一词也势必在这一衰落的进程中被推向人类食物链的最底层。
大航海与工业革命极大刺激了欧美列强对于工农业劳动力的需求,然而自1833年大英帝国解放了其领土中大部分黑奴以来,奴隶制在世界范围内的消亡使得欧美列强能够支配的劳动力越来越少,于是其眼光自然而然投射到了人口稠密而又落后迟钝的东方。早在嘉庆十五年(1810年),葡萄牙人便曾强掳了一百名清朝茶工至巴西做奴工,相似的事件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已不算罕见。然而,强掳华工毕竟是海盗行径,一方面每次行动均需顶着违法甚至与清帝国开战的压力,另一方面仅依靠强掳也远远不能满足列强对劳动力的需求,于是列强均期望清帝国能从法律层面开放华工出洋的禁令,以实现其招工的合法化与常态化。

《北京条约》签订现场
有需求便有市场。一方面是列强对廉价劳动力的巨大刚需,另一方面大量生活贫苦的华人也的确希望通过出洋打工求得生存,于是在双向需求的动作下,出现了劳崇光所言“内有拐匪诱骗、外有洋船私运”的残酷现实。
其实在劳崇光所处的时代,华工出洋现象虽然仍然为大清律法所禁止,但其规模已非嘉庆年间可比,而且多披上了“契约”的外衣。拐匪与洋商先以半强迫半欺骗的方式令华工签下契约,一经出洋之后这些华工便会遭受到不亚于奴隶的压榨。更为可悲的是,这里的“拐匪”其实包括一些清朝的地方大臣,比如劳崇光的前任两广总督柏贵早在咸丰九年(1859年)便私自赋予了英国招工公所招收华工的权利。同年,柏贵病逝于广州,劳崇光随即继任,并于翌年最终以通过照会的形式认可了列强招工的合法性——这个照会,是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
就在《准许各国招工出洋照会》做出的同年,清帝国分别与英国、法国签订了《北京条约》,正式以朝廷的名义取消了华工出洋的禁令,由此正式开启了晚清华工出洋的血色浪潮。这两份《北京条约》的相应条款如下:
中英《北京条约》第五款:“戊午年定约互换以后,大清大皇帝允于即日降谕各省督抚大吏,以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英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俱准与英民立约为凭,无论单身或愿携带家属一并赴通商各口,下英国船只,毫无禁阻。该省大吏亦宜时与大英钦差大臣查照各口地方情形,会定章程,为保全前项华工之意。”
中法《北京条约》第九款:“戊午年定约互换以后,大清大皇帝允于即日降谕各省督抚大吏,以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法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俱准与法民立约为凭,无论单身,或愿携家眷,一并赴通商各口,下法国船只,毫凭禁阻。该省大吏亦宜时与大法钦差大臣查照各口情形,会定章程,为保全前项华工之意。”
两份条约,两个条款,除国名外居然一字不差。可叹的是,条款中的“戊午年定约”所分别指向的两份文件也有着相同的名字,那便是咸丰八年(1858年)清帝国被迫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而签订条约的另一方,同样是英国与法国。

“奴隶船”上的华工
招工章程:清帝国对留洋华工态度的转变
如果说《南京条约》敲响了清帝国的丧钟,那《北京条约》则奏响了华工悲惨命运的哀乐。华工出洋的生活显然与条款中的“情甘出口”相左:这些名义上“自愿”的华工大多是来自清朝沿海省份的穷乡僻壤,在招工公所的强迫欺骗下,领着一笔预付薪酬踏上了海外。他们不知道,曾经的帆船早已变成了蒸汽轮船,这意味着海外中的“海”也不再是那些散落在大清帝国东南边界的小型水域——他们中的很多人会横跨整个太平洋来到拉丁美洲,而这其中又会有很多人在高强度的工作下客死异乡。
因为这些华工均有契约在身,故被称为契约劳工(Contract Laborers)。与此相伴而生的还有一些历史名词:苦力贸易(Coolie Trade)、负债劳工(Credit laborers)和猪仔贸易(Gigs Trade)。通过“猪仔”这一侮辱性极强的词语可以看出,华工虽然是契约劳工,不是奴隶却也近似奴隶。当然,与奴隶市场无异的“猪仔”客馆早在《北京条约》签订之前便已遍及东南亚,尤以新加坡、槟城为中心——“卖猪仔”一词早在道光七年(1827年)便被出现在了张心泰所著是《粤游小志》一书中,这一年,甚至比鸦片战争还早了整整十三年。
如果仅以华工的视角来审视这段历史,可能并不容易了解为什么柏贵与劳崇光前后两任两广总督会推进华工出洋的合法化;但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整个历史线条便豁然开朗:柏贵于咸丰七年(1857年)升任两广总督,劳崇光1859年升任两广总督,这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期间,而《北京条约》也正是这场战争带来的结果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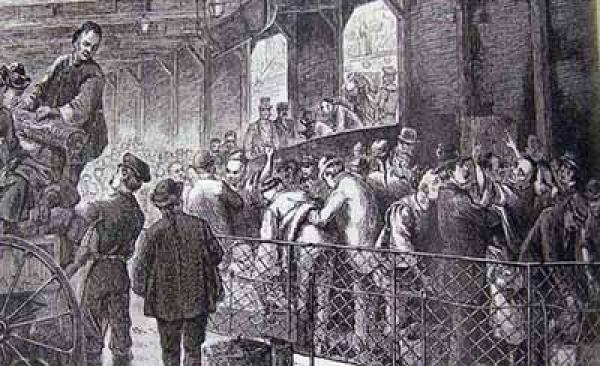
“卖猪仔”市场
如果说《北京条约》首次破除了华工出洋的禁令,那同治五年(1866年)清廷与英国、法国签订的《续定招工章程条约》便进一步以法律形式完善了关于华工出洋事务的具体细节。与《北京条约》中的丧权辱国不同,这一条约反而是对出洋华工的人道主义保护,如第十款规定“一日之内作工不过四时六刻……不准强其工作过时”;第十九款规定“运载客民之船……预备伙食、保其整洁,俱有定例”;第二十二款规定“夫妇不能分派两处作工,幼儿不及十五岁不准令其离父母”等,其规定甚至比华工在国内务工所受的待遇为优。
如果能严格执行,那《续定招工章程条约》便能在相当程度上保障华工“契约劳工”的身份,使其不会沦为事实上的奴隶。清廷与英法两国签订此条约后,同时照会欧美列强,声明若不符合《续定招工章程条约》22条规定则不许再招工,这其中也饱含着羸弱的清帝国在外交方面的努力。
对比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清廷对海外华人的不闻不问,这一努力态度的转化实在是殊为不易。事实上,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期美国便曾建议清廷派遣领事驻扎美国以保护其留美华人,当时代表清廷谈判的直隶总督谭廷襄竟如此回答:
“我大皇帝统御子民数万万,区区流徙海外之地的流浪之人,何足异哉!大皇帝之财宝富盈天下,区区流徙海外远离其家国的流民之财富,有何足惜!”
谭廷襄所代表的依然是清廷对待留洋华工的传统态度,不过很快,当清廷正式签订《北京条约》之后,如谭廷襄这样的士大夫阶层也不得不正视华工这一台面上的问题了。在谭廷襄说出这一番“豪言壮语”的七年之后,《续定招工章程条约》出台,这也意味清帝国终于在其“统御子民数万万”“财宝富盈天下”的迷梦中走出了一步,开始用心审视天朝上国此时的处境了。

保定直隶总督署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