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范晔、郑楠:复调世界:新世纪西语美洲文学二人谈
对谈人 / 范晔、郑楠(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葡语系)
我没读过波拉尼奥任何东西。——[墨西哥] 卡洛斯·富恩特斯
我(也)没读过波拉尼奥任何东西。——[阿根廷] 塞萨尔·艾拉
我不欠波拉尼奥任何东西。——[智利] 尼古拉斯·克鲁斯·巴尔迪维索
未来不是我们的。——[秘鲁] 迭戈·特雷列斯·帕斯
范晔:最近看见一本谈拉美艺术的书——Arte desde América Latina(《自拉美的艺术》),挺有意思。题目中用的前置词不是de,而是desde(西语含义是“自,来自”,作者特意用不同字体强调),不是拉美“的”艺术,而是自拉美(而出的)艺术,“拉美”不是限定语,而是语境设定之一。我们今天聊西语美洲文学,是不是也可以沿用类似的思路?毕竟从来就不存在某种单一的、同质化的“西语美洲文学”,或者说西语美洲文学永远是复数。
郑楠:desde这个介词用得太棒了。作为一个西语美洲研究者(hispanista),我个人特别关注作为前殖民地的美洲如何向前宗主国、从“边缘”向“中心”反向“投掷”本土的艺术文学——不知道脑海中为何会突然出现苏珊·梅塞拉斯(Susan Meiselas)的那幅摄影作品《莫洛托夫男人》(Molotov Man)!如何打破欧洲文明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中被视为弱者的美洲形象,这是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这种反向“投掷”,众所周知的有美洲现代主义诗歌,有“爆炸文学”,还有波拉尼奥。我还记得,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看到的古巴华裔画家林飞龙(Wifredo Lam)的画《丛林》(La Jungla),就将代表殖民经济的古巴甘蔗“投掷”到超现实主义的审美中。还有加西亚·洛尔迦(Federico García Lorca)在1930年访问哈瓦那,向当地文化圈推销西班牙黄金世纪文学时,被古巴混血诗人尼古拉斯·纪廉(Nicolás Guillén)的加勒比“颂诗”(son)“投掷”,然后创作了《诗人在纽约》中那首《古巴黑人的颂诗》(Son de negros en Cuba)。

Susan Meiselas摄影作品《莫洛托夫男人》(Molotov Man)。图片来源:Times
当然,还有新世纪西语美洲文学将各种源自旧大陆的审美范式和文学传统进行拉丁美洲化(latinoamericanizar)的戏仿和颠覆,比如,塞萨尔·艾拉(César Aira)的短篇集《音乐大脑》(El cerebro musical)——其中有一篇叫《杜尚在墨西哥》(Duchamp en México)的故事,阿尔瓦罗·恩里克(Álvaro Enrigue)将巴洛克精神拉美化的《突然死亡》(Muerte súbita),还有我个人十分欣赏的将哥特文学拉美化的阿根廷当代文学三女杰、新叙事代表——萨曼塔·施维伯林(Samanta Schweblin)和她的《吃鸟的女孩》(Pájaros en la boca),波拉· 奥洛伊萨拉克(Pola Oloixarac)和她的《野蛮理论》(Las teorías salvajes),以及玛丽安娜·恩里克斯(Mariana Enríquez)和她的《火中遗物》(Las cosas queperdimos en el fuego)。
范晔:《杜尚在墨西哥》是个好题目,古巴的佩德罗·胡安·古铁雷斯(Pedro JuanGutiérrez),那位“肮脏现实主义”的旗手,写过一本《我们的GG在哈瓦那》(Nuestro GG en La Habana, 2004)——GG是指格雷厄姆·格林。奥拉西奥· 卡斯特利亚诺斯·莫亚(Horacio CastellanosMoya)的《恶心》(El asco:Thomas Bernhard en San Salvador, 1997)的“副标题”是《伯恩哈德在危地马拉》……这倒是可以成为一个系列了。
我们今天对谈的“规定动作”是聊新世纪的西语美洲文学,不过实际上也很难绕开老故事,即所谓的“文学爆炸”。当代墨西哥文学代表作家之一的塞尔希奥·皮托尔(Sergio Pitol)在1992年的一篇文章里说自己读到文学评论家胡里奥·奥尔特加(Julio Ortega)开列的一份拉美当代作家的作品名单,对他而言,其中很多名字都是陌生的,于是感喟“爆炸”风光不再,拉美出现了一种内部隔离的情形,只有像奥尔特加这样在美国的大学里教书的专业人士才有条件做这样的“点将录”,而拉美作家自己反而不容易了解其他拉美国家作家的创作。以您对西语美洲(中)新生代作家的了解,这种情形是不是早已成为过去时?
郑楠:西语美洲各个国家的文学界彼此感到越来越陌生,这也许是因为“爆炸”后的西语美洲文学——不论站在文化商业运作,还是学术科研的角度——不再寻求自身在世界文学的“自主自治”。但“文学爆炸”之于西语美洲当代文学,就像美洲现代主义诗歌之于“爆炸”,不论后辈作家如何想摆脱这个庞大的阴影,阴影总会拖在他们身后,像一块巨大的幕布,这是他们文学成长和反抗的背景。博尔皮(Jorge Volpi)在《玻利瓦尔的失眠症》(Elinsomnio de Bolívar, 2009)的前言里提到自己读研究生时在萨拉曼卡住过的一段日子,他说,班上的拉美同学对彼此的国家一无所知,让他们产生绝对共鸣的是这么几个名字——博尔赫斯、米斯特拉尔、“爆炸一代”;但是对于同时代的年轻作家反而列举不出几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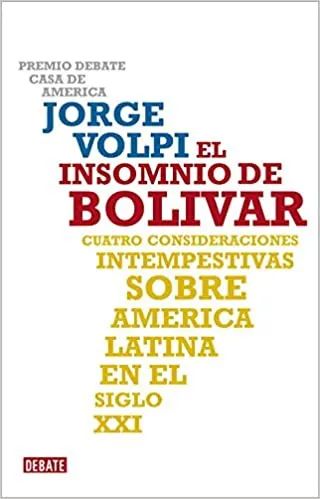
Elinsomnio de Bolívar
Jorge Volpi
DEBATE 2009-11
范晔:博尔皮对“未来文学考古学”颇有研究(此处有笑声)。他说,2055年有位美国学者发表了一篇论文,叫《拉美文学:2005—2055》,宣告拉美文学的覆灭。在他看来,这一悲剧的原因主要是拉美作家被全球化市场左右,追求一种国际化写作文体,有意抹除语言上的地域化特色。题材上也是,拉美作家不写拉美偏要写古希腊或纳粹德国——这里博尔皮拿自己开涮,想想他的《追寻克林索尔》(Enbusca de Klingsor, 1999)。谁说拉美作家一定得写拉美?博尔赫斯在《阿根廷作家与传统》中早就说得一清二楚。但这种国际范儿(estilo internacional)或许真的是个问题?
郑楠:这或许可以归结为一个无法得到明确答案,但我们一直在追问的问题——什么是拉美文学?关于这个问题,我想“本土范儿”和“国际范儿”之间其实并不存在一个明确分割或者二元论式的对立,不论是我们对21世纪西语美洲新文学动向的观察,还是追溯自殖民时期以来的西语美洲文学史,并试图做出某种关于“文明还是野蛮”的定论。因为,以真实或扭曲方式,或多或少投射到文学中的拉美民族身份(latinoamericanidad),是殖民和后殖民多元文化的产物,是永远流动的和模糊的,是“块茎”(rhizome)和永久的“生成”(becoming);西语美洲文学过去和现在都是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笔下那种“众声喧哗”(heteroglossia)的复调世界,不论是最具国际范儿的博尔赫斯,还是拥抱“土著主义”(indigenismo)的秘鲁作家何塞·玛丽亚·阿格达斯(José María Arguedas)。
这个复调,不仅仅指不同作品之间的差异,也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西语美洲文学永远是复数”,还包括此刻我更想强调的在一部个体作品内部因本土与世界对话/争吵/碰撞而诞生的众生喧哗感。比如,写纳粹德国的波拉尼奥,写安提戈涅的阿根廷女剧作家格里塞尔达·甘巴罗(Griselda Gambaro),写僵尸故事的波多黎各作家佩德罗·卡比亚(Pedro Cabiya),等等。我想,拉美文学不一定要写拉美,重要的是它是否有关拉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不论是纳粹德国、古希腊罗马神话还是美国大众文化中的僵尸,它们也许是爱丽丝的镜中世界(through the looking-glass)——我们无法想象这些白纸黑字所展现的、世界性的历史和文化话题与西语美洲有任何相关性,但它们是媒介,是脱离美洲语境却又紧紧围绕美洲的比拟和譬喻,是在文学中寻找拉美身份的工具。
我想暂时跳出西语美洲民族和文化身份多重性的文化研究视角,回归文学性(虽然绝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问题),来思考博尔皮作为“拉美新一代叙事”(Nueva Narrativa Latinoamericana)代表,对于全球化市场中的西语美洲文学定位的反思。我想请教您,“本土范儿”与“国际范儿”之间的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关乎“文学经典”(canon)和“经典化”(canonization)问题,以及文学新老一代交迭和派别斗争吗?
范晔:也关乎那个“北方的帝国”。就像“爆炸一代”中的何塞·多诺索(José Donoso)在《大象葬身之地》(Dondevana morir los elefantes, 1995)里借书中人物之口吐槽,美国人“要求”我们是野蛮的、暴力的,希望在我们的文学里看到革命、社会不公、独裁者、贫困、无知和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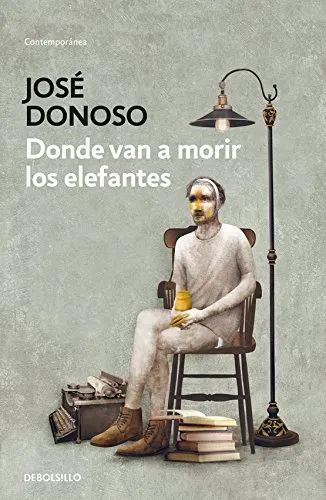
Dondevana morir los elefantes
José Donoso
DEBOLS!LLO 2017-9
其实博尔皮是想为真正的“国际风格”辩护,他认为文坛的民族主义者以前是指责世界主义者不够扎根祖国,现在则换了批判的语汇,说后者被全球化市场所裹挟。但所谓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本土与世界的二元对立是不是个“假问题”?这个古老的论争绕不开那位身材矮小却雄踞墨西哥知识界多年的文化巨人阿方索·雷耶斯(Alfonso Reyes),后世学者称他“为整个西方传统找到了拉美表达”。博尔皮还援引另一位墨西哥作家豪尔赫·奎斯塔(Jorge Cuesta)的友情提醒:以民族主义者自居的别忘了,民族主义这个词本身就是舶来品。
之前跟人聊天,我开玩笑说可以做一部拟声词拉美文学史:Boom、Crack、PAF……2019年我在诗歌节上碰到一个智利的年轻诗人,他是1985年出生的,比我还小。这是我们研究者遇到的新情况——以前都研究已经去世的人,现在开始研究比我小的人。他送了我一本诗集,名字叫PAF,这是一个拟声词。他们几个小伙伴搞了一个出版社,叫pornos,这个词有“情欲”的意思,但将其拆开,就成了por nos,又有“为我们”“凭借我们”的意思。因此,出版社的名字既是情欲的书写,又是为我们自己发声。他说自己是智利诗人,我还挺同情他的,在智利当一个诗人太不容易,有聂鲁达巨大的棺材一般的影子,两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都是诗人,还有帕拉……大诗人太多了。但他还是成功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全书主体的三个部分都以象声词为名:SHHHHH、CRASH、PAF。这里有明显的视觉文化、亚文化的影子。或许可以说,这是新一代写作者的特质之一?
郑楠:文学中的视觉文化,或者文学与视觉文化之间的共生、张力和“越界”(transgression),是让我感到十分兴奋的话题。在我读博士期间,我的导师开了一门研讨课——混合文本性(hybrid textualities):拉丁美洲文学中的文字与摄影——对我影响很深;在我开展的学术科研中,西语美洲文学和艺术作品中文字与影像(电影、摄影和绘画)之间的关系也是重点。说起在情节中出现摄影艺术的叙事作品,我们可以很快想到科塔萨尔的《魔鬼涎》(Las babas del diablo)及安东尼奥尼由其改编的电影《放大》(Blow-Up),波拉尼奥的《“小眼”席尔瓦》(El Ojo Silva),还有将奇幻题材和女性主义融合的阿根廷女作家安赫丽卡·格罗迪舍尔(Angélica Gorodischer)的《暗箱》(La cámara oscura, 2009)。关于人物肖像的长篇小说,则不得不提博尔赫斯生命中另一个“诺拉”——阿根廷先锋文学代表作家诺拉·兰赫(Norah Lange)的《两幅肖像画》(Los dos retratos , 1956)。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执导电影《放大》剧照
《暗箱》这个标题让我想到巴特(Roland Barthes)关于摄影的经典著作《明室》(Camera Lucida),《放大》里最经典的一幕——主人公突然发现照片中隐藏的谋杀案细节,就是巴特所说的那种突如其来、被摄影作品中某个令人不适或丑陋不合时宜的细节瞬间“刺中”(punctum)的感觉。我个人偏爱的、突出文学和视觉文化合作的西语美洲当代作品,都是因为我被瞬间“刺中”了。
另外,文学和视觉文化之间的合作也必须有趣而充满内在矛盾,图像绝不是文字的奴隶或为文字而生的插图(illustration)。这样的西语美洲文学作品太多了,而且非常棒。墨西哥怪才作家马里奥·贝亚丁(Mario Bellatín)(他的右手是个特别酷的钩子!)的虚构人物传记《志木长冈:一个被虚构的鼻子》(Shiki Nagaoka: unanariz de ficción, 2001)里加入了很多所谓志木长冈的照片(看不到鼻子)。智利女作家、反皮诺切特独裁的“集体艺术行动”(Colectivo Acciones de Arte)代表提亚梅拉·艾尔缇特(Diamela Eltit)与女摄影师帕斯· 艾拉苏利斯(Paz Errázuriz)合作的《灵魂梗塞》(Elinfarto del alma ,1994)特别令人动容,关注到首都圣地亚哥城郊一座疯人院中情侣的“疯狂”与“爱情”。我翻译的《牙齿的故事》(Lahistoriade mis dientes, 2013)一书的作者、墨西哥女作家瓦莱里娅·路易塞利(Valeria Luiselli)的很多作品中都配有摄影作品。比如,《牙齿的故事》中的照片是胡麦克斯(Jumex)果汁厂和艺术馆的工人照的,《牙齿的故事》也是献给工人的一部作品。关于绘画和文学之间的对话,我想到的是出生于英国,却被认为是墨西哥画家和作家的莱昂诺拉·卡灵顿(Leonora Carrington),她的艺术作品和文学作品有着共生共荣的互文关系。比如,画作《在下方》和传记小说《在下方》(Down Below, 1944);再比如,最著名的那幅独立宣言式的自画像《黎明马客栈》(Inn of the Dawn Horse)和短篇小说集《恐惧之屋》(The House of Fear, 1938)。在卡灵顿一百周年诞辰时,《纽约书评》出版了她的短篇小说全集以及刚才提到的《在下方》,推荐给大家看,惊悚而有趣。
范晔:古巴作家莱昂纳多·帕杜拉(Leonardo Padura)的《异教徒》(Herejes, 2013),厄瓜多尔的另一位莱昂纳多,莱昂纳多·瓦伦西亚(Leonardo Valencia)的《卡兹别克》(Kazbek, 2008)里都有绘画作品的元素。
郑楠:所以我想到的是,关于西语美洲文学研究,我们作为研究者十分有必要跳出所谓纯文学的圈子,多关注文学与其他审美表述方式之间的越界行为——“越界”和“边缘”是我在试图解读西语美洲文学和文化时的两个基本立足点(需要声明一点,这两个词在我看来完全是褒义词)。
这里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范老师:您翻译过很多西语美洲的诗歌和小说,您认为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这个语境下,诗歌和小说,哪种文体更具“拉美性”(latinoamericanidad)和边缘性?
范晔:这是个好问题,好到明显超出了我的知识储备和判断力。如果一定要说哪种文体更具“拉美性”及/或边缘性,我认为不是诗歌也不是小说,而是某(些)种无法归类的文体。这(些)种所谓的无法归类或抵制分类或消抹文体分别的文体,在拉美也有自己的传统。这里不可避免地又要提到博尔赫斯和他所尊崇的马塞多尼奥· 费尔南德斯(Macedonio Fernández)。后者有很多“作品”没有“成文”刊印,笔底明珠,闲抛闲掷,只存留在包括博尔赫斯在内的小圈子听众的记忆中。有文学史著者称博尔赫斯的作品都是“三位一体”的——既是诗歌又是短篇小说(cuento)也是散文(ensayo)。波拉尼奥的某些文本也属于这种情况,同时被收在诗集《未知大学》和短篇小说集里。他的不同文体的创作,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杂文和演讲,甚至访谈,都可以被视为一个整体(corpus),一个无法被分类的文体(la Obra),或者借用富恩特斯的书名——《拉美伟大小说》(La Gran Novela latinoamerica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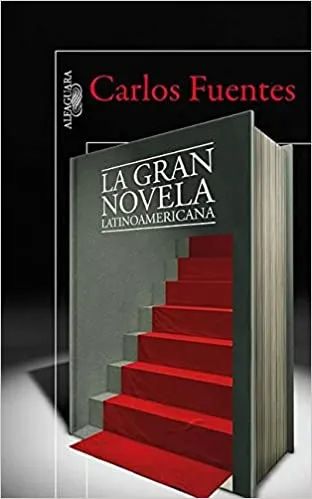
La Gran Novela latinoamericana
Carlos Fuentes
Alfaguara 2011-9
还有您刚才提到的艾拉,整个儿像是一架文学机器,他已经写了一百多本书,这让我想起贝亚丁(Mario Bellatin)在当代艺术项目《贝亚丁十万本》(Los cienmil libros de Bellatín)里说的,他不跟常人一样用年计算岁数,而是用写书的数目,比如“今年我一百零八本了”,这比说我多少岁酷多了。他那些平均一百页以内的小说,构成了一种独具一格的“艾拉体”。他也是文体急转弯的高手。一部看似是19世纪的旅行文学、潘帕斯气息的风俗主义小说,很快就露出了俨然哲学随笔的另一副面目,飞行的《野兔》(La liebre, 1991)后面闪现的是蒯因的影子,这野兔一会儿变成钻石,一会儿变成伊拉斯谟的单片眼镜,但最后还是不无恶趣味地回到肥皂剧的桥段,变成让亲人相认的私密胎记。
据说,博尔赫斯曾坦承自己的有些想法(脑洞)写成哲(玄)学论文怕没人看没人发,就伪装成小说。照这个策略,很多拉美作家的小说的“合法身份”也颇为可疑。很多“后《荒野侦探》时代”的侦探小说、黑色小说骨子里的都是元小说,或者按巴雷内切亚(Ana María Barrenechea)论博尔赫斯时的说法——“自我分析的叙事”(narración que seautoanaliza)。
乌拉圭作家马里奥 · 莱夫雷罗(MarioLevrero)的那本奇书《发光的小说》(La novela luminosa , 2005),2019年出了中译本,也可以看作是书写本身的不可能的小说,不是“伟大的小说”(中文里“小说”之“小”配上“伟大”之“大”,别有韵味),是“伟大的草稿”。博尔赫斯不是说自己的短篇作品都是不存在的长篇的梗概嘛,塞万提斯更号称自己的小说是从旧货市场买来然后请人翻译的……
继承“塞万提斯的遗产”,当代拉美小说里也不乏寻找失踪作家或神秘手稿的“标准件”,像智利作家塞尔希奥· 戈麦斯(Sergio Gómez)的《马里奥·瓦尔迪尼的文学作品》(Laobra literaria de Mario Valdini, 2003),墨西哥作家大卫·托斯卡纳(David Toscana)的《最后的读者》(El último lector, 2004)……对了,听说智利作家和电影导演阿尔韦托·富格特(Alberto Fuguet)有本小说偏偏叫《非虚构》 (Noficción, 2015)。
郑楠:富格特也挺逗的,2001年写了一篇叫《魔幻新自由主义》(Magical Neoliberalism)的文章,里面说,瞧,魔幻现实主义把拉美整个形象弄得太“可爱”(cute)了,但实际是“古怪”(weird)。
范晔:再说“越界”,咱们都是游戏爱好者,虽然这两年没时间拿起手柄战斗了……波拉尼奥的《第三帝国》(El Tercer Reich)里主人公玩的是二战桌游,到了艾拉的《万境游戏》(El juego de losmundos, 2000, 2019)里可就是异托邦时代的虚拟现实游戏了。智利作家卡洛斯· 拉贝(Carlos Labbé)更执着,他写一个挪威女孩逃亡到智利南端临近南极的艾森区,设计了一款叫《艾森》的电子游戏,每一章末尾都像游戏对话树一样让读者选择,这是21世纪“黑客帝国”版的《跳房子》。这位小说“黑客”拉贝——“作家必须成为语言的黑客”,以前的作品往往是电子版先行甚至只有电子版,大玩超链接、超文本与读者互动,发扬与读者“共谋”的科塔萨尔精神,在2014年出版的《对抗世界的秘密武器》(Piezas secretas contra elmundo)中,他索性把小说写成电玩文化批判启示录,认为电子游戏本来是一种潜力无穷的艺术形式,但被文化工业的单调思维模式绑架,充斥着暴力、男权,本该给玩家展现更多自由,反而被单一排他的世界观所辖制。他选择的是与20世纪的先锋派不同的路径,或者说反其道而行,抛弃个人主义。感觉他所谓的“集体小说”是想营造一种网游般的小说,以(超)文本建立新的共同体。
当然还有您研究的对象之一,智利的诺娜·费尔南德斯(Nona Fernández)的《宇宙侵略者》(Space Invaders, 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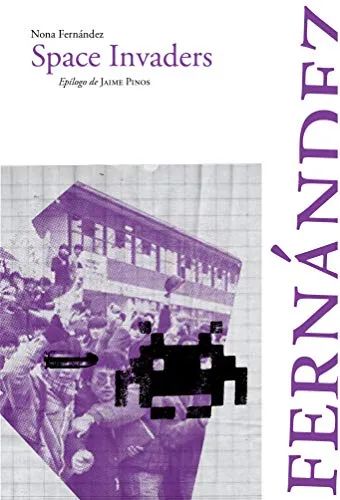
Space Invaders
Nona Fernández
Alquimia 2013-1
郑楠:《宇宙侵略者》这个名字来自小时候玩儿的经典红白机游戏,但是读了之后就知道,书中的童年是多么恐怖。这部小说,或者说费尔南德斯大部分有关独裁下和独裁后智利的作品——比如成名作《马波乔》(Mapocho, 2007),这也是我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让我个人有很大触动——往往关于不要遗忘历史,不要将历史的灰尘扫到地毯底下。这类作品近几年在智利和阿根廷出版了很多,比如,帕特里西奥·普隆(Patricio Pron)的《我父母的灵魂在雨中上升》(Elespíritude mis padres sigue subiendo en la lluvia, 2011),阿利亚·特拉普科·塞兰(Alia Trabucco Zerán)2019年被译成英语的《余数》(La resta, 2014),作品中那种对抗遗忘的文学力量都很触动人心。
范晔:那我们今天就结束在“对抗遗忘的文学”。就像阿根廷大诗人胡安·赫尔曼(Juan Gelman)说的:
……你是唯一的祖国
对抗遗忘的野兽。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6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