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猪与资本:人畜共患病的当下,审思工厂化农业
特洛伊·维特斯(Troy Vettese),环境史学者,哈佛大学Weatherhead Center博士后研究员。他与Drew Pendergrass的著作《半个地球的社会主义:拯救未来的宣言》(Half-Earth Socialism: A Manifesto to Save the Future)将于明年春季由Verso推出。原文载于2020年7月23日Boston Review,原文地址:http://bostonreview.net/class-inequality-science-nature/troy-vettese-pigs-and-capital。中译版首发于“它们想过什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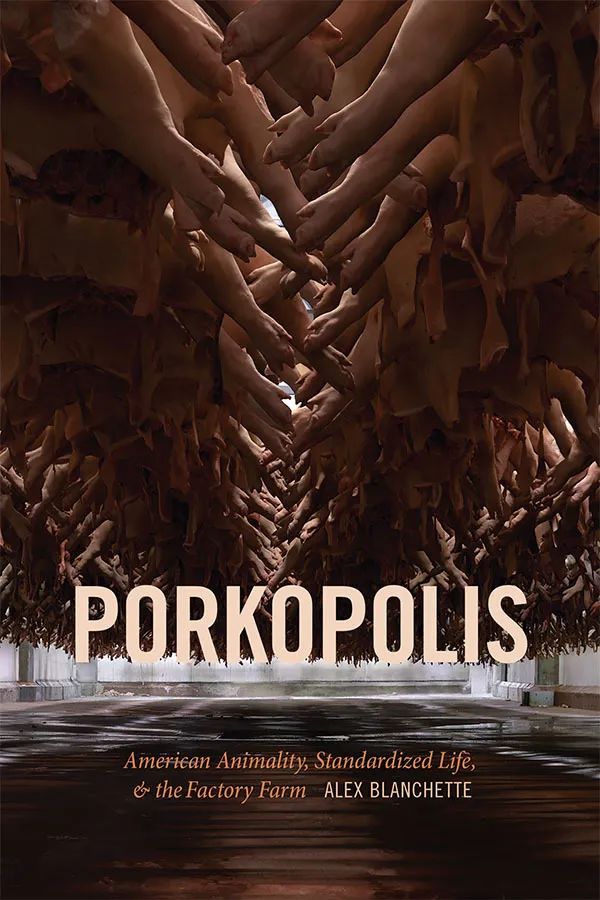
1.
“永远不要看猪的眼睛”,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手在准备人工授精母猪时告诉人类学家亚历克斯·布兰切特(Alex Blanchette)。“如果这动物认为你在看着它们,它们会僵住。”就像一个活的颠倒的全景敞视口(panopticon),成百上千只猪会从它们的圈中惊呆地注视要处理它们的工人。“它们的视力几乎达到360度”,一位前工人回忆道。“有时候它们看起来好像并没在看你……但如果你看它们的眼睛,就会发现它们一直跟着你。”
布兰切特对现代工厂化农场的民族志式新研究,《猪肉城邦:美国动物、标准化生命和工厂化农场》(Porkopolis: American Animality, Standardized Life, and the Factory Farm, Duke UP, 2020),在很多方面是对观看的沉思,或对我们没有看见的事物的沉思。我们通常很难发现肉工业的痕迹,无论是悬浮在空气中的粪便颗粒,还是弥漫于长期关押成千上万只动物在室内以加速生产的“集约养殖场”(concentrated feeding animal operations; CAFO)环境中的猪病原体。在1970年代末,集约养殖场仅占农场的一小部分,但现在却生产了美国绝大多数的肉蛋奶。布兰切特强调,他研究的工厂化农场不仅产猪肉,也生产用于凝胶药、黄色碳酸饮料、化妆品和计算机的原料。他告诉读者,这本书的封皮可能含有明胶,墨水和纸可能含有死猪。对此的感知还通过其他重要(即便更不物质)的方式影响了养猪业。行业负责人依靠来自全球市场的统计模型和价格信号不断地重塑他们的畜群。工人靠繁复的生物安全程序和鼓励闲时安全社交来预防流行病。猪肉工厂化农场预示了它所创造的未来和我们如今忍受的现在——一个为维持工业化动物榨取而被封锁的世界。
可怕的曝光事件与肉类产业本身一样古老,但布兰切特对丑闻写作不感兴趣。这一写作类型暗含着肉类产业是一个处在外部的隐秘处,或者可以通过自由化改革加以改善。这种模式下的著述常常徘徊于工业恐怖和素食主义禁欲间,最后到达小农场的安全港,但布兰切特在此也偏离了常规。他不相信田园浪漫主义在当下能为我们提供任何事物,这是政治经济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在一个世纪以前的见解。凡勃伦嘲笑“独立诗人农民”是“过时过去”的“残余”,并预测了其在“缺席地主所有制(absentee ownership)控制的晚期”的必然失败。凡勃伦还强调:“美国农民的案例很显著;尽管很难称其为独特。”布兰切特以类似的方式辨别到,肉类产业并非一个可怕的例外,而是一个当代资本主义的典型,哪怕它的极端情境使当下的趋势更为明显。肉类产业就像它所改变基因的猪的身体一样,已成为一个庞大而脆弱的野兽,濒临生态和经济崩溃的边缘。
布兰切特承认,他也曾经相信独立农民。他在安大略省西南部的一个“紧密联结的农业社区”长大,这个社区因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的故事而为人所知。作为一个年轻的研究生,他曾希望他的研究能让他看到他“童年的故土有一天能变成什么样,并向那些拒绝默许的人学习”。他很快意识到,在1990年代的“猪之役”(Hog Wars)中抵制集约养殖场向他们的城镇扩张的英雄已经消失、被击败或死亡。一些曾持不同观点者并不愿与布兰切特对话,因为他们在经济上仍然依靠以前的敌人来购买他们的农作物。他最接近采访的一次,是发现贴在一位前活动家门口的道歉信,以及一些旧的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的小册子和一张给他的5美元的油费。肉产业的愚众力量(agnotological power)遍布在全文,竭尽全力阻止光亮穿透它无知的面纱。读者不知道研究在哪儿进行;布兰切特称该城为迪克逊(Dixon),他所工作的畜牧公司以化名“多佛食品”(Dover Foods)和“伯金肉业”(Berkamp Meats)。考虑到这些障碍,《猪肉城邦》完成的清晰度和分析能力很是了得。这使布兰切特的全知视角引导着读者,如一个颠倒的维吉尔带领盲人穿越血腥的地狱一样带领读者穿过猪肉生产的各阶段。得知布兰切特的同行将他视作他这一代中最好的民族志研究者之一,也便不足为奇了。这本精巧组织的书所拥有的敏锐洞察和共情,令人想起门罗的短篇小说。
尽管大农业集团从外面看来不透明并不奇怪,但更引人注意的是,管理人员和工人自身也在努力理解他们的工作场所中复杂而零碎的运营。与其他资本主义产业一样,精神工作与身体工作间也存在差异。在多佛,管理人员的“工作”(work on)是他们称之为“畜群”(the Herd)的一个抽象概念,而员工则亲身与这些动物一起“工作”(work with)。管理人员以“统计、抽样、巡回检查或纸质表格”来产生定量的知识。一位负责监督一脉猪系的畜群经理向布兰切特解释说:“过去的养殖观念是管理个体的猪……但我们的观念是,我们管理畜群。”与其像传统农民那样偏爱任何一只具体的动物,多佛的政策是“定期淘汰和替换他们养殖的动物的遗传繁殖群……无论一只动物的历史如何。”但大多数管理者仍然缺乏概观视角,因为这样的视角在一排排畜群面前,在“活的”一端(养猪的地方)和“厂子”(屠宰猪的地方)之间,是分裂的。
工人阶级的知识看似来自直接接触,但也因劳动分工而碎片化。当布兰切特第一次站在快成年的猪圈旁时,他惊讶地发现自己是多么地不稳定。在与怀孕的母猪和仔猪呆了数月之后,他以为自己“知道如何很好地应对猪只”,但是工厂化农场的经验并不能运用于一只猪的整个生命周期。泰勒主义在“厂子”这端发展到极致,上千名工人沿着生产线刺杀,上钩,掏肠,切块。经过两个世纪的调试,专业化程度是如此普遍——对人体的压力也是如此巨大——而生产收益几乎没有增加。在这个高度碎片化的空间里,很少有工人能感觉到它巨大的工业规模,这里每三秒钟杀死一只猪。工人们悄声谈论机器将无数死仔猪碾成泥的“死屋”,以及杀戮层下面的房间,“据说会有人整日呆在那里……留意可能堵塞排血水的洞口的游离肉块。”
肉类产业的极端分工不仅意味着从每磅猪肉身上榨取额外的“一分钱”,也是为了保护公众健康。在公司之间和公司内部都设有卫生警戒线。同一个家庭的成员不能同时在活的一端和“厂子”一端工作。管理人员害怕流行病,这被委婉地称为“疾病事件”,它可能因为工人在闲余时间染上的污染物而引发。布兰切特解释说:“尽管有现场淋浴规定,猪的唾液、血液、粪便、精液或谷仓细菌的微粒仍可能留在工人的耳朵、指甲和鼻孔中。”在将猪的身体推至极限时,公司也创造了一个他们的工人“一起喝酒或在教堂长凳上祈祷”都可能带来问题的环境。这种繁复的程序——以及将人为错误,而非系统本身的过度复杂,作为要预防的问题——都使人想到核电站的高风险管理。布兰切特甚至在书中引用了核事故最重要的理论家查尔斯·佩罗(Charles Perrow)。猪肉产业的流行病管理也延伸到了白领工人。一位屠宰场经理感叹他在活的一端的同事对他而言只是电子表格中的名字,就跟抽象的畜群一样。最让布兰切特感到惊讶的是,“人们普遍没有太多抱怨,便适应了所规定的这种已工业化到丧失正常行为的动物的性质和需求。”
多佛唯一能完整看到畜群的人是执行官德鲁·柯林斯(Drew Collins)。他负责监督公司的纵向整合,“是唯一负责对猪从出生前到死亡后的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作深入生产计划的员工。”如果养猪户从前意味着从出生到宰杀都要饲养动物,那么柯林斯“就是这个体系中最后的农民。”他在中西部的乡村长大,但无力承担自行耕种,于是在多佛找了份工作。柯林斯用从管理工业化养殖得来的财富购买了一个小农场,近乎诗意地证明了支撑大规模肉类消费的幻想。正如凡勃伦所说,美国农民坚持“仍在继续说服自己,通过艰苦工作和精明管理可以获得“权能”;比如可以使他某天在缺席所有人的土地上占得他应有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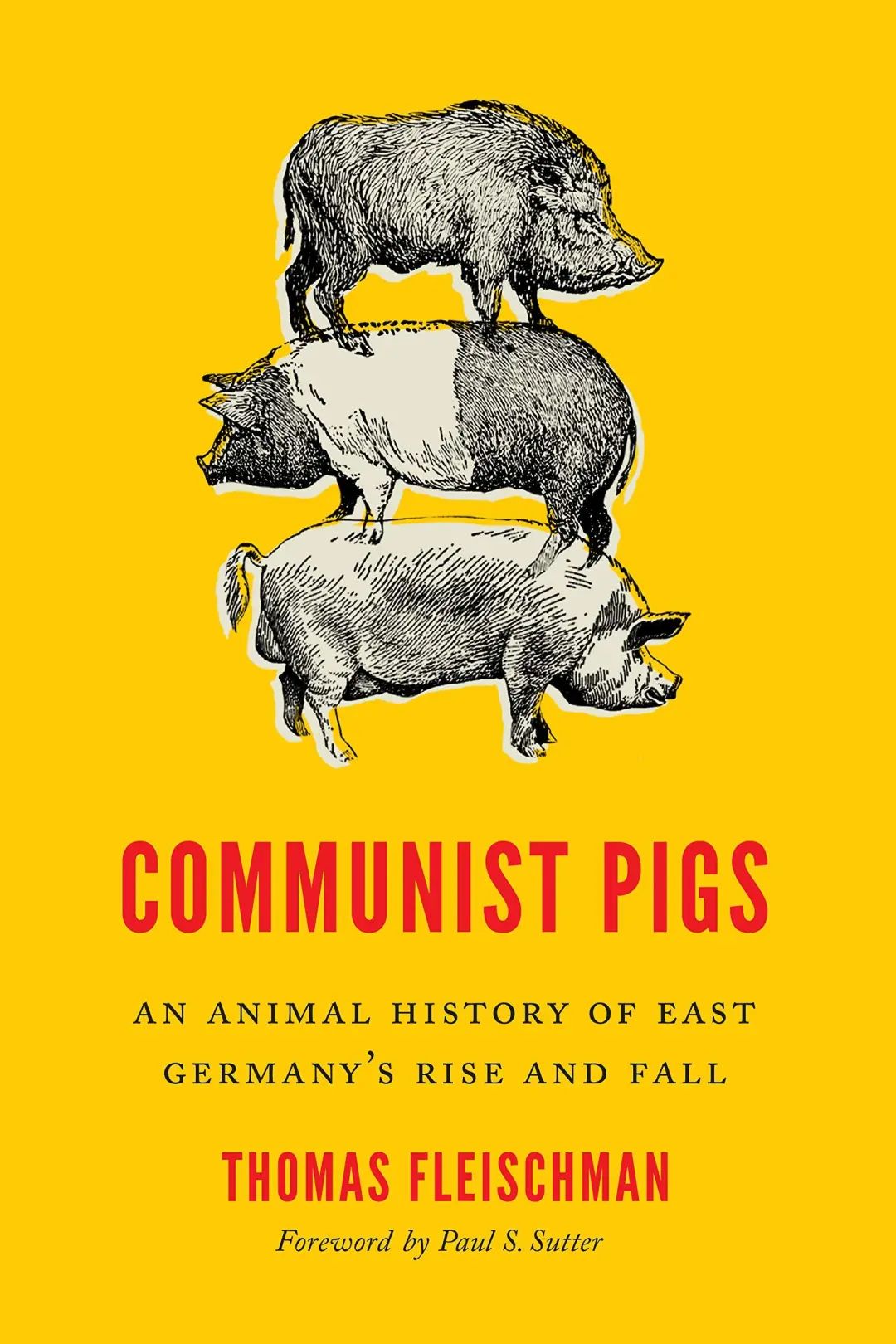
2.
环境史学家托马斯·弗莱施曼(Thomas Fleischman)的《Communist Pigs: An Animal History of East Germany’s Rise and Fall》(U of Washintong P, 2020)提供出一个与布兰切特的《猪肉城邦》相抗衡的有效叙述。弗莱施曼认为,东德的工业化猪肉产业表明,工厂化农场不是特定经济体系的结果,而是跨越了冷战分歧的“现代主义”冲动。毕竟,东德猪肉业饱受有毒猪粪湖和流行病的困扰,与我们现在在爱荷华州和北卡罗来纳州所看到的景象不仅是表面的相似。于是,这本书可被归于研究社会主义背景下如何运用资本主义技术的广泛文献中。比如,在《磁山》(Magnetic Mountain, 1995)中,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研究了苏联如何在当时的印第安纳州加里市先进铸造厂的启发下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Magnitogorsk)建立钢厂。前东欧集团的汽车通常是西方车型的仿制品;前东欧高官坐在司机开的ZIL-111上,这是1961年凯迪拉克弗利特伍德75的副本。然而,弗莱施曼不仅评论了前东欧集团的模仿,而且还断言前东欧集团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是资本主义。运用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1945)的文学构想,其中的猪首领变得跟被他们推翻的人类压迫者一样残酷和腐败,弗莱施曼以工厂化农场为例来展现前东欧集团的“国家资本主义”如何与资本主义融合,两者变得几乎“难以区分”。
尽管弗莱施曼并未深入展开有关“国家资本主义”的辩论,但从尾注中可以看到,这一思想来源自英国托洛茨基主义者托尼·克利夫(Tony Cliff)。他在1940年代提出了这一术语,将斯大林主义解释为一种经济模式,国家官僚机构扮演着缺席的资产阶级的角色。虽然国家社会主义缺乏赢利机制,但积累的驱力来自要与军事对手保持同步的需要。考虑到克利夫的概念对弗莱施曼该书的主要论点的重要性,可惜的是,弗莱施曼并未为读者提供更多关于这场辩论的背景,特别是当它代表了苏联历史学中的少数派观点。确实,有充分理由强调而不是淡化东德这样的社会主义经济体与其资本主义竞争者之间的差异。
弗莱施曼的这本书主要关于埃伯斯瓦尔德(Eberswalde)镇(“公猪林”),那里一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工业猪肉产业设施。引用东德规划人员自己的话,弗莱施曼解释说,在社会主义的头几十年里,他们寻求国家在食物上的自给自足,到1960年代,他们希望将东德从“进口地转变为出口地”,而工厂化农场被视为实现这一目标最可行的途径。东德规划人员需要一只能承受集约养殖场局促和恶劣卫生条件的“工业猪”,便转向南斯拉夫,那里的工厂化农场已经使用了耐受的美国品种。东德自己的家养猪仍然是田园动物,缺乏在工厂化农场里生存所需的足以存活到宰杀重量的“活力”。埃伯斯瓦尔德的建设在南斯拉夫的支持下始于1967年,结束于1970年代中期,一家西德咨询公司建造起了立即可用的屠宰场和加工厂时。最初,东德的赌注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尤其是在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货币管理崩溃之后。廉价的资金使规划者可以在全国各处大量借贷并扩展设施,到1981年,东德的猪肉生产超过了丹麦和英国——这是厉害的成就。在某段时期,还可以利用工厂化农场将外国谷物转换成出口猪肉,以偿还西方的贷款。然而,到1980年代初期,这个模式已受到一系列冲击:美国高幅度加息,两次流行病消除了大批东德畜群,国家的环保运动出现。
尽管前东德的“工业猪”的兴衰是弗莱施曼叙事的核心,但他也追随另外两只“猪”的命运,“花园猪”和野猪。前者是一种受欢迎的动物,由私人公民在其被分配的土地上照看。在这一点上,弗莱施曼热烈赞美了易北河东边的独立农场主,展示出了与工业猪相对立的健康猪。另一只猪是蓬乱尖牙的野猪(Sus scrofa),在1960年代依赖进口饲料的工厂化农场使得乡村可以退牧还林后,野猪数量激增。弗莱施曼该书里最有意思的人物是业余博物学家海因茨·梅恩哈特(Heinz Meynhardt),他自称是公猪的珍·古道尔(Jane Goodall)。梅恩哈特凭借纪录片、书籍和广播节目试图将野猪(Wildschwein)从“瘟疫”打造为本地魅力动物。尽管他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人们还是普遍鄙视这些猪,因为它们将疾病传播给家养猪并破坏了心爱的花园地。富有远见的生态学家梅恩哈特认识到,这些不愿看到的互动不是动物的过错,而是因人类对它们的栖息地所带来的退化造成。梅恩哈特以谦虚的态度,在被破坏的工业化乡村中,可代表更具生态思想的社会主义。
弗莱施曼有趣而睿智的研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猪肉产业是东德社会主义兴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有助于我们对前东欧集团的理解,以及对环境史本身的理解,弗莱施曼在铁幕另一边挑战了他的同行,更关心经济、动物和生命。冷战的历史学家也需要考虑弗莱施曼对东德的描述,将东德视作工业化农业中不稳定但强大的竞争者。它在将廉价进口谷物转换为猪肉和硬通货方面取得的早期成功,应该被理解为东柏林领导层的一个秘诀,意在将国家转变为一个能满足市民对消费主义美好生活需求的工业强国。虽然最后,过量的粪便堆积损害了农村,硝酸盐对国家饮用水的污染都促发了东德的环保运动——政权的掘墓人之一。
虽然弗莱施曼的这本书极富原创性,开拓了新的知识领域,但也重现了美国当代史学尤其是环境史学的某些缺陷。像这一领域的其他人一样,弗莱施曼的书细节丰富,以精彩的档案研究为基础,但其理论工具却不那么可靠。他含糊其词地谈及“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却未对二者作定义。他对奥威尔的敬佩是典型的只在研究中粗浅联系马克思主义的看法,甚至只是当其在此所涉主题是社会主义国家时才做此联系。这些理论上的决定导致了这本书值得存疑的结论,特别是其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没有有意义的区别的论点。弗莱施曼在智性上粗野的(risqué)姿态在美国历史学家中很流行。例如,凯特·布朗(Kate Brown)在对美苏钚工业城的研究《钚托邦:核家庭原子城市和美苏钚灾难》(Plutopia: Nuclear Families Atomic Cities, and the Great Soviet and American Plutonium Disasters, 2013)中也作了类似的论点。
在概括具体经济领域的表面现象时,在理念和经验两方面都需要谨慎。仅仅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移植了资本主义技术和方法,并不意味着它已经成为资本主义。毕竟,社会主义缺少资本主义的主要机制:失业、市场和利润。社会理论家克里斯托弗·亚瑟(Christopher Arthur)称国家社会主义为“没有发条的钟表”,它模仿资本主义的发展,但缺乏使资本能够充当“自我扩展的价值”的条件。弗莱施曼忽视了社会主义社会运转的驱力和约束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正如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在对苏联经济发展的研究《从农场到工厂:对苏联工业革命的重新诠释》(From Farm to Factory: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Soviet Industrial Revolution, 2003)中成功展现的那样。有充分理由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结构性差异会导致不同的环境结果。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社会主义国家通常更少汽车,拥有便利的公共交通,从而避免了城市蔓延与汽车尾气的困扰。然而,由于没有竞争压力,社会主义企业在资源和能源方面往往极其浪费。
工厂化农场也是如此,从弗莱施曼自己的证据中也可推导出这一点。与布兰切特研究的高效创新型企业相比,弗莱施曼的社会主义企业更加盲目,因为它们缺乏能指导他们决策的价格机制。东德国家规划委员会和农业部无法知道养猪业是否有利可图。规划者也没有承受得不断创新的压力,就像多佛食品公司的柯林斯所说的那样,“在猪中找到新的钱”。互相竞争的工厂管理者在饲料生产和囤积上的瓶颈意味着“工业猪”需要在户外觅食,被饲喂了不均衡的饮食,或无法达到理想的屠宰体重。社会主义经常试图复制资本主义,但它缺乏首先创造了集约养殖场的结构性条件。
这些观点可能看起来像学术上的争论,但在政治上也很重要。暗示社会主义注定要退化为资本主义,甚至再现其最丑陋的表现形式——工厂化农场,弗莱施曼也许会使读者质询超越今天的资本主义是否有任何意义。相比之下,布兰切特清楚地表明,资本的进步是深化对自然的奴役的代名词。弗莱施曼自己的研究迫使人们看到,无论新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以什么形式出现,模仿资本主义只会导致灾难。
3.
布兰切特和弗莱施曼的故事分开了三十年,肉类产业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也令人震惊。在布兰切特所研究的全球化、无情和高科技产业的比较下,埃伯斯瓦尔德显得很古朴。比如默克PG 600,一种用于准备为母猪授精的血清。它的主要成分是从母马的血液中收集的激素。在南美的“血液和木材种植园”,野马被定期捕获、授精和放行,仅仅是为了再次捕获它们来使它们流产,“被棕色长软管吸取后,只有70%骨瘦如柴的母马幸存下来。”收获后,荷尔蒙就会由像布兰切特这样的工人再注射入母猪,以重新设定它们的发情周期,缩短几天怀孕间隙的“无产量的日子”。卡尔·马克思可能写下“资本……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吸吮活劳动才有生命”,而布兰切特展示了,这在养殖业并不是一个比喻。
《猪肉城邦》的确显示了你可以诅咒工厂化农业的很多原因,但你不能称其为效率低下。企业对其经营状况看法不一,但对市场波动保持敏感,能够校准由数百万头猪的身体组成的上千种不同产品的化学成分。很难想象社会主义工厂化农场能够精细地管理如此庞大的业务。布兰切特惊讶地发现像多佛这样的公司没有将“成堆的骨头”送至垃圾场。正如迪克逊的卫生工程师向他解释的那样,“从这工厂里出来的真的没有什么还看起来像猪。或者,好吧……除非可能……有些血,但大多是油脂。”资本主义肉类产业可能会在钢丝上保持平衡,但是其社会主义的模仿者很快就会掉落在永远无法绷紧的绳索。但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公司不会倒下,正如COVID-19大流行所表明的那样。它们的高效率使公司的运作几乎无法有任何懈怠,这就能导致整个企业崩溃。随着越来越多的屠宰场工人在这一流行病热点地带染病,精心调校的机器无法运行,畜牧公司只能将数百万只动物“安乐死”。大流行带来了一个罕见的情境,全球肉类消费量下降,尽管只下降了3%。
尤其是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被人畜共患疾病困扰的世界中时,需要清楚地看到,跨物种团结对建立任何愿景下的公正社会都至关重要。产业的冷血精确——默克PG 600也许是一个最清晰的表述——使布兰切特得出结论:“提倡只是保留一部分事物不运作……拥有成为“没有效率”的生物的权利,已变成了激进观点。”换句话说,社会主义缺乏“发条”可能是它最大的优点。然而,回到独立农民不会是历史的终点。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在学会与其他生物(包括卑贱的猪)相共情之后,才能蓬勃发展。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在布兰切特出色而残酷的书中,也可以找到乐观的理由,他发现,工业化残忍还引发了无产阶级的关怀伦理。
这一伦理之所以出现,部分原因是这一产业将幼崽的平均大小催发得增加了一倍,导致了普遍的矮小化。如今不是五十只仔猪中有一只会虚弱得无法存活,而是几乎所有出生的猪都需要人工协助。(苏瑙拉·泰勒(Sunaura Taylor)在《重负之兽:动物与残疾解放》(Beasts of Burden: Animal and Disability Liberation, 2017)一书中深度分析了作为增加利润手段的驯养动物所获得的生命空间的日益狭窄)。在布兰切特的田野工作期间,他与罗宾一起喂养仔猪,罗宾是一位“熟练的对罕见身体和怪物的档案员”,能够照顾其他人无法养活的动物。她的技艺只能在工厂化农场里才能打磨,因为生产的仔猪数量是如此庞大;她的经历是照顾数十万只动物的结果。举个关于她的技艺秘密的例子,她可以用胶带制作肌体模型来支撑小猪的肌肉组织,使它迈出最初的步伐,有望存活一段时间。罗宾决心挽救每只猪,无论它看上去多么无望,即使她的努力只能让猪在被送往“厂子一端”之前多喘息几个月的时间。布兰切特并没有把她的努力视作非理性,而是看到了罗宾的行为是她自称的对她的照料者的“爱”,在工厂化农场所创造的条件下,“保持开放和适应动物生命的新表现形式的伦理实践”。
一天,布兰切特发现他的同事们在讨论如何处理一只怀孕的母猪,她子宫脱垂,阻塞了产道。工头弗朗西斯科向布兰切特解释说:“我们必须给她剖腹产,否则她的猪崽会死。”布兰切特和另外三名工人用力将母猪的腿固定住,另一名工人用螺栓枪顶住她的头,第六名工人,费利佩,躺在她旁边抓住螺栓刀。她被杀死的那一刻,费利佩疯狂地切辟出一条通向猪崽的口子。他浸泡在鲜血中,失去了对螺栓刀的控制,开始用双手撕开通往子宫的路径。弗朗西斯科在它们的母亲去世后大声数着秒数,费利佩抱出了第一只一动不动的猪崽。按照工厂在生死上的性别分工,布兰切特看到“女人们朝着猪崽的小嘴吹气,活动它们的前腿和后腿来使它们复苏,她们的手上全是母猪的血液。”最终,当第七个婴儿出来时,罗宾大喊:“它还活着!”一只猪崽开始在她手中蠕动:“在猪崽出现一丝生命迹象时,更多的欢呼声响起,欣慰之情漫延在走廊上。”这样的时刻暗示着新社会正等待在子宫内。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