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不红的歌手尹吾:我既不成功,也不自由
1994年,24岁的广西人尹吾背着吉他来到北京,北漂六年,他留下了一张已成传说的专辑《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次远行》。
这张专辑的制作阵容今天已经无法复制。吉他是超载乐队李延亮、眼镜蛇乐队肖楠,贝司是零点乐队王笑冬,鼓手是鲍家街43号赵牧阳,键盘是小柯、指南针乐队郭亮。
当年录音的时候,尹吾不好意思麻烦他们排练和编曲,都是在棚里现编现录,3天就录完了,发现问题时已经没钱再改。
他本来是麦田音乐力推的红白蓝之红。“白”是朴树,“蓝”是叶蓓,后来白和蓝成为校园民谣的代表人物,唯独尹吾没有“红”。
此后18年,他的人生与音乐无关,回到老家南宁专职炒股,股市浮沉让他的轻度抑郁症偶尔转为重度,严重时意识清醒,但身体僵在床上无法起身。
2018年,第一次给手机装上音乐APP的尹吾发现自己歌曲下面有上万条评论。于是,他决定上路巡演,回馈歌迷、拜访老友。
去年,尹吾和好友罗春阳背起吉他从南宁出发,走过了中国35个城市。
以下为尹吾自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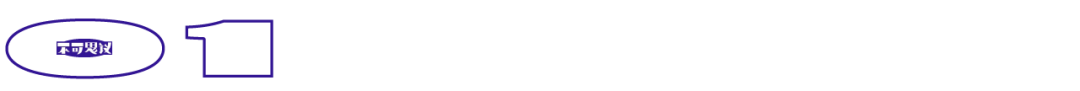
我母亲年轻时是地道的北京姑娘,家住大栅栏,同仁堂老店对面的胡同里。解放后,中专毕业的她被时代大潮卷到了两千公里远的广西南宁,遇到了刚从农村领了一身军装进城的我父亲,她在一所名叫东方红的医院生下了我。
24岁那年,我背着吉他到北京投靠在舅舅家,做了六年的音乐梦。
北漂回来后,炒股是我唯一成功的主业,我有很多年不主动听音乐了。两年多前,当年帮我代理出版实体唱片的新蜂音乐联系我,说网上的音乐开始正版化了,“有版税,你把钱收了”。
我也想了解互联网音乐到底是怎么回事,就装了那个APP,才发现有这么多的评论,而且看到丁磊给其中一首歌点过赞。
然后我就产生了一些想法。回家的这些年,我都不好意思管自己叫歌手,就叫作者吧,还陆陆续续有一点创作,突然间看到这么多听众,就录了几首歌传到上面,算是上线了所谓的第二张专辑。
我们这代创作者受六、七十年代美国很繁荣的那种音乐文化影响,我猜测跟中国现在有点像,因为有了一大批能够消费这些精神产品的市场和受众。二十年前,中国是没有这么多文艺青年的。
我是典型的小众文化作者,你要我去做纯娱乐我肯定不行的,完全不具备那个条件,朴树的东西才是雅俗共赏的。
突然间有了受众,我也想走出去看看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还有一个很大的因素是回馈歌迷。我本来以为那张二十年前的专辑已经淹没在尘埃里,很感动还有那么多朋友在听它,我就想到各地回馈他们一次。
巡演出发前,我受邀到漓江边举行的一个诗会演唱,嘉宾是我的偶像北岛,我有很多歌都用了他的诗。
那天上午,我满仓又加了杠杆的一个股票开始跌停,后来渐渐跌到不斩仓就要破产的地步,就在我隔了十八年再次登台的日子。
最后一幅压轴的是北岛非常著名的那句诗,我想每一个认识中文的文艺青年都知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虽然白天有一个跌停板,但我觉得拍下来应该没什么问题,我就抢拍了。当时不知道一块儿抢拍的还有很多知名企业家,最后落锤价是12万5,我抢到了,还挺高兴的,付了4万定金,北岛老师帮我签了名。

< 尹吾与诗人北岛 >
到了第二天,我的几个股票连续跌停,钱都取不出来。我跟北岛那边的代理人说,股票跌没了,我去演出,可能有些收入来付尾款。他们人挺好,出现这样的情况按行规拍品卖给别人,定金也拿不回来,但人家还是把定金退给我了。

2019年过了大年初八开始巡演,因为我的吉他太烂了,必须要有弹得很好的乐手跟我合作,就请了我们南宁民谣的扛把子罗春阳老师一起合作。他的“新东西”民谣酒吧开了24年,跟成都的小酒馆历史一样长。
我们俩经常在他酒吧对面的路边摊嗦粉撸串,去年还录了一首歌的视频,那天正好没有城管。
第一站是昆明,一上来先走的长江以南地区。路上还是挺单调的,我不爱东转西转,春阳喜欢旅游,很兴奋地到处去走。

< 尹吾和罗春阳 >
对我来说,国家这三四十年的城市化、工业化,它带来了物质的极大丰富,前提是很多地方都标准化了,你到任何一个车站或机场,都分辨不出是哪个城市的。走到街上,所有的道路也都是标准化的,人们的衣着也都一样,所以在路上我都会待在住的地方,把脑子里想表达的东西写出来,完成了几首歌。
在成都那场给我很大触动,首先我没想到能来那么多人,几十最多上百人的场地来了三百人,整个酒吧挤满了人。
演出结束后是我的专辑签售会,有一个长相普通的女孩,打开专辑说你帮我写几个字:我既不成功,也不自由。
这是我那首《好了好了》的歌词,我一边写她一边对我说:“30岁之前,我还想去争取一下,现在什么都无所谓了。”

< 尹吾在签名 >
当时排队的人很多,我只想快点儿签完,但是在她说这句话的一瞬间,我马上就感到了灵魂跟灵魂的对接,我知道她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但后面人很多,我连“你等我一下,咱们多聊一会儿”都没来得及说。
一个30岁刚过的女孩子没有打扮素颜前来,还说自己什么都不在乎了,作为资深的抑郁症患者,我太了解这种状态了,就是没有希望,活着也行,死了也行。
签完后我马上在现场找她,当然不在了,再走出大门看,晚上的大街也是空空荡荡的,这是我巡演路上最大的一个遗憾。
还有一场印象比较深的是在上海,那天也是满场到不能再进人了,观众里至少有两三对是带着孩子来的,孩子很小,大概四五岁这个阶段。
在台上时我没有注意到,因为我必须集中注意力唱好每一首歌,包括把每一句衔接的台词说好。完了之后我才放松下来,看到一个大老爷们在台下不停地哭,抱在怀里的孩子已经睡着了,演完他就走了,没过来跟我打招呼。
另外一对带着女儿来的父母给了我他们亲手写的信。这位父亲有点义愤,他觉得现在年轻人听不懂这样的歌。旁边的母亲说他们去各个国家游历过,曾经去法国专门看过肖邦的墓。其他的墓历经几百年都凋敝了,没有人去护理,但肖邦的墓每天都有气球、鲜花、蜡烛。
我明白她的意思,觉得过于谬赞了,真是这样我就死得瞑目了。
这对夫妻是从国外回来创业的,在合肥那场还有中科大的物理学博士,我发现我的听众群学历普遍不低,这是让我感到非常光荣的一件事情,他们不畏负担带孩子来听我的歌,也是想让孩子知道还有这种音乐,这种传承式的认可也让我感到压力,觉得自己有愧于这种偏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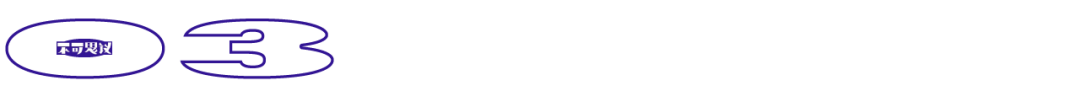
走了15个城市后,我家里有事回了趟南宁,虽然路上各种磕磕绊绊,总算完成了南方的巡演。5月份,我们去参加了3个音乐节,在惠州沙头角的海滩上,我突然不想再继续往下走了。
我不是一个享受舞台的人,真正让我感到兴奋的是创作完成的时刻。我到现在还记得,当年写完《各人》这首歌时,我激动得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这个状态持续了几天的时间,我觉得写到位了。
但是到了观众付费,我上台表演的时候,就浑身不自在,我得非常努力地强迫自己把那些规定动作完成下来,压力巨大。我知道有一些艺人非常享受舞台上的状态,他们不上台还不舒服或者不自在,我是能远离舞台就远离舞台。

< 尹吾在路上 >
这回巡演的主题是“生于中国、走遍中国”,《生于中国》是我纪念母亲的一首作品,发布后也投入了相当的时间和金钱去推广,但效果离我的预期差距很大,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
春阳不这么看,他认为不能用流量多少来评价这首歌的价值,虽然很小众,但它绝对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一首悲怆却振聋发聩的史诗级作品。
没有商业价值、无法变现的“史诗”。
在家的日子,那种让我动弹不了的失败感又回来了。北漂回来这些年炒股赚钱的时候,我有过几次创业的经历,做过儿童音乐教育、草莓种植园……一句话,到现在都失败了。
失败的过程很挣扎,因为它不停地往失败的方向滑行,不停地往死亡的方向滑行,不停地去做努力让它不要死不要死,到最后你发现,还是没办法控制住命运的节奏,这可能就是我抑郁症的来源。
我最受欢迎的一首歌是《你笑着流出了泪》,写这首歌的时候也处于抑郁的状态,只是当时并不知道。我最早听到抑郁症这个词还是跟朴树聊天,他在高中退学后就需要服药,我那时还开玩笑地跟他说,“长这么帅还抑郁。”
那年我签了高晓松、宋柯成立的麦田音乐,但一直没钱把专辑做出来,我就一天天地焦虑等待。那会儿我在北大西门租房,一天中午在北大食堂排队打饭的时候,突然想到了几句歌词,我怕吃完饭忘了,就骑着车返回出租的小屋,一边记一边拿着吉他唱了出来。
我知道很多有抑郁症状的朋友都喜欢这首歌,里面传唱最广的歌词是“走他妈再长的路,还不是通向坟墓”,它唱出了一个人的终极命运。

< 巡演到石家庄 >
有一回,一个黑龙江读大学的广西女孩儿加微信跟我说,这首歌陪她度过了一段很难捱的日子,她曾把医生开的几个疗程的药,一下子全吃了,醒来人已经在医院里。
我告诉她,“让生活有意义,是最好的治愈。”她爽快地答应了我,还建了一个歌单,普通人听着很灰暗的音乐,但是能够给抑郁症患者在发病时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8月初的一天,我对春阳说,“咱们还是按计划完成剩下的巡演吧,做完,这事就算了了。”
春阳有点惊讶,说了一句,“这屁放了肯定收不回,好吧。”
于是,我们俩又上路了,1个半月里走完了北方14城,有天深夜为了买便宜的机票,我们转道赣州坐了几个小时的飞机,跨越3400公里到达最北的哈尔滨。
有人问我,20年后再唱起那些老歌,跟20年前的感受有何不同?我的回答是,没有。如果一首歌引起了一个群体的共鸣,不管过了二十年还是二百年,它最动人的点都不会变。
我不是一个追星的人,我会感受鸡蛋,但不会去看那个下蛋的鸡长什么样。不过,当我在旅途中真的见到了自己的偶像北岛和芒克时,也会觉得有点兴奋。芒克已是一头白发,北岛还很精神,不知道头发染没染。

< 当年的高晓松与尹吾 >
北岛、芒克、崔健那一代人是我的精神启蒙,我觉得人的情感就应该这样说出来、唱出来,不管是不是被官方认可。
二十年前,我在出租屋写歌的日子,心里总会出现一句话:语言的尽头,是音乐响起的地方。
-END-
口述 | 尹吾
撰文 | 成斌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6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