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失能失智以后的人生,是否还值得活?|翻翻书·书评

“病房里,被科长认为活得没多少意思的老人们,却还在千方百计地活着,哪怕像植物人似的活着。”
2012年作者薛舒的父亲确诊阿尔茨海默病,而后三年时间里,父亲从失忆,发展到失智、失能,最后,在2015年的春天,因失能被送去了一所小镇医院。
在这所被称为“临终医院”的病房里,有二十六张病床,除了阿尔茨海默病人,有的因为中风、脑溢血而导致瘫痪,还有少数癌症晚期病人……他们都在这里等待着生命最后的归期。
薛舒父亲的病房里有四名病人:6 号床已经九十岁,心梗、脑梗、痴呆;7号床就是我的父亲老薛,阿尔茨海默症,正亦步亦趋地走在丧失所有功能的路上;8号床年龄最小,七十二岁,脑溢血抢救过来,成了一个整天打呼噜的人,睡着时打,醒着时也打;9号床八十五岁,中风,除了不能下地,恢复得不错,能简单对话。
作者还是一个青少年的时候,总认为,每个人天然都有“尊严”的意识,却从未想过,当生存遭到怎样的威胁时,人类才会放下尊严?在临终医院,老人们过着这样的生活:被捆绑在床上的日子,被打成浆糊的餐食,被打屁股的警示,被护工挑来拣去的去人化。
老人以一具肉身的存在,给予我们精神上的抚慰。而我们已然遗忘了某种质疑,他痛苦吗?他有没有感到生不如死?他是否愿意持续经受疾病的折磨,只为活着?
此前,我们发起了「一个有阿尔茨海默病人的家庭,会经历些什么?|翻翻书·送书」的征集活动,最后选出三位读者寄送了《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的样书。十天后,三位读者都已经阅读完,并写下了他们对这本书的理解和看法,以下是他们的书评。
在这部作品里,薛舒讲述了父亲完全失去自理能力、住进临终病房后的五年时光,这五年里,父亲从精神上的告别走到了生命的终结。同时,她也将目光从父亲个体、家庭内部转移到更广大的社会图景,生动地讲述了鲜少被留意的医院护工的生活,描述了病房中其他病人和家庭相似但也不同的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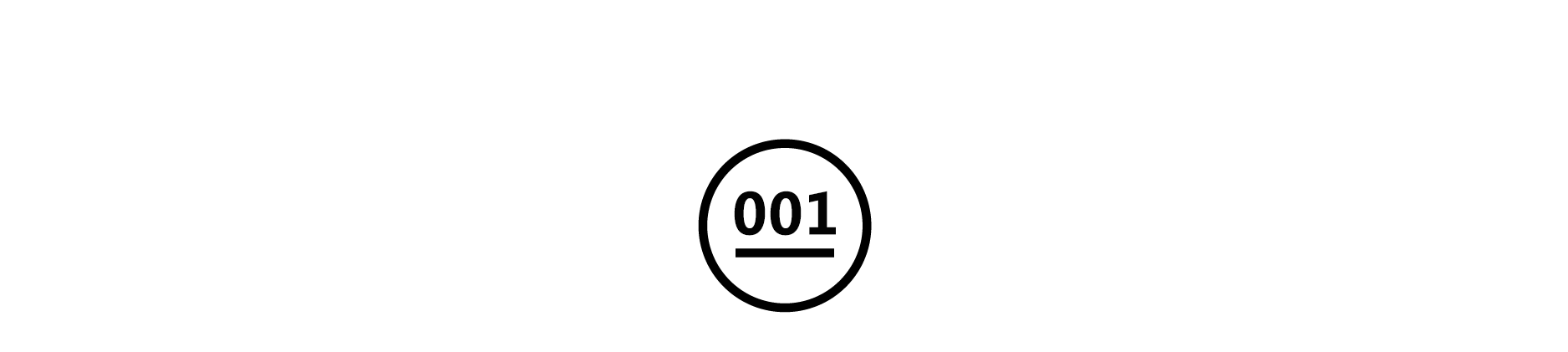
关于告别,不止静穆
文/李百川
刻板印象中,「临终医院」常常与「养老机构」并行,内嵌在失能者家属不愿托付于此的游说和抱怨中。仿似竖放的棺木,大方而静穆地迎接进入生命终尾的告别者。而这本书完全打破了我对于场景和人物的既定想象。那些交织记录的人物故事,带我在关于临终照护的社会图景上,踏上来,又跨过去。
作者强大的记录和探寻能力像一处镜头,完整还原了两所微小而悠远的临终医院生态。在这些促狭的空间里,不仅记录了生命的离去,更描绘了关于失能照护和告别的真实底貌。无论是曹镇社区卫生院的27张病床,还是安平医院的6张病床,都床位炙手,等位遥遥,生死交接。在这里,老者们的称谓随之转变为床号或是各自具备代表性的符号。他们有的吝啬,有的自负,有的荒诞,有的清醒。虽然进食和自理方式都以缴械的姿势交出了他们大部分的自持,但在混沌状态下依旧鲜明的性格底色却不断抗衡着死亡的苍白,意外地衬得他们每一位都如此无畏。由此,「吵闹」成为了一种「平常」,用来对抗静穆和肃杀。而寄生于他们背后的,是一组组家庭和护工们共襄的照护故事。

家属对护工的防备和信任程度不一,但在亲临病人的矛盾感受上,他们又是具备共时性的:混沌而倔强的病患会成为家属眼中“狡猾还耍赖的孩子”而被短暂厌弃,一如护工小彭疾言怒色地抄起一小根短棍的鼎沸呵斥。还有敏感和在意,家属们探望时所带的羊肉和未打碎的红烧肉,一如护工也会纠结于一个水果带给老人的临终遗憾。那些穿梭于唇齿间的,带有传说色彩的“升天”说辞和惯常的琐碎闲话,成为了一种纽带,让病房的场域得以延伸。以一种仿似邻里的生气,不断冲刷着告别之为告别的未知、凶险和沉重。
这是一本鲜活的临终照护非虚构,也是一部丰富的临终医院民族志。它以实证的效力给人一种直面告别和选择临终专业照护的勇气。毕竟,故事并非想象中的冷硬。从那些微小的线索中:患者嘴唇的干裂程度、未绑缚双手所及之处的皮肤肤质、尿袋的重量和尿液的色泽,都有迹可循地捍卫着道义互惠的在场,也让社会学中关于离世扫描的推演和构建落下了普适的一步。
在通往明天的路上,我们终会遇到临终告别这一无可回避的时日。而在背后,能激发并形成自我保护机制的,仍旧是那些沉浮在彼此之间的闪光回忆。

这恐怕是最美丽的「存在的意义」
文/席林
一口气连续翻完了《当父亲把我忘记》和《生活在临终医院》。尽管有在脑科医院工作的背景,对Dementia(失智症,阿尔兹海默症只是失智症的一种)并不陌生。但是真正从患者家属的角度事无巨细去了解这一切:当你爱的人因为疾病心性大变、逐渐地把家人、甚至自己都忘记,这才切实体会到“失能失智”这四个字的无法承受之重。
因为《当父亲把我忘记》的叙事铺垫,第二部《生活在临终医院》里描写的故事,和我所期待的有些不同。我第一次了解 “安宁疗护”的概念是在2023年“死亡是温暖的”主题峰会上。当时的一位受邀嘉宾王教授分享的内容特别精彩。他说自己经常会问那些医学生,“在医院里患什么病,患者的死亡质量是最高的”,几乎所有人都第一时间想到了“猝死”。但是王教授却借此机会引出了他想要大家去思索的话题:怎么样提升医院的人文关怀,哪怕是那些得了不治之症的病人,也可以帮助他们去接纳自己的命运,让他们有尊严地离开。在听了他分享国内安宁门诊的一些探索和挑战以后,我也很想知道从患者家属角度,安宁疗护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失智症作为一种慢性病,在《生活在临终医院》中,更多展现的是那些照顾长期瘫痪在床,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甚至认知能力的老人的社区医院/养老院。虽然没有安宁门诊那种快节奏的生离死别,但是另一群被忽视的群体却被鲜活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我在读完作者笔下这些素未谋面的女护工们的故事以后,也对她们充满感动。这些离开农村到大城市打工的妇女们,可能自身连小学教育都没有念完,但是她们身上那种质朴与活力、勤劳与节俭,甚至城市里所谓“体面人”身上那种不多见的温情,都令人十分的动容。

其实,这两本书都绕不开一个终极的哲学问题:失能失智以后的人生,是否还值得活?在看完《当父亲把我忘记》时,我认为作者内心倾向的答案是不值得。当看到文中作者关于自己的哲思心理路程时,我其实不知道应该作何感想。因为我在和哲学群里的朋友讨论相关话题的时候,突然意识到生来就身体健康、智力正常其实已经是一种特权了。当我们在谈论丧失了某一或者全部行为或认知能力的人应该被放弃的时候,我们其实否定了那些先天不足或者后天因为意外等原因残疾、失去意识的人的生命权。
在第二本书《生活在临终医院》里,作者重提了这个话题,但我逐渐感受到她内心的答案已经变成了肯定的“值得”。她从“不知道”到贪恋父亲手心的余温,哪怕他此刻早已经忘记了自己,没有任何行为能力,甚至对于家庭而言都是一个“累赘”,但这是他还在自己身边的证明。尽管这样漫长的告别对于患者本身和家属而言都十分痛苦、甚至过于残忍,但是他依旧被需要、被爱着。这恐怕是最美丽的存在的意义。
非常开心可以看到如此细腻的生命路程,从患者家属角度描写这种慢性病患者的临终实在难能可贵。就像作者在文末所说,为什么要记录,可以带来哪些好的社会性转变或者是改善失智症患者及家属的处境吗?短期内恐怕不见得。医疗与养老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个很复杂的行业,非常具有挑战性。但是写作的意义也在于可以忠实记录,提出问题,引发思考。衰老是我们都无法避免的事情。我们此刻读到的只是故事,但却不排除某一天它成为我们的父母、甚至我们自己身上的事故。
我想读这两本书,可以让我们得以管中窥豹。

我们将如何老去?
文/虞央央
人都有生老病死,但只有当我们亲历时,才真正能知晓“生老病死”这四个字的分量。在薛舒写的《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中,作者的父亲因为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后期完全失智失能,在家由母亲照顾实在是太辛苦,不得不把父亲送进了一家社区医院。作者每周都会驱车前往离家四十多公里外的社区医院看望父亲,自此作者接触到父亲所在病房里的护工和病友,听到他们的人生故事。
通过阅读本书,我能感受到,在这段漫长的告别中,父亲的病变衰老,病房里的人生百态,给作者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感想和感触。而我在读完本书后,也开始思考,我们该如何面对老去?
书中的父亲,从记忆中家中的顶梁柱、决策者、气氛活跃的选手,逐渐蜕变成了只能躺在床上,嘴里只剩下“哎呦噻”的老小孩,然后无奈被家人送进了一个社区医院。而之所以父亲会被送进这家医院,也是母亲的坚持。母亲坚持认为父亲不会想成为子女的负担,所以选择的医院每月的花销不能超过父亲每个月的养老金。正如作者写的,父亲失智失能像个婴儿一样躺在病床上,对于社会来说已经不再创造任何新的价值,他也不像真正的婴儿一样,给人以希望,他不会重新成长为可以自己讲话、走路、吃饭的大人。他已经衰老了,他只会越来越老,同时丢失这一生的记忆,直到死去。他的存在,只对爱他的家人有意义。

而作者的父亲,是非常幸运的。他有养老金,可以让他住得起一家社区医院;他有一个好老伴,每天像上班一样来病房替他擦身子,带上好吃的,耐心地喂,甚至春节给自己放假三天都觉得愧疚;他有一群孝顺的子女(包括作者),每周都来看他。
相比之下,同病房的老人,就没那么幸运。比如8号床的老肖,他的老伴也生病了没法来医院照顾他,而老肖的三个儿子,只会在每个月给医院护工结算费用时,才会同时出现,他们甚至盼着老肖赶紧死了,这样就可以分遗产。而老肖,防三个儿子也防得厉害,他宁愿让毫无关系的隔壁病患的儿子去帮他取钱,买吃的,也不让他的儿子们过手他的钱。
作者在介绍老肖的时候,说老肖是这个病房最具“优越性”的老人。因为只有他可以自己下床去洗手间上厕所,坐起来吃没有被搅拌机打碎成“糊糊”的饭菜。因此作者能从老肖身上,感受到这个老人作为人的骄傲感。在这个病房里,其他的老人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只能躺在床上,由护工喂“糊糊”吃。这些老人,他们先是在老去的过程中,慢慢失去行动的自由。当他们终于老到无法自己去厕所,无法咀嚼吞咽下饭菜,他们失掉尊严和人格,变成一具躺在床上任人摆布的躯体。
在病房里,摆布这些躯体的,是一群从外地进城打工的中老年女护工,她们有一身的力气,嘹亮的嗓门。她们在照顾这些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时,没有性别意识,对死亡毫不避讳。作者写到“她们壮阔的嗓门,她们劳作的身影,她们热火朝天地生活在这里”。因为有她们,整个医院有了一丝生气。她们的身上,有自己的故事,但是在这家医院,她们是一群连名字都没有的“小彭”、“小张”、“小丁”。她们管老人死去叫“升天”。也正是这些人,在临终医院干着最脏最累的活,把一个个老人送走。
我之前从没想过老去,一直在互联网公司工作,这个行业员工的平均年龄一直保持在相对年轻的水平,我们一直往前冲,但没有意识到,我们终会老去,也终将面对如何老去这个问题。
曾在某位学者的播客节目里了解到一组数据:老龄人口翻番,法国用了115年,英国用了47年,日本用了24年,但日本在此前用了将近三十多年的时间为老龄社会做准备。而我们同样也需要在老龄化的问题上,做好准备。
我们将如何老去?把它牢牢抓住,直至放大到可以克服恐惧,或是遗忘到足以将代际之间的羁绊抽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